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铁皮马车刚走到大雪纷飞的圣彼得堡街的转角处,第一名袭击者迅速上前把炸弹扔到了马蹄下,炸弹重量仅为5磅,爆炸范围为1米,但它依旧破坏了马车,炸死了人群里的一个小男孩和一名沙皇的哥萨克卫队成员,爆炸的冲击力将袭击者抛进了一处围栏。 毫发无伤的沙皇从受损的马车里出来察看,幸存的随从们恳求他立刻离开这一区域,担心第二名刺客可能就在附近。
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俄国皇帝、波兰国王和芬兰大公爵,一个截至当时已经躲过了八次暗杀行动的男人——决定原地按兵不动。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第二名炸弹袭击者伊格纳蒂·格里涅维茨基(Ignaty Grinevitsky)一路肉搏冲上去,尽最大努力带着炸弹前进到距离沙皇最近的地方。他明白,炸弹的有效范围很小,爆炸之后他也将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亚历山大二世必须死,”他在不到24小时前写下了这段文字,“他将会死去,我们、他的敌人、他的刽子手也会一道陪葬……我将看不见我们的胜利,我将活不到胜利的光明时节里的一天乃至一个钟头。”
烟雾散去后,沙皇被发现横尸街头,被炸断的手臂淌着鲜血,胃部被炸开一个大口,脸被撕成两半。他在接受完最后一项仪式后没多久就死去了。杀死他的人也受到重伤,于当天晚些时候过世。这是1881年3月1日。自杀炸弹的时代——复活节周日曾有250余人因之丧生——就此开始了。
调查记者、作家伊恩·奥弗顿(Iain Overton)的《天堂的代价》(The Price of Paradise)一书对此现象做出出色的研究,书中探讨了自25岁的革命政治组织“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People's Will)成员格里涅维茨基舍命行刺俄国最具权势之人以来自杀炸弹袭击的演变历程。历经138年里的数千次爆炸事件,自杀炸弹袭击业已成为当今这个恐怖时代的核心,依照奥弗顿的说法,这个角色不仅主导了西方社会的恐惧,也影响了我们从事战争、保卫国家、通过国安立法乃至于定义自身的种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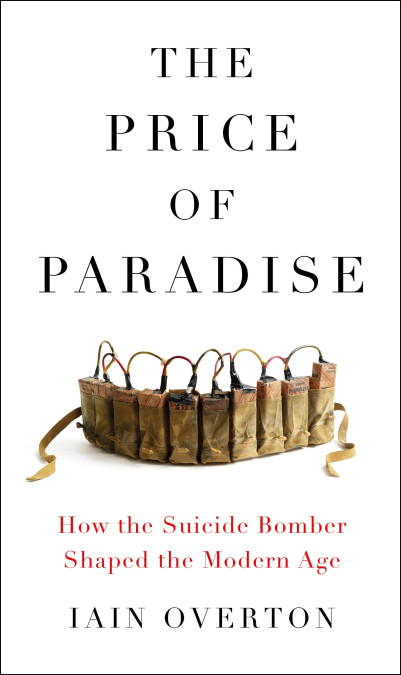
在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自杀式袭击之前,英国公众对来到欧洲寻求避难者的反应总体上是正面的。然而在巴塔克兰流血事件后的几个星期里,民调显示,有44%的英国人表示应彻底向难民关闭边境。

自杀炸弹袭击在传统的暗杀行动里有其根基,即行动者已经准备好付出生命代价来完成任务,如今这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极端。以前使用匕首或手枪的刺客或许已经有死的准备,但仍有生还希望。自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炸弹以来,对于自杀炸弹袭击者来说,死亡乃是其行动的本质环节,是其业绩的生动宣传。
恐怖袭击的破坏性效应在2001年9月11日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19名自杀袭击者以飞机为炸弹,击中了美国的一系列目标,这场行动击穿了全球的心理底线。世贸双塔的毁灭乃是有史以来目击者数量最多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当天的袭击夺走了将近3000条人命,并开启了一场仍未结束的、为期18年的反恐战争,它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左右程度堪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以来之最。
说回来,虽然比“911事件”更可怕的恐怖袭击迄今为止几乎是没有的,但随着各恐怖组织意识到不怕死的袭击者所蕴含的巨大威力,且这种威力足以挑战国家安全部门的垄断地位,自杀炸弹袭击的频率也有了指数级的增长。奥弗顿提到说,1976年时还没有自杀炸弹袭击,2016年则有28国遭到了469次袭击。
作者对这一宏大、紧凑且阴暗的主题几乎是信手拈来、驾驭自如,以一种达尔文式的眼光对自杀炸弹的传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透视,从1881年的圣彼得堡一直讲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里,中国军队也曾派携带大刀和“身穿挂满手榴弹的自杀式背心”的“敢死队”突袭日军。
这一传承接下来又体现在二战日本的神风(Kamikaze)文化里,接着则是1972年以色列罗德机场的流血事件,后来再传到两伊战争和黎巴嫩——如今它掌握在逊尼派和世俗团体手中——它被用来对付以色列目标以及美国和法国的部队。传承的路线在当时绕过了斯里兰卡,但两周前又回到了那里(指今年4月21日的复活节连环爆炸案——译注),最终一跃成为哈马斯、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一系列依附者的杀手锏。这些组织在包括马德里、伦敦、曼彻斯特、莫斯科、巴黎、布鲁塞尔、摩加迪休、巴格达、摩苏尔、特拉维夫和喀布尔在内的世界各大城市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
奥弗顿不仅一路记录下了这一恐怖战术的流变历史,而且完成得引人入胜、绘声绘色。《天堂的代价》清楚地描述了民主制度所陷入的左右为难处境,它既希望保护公民自由,又想要保障人民免于袭击,也谈到了其安全部队的一系列过度反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自“911事件”以来,这与其说抑制了暴力,不如说加剧了暴力的循环。

作者对媒体上流行的、将自杀炸弹袭击者刻画为有缺陷的“失败者”之类的套话不屑一顾——它们旨在对恐怖分子的牺牲神话加以反制——而是考察了在袭击者动机里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并提到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自杀式袭击乃是利他主义的(altruistic)事业,是迈向乌托邦之路的一个必要阶段。这种自我感知对1881年的格里涅维茨基来说是成立的,对2017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演唱会上引爆炸弹、导致22人丧生的22岁男子萨尔曼·阿比迪(Salman Abedi)也成立。
尽管两个人都是受外界因素刺激并催生了内心的恶魔,阿比迪的自杀袭击却更具复杂性,因其信奉逊尼派恐怖团体所宣称的圣战式自我牺牲和通往天堂的钥匙之间的关联性。从本质上讲,格里涅维茨基死时也相信他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阿比迪自爆时则认为他不仅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且会上天堂。
某些年轻的保守派穆斯林在性方面的挫败也对自杀炸弹袭击有一定的催生作用,许多袭击者相信圣战式的自杀可以让他们在天堂里享受72个处女的性崇拜。一些圣战的鼓吹者甚至以更大幅度的奖赏来为自己打广告。《迦纳特的女子们》(The Maidens of Janaat)起初在巴基斯坦出版,后来在英国莱彻斯特的一家店里售卖,书中称合格的袭击者实际上可以得到500个老婆、4000个处女和8000个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她们的崇拜从自杀炸弹袭击者死去的一瞬间就立即开始了,届时每个女人都会奔向袭击者,“她们就好像一只哺乳期的骆驼在空旷而贫瘠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失落的孩子一样。”
奥弗顿在其研究中融入了自己在爆炸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里的亲身经历。书里有许多细致入微的插曲。透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为格里涅维茨基制造炸弹的尼古拉·基巴尔奇克(Nikolai Kibalchich)后来还在等待处刑期间设计了一种简陋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这件事让他在天上有了自己的纪念,月球远端的一处环形山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这本知识量颇大的书里,奥弗顿也从未忘记过自杀炸弹袭击的凶残本质,也没有忽视这种行为所包含的幻觉性的自私。事实上,其中最有力的一章“受害者之山”(The Mountain of Victims)就专门讲述了炸弹袭击之后的幸存者及丧亲者的经历,后者哀悼的是那些姓名与命运皆不为人知的人们——与杀手构成鲜明对比。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死亡。”母亲费根·穆雷(Figen Murray)告诉奥弗顿说,她的儿子马丁·黑特(Martyn Hett)在曼彻斯特竞技场袭击中丧生。根本无所谓夸耀什么“胜利的光明时节”,她的言辞没有一丝矫饰,只充满了一个母亲的沉重悲哀。“如果马丁是因绝症而死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但这种死法……它让我感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被害死了。”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