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她的第十一本小说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数字世界里走向了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我确实担心过自己要去看男人和性爱机器人做爱。”她在伦敦一间高级餐厅里边吃甜点,边兴奋地说。充气娃娃起价“大约2000美元,质量很糟”,她说,难怪她们“纯粹是为了满足幻想,她们有着大胸、细腰和长腿”。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一桌的母女正在就着下午茶庆祝生日。“但是这些充气娃娃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阴蒂。她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她的新小说回到了200年前,重新审视了玛丽·雪莱的作品和工业革命,也带我们走进了当下的人工智能、性机器人和低温学的革命。《弗兰吻斯坦》(Frankissstein)用尼龙粉色的封面张扬着内里这个故事的文学底蕴,以“一部爱情故事”作为副标题,毕竟温特森的所有小说都是爱情故事。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爱有时候流行起来,有时候又会过时,但我坚信爱,”她说,“因为所有事情都彼此关联,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与其他事情的互动。”

未来的非生物体形式正好也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上个月出版的小说《像我一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的主题。虽然麦克尤恩选择了另一种历史,把他笔下的机器人亚当放在了上世纪80年代,但温特森想要表达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由此带来的后果”。正如她所指出的,“我们发展的步伐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快”:我们见面的那天,新闻里正在播放猪的大脑在死后被成功“复活”的故事。(“唐纳德·特朗普会冷冻他的大脑吗?”《弗兰吻斯坦》中的一个角色问。答案是:“要想冷冻大脑,临床死亡时的大脑必须要运转正常才行。”)这种机器化的未来“可能会很美好”,她用特有的顽皮语气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总是会把未来搞得一团糟!一种远比人类聪明的超级智能生物,为什么会让我们虚荣、丑陋、鲁莽、自毁、愚蠢的人类保持原样?”
温特森身上充满了弗兰肯斯坦式的特质,她总是用手揉自己的头发,发型也因此乱糟糟的。虽然她不再自己骑摩托车(出于温特森的妻子、作家、精神分析学家苏西·奥巴赫的坚持),但她仍然会通过出租摩托服务出行。今年温特森即将迎来她的60岁生日,这个在阿克灵顿度过了悲惨童年的小女孩,在文学界已经发光发热了三十余年。“人们还会买我的书,这是个好事。”如今她把自己比作粘人的小狗:“我不会放弃,我也不会离开。”在2003年,温特森生活中“母亲一样的角色”——露丝·伦德尔(Ruth Rendell)——把她的惊悚小说《警犬》(The Rottweiler)献给了温特森。
我们都熟知温特森的故事,毕竟她已经讲过两遍了。1985年,她在处女作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讲述了一个被领养的女孩在虔诚的五旬教派家庭长大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事帮我熬过了艰难的时期。”她2001年的畅销传记《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她在没有爱的童年和中年里一系列崩溃的痛苦反思,传记的书名来自她的养母在发现她性取向时的回应。“她是个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温特森这样评价她的养母,温特森夫人显然是当代文学史中最邪恶的继母之一。“我过去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温特森如今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追上我,但我知道它们会追上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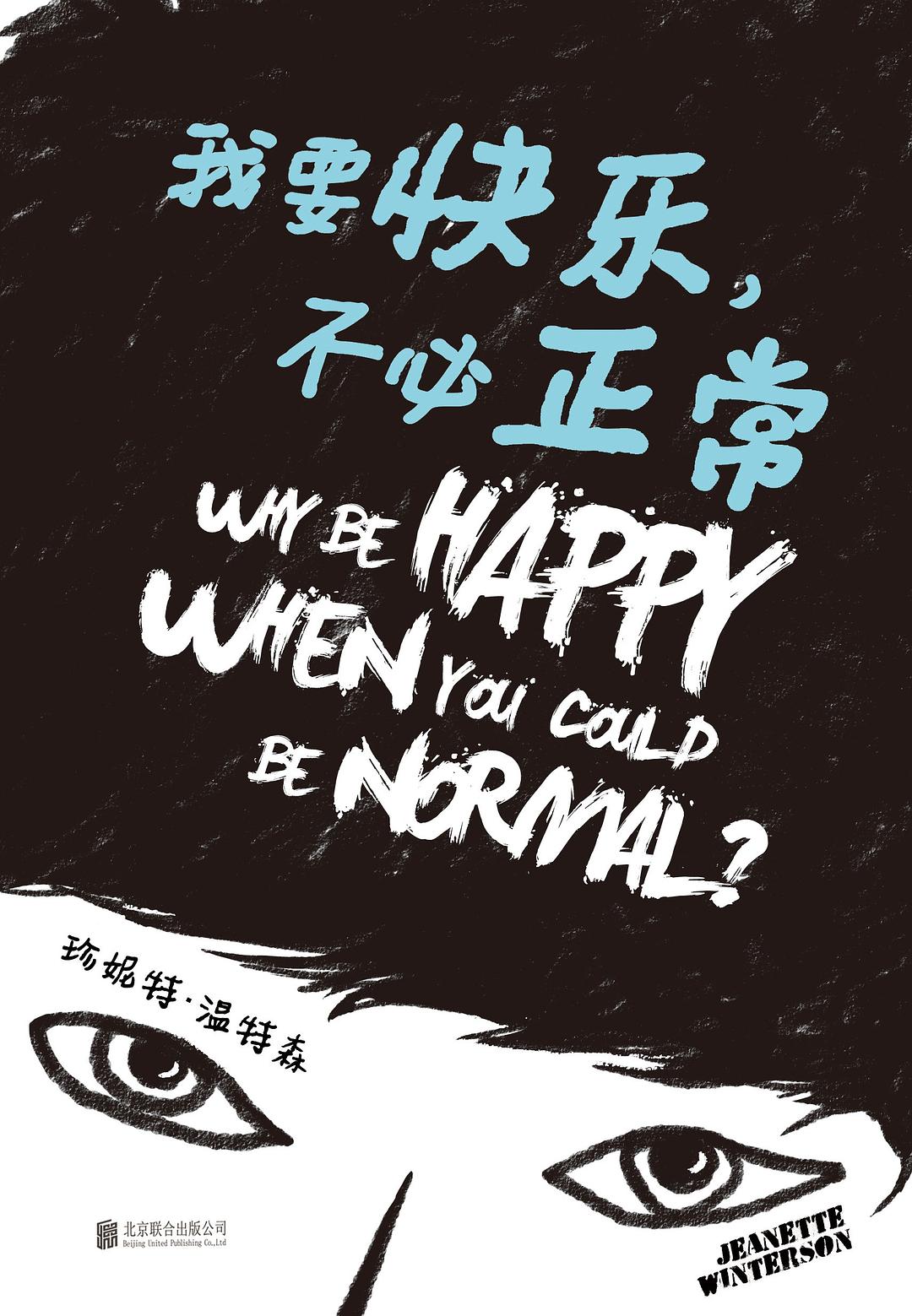
[英] 珍妮特·温特森 著 冯倩珠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在她自杀“彻底失败”之后,在《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令人震惊的爆料之后,她正在享受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和话剧导演德博拉·沃纳(Deborah Warner)的分手“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但分手不是她的错。这让我回想起了我以前失去的所有事物,但我坚持了下来,并遇到了苏西。我开始了另一段生活,这让我感到开心”,她说,“我就像是面对着一堵空白的墙,而我找不到绕过去的办法。这让我体会到了最纯粹的失落感和最深的孤独。我热爱生活,我也知道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根本算不上是生活。”

抛开机器人题材的新颖性不谈,这个主题得以让她回归塑造她从《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起的那些小说中最棘手的主题:宗教和性别。“我突然发现,等一下,这一切都可以连起来了,”她说,暗指她正统派基督教的家庭背景,“我们不是总说,肉体终究会消失,灵魂会继续存在,世界上是有不朽存在的吗?这就是科学给我们许诺的未来,我们只需要上传大脑中的内容,或者植入智能长寿基因来延长我们的寿命。我们人类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缓慢进展到这一步,我们终于可以像长久以来的梦想那样,永垂不朽。”
如今,声音顺滑的私人智能助理和充满大男子气概的紧急新闻播报,让我们不再有冲动去给任何事物赋予性别。而《弗兰吻斯坦》最感兴趣的,是我们与这些人造机器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对性别的看法。温特森的小说中总是有无性别的、可以穿梭时间的角色,她的问题极具流动性,一直挑战着“界限和欲望”:1987年出版的《激情》有着交错纵横的十九行诗题材(她认为这是《杀死伊芙》的灵感来源);《写在身体上》是“1992年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一本作品”,主角仅仅以介词“它们”来称呼(这也是温特森唯一一部没有有声书的小说,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性别中立的声音来朗读);《苹果笔记本》是21世纪首先探讨互联网多变性的小说之一。“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在互联网上扮演任何角色,这太天真了。但那时候互联网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诱惑太多。”

《弗兰吻斯坦》中的一个主角“丽”(玛丽的简称)是跨性别者。“跨性别很有意思,因为性别是一个恼人、无聊、麻烦的话题,”温特森说,“我不把自己定义为男性或者女性,我就是我。我甚至不确定会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人类,我不觉得自己有特别人类的特质。我最好的朋友会说,‘也许吧,她更像是某种生物——不是动物,而是某种生物一样的东西。’我并不总是理解人类。”但她也说,她“知道世界是怎么看待我的”。作为一名作家,她觉得“女性并不是总能获得同等的机会和纵容。如果女性想成为一名作家,你要很擅长写作,并希望给小说带来改变。而如果你是男孩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温特森不止想给小说带来改变,她也想改变世界:你可以让一个小女孩离开阿克灵顿,但你永远不能让她离开她的宗教背景。“宗教是逃不掉的,你必须把它变成一种优势。我是个正统派基督教徒,我很狂热,”她说,“我知道人们这些年为什么讨厌我。但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要利用这一点。”
她不仅借此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世界上存在着太多厌女、恐同和反工人阶级的事情”——但只有这样,十年以后涌现的一批作者(比如阿里·史密斯和萨拉·沃特斯)才不用面对类似的恶意。她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她对这样的变化做出了一点贡献。“这是一种特权。其他出生在我之前的女性为我提供了机会。每一代新作者出现,”她评价萨利·鲁尼(Sally Rooney)这一代年轻作家,“我们就扩展了一点空间。”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已经成为了英语考试的必读书目,并且即将由1990年电视剧版的导演比班·基德龙(Beeban Kidron)改编成音乐剧。“许多年轻人对我说:‘你必须得把这本书改编成音乐剧。’这让我觉得这本书仍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她说,“作为英国人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一直写作发声的话,人们会忘了那些批评,开始喜欢你。”

她现在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严肃。“我不会为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写作,”她带着一点傲慢的语气说,“有许多书是专门为了那些无法集中注意力、不想阅读的人准备的。这不过是打印出来的电视剧罢了。”
也许温特森已经成熟了(她最近唯一惹上的麻烦是2014年在推特上和伴侣的疯狂前任吵架,她毫无歉意地写道,“那个婊子吃了我的窝边草”),但她仍然总是“遇到麻烦”。在我们见面前,她遇到了两个在邦德街疯狂购物的女性,“她们拎着大包小包冲进巨大的商场。”“女士们,”她用最标准的兰开夏口音上前对她们说,“这不是生活!”(温特森夫人会为她自豪的)。
她仍然很生气。“我就像是无敌绿巨人一样,总是在生气。”(“有些人永远不可能杀人,”她在《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写道,“我不是那样的人。”)但她觉得自己的怒气“被转移到了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弗兰吻斯坦》给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带来了灵感,这些文章将会集结成书,以《侏罗纪停车场》(Jurassic Carpark)为题,于今年晚些时候出版:“因为我们会被扔到某个地方的保护区或者某个停车场里,让我们开心地驾驶污染环境的汽车。”她12岁时接受的街头布道训练得到了回报:“现在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时刻,因为右翼正在拼命采用布道的方式去传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很多自由党人并不擅长于此。我很乐意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布道,也不用担心人们的回应,”她笑着说,“我也很愿意步入政坛,但我不能加入现在这个状态的工党,对吧?”
她在撒切尔的时代长大,“我们这代人很疯狂,”她说,“我们让整个世界都打了鸡血。”她觉得自己现在有责任尽力去“弥补”。从2012年起,她就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创意写作,“我从这些小孩身上看到了很多同情和焦虑,因为他们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继承到的世界如此混乱。”她邀请有抱负的作者在她位于科茨沃尔德的独立公寓工作,就像她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露丝·伦德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写作的空间:“我这样做是为了她,因为她为我做过同样的事情。”
温特森坚决不要孩子,她对“写作”抱有太多热情,也因为她自己的童年让她“不想变成那种会忽视自己孩子的父母,而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但有一段时期她曾经觉得,“如果我和一个人在谈恋爱,而她说,‘我真的很想要孩子,’我会同意的。”

虽然她和苏西·奥巴赫于2015年结婚,但她们并没有同居,“苏西是那种纽约式的犹太人,她需要生活在伦敦那种繁忙的环境里。”而温特森“在独处时是最开心、最自我的”。她在斯皮塔佛德开了一家有机食物商店,也仍然保留着楼上乔治王风格的破旧公寓,但她大多数时候住在乡下的一处小屋,有两只猫和一只拉布拉多陪伴,背靠着树林,在花园的木屋工作室里写作。她仍然想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不会放弃的!我希望在工作的状态下死去。如果你足够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它就不算是工作了,对吧?”
但她仍然在“从伤口里写作”,她描述道,“伤口是不会愈合的,它们会结疤,但仍然能给你带来疼痛。伤口和疯狂不一样,它展示着你的弱点。你试着与它们共存,这让我更容易接受这个世界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最近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她会提醒自己:“你还没死,你也不再生活在阿克灵顿。”
(翻译:李思璟)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