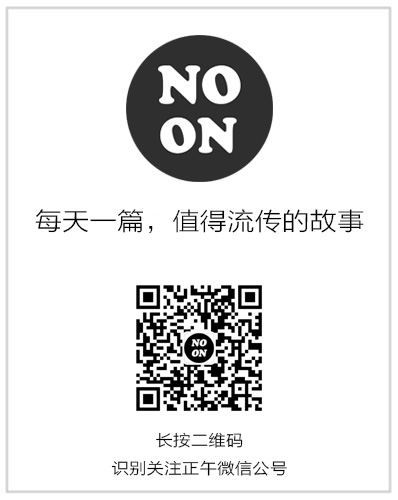廖凡的角色是一个咏春高手,北上搏名。我和他有个约定,看拍摄结果,打得好,说是“咏春”,打不好,叫别的,编个拳名。
开机后,遇到自报门户的台词,均拍了两套话。
杀青日,我通知他:“咏春。”
廖凡的武术课
理性是总结能力,往往总结的不对。感性是丰富性,汪洋大海。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原始盲动、痛苦罪恶,如大气层外的茫茫宇宙,平时等于不存在,但刹那陨石袭来,对人生造成伤害;荣格反叛师说,认为潜意识是智慧宝库,可惜被正常意识屏蔽,一叶遮目不见泰山,我们的理智让我们失去了伊甸园。
感性优于理性,音乐可做验证。音乐不从小学起,这辈子便会错失音乐,乐器是弹的,音乐是用手感理解的,儿童的手是音乐之门。再资深的唱片发烧友,再勤力的音乐厅常客,仅靠耳朵感受的音乐,就还不是音乐,是音乐的水中倒影。
吴清源说,八岁学围棋已太晚。人对棋的感性,最佳开发时机是四到六岁,错过了,便一生棋感平庸。棋感,如拉小提琴的手感。程晓流说,聂卫平凭着棋感好,掌控大局,已足够遥遥领先,遇上难缠的赵治勋,被逼急了才算一算。算得吃力,比赵治勋耗时长,说明他大多数时候不干这事。
我能导演武打片兼任武术指导,源于十五岁曾经习武,虽然放下已久,但这份少年感性,让我常得天助,拍摄条件有亏,武打设计无法完成,却生急智,想出一个易操作的新动作,甚至更具视觉效果。
开机前,廖凡训练时间仅两月,我向他保证:“你失败了,就是民国武林的失败。”
他知我夸张,但选择了信任我。
之前,我有过一次成功范例。导演《箭士柳白猿》时,训练出了赵峥,他是话剧演员,无武术基础,两月后可和真正高手于承惠对搏长枪。有香港影人看过此片,以为他是武术运动员,反夸他会演戏。
于承惠成名于1983年的《少林寺》,李连杰正一号,他反一号。他原在山东武术队,从事套路表演,看到老队员们跟体操运动员一样,年过三十岁,便技巧退化,等同普通人。他跟我说:“我那么热爱武术,付出这么多,一过三十,就什么都不行了,那我还追求什么?”
出于不甘心,他去民间访传统武术,访到一位民国时代山东国术馆的师父,之后又转学多师,修行实搏武技,年过七十仍功力不坠。
一次剧组小范围聚餐,于老要结账,我拦他。一搭手,我俩都本能地把手伸到对方肋下。于老肋下肌,坚实得如摸在马背上,勤练不辍的标志。
听到安排了长枪对搏,他拒绝用剧组准备的枪杆,用自己的。长枪对于武人,类似戏班演关公。关公戏,要上香禁语,娱乐事里出了敬神事。老派武人都敬长枪,长枪最练功夫、最显功夫,于老有根用了三十年的枪杆,已泛红色。
于老很关注跟他对枪的人,剧组人也觉得该是于老这级别的高手,才对得起这场戏。当我告诉是位话剧演员,正在勤学苦练,于老没评价,可能很沮丧。
看过赵峥练枪的视频,于老说话:“两月练不到这样,此人有十年枪龄。”
我把赵峥送到八卦门,进行站桩、走桩训练,先有了习武人身形,再教他一种速成枪法。于老练的枪法叫岳武穆十三枪,形意门、太极门练的枪,以腰使枪,所向披靡的发劲,一碰便将敌兵器打飞。
十三枪是功力型枪法,招法简单,不以招克敌,以劲克敌,劲不好练,悟性不佳,往往虚耗岁月。
幸好还有赵子龙十八枪,燕青门和三皇炮锤所练。燕青门从事天津码头搬运,纠纷一起要群殴,三皇炮捶门押送镖车,遇上土匪要开战,都需要大量人手,必须速成,学了就得能参战。
燕青门名宿张克功晚年由我二姥爷照顾,我的十八枪源于此,没学全。《箭士柳白猿》中,赵峥亭阁练盲枪,蒙眼打四人,是这残本十八枪。
十八枪是技巧型枪法,腰劲很难练,脚脖子好练,便避重就轻,以转脚替代转腰,发劲大差不差,所以可速成。赵峥视频是仰角拍的,脚部不显,瞒过了于老眼睛。
开机后,赵峥一日说:“没瞒住。”
昨夜于老带着烟酒零食,来赵峥房间聊天,一片友好中忽然要求搭手,将赵峥挑飞,跌到床上。于老一战心安,悟到自己戏份,在我动作设计之外,献出两个转腰枪技,实拍时漂亮得惊了现场。
他俩的对枪戏,赵峥转脚行枪,于老以腰运枪,十八枪和十三枪技法分明,赵云对岳飞。
廖凡的角色是一个咏春高手,北上搏名。我和他有个约定,看拍摄结果,打得好,说是“咏春”,打不好,叫别的,编个拳名。
开机后,遇到自报门户的台词,均拍了两套话。
杀青日,我通知他:“咏春。”
《师父》以械斗为主,应称“剑戟片”。剑——短兵器,戟——长兵器,“剑戟”二字概括所有兵器,日本武士题材电影也叫剑戟片,少有徒手格斗。拳打脚踢是香港特色。
古代军营不训练徒手格斗,因为战场用不上,兵器都没了,还打什么?拳打脚踢没法反败为胜,只有被歼灭的命运。
明朝抗倭,戚继光编了一套拳,编好又怕给士兵增加负担,空留下拳谱,没用于训练。于志钧考证,戚继光放弃的这套拳,遗落民间,成了今日的陈氏太极拳。
日本武士是军官蜕变的公务员,军事集团占地成功,转成政府,军官转成公务员。武士习武保持军队旧习,劈剑刺戟,少练拳脚。徒手技不属于武士阶层,柔道是捕快练的,空手道是渔民练的。
中国武术谚语“拳成兵器就”,拳练好,兵器就会使了。日本武士正相反,剑戟练好,也会了徒手打。
不是武术体系差异,是政治不同。日本沿袭汉唐观念,男子佩刀是礼仪,家家有剑戟,宋元明清都民间禁武,不许私藏兵器,想练也没有,只好练拳。
咏春门仅有两件兵器,六点半棍和八斩刀,《师父》表现的便是这一刀一棍。棍有甄子丹的前科,观众可做比较,刀无先例,是廖凡的新天地。
咏春拳一般教学流程是:1、第一套拳小念头、黐手(类似太极推手);2、第二套拳寻桥、大半套木人桩、六点半棍;3、第三套拳标指、全套木人桩;4、八斩刀。
咏春门披露,李小龙学第二阶段时离港去美,断了师授,木人桩不全,标指、八斩刀未见。一个肄业生,已可在世界封神,可想咏春的水深。
训练廖凡,本末倒置,直接是八斩刀。
咏春得梁绍鸿赠艺,八卦掌则是少年所习,明白冷暖。我偷机了,对廖凡讲咏春拳理、做八卦训练。
又得感谢燕青门和三皇炮捶门了,他们争码头、开镖路发明的种种速成法,太适合训练演员,我又借用了一法。
廖凡课程,便如是。
有人说,导演分两种,一种是懂画面的导演,一种是不懂画面的导演,但凭着编剧功底或指导演员的经验,在摄影师的辅助下也能完成电影。我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导演——懂画面的,所谓第二种,就不是导演,是个票友。
剧作真相
电影制作流程中,有三处,不是电影效果——故事板、影片定剪、剧本定稿。
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制作少有故事板,导演的分镜头少有画面,镜别大小、是否运动等画面要素由文字标示。受好莱坞影响,我们也开始画故事板——把整部电影画成小人书。著名典故是,沃卓兄弟筹拍《骇客帝国》,没人能听得懂他俩说的故事梗概,于是请人画成小人书,制片方看得高兴:“故事很棒。你俩怎么说不清楚?”于是投资。
导演工作最重要的是镜头设计,体现风格,决定艺术成就,怎会委托给故事板画家来完成?
导演面对的是影院观众,故事板画家面对的是资方和制片方。故事板的视觉逻辑是连环画式的,虽然当今连环画借用了许多电影手法,毕竟还不是电影。
我上大二,高年级毕业,一师兄送我厚厚一摞《城市猎人》漫画,说:“这样设计镜头,你能胜过所有人。”
看后,知道师兄走偏了。
《城市猎人》的动漫与漫画也不一样,电影与连环画不是一个视觉逻辑,一个是观影一个是阅读。故事板的最大功能是让资方通顺地理解故事,对项目有信心。
故事板无法指导创作,不属于导演,属于制片。
故事板,作为画面太简单,线描,稍微涂涂明暗。而现场拍摄,导演从监视器里看到的才是画面,电影画面是综合性的,除了线条,还有色彩、情节细节、演员表演。电影表演是高度画面化的,没找准景别,好表演就显得糟糕。
导演也会画电影画面,即分镜图。即便是早年混画家圈的希区柯克,所画分镜也是寥寥,构图得现场确定,纸上没法完成。黑泽明有“拍不成电影,我就先画下来”的励志名言,电影杂志爱做黑泽明分镜画和成片画面的对照,影迷们赞叹“完全一样”。
画里有什么,电影就拍了什么,内容一样——在外行人眼里,就是完全一样。从专业角度看,构图不同,光影不同,就根本不一样,对摄影没指导意义啊。所以黑泽明的分镜画,只能叫气氛图。
分镜图,即便是摄影师,也得边看边听导演解释,两人在监视器上揣摩确定,况且还有这个画面和下一个画面的组合问题,为降低交流成本,老道的摄影师是先拍了再说,不跟导演纠缠。
电影不是绘画,导演是个现场艺术家,创作流动画面的人。工作性质,决定了导演可以不看故事板、不画分镜图,现场艺术家的意思是,像拳击手上拳台,好坏是上台打得如何。现场构图的能力,来自长期的画面素质培养,而不是因为执行了画草图的程序。
有人说,导演分两种,一种是懂画面的导演,一种是不懂画面的导演,但凭着编剧功底或指导演员的经验,在摄影师的辅助下也能完成电影。我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导演——懂画面的,所谓第二种,就不是导演,是个票友。
电影的世俗性太强,凭着专业之外的因素也能成功,世上有很多有名的票友。但票友就是票友,不能称为“一种”。
电影定剪,还不是电影,只是导演确定了画面组结方式,没有声音,就还不是电影。
电影的节奏、氛围很大比例是由声音决定的。画面是体格,声音是气质,杜琪锋的《枪火》去掉音乐后是一部拖沓的电影,音乐让它有了“调皮的认命者”的妙味。
导演没法对未做完的事负责,观者也没法对未做完的判断。但人们喜欢看声音缺欠的定剪,表示:“没完成没关系,我看过很多电影,可以自行补充。”
不要信任这种许诺,与专业素质无关,生理决定的。看电影,是综合印象,没人能把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分轨。即便补上参考音乐和关键音效,也是螳臂挡车,无法避免他人对你电影的误判。
因为观感不良,人会有很多意见,提出重大的剧情修改。其实,源于某一个环境音令他不舒服,或一句台词没听清,但作为生理的人,是总结不出来的,只会想“我为何不舒服?一定是剧情有问题。”
组织人看定剪,现今是后期制作的重大步骤,让资方验收,让宣发部门和一二影院经理“拯救这部电影”。
原是导演工作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 找几个专业的熟人,帮忙检查有无剪辑技术的纰漏,听听观感,有助于导演的自我判断。因为是熟人,导演了解每人的审美趣味,对他们的反应也有判断,不会迷惑。这些谈话,是秘而不宣的,是导演个人的事。
现今请的看定剪者,多是导演不认识的人,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莫测,他们会误判,导演也会对他们的反应误判。
一些电影经过反复论证修改,信心百倍地投放市场,不料观众反应天壤之别。说明程序不科学,以看定剪的观感作为依据,便会怎么改怎么错。
好莱坞试映,请人看的是声画完备的成片。源自导演誓死抵抗制片方的修改意见,相持不下,便办几场试映,以观众反应为裁决,等于扔钱币猜正反面,“别争了,听天由命”。
试映观众不是少数几个审美独特的资深圈里人,是常规影院人数,三四场,如法院陪审团一样,经过挑选组合,保证观影反应属于常人。《教父1》《猎鹿人》《苔丝》便是这样赌赢的。
好莱坞试映,保护了导演。
世上很多人,都在写剧本。编剧界,常闻拖稿逸事,理由无外乎电脑被窃、家人病危、自己摔伤,想象力之匮乏,令人为他们难过。
偶有新招。某君在交稿日失踪,三周后,夜敲导演家门,怀揣一支牙刷:“能否借宿一宿?”进门翻冰箱,几日未食的饿容。告知真相,因一桩陈年情事,三周来遭仇家追杀------
导演不为所动:“我现在就杀了你。”
拖稿,出于厌恶。叙事要遮遮掩掩、轻重缓急,剧本的灵魂是取舍,但编剧大多无权做这事,沦为素材提供者。
剧作不等于见闻,剧本是深度而非广度,但大家潜意识里的理想剧本是晚报合订本,应有尽有。选编剧,先要面谈。拿下预付款的秘诀是,导演说个事,你能列举出三件类似的,便会赢得信任。某君入行后没写成一个完整剧本,四处列举,靠拿预付款,也买车了。
桥段不能拼凑,一凑即死。三个好主意凑在一起,一定是坏主意。
古龙有本小说《那一剑的风情》,代笔之作,将古龙以往小说的桥段集中在了一起,看得人毛骨悚然。好桥段是在一个故事里自然生出来的,有前因后果,如同脑袋长在身上。此小说,则是一堆脑袋簇着,无身无脚,状如闹鬼。
没人认为它是古龙最好的小说,但它是我们追求的剧本。
观众常有疑问:“既然肯花上亿元请明星、建场景,为何不花点钱请个好点的编剧?”其实花了,甚至价格不菲,但剧组高层一日有闲,上网观片,学了个桥段,于是全毁。
跟韩国电影人交流,他们热爱金庸,告知我在九十年代之前,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版权这回事,金庸作品飞速翻译成韩文,痛快了几代人,造成韩国武侠小说特征——侠客只在中国活动,如出现韩国地名,韩国读者会很不习惯。
当金庸在韩国能拿到钱了,我们仍习惯性地见不得他人的好,好就直接拿来。有人咨询过:“稍作改变的伪装都不做,一点剽窃的羞耻心都没有么?”回答:“有。但怕改了就不好了,原样保险。”
器官移植,会产生抗体,况且是三个心脏、四只眼的移植法。
希区柯克告诉特吕弗:“我们行业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外行。”后来,特吕弗成了大导演,认为希区柯克的处境比他好,说少了。
其实都懂行,只是不懂得尊重导演。
特吕弗认为,好导演都有放弃署名的冲动,将导演一栏署上“所有人”。人们不会要求小说家、音乐家听取所有人意见,但人们会这样要求导演。
导演是最不被信任的人,说导演坏话是剧组风俗,科波拉拍《教父1》、他女儿拍《迷失东京》,都是各部门小工起哄,差点丧失了导演权。
按佛家观念,小说和电影创作都是“行门”,在行动中获得正念,保证导演行为顺畅,他才能达到思维准确。得容许导演做些无用功,浪费点钱,等他活动开。
导演越犯低级错误,说明他想找的东西越好,起码不同以往。科波拉父女同命,“找准”阶段,一片“我们的导演不会拍电影”的喧嚣。
不要担心导演浪费钱,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能调整过来,精准了自然不浪费。对导演盯得过紧,导演束手束脚,迟迟进入不了精准阶段,势必越拍越多,每笔钱都省,但都花得不到位,总账上反而浪费。
电影前期策划得越完美,前景越堪忧。讨论得越充分,剧本越写不好。
集体讨论,敲定一个主意后,势必造成“这是共识”的心理,实写时不敢超越。集思广益,开阔思路,但没有分寸感。艺术品质的高低不是思路广,是分寸感,实写实拍,才能获得。
常有人问:“写作时的灵感和原始构思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选择?”——这是外行话,写作者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原始构思,不存在纠结问题。
因为写作时思维程度深,构思阶段思维程度浅。很多作家在生活里都是不动脑的人,生存技巧就是不说话,少惹事。看作家,只能看他的作品,他小说中的智商比他生活里高好几倍。
编剧的痛苦在于,人人能看懂的好剧本,往往不是剧本,是一个像小说、素材、公告的怪物。
比起诗歌小说,世上更多的文字是公告。《昭明太子文选》不单是文学名著,主要是官场必读书,唐朝时,普及到日本、朝鲜的官场,因为总结出三十七种文体,大部分为政府公告体例,不熟悉没法做官。
写诗歌小说,则要像防敌一样,避免公告的概括性和逻辑性,支离破碎才是诗歌小说。断处,读者自会补上。概括性和完整性不能在文字上完成,应在读者脑海中完成。指导小说初学者,帮他们删就好,删去五分之四,能有个直观感受——噢,小说是这样的。
诗经楚辞那么多感叹词,为时不时断一下叙事,不让人拘束在字里。文有虚词,曲有韵——韵是暂停,曲子断断续续才好听,不断无名曲。
但多数人用公告之法写小说,以读报的方式读小说,常有“真棒,几乎是报告文学!”的赞语。社会信息含量多,并不等于艺术价值高。小说的艺术价值在于洞察不同时代的人类处境——我们活在什么局面里?局面就是命运,小说的美感是揭示命运,而非论证和评判。
电影是具象画面,但概括性惊人。小说写一人经济窘迫,几个细节才能让读者有感受,读到他袜子有洞、舍不得花钱洗澡、自卑的眼神,才能感受到窘迫的力度。电影拍一个细节,对观众就有力度了,另两个细节便不用拍了。
视觉的概括性大于文字,所以电影镜头要比小说诗歌更“断断续续”,四处留白,才有镜头美感。一览无遗,观众会烦,总接受重复信息,谁受得了?
快过观众脑子的,便是好剪辑。
快,不是剪辑速度快,几格一个镜头,一个撞车用了七个镜头,视觉上迅雷不及掩耳,但观众还会不耐烦,因为看一眼就明白了,不就是撞车么?
观众以生活经验看电影,良马见鞭影而驰,眼睛看到一点,脑子就全明白了,所以不能按照生活逻辑剪辑,否则剪得再快也还是慢的,慢来慢去,观众就失去观看兴趣了,你的剪刀快不过人脑。
电影要让观众“追着看”,但电影剧本得回避电影特性。
读者和观众是两种人。电影剧本不是用电影手法写的,是小说手法,甚至是文章手法,因为导演、制片不管多专业,看字就还是个读者。况且剧本多是给外行人看的,用于“小心求证、博采众长”,指望他人读剧本时产生电影观感,一定遭重创。
按照电影手法写,会被指责“没写完,没力度,看不懂”,所以编剧要写许多累赘重复的东西,卖好于常人的阅读感。
导演要知道编剧的苦衷,工作的第一步,是将剧本删减得谁也看不懂,拍成了则会简单易懂。许多电影让人看不懂,因为画面用的是文字逻辑,层层论证的方式。剧本能看懂,拍成电影反而看不懂,由于视觉强大的概括性,一下看懂了,可你还在论证补充,便信息混乱了。
很多时候,观众不是没看懂,而是给搞糊涂了。
我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拍,总给自己骗。写出一场好戏的成就感,是文字快感,但我常忘了,以为就是电影了。
——————————
本文节选自徐皓峰新书《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下周即可在书店或网上购买。请粉丝们踊跃购买。
本文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