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样的好天气在北京难得一见。6月1日下午四点半,我从东直门地铁站C口上来,雨还在下,太阳已经从灰云里钻出,满眼亮堂堂的,四面的楼宇因阳光和雨的混合而显得奇幻。旁边小小的公园里,十来个穿着天蓝色T恤的年轻人站在中央,有人脚踩小气泵,鼓起一个个天蓝、或明黄的气球。
他们是微信公号“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以下简称“一览”)的志愿者,这天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在城市中漫步,分辨街道中对行人友好或不友好的细节。一个短发女孩站上花坛的水泥边,吹了吹小麦克风。报名的60个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我们先破冰吧!”女孩说,“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麦克风传递着,我打量了一下人群,发现大多数都很年轻,带着书卷气,从自我介绍来看,八成从事或正在学习交通、规划专业,剩下的有做金融或者互联网的。他们三三两两地聊天,我转了一圈,发现术语太多,听不懂。
五点,人群向西出发,第一个挑战就是:过两次马路,从东直门环岛的东南角走到西北角。
宽阔的街道上,有斑马线,却没有红绿灯。人群在路边拥堵着,伺机待发。一辆辆汽车驶过,转弯,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人群焦躁起来,终于有人找到空子,从车流中穿过。车缓下来,又不甘心地地想在人群中插空。人和车纠缠成一团,我提起精神,跑了几步,终于成功过了马路,往回看,人群已被车流截成三段。
接下来的路程,我们需要提防:小小的水洼,占据一半人行道的树坑,突然停下的快递三轮车和垃圾车,还有因自行车道被占据而骑上人行道的自行车……几乎是一场小型冒险,连续的紧张让人感到疲倦。
在下一次过马路之前,我忍不住疑惑: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漫步?

2
刘岱宗是“一览”的发起者,但是漫步那天,他在国外,直到6月下旬,我才在东直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他。他的本职工作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和中国交通项目主任。
那是早上9点,办公室没什么人。他习惯每天比别人提前一小时到,搜索资料,校核推文,然后,推送。这种带点专业性的文章早上推送比较合适,刘岱宗测算过。通过数据和案例看问题,是他工科生的思维方式。
刘岱宗生于南京,从小在城市生活,1995年,听从父母安排,他在大学选择了交通工程专业,学习修桥造路;2000年,他到新加坡读研,交通管理和控制专业。毕业后,他又在那里工作了三年,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协调信号灯,让每天早上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上班的十万摩托大军快速通过海关关卡。交通专业的先在设定是服务小汽车,刘岱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设定。
2005年,刘岱宗回国,成为美国能源基金会在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的第一位技术员工,工作是促进公共交通,推动中国交通领域的减排。北京从德茂庄到前门的BRT1号线,是刘岱宗回国后接触的第一项工作。后来,他又去重庆、济南、成都等地推动BRT,每到一地都是从零开始,向不同部门不同人一遍遍不停地说。
BRT,是Bus Rapid Transit的缩写,意思是快速公交系统,在地面设置公交专用道。这种方式吸收了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长处,成本比地铁低,建设时间比地铁短,最快16个月就可以完工。
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小小的会议室里,刘岱宗端来了他的THINKPAD笔记本,打开了一个PPT,在300多页中,他找出了一张广州的照片:宽阔的双向八车道上,密密麻麻的小汽车首尾相接,连成一片。要想在这已经很拥堵的地方拿出四条专用道给公共交通,就意味着道路所有权的重新分配。
交通工程理论中有个词叫“当量小汽车”,刘岱宗解释道,按占地面积,将所有交通工具都折合成当量小汽车,家用轿车是1,公交车是2,铰链公交车是4,“你可以看出交通工程的概念: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小汽车”。以小汽车为单位,拨出车道给公交,通行能力下降了——但是如果以人为单位呢?通过的人变多了。
从“为车”到“为人”,是他思路转变的开始。但推动“为人”并不容易。
比如他去开会,一说要保护行人和骑行者,对面的专家和领导就开始反驳,“行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行人总跨栏杆!”显然,他们自动代入的是驾驶者的角色。
刘岱宗经常驳回去:你可能一辈子不开车,但你可能一辈子不走路吗?即使从停车场走回家或者过马路到对面的商场,短短几十米,你依然是个行人,依然需要保护。
刘岱宗当时的工作地点在长安街,下班后,他去乘坐回家的公交要穿过长安街,有时,在暴晒或者寒风里,他要等待十分钟才能红灯变绿。他因此切身地理解那些不按规则过马路的行人:当你不尊重我过马路的权利,为什么我要尊重你的规则?
说到这儿,刘岱宗有点激动,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坐在车里的人不愿意明白?
“还有一点特别难受,回国工作的头几年推动公共交通,反而得不到公共交通乘客的支持。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因为这些人的梦想都是开车。尽管中国今天1000人里面只有300人能开上车,但大多数人会把自己放到驾驶者的位置。即使自己开不了,儿子也会开,所以一定要把路权交给车,即使自己要忍受公交的拥挤和不准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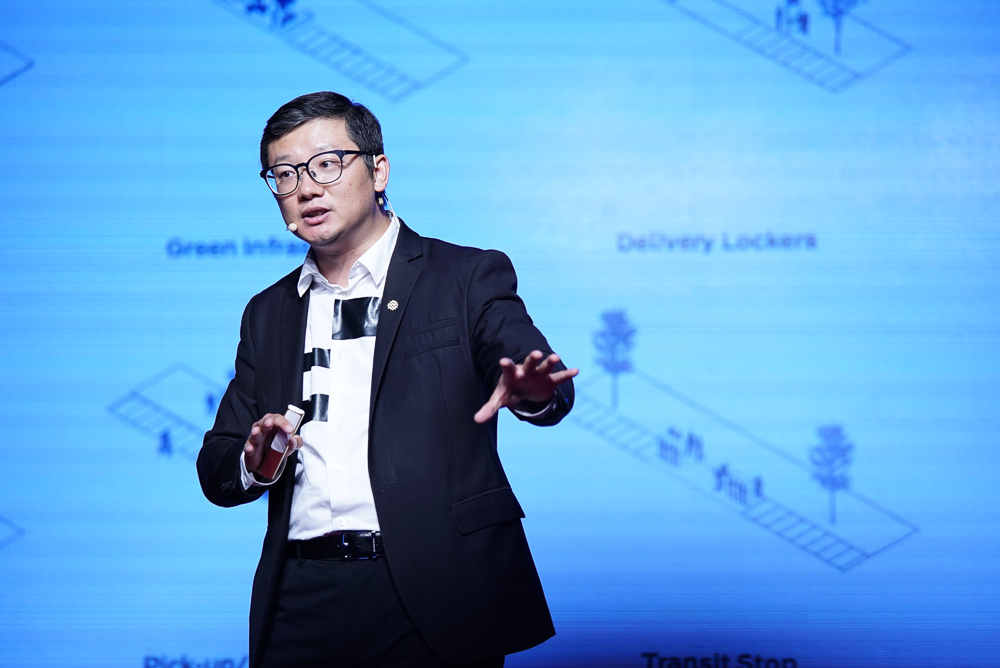



3
做了几年BRT后,刘岱宗开始琢磨街道——BRT意味着街道空间的重新分配,而除了私家车、公交车外,街道上还有自行车。刘岱宗听说哥本哈根是自行车规划做得最好的,2008年,他邀请哥本哈根核心区无车化的设计者杨·盖尔来到中国。
那时他甚至不知道杨·盖尔是谁,见面了,才知道杨是城市规划师。有了初步了解,他又跑去哥本哈根看,那是2009年11月,下午四点,太阳就落山了,天气很冷,但刘岱宗看到依然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从小汽车到自行车的逆转,杨·盖尔居然实现了。往后几年,经由与杨·盖尔事务所的合作,交通专业的刘岱宗逐渐进入城市规划领域。
2014年,美国能源基金会战略转移,不再全力支持公共交通项目。刘岱宗也已回国十年,他总结自己的工作,不能说是失败——北京、济南、常州等城市都建设了BRT,重庆公交集团甚至专门成立了一支小分队,全天候跟着刘岱宗和相关领域的国际传记学习公共交通网络模型,济南则建成了中国第一个BRT网络,但他觉得很累:与相关部门打交道,他经常只能得到20分钟,与决策者的会面只有5分钟。他被“磨”出了很快的语速,清晰的逻辑,还有和不同的人交流的不同话语,对某些部门,他还得讲讲江湖话,以免显得太书生气。但是,公共交通优先依然没有形成社会氛围,用刘岱宗的话说,他的价值观没有实现。
郁闷中,他发现有个“不要钱还能发言”的东西,微信公众号。2014年2月,他注册了“一览众山小”,副题是“可持续城市与交通”,发布自己在十年工作中积累的资料和案例。当年5月,订阅数达到5000,他十分惊讶,没想到在城市与交通的交叉领域有这么多人关心,他决定让“一览”的推送更正规更规律一些,萌生了找志愿者的念头。
至今,“一览”有380多位志愿者,推送了近1700篇文章,其中约九成来自刘岱宗提供的国外最新资料,排版活泼,一开头就是志愿者的名字和脸萌图片,然后提示阅读时间,标识参考文献,所有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他愿意更多人把这些东西扩散出去。找到更多人和他一起,就像一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队伍,推动城市和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4
Sunny是6月1日漫步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她31岁,出生在齐齐哈尔,是国企子弟,习惯了在满是熟人的大院里跑,那里让她感到安全。在内蒙古一家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她来到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六年里搬了七次家。她喜欢养花,住过的一套房子有宽敞明亮的阳台,但经历过两次因为房东卖房而忽然被赶出的窘迫,花了好多草图还是没有把阳台变成花园。这种不安定感不是她也不是她的父母想要的。三年后,因为羡慕同龄人的安稳,Sunny回到老家,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设计,只做了一年,她又一次觉得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又回到了北京。她跳槽多次,在婚庆公司、广告公司和金融公司做策划,又自己做了个小工作室,承接婚礼的鲜花订单。她面容清秀,说话很快,讲求效率,愿意不辞辛苦地工作,偶尔又流露出一点文艺女青年的迷茫。
最初做景观设计的那几年,她形容自己是“指哪儿打哪儿、尽力打好”,没有思考。要设计一个新楼盘,常常是托斯卡纳风格,卖点是顺理成章的,“地中海的阳光”,“北纬42度的洁净空气”;或者请来国外的设计师做主创,古典主义元素在平面图上一一堆叠,描绘出欧式贵族的生活场景。所有这些都会辅以抽象的概念、漂亮的图片、精致的排版,变成PPT中的一页,呈给政府和开发商。
Sunny认为这是广告,或者,“讲故事”,“给你创造一种想象,让你相信现在赚20万,买了它,你就过上了年入50万的生活。人们是愿意为此付费的。”
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做的“不是合理的事情”。白天上班,她告诉客户这个楼盘是精英的、高端的、安全的、私密的,但加班到深夜回到自己住的还不错的小区,她却感到害怕。她只租临街的房子,不敢设想在加班回家时还要在小区内七拐八绕。楼下有个711,如果太晚,她就买点东西,恳请售货员送她上楼。她发现楼盘的“私密”有时打碎了路网,造成了割裂。
“不开心”在加剧,有段时间她在公司不说话,六点下班立刻走,“做得越好越强烈觉得我是一枚螺丝钉,努力帮资本家赚钱。我跟朋友讲了,她说,至于吗?不都这样吗?我不喜欢‘都这样’这个词,都这样,不代表就对了。”
在买花的时候,她感到“又活过来”。婚礼鲜花订单有一搭无一搭的,赶上北京好几个花卉市场拆掉,半年后,她才在另外的市场看到曾经熟识的几位卖花人,“又来啦!”他们打招呼,带着重逢的人情味儿。开开心心地,Sunny穿着T恤短裤,抱着好多好多花,走在水湿的地面上。
2018年11月,Sunny看到一则招募启事,亚太青年交流计划招募18-30岁的青年,推动可持续发展。简历通过后,她在泰国两周,了解了2015年9月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性别平等、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等。经过简单的培训,两百多位如Sunny一样的年轻人被分组,分别到泰国不同的村庄,进行为期6天的调研,形成报告汇报给当地居民。调研很辛苦,但Sunny记得村子里的湖,湖中有个竹子搭的凉亭,几十个来自亚洲各地的年轻人在亭中讨论和分配任务。竹子拼成的地板有点硌脚,阳光穿过亭顶的竹叶,打在潋滟的水波上。在她常年围绕“职场核心竞争力”的生活里,那像个假期。
Sunny感到自己打开了视野,开始对性别、医疗、环境等等问题产生兴趣,尤其对与她专业相关的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议题。回国后,她搜寻这方面的信息。朋友推荐了“一览”。
今年三月,Sunny申请成为“一览”的志愿者。每个申请者都要经过刘岱宗的测试:用一周时间翻译一篇三四千字的英文文章。Sunny分到的文章主题是智慧城市,满是专有名词,她三天没出门,译了出来,成为“一览”第332位志愿者,进了大群。后来,她听刘岱宗说,并不是要用英文水平来“卡”,而是设置门槛,这样加入进来的人会更认真。
群很活跃,大多数志愿者来自建筑、交通、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很多人正在国外留学或者有留学经历。刘岱宗依然是主心骨,所有文章推送前都经过他校验,九成由他筛选,原文发到群里,询问谁可以翻译。不需要分配,志愿者们几乎争抢着来做这件事。群里也会聊点行业八卦,或者分享资源。Sunny说,加入一览很重要的作用,是保持在行业内的活跃度和敏锐度,持续学习,保持前沿。
她也开始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它几乎是个网红书。
这本书的作者简·雅各布斯1916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学毕业后,她做过速记员、自由撰稿人、记者,在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产生质疑,并写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认为,城市是属于人的,城市的活力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能够如何使用它,只有当城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的多样性需求时,才能聚集人气,构建有机的人际网络,使街区拥有活力。这本书1961年出版,逐渐被视为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2005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至今,它仍常常摆在国内书店的显眼位置。
读这本书时,Sunny感到可怕,书已经出版了近60年,但为什么今天跟当时依然相似?频繁搬家,夜晚回家的恐惧,愈加偏远、不断消失的花市,散布在她生活中的感受被串联起来。
“我可以努力工作,获得一定的地位,一定的钱,但如果还是这样的环境,生活并不会因为我有钱有车了就变得更好。”以前她是看看三毛听听音乐现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的人,现在,部分是自我的寻找,部分是被迫,她要去关心更大的世界。
简·雅各布斯去世后,她的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纪念她的活动,Jane' s Walk,每年5月在城市步行,了解自己的街区、道路。目前,全世界有许多城市都加入了这一活动。今年5月,Sunny看到了一览志愿者在上海组织了漫步,她在群里问,北京能不能也组织一场?
刘岱宗说,那你来吧。
“刘老师是这样,不给你任何犹豫的机会”,Sunny说,又有其他人加入进来,很快形成一个九人的小团队,他们打开地图,选取了一些道路,有的路线太长步行太累,有的如刘岱宗所言,“不够多样化”,最终他们选择了从东直门到雍和宫一线,包括东直门环岛这样适宜车行的道路,和以胡同为主的适宜人行的道路,末尾的五道营胡同有很多咖啡馆,算是个舒服的收稍。
5月18日,这个小团队建立,开始做设计,推送宣传文案,找工厂定制周边T恤和手机壳;25日,他们实地走了一趟,写好讲稿;26日,报名入口开放,当天晚上就有40个人报名,第二天中午达到60个。我看到报名信息时,名额已经满了,通过刘岱宗和Sunny,我加入了这个叫做“童步简行”的群,感受到这群年轻人的热切与高效。

5
走了半小时,进入民安街后,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四周变得很安静,当然不是无声的:左侧的老小区里偶尔飘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婴儿的啼哭声,右侧,东直门中学操场上,一小队男孩正在打篮球,嘭,嘭。人行道容得下两三人并排,头顶上,国槐树细碎的圆叶子透出清凉。向南进入南馆公园,看着公园中央的湖,湖中央的小喷泉,漫步的愉悦感终于出现了。
南馆公园始建于1956年,2002年9月改建成北京第一座以中水造景的生态水景公园。绕着湖,大爷大妈摇着蒲扇,穿着白衬衫的中年人挂着耳机快步走,还有小男孩背心短裤,又跑又跳。
公园深处有一个“低碳生活示范小屋”,工作人员介绍它采用的低碳技术:墙壁是麦秸秆压制而成,比人高半米的地方有一排小小的换气扇,内有滤网,可以过滤北京春天的风沙、冬天的雾霾。天花板上是细细的蓝色管线排成的网,叫“顶层毛细辐射技术”,夏天充冷水冬天充热水,水流循环调整室内温度,不会像空调那样直接将冷风吹到人身上,或者令房间变得干燥。
那冷凝水怎么办?有人问。
讲解员看起来有点懵,她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人能问出这么专业的问题。她继续往里走,介绍白色的、压有凹凸花纹的墙壁,“它是硅胶泥环保涂料,来自海中的硅胶土,具有极强的呼吸能力和自洁能力。9年了,乳胶漆会开始发黄,我们这个墙面还是光洁如新,不小心蹭脏了,湿抹布擦擦就可以了。”
造价高吗?我问。
“比普通的墙漆高一点。一般乳胶漆三四十一平,这个六七十一平。”从斜后方传来一个男声。
讲解结束后,人群走出小屋,绕着湖转了半圈,从西门走出,对面就是通教寺。一个志愿者开始讲解这条短短的针线胡同的由来:嘉靖年间一位来自扬州的宋姓裁缝开了家针匠铺,因为裁剪技术精湛,人们把这条胡同也称为“针匠胡同”,到清又改称“针线胡同”。至于通教寺,是明朝太监所建,清成为尼寺,1978年后,寺庙重修,恢复了停滞多年的宗教活动。他提醒人群观察名胜古迹附近的人行交通。
在东直门北小街走短短一截,左转,进入后永康胡同。
如果说东直门环岛是车占据了几乎全部道路,民安街和东直门北中街就是让车与人有了些许区隔,而一进胡同,市声贴身而来。黄的蓝的外卖电动车急促地嘀嘀响着,旧三轮快速驶过坑洼的胡同发出的噼里啪啦零部件快散架的声音,停在路边的电瓶车被碰到了,尖锐地警报。有人在往路边的小卖部卸啤酒,玻璃瓶清脆而又令人心安地撞击。
戴着麦克风的男孩谈起胡同的起源,又说,“艾伦·雅各布斯曾在《伟大的街道》中说,‘最好的街道能激发大家的参与性,人们会停下来聊天或者仅仅是坐在街边随意观望’。好的街道,作为公共空间,应该能增加人们的互动,使整个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他提示道,前面的后永康胡同和戏楼胡同两段,是北京比较典型的没有经过大型商业开发的胡同,大家可以观察和思考一下,如果对胡同进行保护和开发,有什么方法。
一辆小轿车在人群身后不耐烦地按喇叭,骑着自行车的北京大妈喊着,“走!走!”人群需要小心避让汽车,避让居民,以及停在路边的小汽车。因为逼仄,车与人对空间的抢夺尤其明显。
就在这时,路边一个进入小区的通道里,有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在溜乌龟。乌龟的壳高高拱起,爪也随之举起,又缓缓落下。男人看看乌龟,又看看我们。
走过后永康胡同、柏林胡同、戏楼胡同,进入国子监。队伍太长了,志愿者提议我们等一等。在国子监的牌坊下,我问杨少雄,就是那个在“示范小屋”里报出硅胶泥涂料和乳胶漆涂料价格的男孩,他是不是从事这一行。
曾经是。他学设计,毕业后找了一份室内设计的工作,觉得应该是理想当中——说到这儿他笑了一下,好像提到“理想”这个词儿有点不好意思_——的职业,可以安排所有的事情。但很快他发现,“你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而是客户爸爸的时间”。他没有节假日和周末,因为客户常在那时要求他陪着逛建材。他装饰了客户的房子和生活,忍不住想,自己的房子和生活在哪儿?
两年前,杨少雄转行进入一家大型保险公司,之前的不满,现在都能满足了,但他依然对今天这样的活动感兴趣,“初心”,杨少雄说,“设计不是仅仅凿墙铺砖,设计最后还是要落在给人住、给人行动的地方。”



6
“街道上是有阶级的”,刘岱宗说,他的使命,“就是带着小朋友们去革命”。
“新一代的年轻人如果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去做工程,会发现自己永远没有发展机会,中国从1990年开始,修桥造路近30年,各种规范、标准已经成熟,我的同龄人已经把持到所有管理层,年轻人只是重复劳动的赚钱机器。一些年轻人从国外回来,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很多行业中国和国外没有那么大差距,甚至是领先的,但在交通领域中国是落后的,更多不是在技术,而在观念、想法和价值观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想要引领,改变一些东西,实现自我价值”,刘岱宗解释那么多规划、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进入“一览”的原因,“但是年轻人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带领,因为街道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不是一腔热血就能改变的。”
刘岱宗梳理过,一条街道要真正改变,涉及30多个部门:这块地如果在马路牙子——专业词汇叫路缘——以内,规划管宽度,交警管划线和执法,涉及到自行车道和公交专用道由交委管,包括下水、排水、光缆等地下综合管廊归市政,旁边的行道树归园林,园林中间有路灯归市政,路灯上如果有通信设施归通信部门,路灯要供电,供电归电力局。路缘两侧人行道的秩序归城管,涉及到临街建筑物,又回到规划……每个部门的愿景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队友,有的是敌人,有的在两者之间摆动。”
他带杨·盖尔去见地方领导,经常地,领导先问,哥本哈根多少人?
刘岱宗答:整个城市300万,核心城区50多万。
领导总是很有风度,客气地,“50万……”不再说下去。在中国,一个县的人数也经常比50万多。
再见到领导,答完50万,刘岱宗会补充,杨·盖尔还在墨尔本做了复兴CBD的十年计划,还说服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将时代广场无车化。
杨·盖尔是简·雅各布斯的学生,传承了她的想法,又将心理学的很多东西融入城市设计中,形成了他的《交往与空间》,从人与人交流的角度来思考城市规划。
不过,与简·雅各布斯的反叛形象不同,杨·盖尔更多采取与决策者对话的方式。在美国,他与珍妮特·萨迪-汗合作。珍妮特·萨迪-汗在2007到2013年间担任纽约交通局局长,他们一起将时代广场周边大道改造成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同时在曼哈顿岛上建设了长达400英里的自行车道。2016年,珍妮特·萨迪-汗将六年间的街道梳理和改造工作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在2018年被译成中文,《抢街》,刘岱宗更喜欢它的英文名,“Street fight:Handbook for an Urban Revolution”,一场斗争,一次革命。
刘岱宗的角色与杨·盖尔类似,“说客”,他身体往后仰,双手托在脑后,一个敞开的姿态,“我们就是有价值观和思想的说客”。
2014年或者2015年,刘岱宗到同济演讲,案例全是国外的。那时,他还没什么国内的案例可讲。座下都是规划方面的学者,有人站起来说,我很认同你的观点——可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上海能跟纽约一样吗?上海能跟哥本哈根一样吗?
刘岱宗说,那你告诉我,上海能跟哪个城市一样?学不学,在于你想不想干这件事,其他都是借口。
在四五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刘岱宗还是有点愤怒,这样的人太多了,总是那一套,先肯定你,话锋一转,“我认同你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或者“我也喜欢骑自行车但我因为这个那个必须开车”。他马上会说,“我有车但我每天坐公交骑自行车上下班,为什么你做不到?”
刘岱宗掏出手机,打开摩拜,展示骑行记录,总是早上八点一刻左右,他在团结湖下122路公交,骑上摩拜,从三里屯路到东直门;晚上,他从东直门沿着东直门外大街骑到团结湖,再坐122路公交回家。每天都一样。他会盯住对方,“为什么你做不到?”
不久前,在“一览”群里,刘岱宗和“小朋友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年轻人赞美简·雅各布斯,刘岱宗说,她是很厉害,写了一本书,跟时任纽约交通局局长罗伯特·摩西争吵,后人说她阻止了一条高速公路,但那是她唯一成功的案例。书出版了,七年后她就移居加拿大,而美国仍在大兴土木修建城市内部的高速公路。她没有改变什么。
刘岱宗甚至没去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认为雅各布斯是位精神领袖,但是缺乏实现其价值观的方法和手段。他更认同杨·盖尔和珍妮特·萨迪-汗,这些实干者,“他们一旦认同了简雅各布斯的想法,就用尽一生、想尽办法去实现它。”
“死活要跟这些人斗争,就是跟他们斗争!所以是Fight!”通常,刘岱宗持有职业人的平稳,冷静的友善,不过在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他加大了声音,“你不听我说,我就要反反复复地说。”
7
近两三年,刘岱宗发现事情在发生变化。去见地方官员,以前他只有5分钟,现在,他常有一两个小时了。公众对街道的关注也在增强。2017年,经由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的推荐,他在“一席”上做了半小时的演讲,用几张动图,他表明了中国城市化的迅速进程,他说,到2030年,中国将有10.5亿人住在城市,但没有那么多土地给高架桥和停车位了,传统的以小汽车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不得不停下来。
2018年5月,北京CBD管委会找到他,希望他参与到CBD改造中来。那里正在建设新的摩天大楼,又将有数十万人进驻,如果继续开车、停车,这个区域将无法承担。项目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从概念和图纸变成了现实。今年3月,改造动工,现在已经进行了七八成。
七月的一个周末,我去了趟光华路,自行车道重新铺装,一片红色看起来十分鲜明,如果有车停在自行车道上,临近的指示牌就会显示“请立刻驶离”。行道树中间划了线,标明“自行车停放处”。一些路口延伸了路缘,缩短了过马路的距离。斑马线更显眼了,有的线旁边的地面上还装了小灯,据说夜间可以更明确地提醒车辆这里有人经过。人行道宽敞而平整,在路口也更平滑连贯,有人正在跑步。
2016年10月,上海发布《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从“完整街道”视角探索城市街道设计的导则。2018年9月,《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市设计导则》在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官网上公示,“从以车优先转变为以人优先”出现在导则中。
2018年,中国的小汽车销量第一次出现下滑。按照日本、美国的经验,这个数据一旦下降,就再也没涨回去过。对刘岱宗来说,CBD改造是个标志,他认为,在对小汽车最初的欲望消退之后,人们也能够理性思考它是不是值得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足以寄托阶层区隔的愿望,未来,街道的更多空间会留给公共交通,和骑行的、行走的人。


8

初夏的晚上七点钟,天色刚刚昏黄,这一纪念简·雅各布斯的漫步行至尾声。在五道营胡同,人群分成两拨,进了两家咖啡馆。接下来,参与者们要谈谈一路观察的心得。
停车是说得最多的。“买了车必须有地方停,停在胡同里又会占道,规划者和建设者必须考虑到居民和行人的需求”,一个女孩说。好多人点头。一个穿灰蓝上衣的男孩站起来,他对裸露的树坑不满,占据了人行道一半的宽度,下雨会积水,刮风坑里的土还会往外跑,人走两步还会踩进去,要是能盖个盖子就好了。杨少雄站起来,他观察到盲道上有很多井盖,这些井盖通常是凹下去的,可以想象,这会给盲人出行带来麻烦。
“应该有一个平台”,灰蓝男孩说,“胡同的居民对每个井盖、每个花坛是最熟悉、最知道方便不方便的,在规划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应该有一个平台能够向上传达这些意愿,持续给城市输出更多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友好的街道”,穿着白T恤的主持人说,她是个长辫子垂在肩膀一侧的娇俏女孩,“我走过胡同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拍婚纱照,很有趣,不光是公共设施很好,是这些人让我觉得有趣,心情上有一些体验。”
一个男孩,穿着志愿者的天蓝T恤,站起来。
“我喜欢树荫繁盛的街道,喜欢有人的街道,但人也不能太多。最好街道两边有一些居民在散步、乘凉,可以找到老北京生活里传统的独特的状态。”
又一个男孩站起来。
“北京的马路总是设计得很宽,一两百米,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很多街道宽度很窄,只有几米,道路两边有丰富的业态,便利店,座椅,人们可以享受街道。”
主持人翻动PPT,页面上出现了一些国外的街道,路边的小摊儿色彩缤纷而富于生机,许多人坐在路边喝咖啡,观察其他人。在巴黎,每年夏天的一个月,一条高速公路会封闭,铺上沙子,人们可以像在海边一样,在那里晒太阳。
在中国,对街道的意见似乎处于一个犹豫期,一个决定做出来,迅速改变街道的面貌,引起舆论的反弹,又仓促地停下来。
“其实可以让大家早期就参与进街道的讨论,专业人员也需要打开眼界,打开思想,提供更多的选项,给决策者做判断。”刘岱宗说。
在北京,刘岱宗喜欢在街道上骑行,他列举了几条街道:后海边上的柳荫街,恰如其名,柳荫垂地;国子监大街,树荫浓密;当然,还有他视为标志的CBD。
—— 完——
题图为6月1日漫步活动,人们走在胡同中。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