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对非洲的前景是丝毫不看好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士·华生(James Watson)2007年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次访谈时说,“我们的所有社会政策都基于一项事实:非洲人的智力跟我们一样——但所有的测试都表明事情并非如此。”华生接着还质疑了一厢情愿地预设人类都是平等的观点,其理由是“必须跟黑人雇员打交道的人们会发现这不是真的。”
偏见压倒理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科学作家安吉拉·塞尼(Angela Saini)在其新书《高人一等》(Superior)里提出,更令人震惊的在于,科学本身就有可能催生偏见,或被利用来为偏见服务。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人类于19.5万年前首先出现在东非的草原上。但此说常常受到质疑;譬如有一些俄国、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就提出过人类的起源在自己国家的观点。科学并非中立,塞尼写道:“科学家群体对理论的选择不仅受到数据的驱动,还可能会牵涉到个人的动机。”
进化的观念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确定不移。塞尼提到,以前说某个人是“尼安德特人”相当于在辱骂他,但现代欧洲人(而非之前想象的澳洲原住民)被发现和尼安德特人颇有渊源后,这个词就不再是骂人的话了。
纵观人类历史,种族是个相对新的概念。往上追溯直到15世纪,假如有人调查欧洲人对“黑人”的理解,就会发现与其相关的词汇是“有王者风范”或者“有特权的”,它们出自名画《三博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i),此画是当时唯一在欧洲广为人知的对黑人的刻画。随后,启蒙运动引入了分类科学。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划分出了四大人种:欧罗巴人、亚细亚人、亚美利加人和阿非人(afer,在古代迦太基和希伯来语言中意指“沙尘”,非洲的全称“阿非利加”一词即派生于它——译注),可以说一开始就带有偏见。林奈详细地描述了他们黝黑而光滑的皮肤、卷发、低平的鼻子以及宽厚的嘴唇,并声称阿非人是“面无表情,呆若木鸡……诡计多端、慢条斯理、愚蠢不堪……被任性统治着”。
塞尼指出,自那时以来,科学“赋予了种族主义以知识上的权威性,正如它是从定义种族开始的”。她对此类实践的探究读来不无警示意味。

例如,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的前身就是威廉皇帝学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1948年以前,其人类实验可谓“血债累累”,学会里的科学家“自愿与纳粹当局合作,学术利益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形成苟合,以确保这些学者自己的财路和社会地位”。2001年,该学会承认,自家的一名老派历史人物、主管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的奥特玛·冯·弗舒尔(Otmar von Verschuer)“知晓奥斯维辛的种种罪行,而他也出于自己的一些目的,与某些雇员和同行利用了里面的人来做实验”。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反常一面而已。但优生学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也有热情的支持者,这些人也相信“雅利安主义”的神话以及种族的纯洁性。《高人一等》还提到,在二战后,许多与优生学有关联的学者巧妙地“调整姿态,融入了诸如基因研究之类的相近领域”。
在写到这些科学家兼具热情和优雅的同时,塞尼还谈到了当时的潮流如何反对优生学的思想和研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1950年宣布全人类“属于同一种群,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
进一步地,在1972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表明,群体内的基因差异大于群体间。这样看的话,举个例子,一名尼日利亚的黑人男子与一名苏格兰白人男子在基因上的相似性,就要大于他与一名坦桑尼亚的黑人男子的基因相似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令我们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基因科学的好处也引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危害和风险,可能会令我们倒退回“基于欧洲人的形象来刻画人类面貌的启蒙式习惯”,主张差异毕竟有等级高低之分这样的东西。
再举一例,塞尼反思了2005年因布鲁斯·拉恩(Bruce Lah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而引发的争议。这一系列研究提出,某个基因层面的变异与人类大脑尺寸的变化有关(这带来了认知能力的迅猛提升),它发生于5800年前的人群中,但这一变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美极难找到。哪怕“认知优势”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证明,这篇论文仍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追捧,被视为证实了他们那套有害的信念。
2018年,《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这一趋势敲响了警钟:“学者担心,极端分子可能会对古代DNA研究实行审查,并试图利用它们来服务于一些错误的目的。”《高人一等》一书也抱有类似的关切。例如,近年来,印度的考古学家就被安排了发掘与印度教古典文献里的场所、人群和事件相关的证据的任务。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来说,遥远的古代“成为了一种凸显科技和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塞尼引用了考古学家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对某些科学论断的不安,“它们可能会令我们得出恶劣的结论,即我们都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她还在另一处陷入了沉思:“假如认识科学事实就能让一个人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机会变得极小,那詹姆士·华生这种人是怎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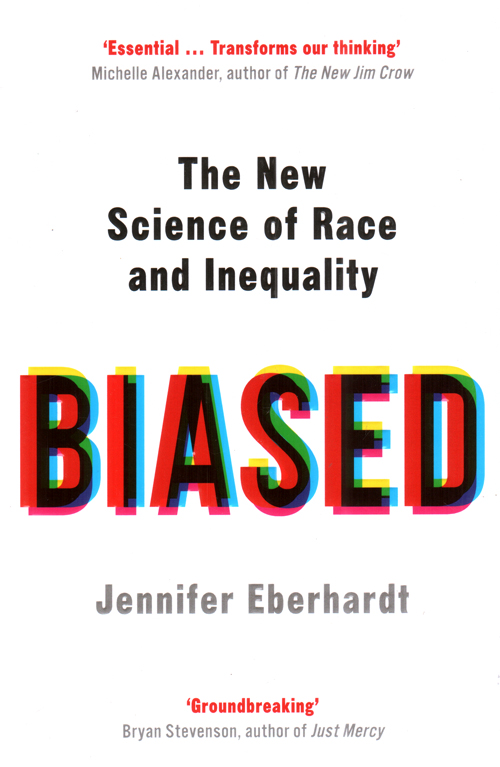
华生这个例子对珍妮弗·艾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的新书《偏见:新的种族与不平等的科学》(Biased: The New Science of Race and Inequality)而言大概也是相当贴切的,该书是对隐形偏见的案例研究。艾伯哈特是一名非裔美籍心理学教授,她也在反思种族主义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将乔治·格里敦(George Gliddon)、乔希亚·诺特(Josiah C Nott)和路易斯·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1854年的畅销书《人类的类型》重新包装了一番,该书对黑人的颅骨有极为夸张的描绘——将其画得跟猿猴而非白人更接近。艾伯哈特认为,这种做法如今“依旧是我们的种族肖像学(iconography)的一部分,限制了黑人进入人类圈子的渠道”。
她的研究重点关注存在于美国的此类偏见,“一旦面孔被认定为属于群体外成员,那它就不会得到处理了……我们只将珍贵的认知资源留给‘跟我们相似’的人。”执法部门的人员大多就信奉这些在1854年颇为风行的、对黑人的领域假设(domain assumptions,即某个学科领域里最基础的假设或曰公理——译注)。不过,艾伯哈特也对科学和技术(可以处理数据,以电脑模拟开枪或不开枪的场景来训练警察)找到解决办法以及带来改变的潜能保持乐观。
鉴于在我们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历史上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观点又有死灰复燃之势,《高人一等》可以说是一篇应景的关于科学与种族的警世寓言。这些观点正在寻求知识上的掩护,塞尼警告称,这些“有害的小种子”只要一丁点水分便能在学术界的核心地带生根发芽,而“如今已经在下雨了”。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