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梁明德·东方历史评论
一
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开始把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手上,而为了加快比较贫困的共和国的发展,联邦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较富庶的共和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份额,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有的共和国的人民产生积怨。但中央的投资与地方需要往往是错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出口原材料,中央对科索沃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比如煤矿,但这些产业聘用的人极为有限。科索沃的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占八成的农业人口陷于经济停滞之中。屋漏兼逢连夜雨,19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党政精英开始公开反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并争取进一步分权,要求获得控制外汇资产的权利,并反对南斯拉夫使用统一的货币。

1966年兰科维奇被打倒后不久,克罗地亚便出现一股改革运动,延续到1971年春。背景是南斯拉夫与罗马教廷妥协,教会不再被视为敌对势力,克罗地亚得以保持宗教自由。克罗地亚共和国党政精英,带领这场地方分权和自由化运动,代表人物是欧洲首名女性政府首长、克罗地亚总理萨夫卡·达布舍维奇-库采尔 (Savka Dabčević-Kučar)。1967年3月,130名文艺人士与学者 (包括80名南共党员) 签署《克罗地亚文字语言名称及地位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Name and Status of the Croatian Literary Language)。南斯拉夫官方立场本来认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只有两种方言: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讲东部方言,克罗地亚讲西部方言。《宣言》却认为,克罗地亚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要求与塞尔维亚、马其顿语等具有同等地位。

铁托面对民族主义冒起,其反应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义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官僚垄断的残余,工人自治要与之进行斗争,并说:“在我国社会条件下,民族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倾向的表现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报告) 铁托又指出,民族主义增长反映着专家治国论、企业“经理独断”以及技术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对经济生产进行垄断的倾向,企图“把共盟变成这些技术官僚主义上层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但在别的场合,铁托又充分承认民族的独特性,只不过是把民族的对立面设置为一个历史的角色。比如他说:“黑山民族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者(即奥斯曼帝国——笔者按) 的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这样就使得本国因奥斯曼统治而产生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群体陷于被动。

1971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生连续多月示威。铁托声言要揪出萨格勒布大学罢课的策划者,认为参加运动的是“流氓无产者、反革命分子、沙文主义分子”,指责“克罗地亚文化协会是一个老窝”,南共“有许多人早该被清除出党”,但并没有交代这些人跟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然后在同一篇演说中,铁托信誓旦旦地保证:新的、更分权的宪法修正案,因为将给予地方加盟共和国“一票否决权”,能为反对分裂主义提供最有力的武器。 (1971年12月1日南共主席团开幕词) 铁托表面上压制了分裂主义,但实际上是在向地方官僚的分权主张投降,更促进了地方官僚对经济资源和生产的垄断,并加速南斯拉夫南北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但铁托的让步并没有满足示威者。铁托于是一转立场,动用军警把运动镇压了下去。及至1972年,克罗地亚共盟共开除了两万五千人的党籍,达布舍维奇-库采尔也被打倒。到了1975年,实践学派也遭到了镇压。铁托早在1971年便指责它“在我们眼皮底下举行了形形色色的鬼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讨论会,如科尔丘拉岛 […]的讨论会等等。”(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实践学派成员大多丧失国内教席,被迫流亡海外,到欧美的大学任教。
1974年南斯拉夫颁布新宪法,虽然指名道姓宣布铁托为终身总统,却主要是一份分权的宪法,而主要起草者正是卡德尔。为了避免克罗地亚之春之类的运动再次发生,新宪法向加盟共和国下放政制设计、公共财政、社会服务、警政、民防和司法等权力,更回应了1967年《宣言》的要求,承认克罗地亚语地位;南斯拉夫于是走向“邦联化”(confederate state)。铁托宣称新宪法“在加强自治方面进行的改革,使民族主义势力感到它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并说明道:“我们一向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和反映本民族存在的权利出发。[…]以尊重他们培育和发展其民族特点、语言、文化和习惯的权利为前提。”(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机构却开始在地方层面上进行集权化。维系着南斯拉夫统一的,就只剩下军队和铁托的个人魅力。

1974年宪法被指偏袒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宪法遭到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贝尔格莱德的左派大学生占领校园,抗议分权改革背弃南斯拉夫劳动阶级的团结。支持实践学派的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osić),则指责新宪法剥夺了塞族人的权利,并以此为契机从左翼过渡到右翼立场,并最后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成为“塞尔维亚国父”。1974年宪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向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区党委,而不是各族公民下放权力;简言之,是以分权化回避民主化。南斯拉夫回避民主化的原因有很多。避免少数民族在选举中成为弱势,重演二战时的民族冲突是一个。这也大概是铁托的考虑;他反覆强调南斯拉夫民族间必须在权力和地位上平等,这就意味着不能放开选票政治。但是新生的加盟共和国党政精英自己搞集权,则成为另一个更阴险的理由。不放开民主,则地方党政领导人要么完全可以漠视民意,要么就在权威被挑战之时,变得完全民粹主义以争取支持。在米洛舍维奇在八十年代末的“反官僚革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下动用民粹主义发动群众所带来的庞大政治力量。

1974年宪法进一步落实党政分开,南共的权威继续下降。虽然按照1952年南共六大决议,南共主要负责思想工作,但南共在这仅余的工作上也表现不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五十年代铁托便提到:“我们取消了中央党校,但有些地方也在当时取消了共和国党校,虽然后来事实纠正了它,又重新组织了党校和训练班。但是,共和国党校的取消就是错误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认为在分散管理以后,一切都将自流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会自然地发展起来。”(1956年3月南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事实证明,铁托一语成谶,南共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失败,并因多次地方分权而滋生地方民族主义。在克罗地亚大学生罢课后,铁托指出:
“南共联盟有思想危机。[…]各种报刊早就出现种种 […]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而我们却并没有予以回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大意了。我们认为,在我国的民主条件下可以这样干和这样说。[…]我们早就该采取措施了。[…]你们看一看大学里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计划吧!比如贝尔格莱德大学每周只上两堂课。至于萨格勒布,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课程。[…]向低年级的小孩还讲一些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 […]可是大学里就松松垮垮了,孩子们已经学到的一点东西到后来也就忘掉了。”(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从铁托的话中,可见南斯拉夫思想危机之深。在1973年石油危机与及后的经济放缓下,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精英急需转移视线,把经济停滞和欠缺民主,刻意解读成联邦中央未有充分对加盟共和国分权的结果,甚至指责隔邻的加盟共和国是自身发展的障碍。1974年宪法为这种言论提供了充分的平台。从1945-1974年,南斯拉夫逐步而持续的采取“宏观去中央化”;1974到1987年,则同时进行激进的“宏观去中央化”和“微观中央化”,即在弱化联邦中央政府权利的同时强化加盟共和国内部的集权。这最后演变成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八个共产党争夺中央控制权”的局面。地方政治精英也试图阻止横跨加盟共和国、涵盖全国的社会运动冒起,以免其挑战加盟共和国的新生权威。即便如此,在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关系仍然良好,主要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远。在1962-1989年间,通婚率也相对地高,平均有12.63%,以科索沃的6.98%最低,以伏伊伏丁那的25.95%为最高。然而好景不长,铁托的逝世将使得南斯拉夫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二
1980年5月4日铁托逝世,联合国154个成员国家有128个派代表出席丧礼,其中有4名国王、6名王子、31名总统、22名总理、47名外交部长,涵盖冷战两方,场面盛大。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但是在铁托晚年,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开始急速走下坡。在铁托去世的1980年,总失业人口达到一百万人,失业率高企达10%。GDP增长从1956-1964年间的8.8%减少到1980-1984年的0.4%。到了1984年,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失业率都高企在20%,而通涨率则达到50%,并且继续上升。及至1985年,失业人口有六成是25岁以下的青年;25岁以下人口组别有四成失业。全国更有四分之一人口在贫穷线之下。

如前所述,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条件差异极大。其中原因包括工人自治企业之间实行自由竞争,促使企业压缩投资比率,减少人手;而且政府自1964-1965年市场化改革后便放弃计划经济,只通过国有银行调节经济。联邦政府向地方共和国下放经济决策权,意味着地方能够决定教育、福利、公营企业薪酬表和招聘量,全南斯拉夫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也一直没有形成,使得“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前景完全取决于他所处的地区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但是铁托的官方立场是:“南斯拉夫只有一个工人阶级 […]在涉及例如就业问题的时候,决不允许计较各民族的人数。我一直主张,在我国的经济部门、社会生活里,首先要看能力”。(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结果企业为了自保,首先开除那些可以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女性和年轻人,其次是移民和农民工,尤其是那些不属于自己族裔的移民,以迫使他们离开劳动力饱和的城市,回到贫困的乡下。
这使得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族群关系十分紧张,比如在科索沃属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就深陷社会经济危机当中。最后连南斯拉夫的塞族人整体都丧失安全感,不再安于多民族的联邦体制。波斯尼亚也开始出现伊斯兰教立国论。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osnia-Herzegovina) 总统的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 (Alija Izetbegović),在二战时曾参与招揽穆斯林的纳粹党卫军外围组织。他在1970年撰写《伊斯兰宣言》,精神上延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伊斯兰现代化论,提出在波斯尼亚复兴伊斯兰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1983年他因此宣言被逮捕监禁。在九十年代波斯尼亚战争时,塞族武装将反覆引用他的著作,来证明波斯尼亚穆斯林有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企图。

挑战还来自南斯拉夫一度想兼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铁托曾说过“…少数民族应当是使各国人民接近的桥梁,应当对他们的民族所属的国家和现在是他们祖国的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贡献。”(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享有自治权和文化自由。他们理论上是与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关键。然而阿尔巴尼亚在1948年苏南交恶后便疏远南斯拉夫,1960年中苏交恶后又向中国靠拢,成为全欧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毛泽东决定全力经济援助阿尔巴尼亚,并最后争取到阿国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席位。1961年起,中国为阿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1.25亿美元借款,建设二十五座化工、电机和冶金厂。阿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识字率从5% 一跃为98%;其曾是欧洲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至1980年建成319公里线路,并于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全国电网,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先进。依靠中国援助实现了发展奇迹的阿尔巴尼亚,自称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对于科索沃的一些阿尔巴尼亚裔大学生而言,阿尔巴尼亚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女性平等,消灭了官僚主义,且不如南斯拉夫,拒绝与资本主义西方妥协,所以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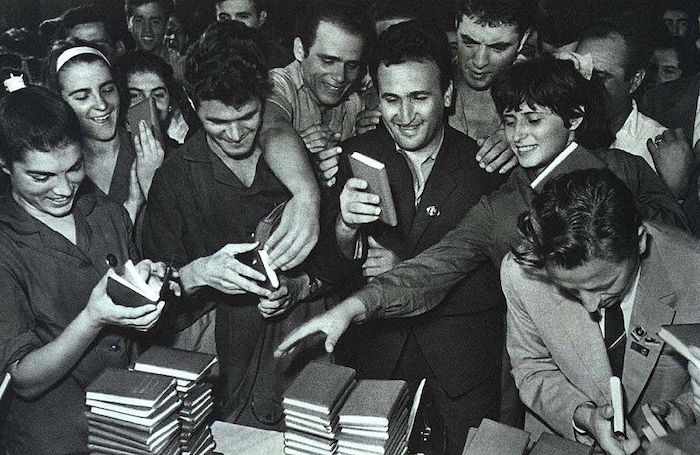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六七十年代开始进入自治省政府工作,形成官僚阶级。科索沃的专上学府因此主要提供投考政府工作所需的文科教育,而不是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职业教育,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然而学生占人口比率极高,巧合跟失业率一样为27.5%。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 (Priština)甚至有十分之一人口是大学生。科索沃的八成人口是在私有企业,而不是工人自治企业中就业,获得招聘与否很取决于家庭关系和族群因素。科索沃当时是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下的一个自治省;大学生们认为,只有当科索沃地位能够上升为正式的加盟共和国的时候,才可以夺回经济决策权。1981年3月11日,铁托去世后不够一年,普里什蒂纳大学生示威,触发点竟然是食堂食物难吃。示威持续多月,终于在军警镇压下告终,近六十万人被抓捕、监禁和审问,科索沃形同占领区。此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党政领导难以放心,但又因地方分权和民主制度,无法简单清除这些人员,于是就衍生在科索沃自治省内属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权益的问题。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黑山、罗马尼亚组成的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总攻击,收回科索沃到伊斯坦堡以西一百多公里处的大片土地。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中古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但1913年塞尔维亚收回科索沃的时候,其塞族人口相对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成为少数。1986年,前实践学派领袖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ć)、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osić) 等人发表《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发表备忘录》(SANU memorandum),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利用高出生率作为对付塞族人的武器,又认为在二战中受纳粹德军、法西斯意军招揽的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无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认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并残留着法西斯倾向。更指出阿尔巴尼亚人从来都受惠于强大国外势力的支持: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到意大利和德国,到泛伊斯兰运动等等。马尔科维奇建议在科索沃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并撤销部分对该自治省的投资,警告不如此做的话就会在欧洲孕育出一个伊斯兰国家。先后担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和总统的伊万·斯坦鲍利奇,虽然不得不公开表态反对备忘录的内容,但还是在明在暗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精英角力,主张削减自治权,宣称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黑山人的权益,甚至即使被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在所不计。

斯坦鲍利奇在出任塞尔维亚共盟书记之后,扶植其好友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出任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支持他在1984成功竞选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以及在1986年接任塞尔维亚共盟书记。米洛舍维奇出生于1941年,在二战时期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下长大,但家庭背景可谓悲惨,父亲为东正教神学家,1962年因故自杀,其母亲在十年后自杀,而他在南斯拉夫人民军官至少将的兄长,也在1963年自杀。米洛舍维奇是个病态政治赌徒,也善于操控媒体。1987年4月24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向塞族人讲话,事先串通塞族人搞事;讲话时,在场的一万五千名塞族和黑山人与阿尔巴尼亚裔警察推撞,遭警察棍殴,群众以投掷准备多时的石块还击。米洛舍维奇马上抵达现场,并在电视镜头前向在场的塞族人说了一句:“你们不会再挨打!”此言一夜传遍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一言丧邦。9月3日,科索沃帕拉琴 (Paraćin) 发生枪击案,一名曾于1984年企图叛逃阿尔巴尼亚被捉捕的阿尔巴尼亚裔士兵,在其他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协助下,枪杀多名塞族同袍后自杀。两族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张。其中一名塞族士兵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丧礼时,有两万人送殡,群众游行到大南斯拉夫主义者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Aleksandar Ranković)坟前拜祭,并高唱南斯拉夫国歌的“嗨,斯拉夫人!”斯坦鲍利奇主张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领导耐心磋商,但米洛舍维奇却主张强硬措施,两人僵持不下。1987年9月22日,塞尔维亚共盟举行十届八中全会,米洛舍维奇精心安排了电视直播,并在镜头前宣读一名党委所写、举报斯坦鲍利奇施压的信,成功打倒了斯坦鲍利奇。
1987年以后,米洛舍维奇逐步解除科索沃的自治权,迫使党政和传媒机关清除阿尔巴尼亚裔干部,以塞族人取代之,并下令普里什蒂纳大学减少阿尔巴尼亚裔学额,增加塞族人和黑山人学额。1988-1989年米洛舍维奇发起“反官僚革命”(Anti-bureaucratic Revolution) ,发动塞族群众抢夺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和黑山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权,并趁机安插亲信。米洛舍维奇所支持的“小将”不少极为年轻,比如26岁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ukanović)打倒了老党委,1991年担任黑山总理时才29岁。1989年2月科索沃举行总罢工,捍卫阿尔巴尼亚裔原省委主席阿森·弗拉西 (Azem Vllasi)。在贝尔格莱德,数十万塞族民众聚集国会前地,要求严惩弗拉西。科索沃罢工遭米洛舍维奇派坦克部队镇压,弗拉西则被控反革命罪,遭逮捕关押。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古战场嘎兹蔑斯坦 (Gazimestan,“画眉坪”) 发表演说,纪念1389年奥斯曼帝国打败塞尔维亚王国的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宣称科索沃才是塞族的发源地,提出要保卫塞族少数权益,并批评1974年分权宪法。在“反官僚革命”发生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政干部人人自危。1990年1月南共举行十四大,斯洛文尼亚党委提出修正1974年宪法,进一步加大分权,甚至成立一个“非对称联邦”(asymmetrical federation),结果被否决。米洛舍维奇利用与会者多数优势,试图向斯洛文尼亚施压,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代表却奋起抗议,中途离场;南共至此分裂。9月,米洛舍维奇宣布收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省自治权,置其于塞尔维亚直接管辖之下;九十年代初的科索沃形同种族隔离国家。
三
塞族人也许觉得,塞尔维亚作为唯一需要划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国,如此安排并不公平。但事实是,一个弱势的塞尔维亚其实对南斯拉夫的团结有利,而“塞族人需要团结的南斯拉夫,多于南斯拉夫需要他们”。其实问题症结,在于经济不平均的问题上升至民族对立。早在六十年代,铁托就指出要“加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报告) 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权之后,联邦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调剂地方发展困局。
1979年南斯拉夫外债达到193亿美元,1984年再上升至212亿美元。其中65%的外债是由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自行索借。1980年代中期,通涨率达到120%。国际货币基金 (IMF) 向南斯拉夫贷款后,向该国施加各种严苛条件,要求实行紧缩政策和结构改革,包括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由于1974年宪法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采取紧缩政策、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责也落到地方身上。但铁托早就给予地方领袖违抗的理由,说过:“如果你们认为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应为了加速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勒紧裤带,那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有发达的共和国和不太发达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说,我们哪一个共和国可以迫使工人阶级勒紧裤带。工人阶级有权反对这样做,我们南共联盟领导也不会给你们这个权利。”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 (Ante Marković,与米哈伊洛无关) 利用高企民望,推动紧缩政策,却遭米洛舍维奇以加印钞票抵制,结果前功尽废。在国家土崩瓦解之际,马尔科维奇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真正的“裱糊匠”。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拒绝接受紧缩政策,也不愿帮助塞尔维亚等南部地区解决债务问题。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89年就已经喊出“Europe Now!”的口号;1990年4月选举中,竞选克罗地亚总统的民主联盟候选人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đman)主打“去共产化”口号,并将之等同于“去塞尔维亚化”。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脱南入欧”的呼声。在1990-1991年间,苏联走向解体;南共在十四大破局后,也实际被解散。塞尔维亚共盟改名为社会党,黑山共盟则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赢得地方选举。1991年春季,南斯拉夫面临无法偿还外债债息的难题,但美国和欧共体国家都不愿再向南斯拉夫融资;另一边厢,又大力援助刚变天的东欧国家。“脱共入欧”似乎有利可图。这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新精英蠢蠢欲动,并于1991年相继宣布独立,其中德国更扮演了怂恿的角色。然而,只有斯洛文尼亚 (人口九成为斯洛文尼亚人,占南斯拉夫全域斯洛文尼亚人99%) 才有能力成为单一民族国家。
南斯拉夫的新仇,不少是延续二战前的旧恨。克罗地亚新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đman)的父亲在1920年代为克罗地亚农民党干部,图季曼更在15岁时曾见过农民党主席。二战时,图季曼参加南共人民解放军,官至少将,但后来退役成为历史教授,主张民族史观,并曾于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被镇压时短暂遭到关押。当选总统后,图季曼主持修改宪法,把克国定义为克罗地亚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共和国,下令各级政府着手开除塞尔维亚人,并取消西里尔字母的法定文字地位。此时的各共和国政治精英都在竭力强调各民族宗教上、文字上、方言上的区别,并在媒体上宣扬一种讯息,即:各民族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见解不同而不能共处,而是因为异民族在文化、宗教、历史上与自己不同,甚至比自己低劣。那些可以勾起对过去“黄金时代”幻想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符号都被发挥极致,尤其是那些与历史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中古王国有关的符号和记忆;人民走向非理性和疯狂。塞尔维亚媒体指责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是二战时乌斯塔沙傀儡政权的延续,甚至正与德国合作建立“第四帝国”,而克罗地亚媒体则把塞尔维亚与残暴的祖国军联系起来。

实践学派领袖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时为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米洛舍维奇副手。他觉得塞尔维亚代表了南斯拉夫的进步因素,甘愿当民族主义旗手,更声称投身政治是为了挽救克罗地亚东部的塞族人免于被清洗。马尔科维奇支持米氏的社会党,是他忠于左翼的表现,即便这个党已无社会主义可言。但马尔科维奇纠缠于自治权,其逻辑是荒谬的。如果克罗地亚里的塞尔维亚人应该有自治权,那么“塞尔维亚族地区的克罗地亚族人,是否也应该有自治权呢?”在塞尔维亚的支持下,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起义,设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最后于1995年被克罗地亚军攻陷;米洛舍维奇意图与图季曼瓜分波斯尼亚,前者在波斯尼亚建立塞族共和国 (Srpska Republika),并对伊斯兰教徒进行清洗。

塞族武装部队人员主要来自失业的年轻人和城市里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当时在他们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一个“假民族”,其本质是受奥斯曼帝国利诱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他们要不是穆斯林化的克罗地亚人,便是穆斯林化的塞尔维亚人。因此,波斯尼亚要不是属于克罗地亚,便是属于塞尔维亚。为了消灭波斯尼亚穆斯林,塞族武装进行清乡,屠杀大量穆斯林男性,最惨烈的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 大屠杀,共杀害八千名成年男性和男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武装又占用酒店、学校等设施,建立了多个强奸集中营,把俘获的穆斯林女性关押在此,日夜施暴。塞族武装明言,目的是让她们怀上塞尔维亚祖国军 (Chetnik) 的孩子。一些女性在怀孕后被释放,但不少却遭到杀害。克罗地亚武装也试图让塞族妇女怀上“乌斯塔沙的孩子”。最后各方在美国斡旋下停战,于1995年12月签署岱顿协定 (Dayton Accord),波斯尼亚由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族共和国组成联邦。话音未落,科索沃战争又爆发,北约以轰炸贝尔格莱德,迫使米洛舍维奇退兵。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塞尔维亚人和88%的克罗地亚人认为战争已经永远破坏了族群关系,两者之间以及与波斯尼亚人再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南斯拉夫从艰难结合,到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与个体跨文化适应相关的能力)高度发展,再到相互残杀的过程,可以说是20世纪中最戏剧化的国家史之一。在社会主义和铁托的个人整合下,南斯拉夫从二战的摧残中冒起,维持了三十五年的民族融合和快速发展,但最后不敌经济与民族危机的挑战。这到底为国家的治理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训?有论者认为,最基本的就是:“如果 [联邦] 组成单位之间有重大文化或民族差异,那么文化议题将几乎肯定会变成政治议题。”但这个结论并不能帮助组建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本身并不承认人有民族区别,故此并不能提供思想资源,引导人们理解、接纳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何况根据铁托自己的分析,在南斯拉夫的教育体制里,有可能连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教育都没有做到。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各地民众都有过英勇反对内战的行动,但最后都杯水车薪。1992年4月5日波斯尼亚战争爆发前夕,大批反感于种族煽动的萨拉热窝各族市民,游行呼吁和平,期间占领国会,抗议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推行其穆斯林多数主义,并冲击邻近的塞族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žić)的总部,最后被塞族枪手枪击而四散。实践学派内忠于左翼的米拉丁·日沃基奇 (Miladin Zivotic) 与米洛万·吉拉斯一道推动和平运动,试图斡旋波斯尼亚冲突,并捍卫科索沃穆斯林,直到1997年在忧愤中去世。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行动造成北约连月空袭和大量士兵伤亡,酿成极大民怨。他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中老年人,而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下成长的年轻人,则对他愈加反感。塞尔维亚恶性通货膨胀达到每月3亿1300万%,物价翻倍只需要34小时。2000年,米洛舍维奇被指操控选举;10月5日,“抵抗”(Otpor) 青年运动和反对派群众七万人兵分五路进攻贝尔格莱德,推翻米氏政权。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会大楼前聚集的愤怒民众不再如1989年般,要求米洛舍维奇惩罚科索沃,而是要打倒米洛舍维奇自己。

其实南共领导人的奢侈生活和腐败,早已广为人知。铁托早在六十年代,也曾提到要打击“形形式式的贿赂”。铁托的副手、副总统米洛万·吉拉斯 (Milovan Đilas,又译“德热拉斯”)在五十年代著书《新阶级》 (The New Class),引申铁托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责南共干部在革命成功后成为新贵族,结果吉拉斯却遭铁托打倒。南共腐败问题,在八十年代经济危机中,成为党政精英的计时炸弹。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恰好达到转移视线的作用,其所掩埋的是新精英的严重贪腐和自肥。南斯拉夫的危机也不能孤立的去看,而是要在国际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美国和跨国金融机构推动自由化、私有化、民主人权等目标的语境中检视。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客们首先以结构调整为名,收回工人自治权,把这些企业国有化,然后再私有化,把经济资源大量化公为私,手段与俄罗斯、东欧新贵如出一辙。克罗地亚的国企私有化,甚至涉及有组织经济犯罪。及至2000-2001年,除斯洛文尼亚外,所有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都在破产边沿。到2001年,克罗地亚失业率仍有22%,马其顿为32%,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高达50%。
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与个体跨文化适应相关的能力)建设如果说有其社会作用,主要就是阻止民粹主义政客转移视线,把可以解决的、乃至针对既得利益的政治经济矛盾,解释成不可解决的族群文化矛盾。文化智商主要是个人层面问题,其提升作为社会系统工程,应该社会整体层面向所有个人推而广之。然而作为行政者,重点乃应该在于保障文化智商不因故倒退。关键是使人们不因文化差异产生反感,特别是当冲突的根源不是文化差异本身,而是与其重叠的经济差异。为政者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民族界线与经济差异重合,因为无论文化智商有多高,都不可能克服实际经济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和生活压力。如果解决经济差异意味着中央政府采取更强力的经济集权措施,以对落后地区进行倾斜投资,这也是保障长远民族融合所不能避免者;只要措施得当,通过充分协商实施,其并不构成对地方的不尊重。在南斯拉夫的情况,1952年以后每十年一次的宪法修正,使得联邦中央政府处于非常虚弱的财政状态,又无法干预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政策,而且从未建立全国范围的劳动市场,使得联邦中央在各地工人自治企业进入转型危机时,难以介入帮助。同时,联邦中央对科索沃等地投资政策失当,忽略农业和地方工业发展,忽视职业教育的加强。工人自治对农业问题也没有帮助,加上工人自治企业在任免员工上有很大随意性,依据通常是族裔身分。这些都使得科索沃在七十年代末陷入经济危机;如此,到八十年代衍生出民族矛盾几乎不可避免。族群之间“可同富贵不能共患难”,恐怕是条铁律,为政者必须有所准备。
铁托过分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统合能力,深信历经战争革命达到独立和联合的各族人民不会背叛联邦,于是即使被迫承认南共思想建设极为失败,即使在生前多次主持分权修宪,还是相信“身后不会有事”。然而,南斯拉夫在可以于文化政策上采取强势的时候,却采消极弱势。铁托、卡德尔等南共领袖,在个人层面表现出极高水平的文化智商,但是只承认文化差异并允许政治分权,而没有积极建构文化融合。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并不是缺乏这样的行政资源,但它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重蹈“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覆辙,从一开头便有削足就履的态度,对那怕是适量的文化融合都采取了投降主义。早在建国初年,卡德尔便宣布:“我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没有 […]以同化各民族语言或文化为原则 […]作为基础。”(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报告)

铁托强调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和剥削阶级成因。这项分析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显示,分离主义确实是与地方党政精英的经济垄断企图乃至腐败有关。然而,铁托没有看到、或是假装看不到:文化差异本身就会滋生民族主义和对立情绪。铁托对可能滋生民族主义的因素掉以轻心。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政府层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甚至是在无必要的时候过度强调“异”而忽略“同”,而且“同”的部分只有虚无飘渺的“无产阶级团结”,这是为政者的一个大忌。其次,是在公民教育上缺乏训练国民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这又是多民族国家一大忌。南斯拉夫文化政策欠缺协调,文化差异于是无序发展。历史遗留问题的未能解决,也是南斯拉夫的大失败。阻碍讨论二战杀戮和历史冲突,并不能阻碍人民自行保存集体回忆,结果当官方社会主义不能给予合理答案时,民粹主义政客便得以乘虚而入。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几个相互残杀的族群,是否真正有文化冲突,还是同多于异呢?从宗教上,确实有其深刻区别,但语言上却是基本一致。文化融合政策,简单如促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达成文字统一,虽然可能会引致一些阵痛,但可以免除最不必要的文化差异,避免为南斯拉夫联邦制造额外行政负担,也避免为克罗地亚之春以后的民粹政客提供现成的武器。从社会主义无神论的角度看来,宗教差别确实是细微末节的分别,在社会主义下将自然消亡;但不积极进行文化融合的结果,就是这三个族群,往往因为类似于《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就“鸡蛋应该是大的那头还是小的那头放到蛋杯里”这样的末节而相互杀戮。实际上,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塞尔维亚语,目前也在社会推动下逐步进行拉丁化,且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文字也早已拉丁化,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塞尔维亚语进行文字改革并不是天荒夜谭。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南斯拉夫崩溃之路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