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你读过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所罗门之歌》或是《最蓝的眼睛》,那么你肯定知道,种族问题是贯穿莫里森几乎所有作品的主色调,她所讲述的故事,与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一样沉重。在2017年出版的作品《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中,始终致力于打破美国文学经典中的种族隔离的莫里森研究了美国文学中的各种思维及行为定式,并探讨了这些定式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决定了“自己人”与“外人”的界线的。
莫里森认为,“他者化”(othering)乃是一种控制手段,运用它的不只有美国白人,任何想要通过排斥来维系自身纯粹性的群体都会如此。在种族议题上如此,在性别议题上也如此,在民族问题上也不例外。以前如此——《他者的起源》整理自莫里森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纵观讲座的92年历史,她是其中的第四个女性以及第二个黑人讲者;今天,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民粹主义泛起的其他各地,仍然如此,甚至愈演愈烈。
88岁高龄的莫里森日前在纽约病逝,而她杰出的想象力和不倦的战斗精神长存,她为我们留下了自己为平等、为人性所作的雄辩,及其作为世界公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敏锐感知。在莫里森逝世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重刊旧文,以寄哀思。
《托妮·莫里森是如何讲述排外视角下的“他者”的?》
一代人以前,文化战争打得正火,托妮·莫里森算是其中的锋线人物,她致力于打破美国文学经典中的种族隔离。在1988年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及其文论集《在黑暗中弹奏》(Playing in the Dark)中,她抨击了文学经典成分过于单一的问题,指出白人独霸文坛的现象看似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但其实是“有意为之”的。她还指责,某些学者在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时候有“刻意剪裁”嫌疑,无视了黑人的存在。然而,拓展大家对美国文学的既有观念,使其超出单纯的白人男性范畴,并不只是对非白人读者有好处。莫里森谈到,有关黑人性(blackness)的文学作品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野蛮”劫持,而一种开放的态度将会有益于美国的精神及智识健康。按她的说法,所谓的白人性(whiteness)是个“很不人性的理念”。
在新书《他者的起源》中,莫里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上述主题。她深入研究了美国文学中的各种思维及行为定式,探讨了这些定式如何在不经意间决定了“自己人”与“外人”的界线:一部分人得到接纳,另一部分则被视为“他者”。早些时候,她曾经撰文分析过诸如威廉·福克纳以及恩斯特·海明威等现代主义作家的种族歧视倾向,指出他们要么把黑人角色非人化了,要么有意淡化了非黑人角色中可能蕴含着的“黑人性”。莫里森观察到,这种把某部分人“开除”出人类行列的做法,不仅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各种习惯当中:战争与经济剥夺使千百万人无家可归,令其难以得到体面的待遇。“他者化”(othering)乃是一种控制手段,运用它的不只有美国白人,任何想要通过排斥来维系自身纯粹性的群体都会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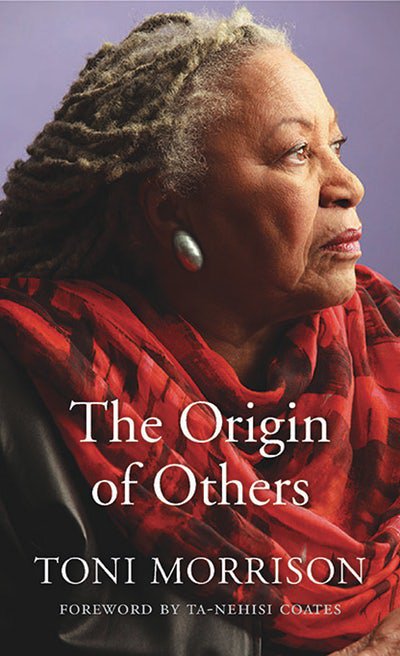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讨论背后,莫里森的个人生活经历构成了支点。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期(1930年代):来访的曾祖母米利仙·麦克蒂尔(Millicent MacTeer)是个厉害角色,也是个纯种黑人。麦克蒂尔打量了一下托妮和她的姐妹,发现这两位女孩的肤色偏白,便斥责她们的脸是“被动过手脚”的。肤色主义(colorism)这个词原本指黑人看不起自己的黑皮肤且倾慕白人的取向,不过,从上面这件小事来看,一切基于肤色来论断人的做法其实都可以算在里面。“很明显,”莫里森写道,“‘被动过手脚’的意思就是,哪怕你还没被打成外人,也已经不那么纯粹了。”从小就遭到“被污染过,不纯粹”这种指责的莫里森发现:与基于肤色的自我仇视类似,他者化的做法在家庭内部就已经有其源头,并且与种族、阶级、性别及权力有着广泛关联。
莫里森为读者展示的这部“他者化”历史,代表着一种从多角度重新反思历史的努力。文学经典的去种族隔离化这一主题在《他者的起源》中没少出现,其次数比起《在黑暗中弹奏》而言是有所增加的。由于莫里森多年以来的努力,美国文学在尊重多元文化及种族多样性方面有所进步,如今已经很难再无视有色人种作家了。莫里森自己也几乎拿遍了作为一个小说家而言可能拿到的所有奖项:普利策小说奖,诺贝尔文学奖,总统自由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不一而足。《他者的起源》整理自莫里森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liot Norton)系列讲座,纵观讲座的92年历史,她是其中的第四个女性以及第二个黑人讲者。
诺顿系列讲座向来以闪烁着智慧光辉著称,莫里森因其性别、种族以及与美国相关的研究主题,在其中显得独具一格。该讲座以前倾向于选择来自欧洲的主题,且较为推崇英国的学者。直到2014年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在那里开了“爵士乐伦理学”(The Ethics of Jazz)之后,诺顿讲座才算是正式认可了源自美国文化以及黑人的智慧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莫里森的系列讲座与专著乃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它们见证了她所归属的那个传统在美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影响——这一传统可追溯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对白人性的批判,年轻一代的代表则有塔-内西斯·科特斯(Ta-Nehisi Coates)。
莫里森早年曾从两个女奴——玛丽·普林斯(Mary Prince)和哈瑞特·雅各布(Harriet Jacobs)——的回忆录中观察到他者化的迹象,二人都有遭受奴隶主的身体及精神虐待的记录。1831年,普林斯的主人曾通过殴打来强化其等级权威;其回忆称奴隶主“袖手旁观,下命令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奴隶……吸着鼻烟,摆出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三十年后,雅各布则谈到奴隶制如何使“白人父亲残忍且易怒;儿子则嗜暴而放荡。”在奴隶制之下,他者化的过程是物理性的,其运作方式是单向的,即从奴隶主到奴隶。
莫里森换了个角度来提问,“这些人是谁?”——她关注的不是作为受害者的奴隶,而是作为加害者的奴隶主。“惩罚者基本上认为受罚者不是人……这才能产生鞭打者的快感。”通过视奴隶为“另类”,莫里森如此总结道,“体现了一种竭力想要证明自己正常的心态”。然而,奴隶主和奴隶总归都有人性,这是奴隶主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主奴关系核心环节的虐待行为,其实同时让主奴双方都丧失了人性。“他们看起来就像在怒吼‘我不是野兽!我不是野兽!’”但这当中没有谁是赢家。
即便在动用物理性强力的情形下,那些视别人为他者的人也会诉诸一些语词来进行自我描述。托马斯·西索伍德(Thomas Thistlewood)是个英国种植园主,也是个强奸犯,1750年去了牙买加。此人详细地把自己侵害女人的行为记录了下来,其记录内容包括他脑子里计划的施暴时间、地点、方式,甚至还包括房间大小。他还在用拉丁文写成的日记里提到了这些性侵行为。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完全是另一个口吻,它讲一个颇为美好的奴隶故事,以此来界定他者。斯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一座奴隶的小屋,莫里森接连用了“格外吸引人”,“很有教养”,“魅力无穷”以及“太棒了”这些表述来赞赏其文笔。在斯托笔下,一个白人孩子可以毫无恐惧地进入黑人的世界,但这种亲切和蔼的语言其实强化了把黑人住所视为他者的取向。

[美]斯托夫人 著 林玉鹏 译
译林出版社 2006年6月
强调归属(belonging)和差异的做法均能造成他者化。一般来讲,英语中用以表达“我们”与“他们”之间界限的各种代词,大多会用到第一与第三人称复数。“我们”表达了归属,而“他们”则造成他者化,否定了归属。用以表达恶心的负面语言,经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是“他们”的人:黑代表着丑陋、不洁。莫里森指出,这种思路等于是给美国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尽可能在各方面与“白人性”接近的人。拥有白人性使归属变得可能,缺乏这些特质则难以得到接纳,显人逊色一等,甚至不算个完整的人。上述特质的有无并非自然的或生物性的。原因其实在别的地方;其间的过程是逐步展开的。
弗兰内利·奥康纳(Flannery O'Conner)《人造黑鬼》(The Artificial Nigger)的故事背景是1950年代的乔治亚州,它表现出奴隶制终结以后他者化与归属的复杂交织。某一天,一个叫黑德的白人和孙子尼尔森一起去亚特兰大游玩。黑德是个穷苦的老男人,一心想把种族等级制的思想灌输给尼尔森。他们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衣着光鲜的黑人男子。尼尔森一开始说自己看到了“一个男人”。接着,在黑德的刻意追问下,他又改口说“一个胖男人……也很老”。这种回答当然是不对的。尼尔森对此有充分意识。黑德继续纠正他说:“那是个黑鬼(nigger)。”在这种情形下,尼尔森就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忘掉这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并转而视之为“黑鬼”的过程,或者说认识到这个男人是他者,而自己以及黑德才真正属于这个社会。
由于种族因素在美国的他者化现象中影响到了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白人作家,“黑人性”对各种肤色的虚构小说作家来讲,都算是一项极大的挑战。莫里森透过《天堂》(Paradise)、《家园》(Home)以及短篇小说《宣叙》(Recitatif)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工作中与肤色偏见作斗争的经历。她表示“对我来讲,为黑人撰写不带肤色偏见的作品困难而富有解放性”。非肤色主义文学不会让种族身份来创造角色。角色可能会有种族身份——这在美国的生活经验中毕竟难以忽视。但种族不应决定一个角色的行为、言说或外貌。
莫里森决心“折断廉价种族主义的利牙,消灭并批判那些日常随处可见的、容易唤起奴隶制记忆的肤色崇拜”。但这并不容易做到。与许多的编辑和读者类似,《宣叙》的演员们也想要根据种族来区分角色——这是美国认同当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一些根植于奴隶制历史以及某些可辨认的刻板印象的简化概括。发明种族甄别乃是为了镇压,它泯灭了一个角色的个体独特性,但那正是莫里森的才华的突出特点。
每当谈到种族的时候,莫里森都在设法与那些对种族的刻板预期作斗争。《天堂》开篇就提到肤色——"他们首先射杀了那个白人女孩。"不过她从来不说那群遭到攻击的女人里具体谁是白人,也几乎没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线索。(莫里森在《他者的起源》里面披露说有不少读者跟她谈过自己的猜想,“但只有一个人猜对。”)接着,《天堂》便转向了黑人肤色主义的纯洁性诉求以及厌女倾向,而这些都是莫里森笔下角色使用过的、致命的他者化手段。在小说故事发生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肤色主义就已经与阶级问题一同出现了;1890年,一个建制派的黑人社群赶走了另一群刚被解放的黑人,理由是他们太穷、太黑。那群自由黑人只好自己建了座名叫Haven的小城(其后继者则为Ruby),从那时起直到1970年代,建制派黑人一直为自己没被玷污的黑人性而自豪。附近的一群女人为了从过去的不幸中解脱,便一起住进了一座老旧的修道院。Ruby城的男人对女人们的强烈仇恨源自于她们的种族异质性——完全没有种族纯洁性可言。但这不是仇恨滋生的惟一原因:在《天堂》当中,厌女倾向强化了这种仇恨并且导致了谋杀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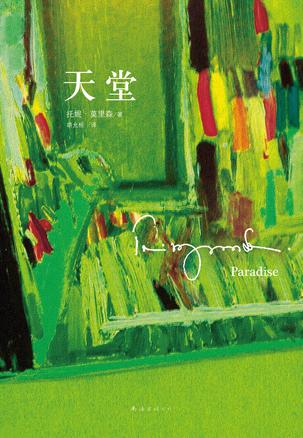
[美]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0年12月
回想起《家园》这本书,莫里森承认自己有些不安。按她的说法,自己在这本书里犯了个错误:根据编辑要求对其中的主角弗兰克·蒙尼做了肤色编码(color-coding,简单来说就是以肤色给人论资排辈——译者注)的处理。另一个稍小的疏漏则体现在:莫里森用了两页的篇幅来描述主角将要离开的那家医院,但其后提到此人的种族身份时,口吻却不太光明正大。读者需要透过主角曾受过非洲卫理公会锡安教堂(AME Zion church)的救助这件事情来作出推测。在稍后一点的篇章中,读者还要注意理解“没法在公共汽车站落座”这句话的细微含义。假如莫里森在个体刻画与种族归类之间不幸倒向了后者——那会让人设变得很苍白,而且会助长种族主义思维——这样的疏漏也许就大事化小了。所幸莫里森终其一身都在跟这些不好的习惯作斗争,无论在从事写作还是担任编辑时都是如此。
在莫里森供职于兰登书屋的19年中,莫里森设法让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及个人认同的人们都有一个被世人知晓的机会。譬如,她策划出版了作家托妮·卡德·芭芭拉(Toni Cade Bambara)、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安琪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以及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传记。1974年,她出版了非虚构选集《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其内容汇编自米德尔顿·哈里斯(Middleton A. Harris)的论集,该书主要探讨黑人的历史,哈里斯本人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编选工作。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各种反映黑人生活的照片:军装笔挺的士兵,盛装打扮去做礼拜的家庭,打字机和洗衣机的发明专利,还有早期的黑人影星,最后还涉及到面带笑容地对黑人动私刑的白人。总之,《黑人之书》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这群非洲人后裔的窗户,使他们了解到黑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而这是打破种族隔离牢笼的重要一步。
莫里森另一部主要作品的灵感,则来自于她编选《黑人之书》时找到的一篇1856年的文章。这篇题为“访一名杀掉自己孩子的奴隶母亲”的文章记录了一次访谈,主角是逃亡中的女奴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 Garner),她全家在俄亥俄州被捕,随后她杀掉了自己最小的孩子。加纳的岳母并不怪罪她的杀婴之举,因为此举反倒让一个小孩子彻底避免了被奴役的命运。这样的支持态度激励了莫里森,而岳母也就此成为她笔下贝比·萨格斯(Baby Suggs)这个角色的原型,即1987年的《宠儿》(Beloved)中的那个倡导黑人要自爱的民间牧师。《宠儿》后来荣获普利策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欧普拉·温弗利接着又把它改编成了电影。莫里森的语言极具力量,《宠儿》入木三分地呈现了奴化行为在情感方面的恶劣影响,其历史叙述动人心弦,生动地将奴隶制刻画为一出悲剧,引起了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这部小说(以及电影)让每一个爱着自己家庭的人都感受到了奴役带来的痛苦,以及“孩子不属于自己”的无奈。

[美]托妮·莫里森 著 潘岳/雷格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6月
令《他者的起源》在当下这个21世纪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个时刻跟历史上那些可怕的日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乃是其中的两段引文,在这里莫里森几乎是全文引用。第一段引文列出了一些二十世纪早期针对黑人施行私刑的证据。另一段则来自前文提到的贝比·萨格斯在对其人民布道时的演说辞。
私刑证据有两页多。以下引文仅能展示其中一小部分:
艾德·强森,1906年(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核桃街大桥附近,被判死缓之后,有暴徒劫狱并动用私刑将其杀害)
劳拉和尼尔森,1911年(母子,被控杀人,也是被暴徒劫狱带出然后杀害,地点在俄克拉荷马州奥克马的一座铁路桥附近)
埃利亚斯·克莱顿,埃尔默·杰克逊,艾萨克·麦基,1920年(三人都是马戏团成员,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控强奸,在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被私刑处决;杀人者未受惩罚)
雷蒙德·古恩,1931年(被控强奸和杀人,在密苏里州的玛丽威尔被暴徒浇上汽油烧死)
接下来则是《宠儿》中那位以女奴岳母为原型的贝比·萨格斯的布道辞,《他者的起源》对此有所引用:
“我们的身体生于斯长于斯,它在这里哭泣和欢笑,它赤着脚在草地上起舞。我们爱着自己的身体,并且是深爱着。那些外人则不爱它。他们怨恨它。他们不爱你们的眼睛;恨不得把它挖掉。他们也不爱你们背上的皮肤。他们抽打它。啊,我的人民,他们也不爱你们的双手。他们只是利用、捆绑、锁定、砍掉或是让它空着。爱上你们的双手吧!爱上它们吧。”
在这个基础上,我打算再贴一个目前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很火的名单,里面是警察射杀黑人最后被判无罪的例子。这里的名单只计算到八九月份,但众所周知的一个悲剧性事实是,它肯定会逐渐变长的(名单里是被射杀的黑人):
费兰多·卡斯蒂尔-无罪
特伦斯·克鲁彻-无罪
桑德拉·布兰德-无罪
埃里克·加纳-无罪
麦克·布朗-无罪
瑞基亚·博伊德-无罪
肖恩·贝尔-无罪
塔米尔·赖斯-无罪
弗雷迪·格雷-无罪
丹鲁伊·亨利-无罪
奥斯卡·格兰特三世-无罪
肯德瑞·麦克达德-无罪
艾亚那·琼斯-无罪
拉马莱·格瑞汉-无罪
阿玛多·迪亚洛-无罪
特雷文·马丁-无罪
约翰·克劳福德三世-无罪
乔纳森·费雷尔-无罪
小提莫太·斯坦伯里-无罪
这些名单以及贝比·萨格斯的布道辞揭示出了黑人长期遭到暴力伤害的现象,以及一个深远的仇恨及杀害黑人的传统。以上各项主题又牵出了《他者的起源》当中谈到过的另两位作家。
塔-内西斯·科特斯是《在世界和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的作者,这本书虽然是个人自述,但却是以给儿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的,它现在卖得很好,并担当了《他者的起源》的前言。莫里森为科特斯的书撰写了推介:“在詹姆斯·鲍德温过世后,我曾经苦苦思考谁能填补这个知识上的空白。显然塔-内西斯·科特斯是不二之选。”科特斯则表示,莫里森的支持是他梦寐以求的。按文化批评家迈克尔·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的说法,莫里森认为科特斯身上有某种鲍德温的影子,而读者也能从她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一些类似的迹象:“雄辩、条分缕析且眼光毒辣,一下子就揭穿了白人所谓的道德无辜性。鲍德温1963年的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为科特斯的《在世界和我之间》提供了灵感,这表现在形式(form)与基调(tone)两个方面。
鲍德温生于1924年,是莫里森和科特斯在智识上的先驱,因关注对黑人的暴力以及对欧洲移民透过建立白人认同而融入美国这一过程的深入观察而闻名。在《下一次将是烈火》开头,鲍德温给自己的15岁侄子詹姆斯写了封信,批评他的美国同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摧毁了并且仍在摧毁千百万黑人的生活,且根本没了解也不打算了解他们。2015年,科特斯以相近的方式,也给他快要满15岁的儿子写了封信,称“在美国,攻击黑人符合传统——这已经是一项遗产了。”到了2017年,莫里森又对此有所补充,笔者在上文曾引用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视奴隶为另类,这表明了一种竭力想要证明自己正常的心态。”上述这些提法又都与鲍德温1984年的短文《论作为白人……及其它谎言》(On Being White…and Other Lies)有所呼应,这篇文章最早发在黑人女性杂志《本质》(Essence)上。透过将研究黑人话语的焦点从黑人转到白人身上,鲍德温为20世纪末的“白人性”研究做出了一项开创性的贡献。

上述几位作者都非常出色,这难免会让观者把他们视为整个美国黑人社群的代表。但科特斯表示他只是为自己而言说。当然,他的大批读者肯定会把他当成代言人。莫里森就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也认同诺奖不单单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全体黑人女作家这样的观点。在1960年代,鲍德温无疑也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激情常常能够感染听众——他1965年在剑桥大学跟保守派人士威廉·布克莱(William F. Buckley)展开的辩论就尤其如此。1968年,鲍德温参加了电视节目《迪克·卡维特秀》,尽管他表现得很积极,但主持人和其它嘉宾却不怎么买账,甚至表现出某种疲态。视频记录里的场面十分难看,但的确有助于读者认识美国白人在历史上是如何刻意对黑人保持无知的。
所幸美国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无论是像科特斯这样只为自己代言,还是莫里森那般为民众说话,这两名黑人作家都已经打出一片天地,并获得了他们应有的荣誉。鲍德温与1987年去世,他的命运没那么好,但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切中时弊的特点,总归还是得到了一些非正式的承认。在鲍德温与科特斯之间,莫里森扮演了一个促使黑人作家从遭到冷遇到闻名于世的关键角色。这当然不是由于偶然或者对其才能的自发认同。黑人追求其历史主体性的努力及其前仆后继的抗争,才是使他们不至于重演鲍德温命运的关键因素。莫里森之所以能够获得恰如其分的社会评价,也应归功于积极的社会抗争。
鲍德温去世后不久,48名杰出的黑人诗人、小说家以及学者一齐为他的命运打抱不平,想要为他正名。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联名信,抗议对鲍德温的忽视,主张历史不应重演。他们集中关注建制派文学对黑人作家的习惯性忽视,并且指出还有另一位出色的黑人作家仍然没得到应有的荣誉,亟需大家予以支持:莫里森的《宠儿》当时没能得到国家图书奖。联名信登出以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宠儿》得到了普利策奖,而莫里森的作品之后也不再遭到忽视了。就此而言,此次事件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随着莫里森的作品及其背后的整个传统逐渐获得承认,美国开始开放自己,这增强了黑皮肤的美国人以及黑人作家的归属感。
从鲍德温到莫里森再到科特斯,读者可以发现:许多历史性的进展都是以“文学接受”(literary reception,是一种侧重从读者怎样理解作品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来研究文学的思路——译者注)的方式来达到的。不过,与此同时,其它一些使莫里森的小说显得突出的因素被淹没了:女人和性别。就《他者的起源》而言,这种淹没不算很彻底,莫里森在里面还是提到了她的两本关于女人的书,特别是《天堂》和《恩惠》(A Mercy),但这里其实也不妨把她另一部关注女人的重要作品《秀拉》(Sula)也加进去。此外,在《宠儿》里面,她也突出了女人之间的母性关系,即那种将塞丝(Sethe,也就是那个被杀死的女婴——译者注)和贝比·萨格斯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然而,考虑到这些操作让种族他者化的主题——前述另两位男作家也处理过——变得不那么突出了,这几部作品在锋芒上就的确稍显不足。
在《天堂》里,莫里森探讨了修道院里的那群女人之间互相拉人做替罪羊(scapegoating)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开篇谈到的射杀行为却是由一名男性做出的,这种野蛮的仇女行为难以完全用种族因素来解释,开篇这段颇能激起读者共鸣的描写——“他们首先射杀了白人女孩”——也不足以解释它。《恩惠》的开头和结尾都谈到了一个母亲在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中被夺去女儿的经历,它拆散了千百万人的家庭,使得父母子女只好天各一方。这位母亲的举动可以部分地用大西洋两岸的奴隶贸易历史来加以解释,她在抵达巴巴多斯(Barbados)时遭到了非洲裔船员的性侵。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历史解释忽视了小孩子自身的情感性意义,以及女性在莫里森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在这本书中,小孩成了主角。惟有在结尾的时候,她才充分理解了导致自己被遗弃的那个复杂背景,走出了贯穿于全书叙事的那种苦涩状态。

无论在某一种族内部还是在不同种族之间,莫里森对女人、母性、厌女倾向、仇恨以及自我仇恨的刻画都是入木三分的,体现了她作为作家以及思想家的天赋异禀。莫里森作品里的主角几乎都是女人,其各方面认同以及叙事轨迹(narrative trajectories)几乎占据了她的小说所构造出来的一整个虚拟世界。这一点在《天堂》当中尤其醒目,一群贫苦女人自发组成共同体,生活在修道院里并相互进行自我疗愈,完全不受男人监管。修道院里的女人们是种族之间相互他者化的受害者,但作为女人而言,她们又建构出了自己的一套归属,而这导致了她们的破灭。自由的女人们激怒了Ruby城的男人,其“纯粹的仇恨”使他们的“恶意”显得分外醒目。在杀害女人的过程中,这群男人“动用了绳索、钉耙、手铐、锤子,戴着太阳镜,手里的枪也擦得锃亮”。
《他者的起源》将莫里森特有的雄辩与其作为世界公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敏锐感知熔冶于一炉。不过,她的人道主义想象力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地方,还是要数她的那些大作。女人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社会以及种族身份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并不决定个体角色的命运;她的小说帮助读者理解了种族及性别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经验,并且没有以泯灭个体心灵独特性为代价。若要把握莫里森的思想,就既要了解她的各种讲座,也要了解那个由詹姆斯·鲍德温以及塔-内西斯·科特斯构成的、围绕种族而展开的文学传统,然而她在《他者的起源》中表现出来的关于人类他者化以及归属的一系列精辟而独到的洞见,已远远超出了上述两者的范围。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