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靖 | 东方历史评论
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1804-1894)是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著名儿童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30年代前后,皮博迪小姐一度与美国“公立学校之父”霍勒斯·曼及作家霍桑过从甚密,同时与爱默生、梭罗、奥尔科特、玛格丽特·富勒等人交往频繁。位于波士顿西街的“皮博迪书店”被称为“超验主义的两大中心”之一——另外一个是位于康科德的爱默生老宅。
爱默生的传记作者小罗伯特·理查森在研究了传主大量书信日记后,得出一个结论:爱默生喜欢在笔记中保留自己过去的情感记录,而且是用拉丁文;对于提到的年轻女子,也从不留下真实姓名(以特殊字母代替)。据说这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保持两性关系秘密的方法,作为“康科德圣人”的爱默生也未能免俗。在《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一书中,理查森用短短的三行字描述了爱默生与伊丽莎白·皮博迪小姐的联系:1821年一段时间里爱默生曾辅导过皮博迪小姐的希腊文,那年她18岁,而爱默生19岁,但两个人是如此羞怯,“他们从来不从他们的课本上抬起头,移动目光”。
皮博迪小姐出生于塞勒姆,自幼聪颖,又勤奋好学,尤其得到哈佛校长柯克兰(John Thornton Kirkland)的赏识,后者将她推荐给唯一神教牧师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780-1842)博士,担任秘书和助手。由于博士年迈体弱,若干布道文皆由皮博迪小姐誊抄润饰,一时名声大噪。多年以后,当皮博迪小姐回首年轻时代与爱默生交往的这一段经历时,她显然有更多的感触。那时她的父亲皮博迪医生率领全家由塞勒姆小镇搬迁至波士顿,就在哈佛学院附近。但勤奋好学的皮博迪小姐却无缘进入哈佛学习,因为学院尚未开始招收女生。于是她一边在女子学校教授学生,一边自学古典语言课程。通过爱默生堂弟乔治·爱默生的介绍,皮博迪小姐结识了刚由哈佛学院毕业的爱默生。
爱默生的教学方法很简单,师生隔着一张书桌相对而坐,学生背诵希腊文诗歌,年轻的教师则以“最具启发性的方式”进行评论和阐释——或许是出于羞怯,或许是某种默契,在此期间二人始终没有正式的交谈。直到这一年年末的时候,科克兰校长推荐她赴缅因州任教——他在给友人的推荐信中说,很少有哈佛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在数学、拉丁文、英语语法和历史方面取得像她那样的好成绩。动身之前,皮博迪小姐要求爱默生寄送授课的费用账单。但等到会面时爱默生却明确告诉她没什么账单,因为他没有教给她什么东西。也许是因为最后一次见面,也许是有乔治在场的缘故,皮博迪小姐发现这一次爱默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甚至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这是二人之间第一次,却远非最后一次。虽然下一次的会面,要等到近十年以后。

这一段经历后来在皮博迪小姐的回忆中被浓缩成两个字:怀念。怀念爱默生和他的希腊文教程。相比而言,前此一年的另一段经历在她印象中要深刻得多。那一年她十七岁,也是由朋友介绍结识了刚从哈佛学院毕业的代课教师雷曼·巴克敏斯特,后者二十五岁,即将被任命为教区牧师。人们普遍认为雷曼前程似锦,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是有名的约瑟夫·巴克敏斯特牧师(亨利·米勒称之为“超验主义的先驱”,他后来的教职由钱宁博士接替)。雷曼殷勤造访皮博迪小姐一家,态度谦和,谈吐文雅,受到全家人的喜爱,被称为“我们的朋友雷曼”。他先给皮博迪小姐赠送《维吉尔诗集》,然后突然在某一天提出求婚。
雷曼的求婚令皮博迪小姐猝不及防,几乎未加思索便断然拒绝。不妨假设,如果意识到这是她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求婚,或许她会稍稍思量一番。但无论如何,正如皮博迪小姐的传记作者马歇尔(Megan Marshall)评价的,作为她女性身份的证明,她一直珍藏着这段记忆,并且其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珍贵。
除了博学多才和斐然文采,皮博迪小姐另外一项过人之处是她的社交才能。从早年开办女子学校起,她与波士顿富商名流多有来往。与爱默生久别重逢后,她又成为康科德“超验俱乐部”最为引人瞩目的访客。此时爱默生已和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结婚,莉迪安参加过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在皮博迪小姐书店举办的“谈话”讲座,彼此都很熟悉。皮博迪小姐将好友富勒介绍给爱默生——但很快二人的友谊迅速升温,以致引起了莉迪安的疑虑。在应邀造访康科德的女宾当中,莉迪安更喜欢皮博迪小姐:在她分娩期间,皮博迪小姐悉心帮助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平易而周到,宛似家人,不像富勒沉醉于和爱默生散步聊天,整日高谈阔论。
莉迪安假如知道爱默生在他的两次婚姻之间,曾和皮博迪小姐有过一次相亲的经历,可能她会更有安全感。相亲的指令是由爱默生家的“祖奶奶”——爱默生的姑妈玛丽·默迪·爱默生发出的。爱默生当时可能已赴欧考察,未能执行指令;他的兄弟查尔斯在收到指令后迅速回复,声称与皮小姐早已熟识,其人也不乏“优雅的品味”,但“我所要求妇女的是要有吸引力”。而玛丽姑母所希冀的,毋宁是“一种智力的,而非罗曼蒂克的匹配”。数月之后,查尔斯迅速与当地霍尔法官的女儿伊丽莎白·霍尔订婚,不知是否由于这次“促婚”引起的反作用。
1830年代,皮博迪小姐与爱默生共同关注并参与的超验主义运动正处于它的全盛时期。二人所要探讨的,除了当时新旧两派争论的宗教神学问题,还有超验主义喉舌《日晷》的编辑出版问题,后来还有牧师里普利“布鲁克农庄”等问题,但无论如何,二人之间却没有超过同志加兄弟的工作关系。作为主编的爱默生要求期刊出版印刷要尽善尽美,却很少考虑皮博迪小姐作为出版商所承担的费用和风险。皮博迪小姐似乎也没有提出异议,仿佛非常乐于承担这样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日后在她与奥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霍勒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以及霍桑等人的交往过程中,人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皮博迪小姐对爱默生虽然不无崇敬之意,但她真正的精神导师则为当时唯一神教领袖钱宁博士。第一次聆听钱宁博士布道时皮博迪小姐才七岁,博士已近而立之年。十一岁时皮博迪小姐抓住一次机会,不仅聆听布道,而且当面向她心目中的偶像提出问题。在博士的勉励下,皮博迪小姐十三岁开始研读《圣经》。到十多年后在波士顿再次与博士见面时,她的渊博学识和关于神学的见解令他大为惊叹。奥尔柯特和皮博迪小姐合作的“神庙”(Temple)学校开办时,博士将两个女儿送入学校,以示支持和鼓励。他邀请皮博迪小姐闲暇时一同散步,与之讨论宗教、历史、教育及社会改造等问题,其中许多见解都被收入他的布道文和演讲,并由皮博迪小姐抄写整理成文。钱宁博士病逝以后,她不辞劳苦潜心编纂并出版《钱宁文集》,赢得文学圈一片赞誉。

一位年近五旬的长者,与一位未婚女子的频繁交往,在1830年代的新英格兰,难免要招致物议。但皮博迪小姐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在她看来能够与她仰慕的导师进行平等的对话,是她一生的荣幸和荣耀,绝无理由轻易放弃。而博士不仅能从和她的谈话中汲取知识丰富他个人的著述,同时也能从中获取巨大的精神享受。当时波士顿上流社会一般的看法是,博士的妻子露丝操持家务、照料博士起居及日常生活;皮博迪小姐则负责他的智性与精神生活。作为博士终身不取报酬的“女秘书”,皮博迪小姐认为这一称谓是对她自我奉献的最高奖赏。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说自己几乎养成了“每晚与博士呆在一起的习惯”;形容二人的关系则用“极其亲密”——与之相反,博士对他们关系的评价则是“伙伴”:追求知识过程中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种亲近关系一直维系到博士的晚年。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仍坚持每天清晨光顾皮博迪小姐开办的外文书店,浏览国外新闻并与之交谈。
作为新英格兰教育改革运动的倡导和实践者,皮博迪小姐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观点不仅影响了钱宁和爱默生,也令另一位著名教育家、美国“公共教育运动”倡导者霍勒斯·曼惊叹不已。1830年代初,作为房客,皮博迪小姐及其姐妹和曼一同寄居在克拉克夫人家中。曼出生于贫困家庭,凭借个人奋斗自学进入布朗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律师。但他不久前刚遭受巨大的打击,他的妻子夏洛特因难产而死,腹中胎儿也未能保全。曼忧伤过度,数日之间须发皆白,看起来像鬼怪幽灵。但皮博迪小姐的长处在于穿透外表,发现天才。她对曼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曼对亡妻的深情追忆更令她敬佩不已。她和曼倾心交谈,鼓励他从人生打击中振作起来,参选国会议员,不久曼被任命为麻省教育秘书(厅长),她又以更大的热忱与之探讨教育改革问题。曼的事业红红火火,但他内心的寂寞哀伤却始终难以排遣。到了夜晚,一有机会,他就会找皮博迪小姐倾诉,甚至依偎在她胸前,泪流满面。而皮博迪小姐,也总能给予他滚烫的胸膛和坚实的臂膀,在他最需要慰藉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段他们的关系如此密切,房东太太坚信他们很快要订婚(曼不久果然订婚,对象却是皮博迪小姐的妹妹玛丽)。
这一时期,恰好她的妹妹玛丽与索菲娅一道远赴古巴,几乎每个夜晚,曼都会到皮博迪小姐房间,听她朗读玛丽的来信,并请皮博迪小姐在信中转达他本人的问候。很快,曼与玛丽开始了直接通信,而皮博迪小姐却浑然不觉。就在姐妹俩回国前,在给玛丽的信中,她还提到最近收到曼的一封信,因为没有能参加周六晚的讨论会而深感抱歉,落款是“你挚爱的,H.M.”。而她本人,是如此喜悦和激动,“她亲吻了那些甜蜜的字词”。相比于女学究式的皮博迪小姐,三姐妹中容貌最为出众且富于文采的玛丽可能更让这位中年丧偶的鳏夫动心。曼本来是个务实派,上大学时就写过《反对小说》,认为流行小说充满恶毒诅咒,会败坏道德人心;后来又声称宁愿去创建一座盲人福利院而不愿创作一部《哈姆雷特》。但现在受了文艺女青年玛丽的影响,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随着玛丽回国并取代皮博迪小姐担任“神庙”学校教师,曼的攻势也改变了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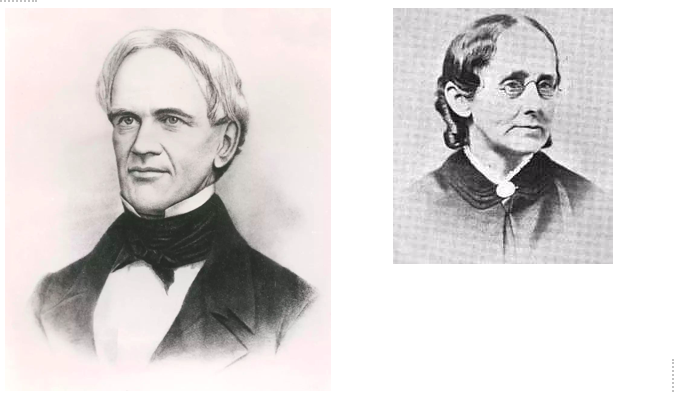
皮博迪小姐黯然离去,怀着对曼兄长一般的爱;对于曼而言,他的移情别恋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皮博迪小姐有了新的情感寄托的对象:奥尔柯特先生。和皮博迪小姐一样,奥尔柯特也是自学成才。他在课堂教学中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开启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皮博迪小姐最早读到的便是奥尔柯特与学生的课堂讨论和学生日记,这也正是她本人早几年在塞勒姆女子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法,而奥尔柯特做得更为出色。在皮博迪小姐眼中,年届三十的奥尔柯特先生是富于激情的教育改革家,性格刚毅,坚韧不拔,而且富于理想主义色彩,“他将注定成为一个社会时代的开创者”,她在写给玛丽的信中说,“我坚信他一定会”。为了帮助奥尔柯特开办“神庙”学校,她首先向钱宁博士求援,同时又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劝说当地富商豪门和上流知识阶层,让他们将子女送到奥尔柯特学校。由于她的出色工作,到1834年9月有十八名学生报名入学,到学校正式开学已有三十名学生——皮博迪小姐似乎从未意识到有这么多学生,她和玛丽完全可以开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当奥尔柯特夫妇提到他们没有资质教授拉丁、算术、地理等科目时,皮博迪小姐自告奋勇地提供服务,每天两个半小时教授上述几门科目,而报酬则由奥尔柯特视其经济状况而定。后来她又两次拒绝了奥尔柯特的报酬。夫妇二人喜出望外。事实上,正如奥尔柯特先生日后坦承的那样,皮博迪小姐不仅担任了繁重的授课任务,而且还肩负着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她还兼任奥尔柯特的书记员。双方这一阶段合作的成果之一,就是日后给奥尔柯特先生带来巨大声誉的《校志》(The Record of a School)。在书中皮博迪小姐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眼光,忠实记录了奥尔柯先生与学生课堂讨论的精彩场面,其讨论话题则涉及宗教、神学、道德、哲学等诸多方面。作为超验主义教育家,皮博迪小姐和奥尔柯特都坚信,儿童比成年人更接近知识的来源即真理,或上帝之道。教育的功能就是要唤起他们的潜能,那种将成人模式强加于儿童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必须摒弃。
这一阶段是二人合作的蜜月期。皮博迪小姐不仅聆听奥尔柯特的课堂问答并做记录,课后也有长时间关于教学问题的相互探讨和交流。奥尔柯特夫人忙于家务和照料三个幼小的女儿;皮博迪小姐与奥尔柯特则在“漫长的夜晚”进行令人愉快的和谐交谈:从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的教育理论到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皮博迪小姐在写给曼(她一直与之保持通讯)的信中称自己每天都在经历巨大的改变,“我和一年以前的我已截然不同,我和六周以前的我已截然不同”。甚至在她自己的课上,也有意无意地摹仿奥尔柯特的教学风格。作为感激和回报,奥尔柯特夫妇决定为新近出生的小女儿取名伊丽莎白·皮博迪·奥尔柯特。而仅仅一年以后,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夫妇二人将女儿的名字变为伊丽莎白·西瓦尔·奥尔柯特。
事实上,皮博迪小姐和奥尔柯特在教学理念方面本来就并非完全一致。阿尔柯特喜欢采用诱骗的手法“唆使”学生犯错,然后以逐出教室或面壁思过的方法予以惩戒。对此皮博迪小姐不以为然,认为违背了教育的仁爱原则。更大的分歧发生在奥尔柯特编著的《与学生论福音书》(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书中。在书中奥尔柯特与十来岁的孩子讨论生育避孕等当时社会禁忌的话题。作为书稿的编校者,皮博迪小姐坚持删除相关的讨论和注释,奥尔柯特则断然拒绝。果不其然,书籍出版后,立刻遭到了教会保守派人士和唯一神教派的一致反对。哈佛名教授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甚至宣称该书“三分之一是荒诞,三分之一是亵渎,三分之一是淫荡”。迫于社会压力,上流人士纷纷开始撤离自己的子女,“神庙”学校形势岌岌可危。
而与此同时,皮博迪小姐与奥尔柯特夫人的私人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奥尔柯特夫人是家庭妇女,言语粗俗,缺乏知识女性的优雅风度和修养。她曾粗鲁地打断皮博迪小姐与友人的谈话,令她尴尬难堪。由于怀疑皮博迪小姐在背后发表对奥尔柯特先生不利的言行,她又私自闯入皮博迪小姐的住处,搜查并私拆她的个人信件。个人隐私遭到侵犯,而奥尔柯特先生又一味袒护妻子,对皮博迪小姐横加指责,伤心绝望之下,皮博迪小姐决定离开奥尔柯特和“神庙”学校(她的工作后来由玛格丽特·富勒接替,因为奥尔柯特无力支付报酬,四个月后,富勒也离开学校)。皮博迪小姐离开后,学校又坚持了近一年时间,只剩下少数几个学生,地点也搬到了“神庙”的地下室。奥尔柯特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他珍藏的图书偿付租金。而他本人,此后再也没有开办过任何学校。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神庙”学校倒闭之后,奥尔柯特遭受四面围剿的时候,皮博迪小姐仍然勇敢为之辩护,捍卫“奥尔柯特先生的书籍和学校”,捍卫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

回到故乡塞勒姆,皮博迪小姐读到新近出版的一本小说《故事重述》,经过打听才知道作者是本镇的居民、一位叫做霍桑的年轻人。以奇文共赏的名义,皮博迪小姐约见了这位尚未崭露头角的作家。初次会面,作家清秀俊朗的外表和他的忧郁沉静的气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简直比拜伦勋爵还要漂亮!”她告诉妹妹索菲娅。当然更为吸引她的是作家的才情。“作为职业作家中最伟大的艺术家”,皮博迪小姐断言,“他将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因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展示出天才的丰富多样性。发现天才并且帮助他们将天赋的才华展现在世人面前,皮博迪小姐一直视为己任。这一次也不例外。
出于惜才和爱美之心,皮博迪小姐决意向世人大力推介这位天才。首先,她在《波士顿季评》(Boston Quarterly Review)等报刊上撰文,鼓吹霍桑的文学才能。其次,向爱默生等友人强烈推荐,并由爱默生等人出面向霍桑约稿。此外,考虑到当时文学市场上儿童文学读物大受欢迎,她建议霍桑转向童书写作。在姻亲霍拉斯·曼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秘书期间,皮博迪小姐又不止一次与之商谈,试图让霍桑的作品进入公共教育系统的课外读物清单。然后令她不解的是,无论是爱默生还是曼,对霍桑的小说故事都不感冒——爱默生甚至断言“其中并无内涵”(no insider)。对于皮博迪小姐称之为“天才的化身”“真正的诗人”,哲学家的反应似乎过于冷淡与苛刻,但这丝毫也没有动摇皮博迪小姐的坚定信念。当然,霍桑对哲学家的冷遇也予以回击——据说《拉帕奇尼的女儿》中古板而顽固的医生形象即以爱默生为原型。在另一部短篇《胎记》中,女主人公服毒身亡,则被指影射爱默生夫人莉迪安从植物中萃取毒物(疑其慢性自杀)。
为缓解霍桑的经济压力,让天才作家得以专心写作而无后顾之忧,与戴金克(Evert Duyckinck)、布里奇(Horatio Bridge)等友人一道,皮博迪小姐运用人脉,多方奔走,终于在1839年为霍桑谋得波士顿海关司磅(Measurer)一职,年薪1500美元。霍桑一开始踌躇满志,但很快发现繁杂的事务严重扰乱了他的写作计划。他于次年辞去海关职务,并于次年利用手头积蓄(1000美元)购买股份,加入里普利牧师(George Ripley)创办的“布鲁克农庄”。在写给未婚妻索菲亚·皮博迪的信中,他描绘了生产劳动和文学创作相融合的美妙憧憬。但好景不长,经过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晚上根本无暇从事文学想象和写作。半年多以后,霍桑不辞而别。他人生中第一次商业投机也由此告终。
目睹霍桑生活窘迫,且在文学市场经营惨淡,皮博迪小姐试图通过自费印刷霍桑的短篇故事和童书——如《生平故事》和《祖父的椅子》系列帮助作家摆脱困境,但收效甚微。在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杂志倒闭后,雄心勃勃的皮博迪小姐又独力主编发行《美学论丛》(Aesthetic Papers),并力邀霍桑投稿。除了霍桑,应邀为《美学论丛》撰稿的还有爱默生、梭罗以及奥尔科特等人。尽管皮博迪小姐在稿件质量方面精益求精,严格把关,但《美学论丛》——正如其他同人刊物一样——并未获得市场认同,仅出版一期便无疾而终。《美学论丛》得以留名青史,一方面由于霍桑身后的文名,一方面也由于本期刊载了梭罗名篇《论公民不服从》——原文是1847年梭罗应霍桑(时任塞勒姆“学园”秘书)之邀发表的演讲。
作为作家霍桑的姻亲和首位出版商,皮博迪小姐为霍桑的才华所折服,不仅为他提供发表园地,而且对他的个人生活照顾有加,此后更为他谋取差事而四处奔波,对此霍桑自然心知肚明——二人的友谊也维系终身。1863年,霍桑散文集《我们的老家》题词敬献前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遭到亲友一致反对,最终商议由皮博迪小姐出面加以劝阻。尽管未能成功,但也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霍桑被波士顿海关解职后,为了让作家潜心创作,皮博迪小姐又通过历史学家、民主党政治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人的关系,帮助霍桑谋得塞勒姆海关税务督察(年薪1100美元)的差事。她和年轻作家深入探讨人性和文学问题,一同携手散步或出席当地上流阶层举办的文艺沙龙和各种研讨会。她的小妹索菲娅有时候也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更多时候,她宁愿呆在楼上的画室,从事她的艺术创作。索菲娅自幼体弱多病,她自己也从一开始打定主意独身,而漂亮的霍桑的到来则彻底动摇了她的决心。

霍桑与皮博迪小姐姐妹三人之间的关系一度是如此紧密,以至外面有传言称作家与本城的两位姑娘同时缔订了婚约。霍桑哭笑不得,但显然传言迫使他必须尽早做出抉择。而皮博迪小姐似乎也预感到了危机,她向作家出示了索菲娅和玛丽在古巴一年间的书信和日记,用以说明她的体质是如何柔弱,根本不适合婚姻家庭生活。但结果是,她的举动倒更激发了霍桑的男性气概,既然索菲娅如此娇弱敏感,呵护她、保护她更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陷入情网中的作家一改羞涩拘谨的作派,大胆表露心迹,送花赠诗,甚至将索菲娅的形象写到自己的小说中。很显然,皮博迪小姐是平等对话的伴侣,索菲娅却是唤起灵感的缪斯。取舍并不困难。1838年,就在皮博迪小姐赶赴纽顿(Newton)帮助兄弟纳特创办一所男子学校期间,霍桑虽然也像誓约地那样偶尔给她写信,但更多的时间则用在了追求她妹妹身上。他们的感情迅速升华,终于很快就秘密订婚。对此皮博迪小姐只能接受,毕竟,她还不想完全失去和霍桑的联系,正如她不愿失去和曼的联系一样。
与崇尚“清议”、不切实际的超验主义朋友不同,皮博迪小姐也不乏商业头脑。女校关闭后,她利用多年积蓄在波士顿市中心投资买房,即日后鼎鼎大名的“西街13号”。皮博迪小姐将前厅改造为书店(兼具流通图书馆功能),同时也附带经营海外书报代购业务。1840年代,她与玛格丽特·富勒曾先后于此开办普及妇女教育的“谈话”讲座,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女性。为了进一步普及知识,皮博迪小姐又自费购置印刷机,在后院开设小型印刷所(1842年起,超验主义的同人刊物《日晷》便由她印刷发行)。超验主义运动式微后,皮博迪小姐成为妇女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爱默生的弟弟查尔斯曾用“缺乏吸引力”描述对于皮博迪小姐的印象,爱默生没有这样明确表露他的看法,他用的词是“女王般的”,似乎对皮博迪小姐雄心勃勃的进取心稍有微词。根据她友人的形容,1830年代时,皮博迪小姐的身材已较为肥胖,而她本人对于发型服饰之类也很少在意,几乎称得上不修边幅。她唯一关心并孜孜以求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求知和帮助他人求知。对于她所结识的同时代的天才人物,她不仅崇拜仰慕更竭尽所能帮助他们展示其才能。虽历经挫折打击,而无怨无悔。除了耶稣基督自我牺牲以成全他人的宗教道德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富勒不同,她清醒的意识到自己身为十九世纪女性的局限性:她帮助奥尔柯特先生兴办“神庙”学校,鼓励曼从事教育改革,帮助霍桑确立文学声望,自费印刷出版《日晷》——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推波助澜,至于她本人则不计名利,甘做无名英雄,因为这也是她自己的梦想。而她自己作为女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却无法凭借个人奋斗去实现这样的梦想。
1850年代以后,随着“显然天命”(manifest destiny)学说日益流行,领土扩张取代社会改进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加上1860年代废奴运动日益高涨并最终导致美国内战,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已日渐衰微。在此之后(尤其是在早年感情生活受挫之后),皮博迪小姐将全部身心投身于美国幼儿教育事业(她终身未嫁)——她发起并创立波士顿首座公立幼儿园,并很快推广至于全美。鉴于她在教育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晚年她被尊称为“波士顿的祖母”——遍布各地的“伊丽莎白·皮博迪之家”成为人们对她最好的纪念。

爱默生曾说,在他所处的时代,“拥有创造性天才对女性生活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幸或不幸,皮博迪小姐正是这样的天才。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