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我从美国跨越边界来到加拿大——这个往常很简单的举动,如今却让人感觉些许不安。在比利·毕晓普·多伦多机场的第三个安检站,快要结束漫长安检的时候,我可以透过大窗户看到安大略湖在闪闪发光。这时候,一个严厉的边界警卫开始盘问我一些问题——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工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来采访的记者。采访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听了这话,这个黑发警卫用一种近乎失望的眼神盯着我。“哦,是她啊,”她说,挥手让我过去,“总是有人来找阿特伍德。”
只是想想的话,这件事似乎很有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一群傲慢的记者冲进多伦多,要见的不是明星德雷克(Drake),也不是歌手“威肯” 阿贝尔·特斯法耶(Abel “The Weeknd” Tesfaye),甚至不是曾经的多伦多猛龙篮球队或加拿大的枫叶,而是79岁高龄的加拿大文学艺术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后来告诉我,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不是真的,当时我们住在酒店的一间套房里,阿特伍德刚刚从酒店的小冰箱里翻出了盐焗腰果,并询问我关于英国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被控告不法行为的事情。理所当然,人不能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写作,这太分散注意力了。阿特伍德几乎总是在写作,但这并不是说她会介意接受采访——相较于刚开始的时候,现在的她已经享受了许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记者“既不能完全地理解女性的写作,也不能完全地理解加拿大人的写作”,而且似乎对两者都抱有相当大的敌意。不过现在不同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阿特伍德高贵地仰起脖子,拨弄着灰色的卷发,把头发向外伸展,在柔和的午后阳光下,七八十岁的她就像傲慢的小孤女安妮(《小孤女安妮》是曾在《芝加哥论坛报》是连载的一部美国漫画,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和音乐剧——译注)。“因为,”阿特伍德向我眨了眨眼睛,“我是值得尊敬的。”
加拿大文学女王、预言者、诗人、《权力的游戏》的粉丝、历史百科全书、布克奖得主,种种桂冠的加持让阿特伍德确实值得尊敬。34年前,阿特伍德出版了《使女的故事》一书,这本颇具预言性质的小说描绘了美国被颠覆成为专制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的未来世界。自这本书出版以后,几乎每次女性生育权受到限制,或者有人援引圣经语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辩护,阿特伍德的名字都会被人提及。《使女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使女,她唯一的名字来自于一个男人,而他们之间说是分配生育,实则是强奸与被强奸的关系——她被称为奥福瑞德(Offred),以表明她是属于专制神权统治下基列共和国的大主教弗雷德·沃特福德(Fred Waterford)的财产。
在很短时间里,《使女的故事》就成为了现代经典小说。这本书中对极端宗教狂热分子在美国发动政变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受到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启发,而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在1984年写成的,当时基督教右翼的道德多数派运动正处于鼎盛时期。那时的德国柏林还矗立着柏林墙,在柏林居住的阿特伍德刚刚开始着手创作。后来她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完成了这本书,阿特伍德在那里曾被警告不要在外面骑自行车,因为这一行为可能会被地人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从而把她赶出公路。在苏联的独裁主义和令人生厌的美国妄想狂的骚扰后,阿特伍德终于完成了《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从未绝版,阿特伍德认为,每一次美国大选,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都会达到顶峰。特别是在2016年,就在Hulu改编的剧集《使女的故事》上映不久后,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搭档迈克·彭斯分别当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更是达到了现象级别。使女的视觉形象——白色翼帽遮住脸庞,身披红色斗篷——成为世界各地抗议和集会的标志性服装。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阿特伍德已经在2016年早些时候就决定续写《使女的故事》了。

我和安特伍德在多伦多的酒店里一见面,就讨论起了本年度最受期待的《遗嘱》。在美国时间今天的发布会上,阿特伍德将正式公布这本书,与此同时全球超过1000家影院将同步直播这场发布会。《遗嘱》一书受到了非常严密的保护,以至于今年8月有人把这本书寄给我的时候,落款和书名都是假的,还附带了一份保密协议。《遗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使女的故事》结束后的15年,围绕三名女性角色的叙述展开。《遗嘱》的发布采用了书商梦寐以求的一种形式,同时世界各地的书迷们还开始了新书讨论会和服装派对(伦敦一家书店举办了一场以刺绣和海报制作为特色的活动)。每次我询问阿特伍德一个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时,她都会本能般地灵巧转移话题,仿佛网球赛场上的费德勒。
在被问及《使女的故事》电视剧集是否改变了她对角色的看法时,阿特伍德提到了Hulu的服装设计师安·克拉布特里(Ane Crabtree)写的一篇名为《五十度红》(50 Shades of Red)的关于使女服装的论文。后来当我问她曾经是如何尝试引导16岁的女孩时,阿特伍德回忆起了一件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在《霹雳钻》片场的轶事。提到《使女的故事》一书中的反派角色莉迪亚嬷嬷(Aunt Lydia)在《遗嘱》一书中的幽默感和自我意识为什么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敏锐的时候,阿特伍德说,“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嬷嬷们在空闲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中世纪德国神学家、作曲家及作家,又被称为莱茵河的女先知——译注)呢?她的生活的确挺坐立不安的。”
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们又聊到了嬉皮士的孩子、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乌托邦式浪漫小说、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对法西斯主义的警告,以及莫里斯舞(我们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是异教的事吗?生育仪式?) 和英国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玛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我开始明白,阿特伍德是真的不想谈论《遗嘱》,而我的问题让她很苦恼,因为我一直要求她解释她不愿解释的一本书。《使女的故事》的最后一行——“有什么问题吗?”——暗示她的故事在故意模棱两可。我试图通过每件事来引导她解释她创造的角色,或为这些角色们创作的故事,但这些似乎都是她虽然礼貌却坚决反对回答的。
我猜——她显然不会告诉我——部分原因是阿特伍德的创作围绕着一条属于她自己的线。《使女的故事》是1990年的电影,是歌剧、话剧、芭蕾舞剧,是一个女人的表演,也是加拿大莱克乐队(Lakes of Canada)一张概念专辑的灵感来源。但在过去的三年里,一波又一波的读者称这部小说象征着“反抗”,正如Hulu改编的电视剧集将她的故事扩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有些改编颇值得怀疑——基列共和国的虚构世界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也很有可能脱离了原作者的掌控。
不过阿特伍德说她并不介意。她骄傲地告诉我,这次的新书发布会的现场直播是制片人有史以来做过的“最大的一次”,而她本人其实在接受宣传和淡化宣传之间反复来回的(阿特伍德说,她在多伦多的家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为了给当地图书馆筹措足够的资金,不得不与当地市长罗布·福特正面交锋)。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许多都是关于二元性的:成双成对,又或是相互对立。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是关于奥福瑞德的被动和无力,那么《遗嘱》的故事则由行动来定义。这本书中的人物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力量,而他们的互动也影响了各自的命运。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读者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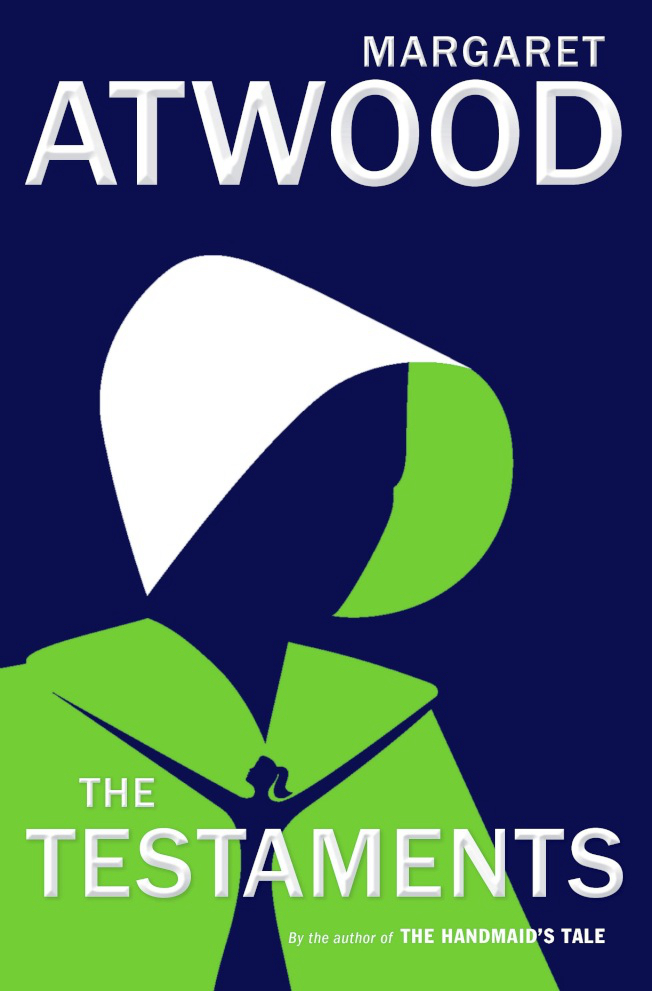
尤其是莉迪亚嬷嬷这个角色的描写,对人们简单解读《使女的故事》的行为提出了挑战。莉迪亚嬷嬷的叙述可以被认为是作者在试图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权威,同时也仍然为有自己判断的读者留下足够的余地。“人们有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判断。”阿特伍德说,她不想把这本书的框架定得太明确,因为她知道,每一位读者“都各不相同,而他们对同一本书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他们面临着与《遗嘱》中人物相同的处境,“他们的问题可能是,你会怎么做?你又做了些什么?”
莉迪亚嬷嬷在《使女的故事》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她却给人一种真实的沉重感。在小说中,当奥福瑞德第一次被基列共和国的特工抓住时,正试图逃往加拿大,结果她被送到了基列共和国的感化中心(Rachel and Leah Center)。而这一感化中心的命名其实来自于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部分章节。《创世纪》第30章1-3节中便有着与《使女的故事》中设定十分相似的情节:拉结(Rachel)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的姊姊(Leah),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吾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这个感化中心的负责人之一便是莉迪亚嬷嬷,她是负责执行这个特殊生育分配制度的嬷嬷之一。在这里,女性被药物管制、受到纪律约束,并被训练成为使女。透过奥福瑞德的视角,莉迪亚嬷嬷与其说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口号的创造者——她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关于女性履行职责的箴言,而这一切仿佛梦魇般困扰着奥福瑞德,始终无法从记忆中抹除。莉迪亚嬷嬷说话时“脸上又出现那种乞丐一般低三下四、战战兢兢的媚笑,呆滞木讷的眼睛眨巴着,目光朝上”,莉迪亚嬷嬷与其说是一个主动的压迫者,更像一个被洗脑刺激的人。当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阿特伍德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告诉我,当她写《使女的故事》时,“根本没怎么考虑过(莉迪亚)。”直到她读了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书中对《简·爱》这部经典名著中作为反面人物的疯女人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改写——译注),才开始注意到罗彻斯特先生的妻子。“她就像一盏灯,只是个固定的装饰。你不会去思考她的过去,她的内心世界,或者其他任何关于她的事情。她的存在只是简·爱结婚的障碍。”说着的时候,阿特伍德递给我一颗腰果。
多年以来,人们不断地询问阿特伍德是否愿意为《使女的故事》写续作,她总是说不。因为阿特伍德觉得,他们问的是她是否会继续奥福瑞德的故事。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那是不可能的,” 阿特伍德说,“你无法真正重现那种声音,再也无法重新构建那种声音。”但如果让时间继续前进,把目光聚焦在基列共和国的第二代人,也许会发现更大的可能性。一旦基列共和国不再像阿特伍德所说的“意识形态冲动而怪异”,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阿特伍德说,每一次革命都有“打碎彩色玻璃窗”的阶段(奥利弗·克伦威尔扮演的角色)和“屠杀哥萨克人”的阶段(布尔什维克扮演的角色),那么接下来的是什么阶段。基列共和国又会发生什么?

当阿特伍德考虑续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开始重新审视莉迪亚嬷嬷——这个眼神呆滞、目光闪躲、死气沉沉的角色——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一直是理查三世的粉丝。” 阿特伍德含沙射影地说)。这本书由三位女性角色讲述:一是莉迪亚嬷嬷用蓝墨水写成的非法记录,藏在天主教主教纽曼(Newman)的《生命之歌》(Apologia Pro Vita Sua: A Defense of One’s Own Life)副本里。二是一位名叫艾格尼丝(Agnes)的年轻女子,她叙述了在基列共和国的成长见证(Hulu剧集的观众应该会很熟悉这个名字)。三是一个名叫黛西(Daisy)的年轻女孩,她在加拿大长大,始终无法摆脱父母对她有所隐瞒的感觉。当我向阿特伍德提到我很喜欢艾格尼丝和黛西的对比时,她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我说:“是……的,你会喜欢的,不是吗?”
莉迪亚嬷嬷是这本书中最受作者关注的人物,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人物。如果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可以说莉迪亚嬷嬷的视角主导了《遗嘱》一书,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关于基列共和国建立的细节和背景。莉迪亚嬷嬷在小说中的叙述章节被冠以《阿杜瓦图书馆的全景图》(The Ardua Hall Holograph)的标题,在这里,全景图(holograp)似乎有双重含义——一个曾经单一形象的角色变成了三维立体的形象。
在Hulu编剧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参与改编的剧集《使女的故事》中,莉迪亚嬷嬷这个可畏的角色由安·唐德(Ann Dowd)饰演,唐德也成功地演绎出了莉迪亚嬷嬷在宗教狂热、同情心和仪式化的虐待之间逐渐迷失的过程。阿特伍德表示,很难说剧集是否影响了她对角色的看法。“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我并不会纠结于这里或那里到底改编了多少。” 阿特伍德说,词汇总是要经过诠释的,而电影和电视则更注重字面的意思。在原著小说中,莉迪亚嬷嬷角色形象的建立多是通过外界的描述。而在电视剧中,唐德的精彩表演和米勒对莉迪亚生平的拓展,都使得莉迪亚嬷嬷的角色形象更加有深度。但《遗嘱》一书中莉迪亚嬷嬷的角色又变得与众不同:她是基列共和国的历史记述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转变对奥福瑞德和读者对她的评价都提出了质疑。
虽然阿特伍德的续作和电视剧集并没有严格遵循相同的故事主线,但其实两者之间其实仍然有着特殊的共生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不同于其它任何文学作品和好莱坞的合作。“我们经常联系,” 阿特伍德把她与米勒的互动称为“非常尊重对方”:双方的目标遵循不做任何与对方已经做过,或者可能想做的事情产生直接矛盾的事情(HBO的《权力的游戏》没能等到乔治·RR·马丁的最后一部小说完结,就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了)。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饰演的奥福瑞德在剧中的名字是琼(June),阿特伍德表示能理解这一点,她说一个没有名字的电视角色是不可能出现的——你不可能让每个人连续几季都说“嘿,你”。同样,虽然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国家,但由于Hulu的种族多元化政策,使得米勒改编的基列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不区分种族(color-blind)的社会。

在《遗嘱》时间跳跃的叙述中,阿特伍德给米勒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来补完琼的故事。《遗嘱》中也透露了一些细节,包括奥福瑞德两个孩子的名字。为此,阿特伍德说,双方要各自取一个孩子的名字。电视剧方面的人选择了Agnes,意思是“神圣的”或“纯洁的”。 阿特伍德选择了Nicole,意思是“人民的胜利”。 尽管阿特伍德确实说过很喜欢米勒,但小心翼翼地没有对Hulu的剧集做出任何评价(阿特伍德还很崇拜加拿大女导演萨拉·波利,特别是她为CBC和Netflix改编的《双面格蕾丝》,阿特伍德称之为 “一流的作品”)。鉴于《遗嘱》中对莉迪亚嬷嬷的特别关注,阿特伍德似乎也把自己的赌注押在了这个角色上。
在阿特伍德的职业生涯中,人们一直试图把她归入女性作家、女权主义作家、政治作家、加拿大作家,甚至是预言家的行列(阿特伍德本人对这些标签中,似乎唯一欣赏的就是预言家,因为世界的发展已经多次证明她是对的)。在1976年一篇题为《论作为一个女作家》(On Being a Woman Writer)的文章中,阿特伍德谴责有人出于各种政治原因,鼓吹她的作品推动了“一元女权主义批判(one-dimensional Feminist Criticism)的发展”,她还抨击了那些坚持“试图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的采访者。她写道,最糟糕的采访者就是那种“信息小姐”(Miss Message),他们无法理解她的作品到底是什么(虚构小说)的人,却固执地想把她的言语引导成为“倡导者、代言人或理论家”(采访过了几周后,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不禁深吸一口气)。
《使女的故事》被当作一部开创性的女权主义作品一直困扰着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多体现在奥福瑞德对母亲的回忆中。出于类似的原因,阿特伍德更倾向于不把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尽管按照大多数现代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她显然是符合要求的。阿特伍德在2005年出版的《移动的靶子》(Moving Targets)一书中写道,她把《使女的故事》作为对《一九八四》那种将女性角色边缘化作品的一种反击——即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创造一个“反乌托邦”。 然而,阿特伍德也澄清道,“这并没有让《使女的故事》成为一个‘女权主义反乌托邦’,只有那些认为女性不应该拥有发声机会和内心生活的人,才会将这本书视为女权主义。”
因此,阿特伍德拒绝“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不是因为她否认女性在智力、地位和人性方面应该与男性平等。这种想法似乎与多年以来她的作品中采用的不完美写法有关。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女权主义比起以往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营销工具——一股轻浮的、听着劲爆歌单、带着粉红猫耳帽(pussy-hat,是2017年众多美国女性为反对特朗普针对女性的粗俗语言举行游行时带的粉红色针织帽——译注)、获利颇丰的潮流。在2018年,就有一个名为“使女的故事”品牌葡萄酒系列招摇上市,这个系列包括了一款“朴实”(earthy)奥福瑞德-黑皮诺葡萄酒,一款“大胆”(bold)奥弗格伦-赤霞珠葡萄酒,和一款“成熟”(sophisticated)的塞雷娜·乔伊-波尔多白葡萄酒,这种行为深刻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最无耻的本能——女性营销(由于遭到强烈反对,这种葡萄酒在发布24小时后就被取消了)。
阿特伍德笔下的奥福瑞德精明能干、引人注目却毫无权力可言——也不是女权主义的象征(Hulu改编的剧集关于女权主义这点可能与原著并不相同)。她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莉迪亚嬷嬷也是。阿特伍德选择把《遗嘱》中相当大的篇幅花在莉迪亚嬷嬷的视角,便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记住她的作品。她笔下的人物并不应该注定出现在在鼓舞人心的符号中,不应该出现在海报上,更不应该被奉为女权主义美德的典范,而应该是引人入胜的读物。长期以来,阿特伍德一直对一种观点感到恼火:有人认为,她把女性描绘成具有与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的复杂个体是在伤害女性。阿特伍德在1978年一篇名为《夏娃的诅咒——或者说我在学校学到了什么》(The Curse of Eve—Or,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的文章中就写道,女人,无论是作为角色还是作为人,都必须“允许她们的不完美”(当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说了一些关于女性团结起来能做些什么样工作的陈词滥调时,阿特伍德立即回答说,“她们和黑猩猩一起也行。”)。
如此说来,《遗嘱》既是一部小说,也是阿特伍德的纠正行为。像阿特伍德一样广泛受人尊敬的作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被全世界解读,甚至被那些意图和想法并不总是与她一致的人诠释(或借鉴)。这也意味着电影或电视剧编剧会把她的故事以成不同的形式改写,并以她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的方式拓展或重塑它们。对阿特伍德作品不完美解读是不可避免的,而她也把类似的情节写进了《使女的故事》: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故事发生后几百年的未来,一位研究基列共和国历史的教授试图分析奥福瑞德的录音磁带,并将自己的偏见带入了研究的过程。
阿特伍德明白这一点。“当你出版了一本书,它就不再是属于你个人的书了,” 她告诉我,“它是属于读者的。如果没有人在读这本书,那么它就静静躺在那,就像没人演奏的乐谱。”受到广泛尊重的同时也有好处:参加艾美奖的颁奖典礼相当有趣——阿特伍德说她是跟办公室的两个女员工一起去的,她们一起“玩得特别开心”。 如果说阿特伍德对这么多人还在看《使女的故事》,这么多人对《遗嘱》充满期待不高兴的话,那她一定在撒谎。“但我不高兴也没关系。事情还会同样地发生。”
然而,在这么长时间之后出版续集,也意味着这是属于她的书,属于她的世界。许多虔诚的《使女的故事》读者可能并不期待《遗嘱》的故事,因为这本书可能会让曾经看似简单的人物变得复杂,曾经容易做出的判断变得混乱。但这本书在不受主观解释影响的情况下,在虚构的世界中留下了作者自身的印记。当我问阿特伍德为什么她的作品中总是有这么多女性的叙述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将其描述为对不可靠的叙事本质的“考古”兴趣。“埋在地下的东西会被发现。隐藏的事会被揭露出来,但是作为一名小说家,”阿特伍德说,“通常——事实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本文作者Sophie Gilbert是《大西洋月刊》文化专栏的特约撰稿人。
(翻译:张海宁)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