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10月22日出生到2013年11月17日逝世,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亲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波澜起伏。
一战甫一结束,她在伊朗出生。1925年,她的父母从英国举家搬迁到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在1949年迁居伦敦前,莱辛在那片前英属殖民地度过了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她13岁辍学,通过阅读书本自学成才;在二战战火纷飞之时,她结婚生子,加入左翼图书俱乐部;怀着社会主义理想,她带着与第二任丈夫戈特弗里德·莱辛所生的幼子彼得前往伦敦,目睹了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桩桩大事。她曾这样评价她所经历的历史:“回顾我这一生,我看到的是一系列大型群众事件、情绪的舞动、狂热的党派热情连绵起伏,当这些事情不断上演时,我们是不可能进行思考的。”
在许多小说中,莱辛探讨现代生活的困惑与复杂性;而在《画地为牢》这本由一系列演讲稿构成的散文集中,她讨论了现代生活最大的迷思之一:尽管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科学)和内部世界(心理学)的理解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人类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即一直被群体狂热裹挟着陷入失去理性的境地。
如果说波云诡谲的20世纪教会了莱辛什么,那就是对权威、集体和看似永远正确的主流意见心存警惕。她指出,“血”是常常被领导者利用以动员民众的词语,然而流血与牺牲的后果承担者往往也是民众。她发现,主流意见的反转时有发生,比如英国人在二战时和二战后对斯大林及苏联的看法。她得出结论,人群中只有少数人有独立思考能力,然而大多数人是权威的盲从者,“这种对权威的服从,简而言之,不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的专有之物,而是普遍的人类行为中的一部分。”
莱辛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在无意识中服从集体和权威的:在米尔格兰姆实验中,志愿者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狱卒两组,“狱卒”跟随指令调高电击的强度,罔顾坐在电击椅上的“囚犯”越来越痛苦的尖叫声;莱辛曾以简·萨默斯的笔名写了两本书,被她的两家主要出版商退稿……“几乎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都源自群体信念、群体需求、民族需求、爱国主义和对忠诚于本地的要求。但更狡猾、需求更旺——也更危险——的压力是来自内部的,这是一种你应该顺从的需求,而这正是最难观测与控制的,”莱辛写道。
在前互联网时代,莱辛就对群体意识和群体行动做出了上述警告——《画地为牢》首次出版于1987年——而在当下,群体控制和意志操作的手段必定比当时更加隐蔽高明,而饱含“你们该死,我们得救”心态的群情激愤亦愈演愈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画地为牢》的第五篇《社会变革实验室》。在这篇文章中,莱辛忠告年轻人在大众思维和群体运动的诱惑中重新认识个体的力量,为自己思考,为自己选择:

“回望过去,我不再看到那些巨大的集体、国家、运动、体系、信念、信仰,只看到个体,我年轻时会看重这些个体,但并不以为他们能改变任何事情。回望过去,我看到个体可以施予多么大的影响,即便是不见经传、深居简出的个体。正是个体改变了社会,个体孕育了思想,个体奋起反抗大众意志,并改变了它。在封闭社会如是,在开放社会亦如是,当然在封闭的社会伤亡率会更高。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教导我尊重个体,尊重那个耕耘和存续自己的思考方式、起身反抗集体思维和集体压力的人,或者那个给予群体必要的安慰、私下存续个体思维和发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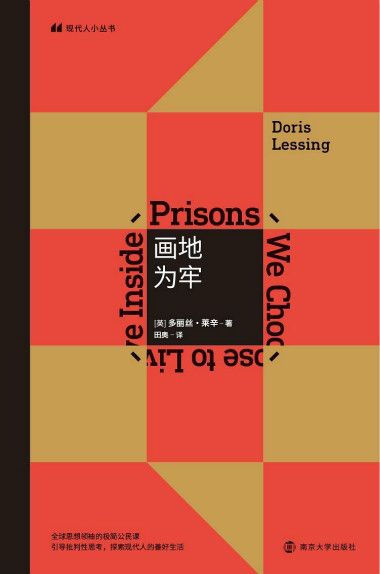
[英]多丽丝·莱辛 著 田奥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社会变革实验室》
文 | 多丽丝·莱辛 译 | 田奥
生活在这样一个似乎日渐恐怖的世界,有时我们很难看到什么好的、有希望的东西。光听新闻就足够让你认为自己活在一个疯人院了。
但是等等……我们都清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闻都是为了将效果最大化,也就是说,至少糟糕的新闻会比好新闻更能激发我们的行动——而这也是人类境况的一个有趣注脚。糟糕的新闻日复一日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是最糟糕的新闻,我认为我们的意识正越来越被设定成有着不祥预感和萎靡不振的态度。但有没有可能所有呈现出来的糟糕事物——我都不需要把它们列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是些什么——其实是一道拖曳的暗流,是一种对我们未曾察觉的前进的人类社会变革的反应?也许吧,回望过去,比如近一两个世纪,人们可能会这样说吗?——“那是一个人们为了争夺至高权力而走向极端的时代。人类的意识迅速朝着自觉、自制的方向发展,但一如以往,一如以往之必然,猛烈的推进唤起了它的反面——愚蠢、残忍、蒙昧思想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一件特别鼓舞人心的事。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少数独裁暴政国家转变成了民主国家,其中就有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阿根廷。它们中的一些目前并不稳定——民主一直是不稳定的,而且必须靠斗争获得。但那些受单一思想、简单头脑和毫无用处的思想体系支配的国家选择了尝试更复杂、选择更多的民主平衡政体。
为了不只看到这充满希望的事实,我们必须再说一个悲观的。许多年轻人在长到可以参与政治运动的年纪,采取了一种与我们这代人相似的立场或态度。也就是他们认为民主不过是欺骗与假装,不过是剥削所戴的面具,他们想要跟民主划清界限。我们几乎已经达致这样一个临界点:如果某人说自己珍视民主,那这个人就会被宣布为一个反动分子。我认为,这种态度会成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态度之一。实则,这些栽培出这种反民主态度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民主的相反面:那些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向往民主。

我不是不明白这种态度——我太理解了,我自己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民主、解放、公正以及其他——这些价值塞满了一个人的喉咙,但突然你看到自己周遭充满了骇人的不公正,你吼叫:“伪善!”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是南罗得西亚,在那里民主只是供给白人少数群体的,黑人多数群体没有任何权利。但当人们处于这样一种思考状态时,就会忘记无论民主多么不完美,它仍然提供了革新与变化的可能性。民主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从历史上来看,这种选择自由是全新的观念。个体应该拥有权利,公民可以批评政府,我觉得我们开始忘记这些观念到底有多新了。
那到底有多新呢?这种概念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降临人类社群?说到这里,有人就会开始唠叨古希腊了,别忘了那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而且仅给少量男性公民提供特定的、极少的自由。由于讨论时间的缘故,我可以说我们关于自由,关于个体权利的概念诞生在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它当然是很晚近的观念,非常脆弱,非常不稳定。
个人有权享有法治——为什么?三四个世纪之前,你说这种话时别人都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如今这种观念却强大到能把强权和暴政打倒在地。
一种观念开始在人们心中扎根,那就是存在一种文明政府,而且人们对何为文明政府是有统一的看法的。要不然阿根廷的公民怎么会统一意见,以邪恶、残酷、不当的施政行为为理由控告他们那已经倒台的政府?这对我来说是最特殊、最鼓舞人心的事——这种事情竟然可能发生,它向所有人证明了世人心中存在一个关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观念。在这之前,有过公民想以施政行为不当为由控告政府的例子吗?我不是历史学家,但在我看来,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想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自视为民主国家的国家,失掉了对民主的信心,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过度简化的思想意识极其猖獗的时代,我说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可怜的经济状况滋养了独裁暴政。
但是好观念不会消失,尽管它们可能被淹没一阵子。
举个例子。我前面一直在谈被称为“软科学”的东西,也就是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以及其他的学科,谈到它们对我们将自身认知为社会动物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这些晚近的科学是如何被诋毁、被资助,被打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公共资金正在减少,大学院系正在关门,各种各样的研究被迫中断。这种类型的学科深受影响,它们通常是第一个被中断的——然而我刚刚读到,在许多大学里,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科学和其他相似学科的院系的紧张状况正得到缓解,因为他们对工业发展有所助益。也就是说,它们在人们认可的方面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还有另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事情,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我们已经忘了共产主义本脱胎于人们对人人都能获得公正对待的古老梦想。这是一场强有力的梦,也是一个引导社会变革的强大引擎。不能因为现状,就否认真正的公正理念无法获得新生。
同时,这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结构不是由特权阶层和贫苦大众构成的。握有权力的精英总是存在的,没有财富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的人民大众也是存在的。
在更沮丧的时候,我的确会对共产主义苏联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就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感到焦虑,他们这个精英阶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精英阶层在财富和特权方面别无二致。一些非洲新兴国家也是如此。但如果就目前来说,这是某种无法避免的过程,所有的社会都会制造出拥有特权的精英,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并且在这一结构中尽可能灵活地做出改变。
无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抑或是按理说能为每一个人谋福祉的民主国家的政党,这世上没有哪个对此提出反对的团体或党派不把自己也视作精英。
精英、特权阶层、受教育群体……这似乎就是目前这个世界正在上演的节目;至少,在任何一个地方,其他的东西都被遮蔽了。
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精英,有倒行逆施、毫无用处的,只会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另有一些,我认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如果我说我认为精英、特别阶层通常是有用处的,我会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精英:像我在前面说的,如果你管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叫精英,那就不一样了,不是吗?或者,如果我说我认为核心小组、压力集团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没能把社会从沉睡与自我陶醉中拉回来,这也差不多了吧——不,值得怀疑的是精英这个词。行了吧,我们该把精英这个词抛弃: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会因为一个字、一句话就被屠戮的时代啊……
有这么一种社会进程,它为人所知、显而易见,但也许并没有到众所周知的地步。当一个新想法被少数人接受时,大多数人会大喊叛徒、垃圾、疯子、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任何一个在那个社会值得被用上的谩骂词汇。少数人逐步发展了这个想法,起初可能是秘密或者半公开地进行的,然后越来越为人所知,有越来越多人支持,直到……你猜怎么着?这种具有煽动性的、不可能实现的、执迷不悟的想法突然变成所谓的“被接受的意见”,开始被大多数人喜爱与重视。当然,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还会有新的想法冒出来,继续煽动,继续相同的进程,继续被少数人培育和锤炼。假设我们依照现实的目的,重新定义精英这个词,将它等同于任何一群为了任何目的而拥抱某些想法并就此让自己走在了大多数人前面的人?
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注定要说这样的话,你们会同意的——你们最能取悦自己的消遣方式之一,就是看着这一进程连续不断地重复上演。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除了一小部分深思熟虑的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仍旧能够轻易地相信永恒。什么!他们珍惜的那些美妙想法注定要被扫进垃圾堆?当然不!
但是假设我们中的足够多的人相信这就是一个持续运行的进程——甚至在那些将新思想宣布为非法的社会,比如共产主义国家——“今日之背叛成就明日之正统”就一定会实现。如此一来,我们难道不会变得比现在更有效率,比现在少一些艰难与残暴,更愿意做出改变?我认为会的,而且我认为终有一天,这一点会和社会的其他机制一样被使用,而不是被抵制与忽略。到时只有那些从不阅读历史的人,才会忽略这一点。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对历史不感兴趣了。在英国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年轻人被问及他们认为最有用的研究学科是什么,调查结果中历史学的占比非常低:仅有7%的人认为历史学是有价值的。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心理学上的,这很明显能看出来,也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如果你也曾年轻过的话。如果你自认为是“年轻人”,从定义上看又是个右派的进步分子或革命分子或其他什么(作为年轻人,与愚蠢又保守的老年人对抗),那你最不想做的恐怕就是回望历史了,因为在历史中你会知道年轻人怀抱这种想法是从未断绝过的,是某种永恒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你将自己视作荣耀的、崭新的、令人惊异的存在,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新奇的,甚至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便不是自己独创的,也至少是从朋友或尊敬的领导那里借鉴来的,觉得自己是一种新的、无污点的生命,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你不会想去阅读任何会动摇这种想法的东西。如果我听起来像是在嘲笑,其实我只是在嘲笑年轻时的自己——但重点正在于此。
我认为“历史不值一读”这样的态度,会打击那些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追赶我们的人。
毕竟,自法国大革命(一些人会说是自克伦威尔时期的乌托邦和社会主义团体)以来,我们所见证的一切,已然累积成了一个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不同种类的社会的实验室。从希特勒治下的十三年战争时期(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到英国的工党政府;从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政权,到古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你会认为那些一心想要创造新的社会类型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落到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例子上,为了从这些例子上研究和学习到什么。
我再重复一次:回望过去这两个半世纪的一条路径是,将之视作一个社会变革实验室。但是为了从中学到教训,人们需要对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所区隔;我认为,正是这种区隔让我们的社会良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沸腾的骚乱或党派热情中,一个人是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我以为,我们不应该以现在常用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历史,亦即教导他们将历史视为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他们出于某些原因应该了解这些事件。我们应该教导他们将历史视作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们不仅能学到曾经发生的事,也能预测未来可能,甚至很可能会发生什么。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知识中的两大分支,它们记录了人类的行为与思想,但如今越来越不受年轻人,甚至教育者的重视。但从这两者中,我们能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还能学会用冷静、沉着、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态度来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这是我们作为文明人唯一可能表现出来的态度,古往今来的哲人圣贤皆如此称道。
然而所有的压力都往另一条路上走去了——学习就是要学即时有用的东西,要学实用性的东西。人们越来越要求的是,为在技术领域的一个几乎完全暂时性的阶段起到作用而接受教育,他们要求短期教育。
我们必须再次审视有用这个词语。从长期来说,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有用的东西是那些留存、复苏进而兴盛的东西。似乎在现阶段,世界的精英阶层所受到的教育是关于如何有效地使用我们的最新技术,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那些以过去被称为人文主义的观念——长期的、全面的、思考性的观念——为受教育内容的人,会被证明更有效率。单单是因为他们更加明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不是我看低新技术,正相反,只是因为这些精英所了解的必需品其实是暂时性的。
在我的思考中,这个世界的推进、延伸与发展是朝着更复杂、更多样、更开放的方向进行的,它允许一个人同时拥有许多想法,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想法。
我们可以看看,当一个社会坚持正统、单一思想和口号式的思考时,它必须为此付出何种代价:苏联是一个沉默的、错位的、低效的、野蛮的社会,因为它所坚持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将思想的多样性视为非法。“生活本身”——套用共产主义者们喜欢使用的词语——向我们展示了,当社会就这么让自己在呆板的思维模式中僵化时会发生什么。(戈尔巴乔夫正试图补救。)我们可以观察,中国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聪明而务实的民族——正试图改变自己;我们还可以观察,基要主义伊斯兰文明所创造的社会由于缺乏多样性,会立马显现出自身的缺陷,被其他更多样化、更开放的社会甩在身后。
从长期来看,我认为人类会朝着民主而多元的社会前进。我知道,当我们此刻环视周围的世界,我的这个想法看起来似乎太过乐观,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关于人类如何行事、如何运转的新信息被政府、警察部门、军队和秘密特务——所有目的在于削弱和控制个体的部门——极富技巧地、自私地利用。
但我坚信的是,从长期来看,永远是个体在确定社会的基调,提供给社会真正的发展。
当世界各地的个体正被大众思维、群众运动,以及小规模的团体性运动击倒、侮辱和淹没时,要重视个体的力量并非一件易事。
对于年轻人更难的是,面对着障碍物般的难以逾越的墙,如何还能对自身改变事物的能力怀抱信心,如何还能让自己的个人观点完好无损。我还清楚记得,在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只会看到似乎无坚不摧的思想或信仰体系——政府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那些政府,比如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政府最后怎么样了呢?那些强大的信仰体系,比如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或斯大林主义又怎么样了呢?还有大英帝国……实际上所有的欧洲帝国,甚至离我们不久的强大帝国,它们怎么样了呢?它们全部消失了,而且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回望过去,我不再看到那些巨大的集体、国家、运动、体系、信念、信仰,只看到个体,我年轻时会看重这些个体,但并不以为他们能改变任何事情。回望过去,我看到个体可以施予多么大的影响,即便是不见经传、深居简出的个体。正是个体改变了社会,个体孕育了思想,个体奋起反抗大众意志,并改变了它。在封闭社会如是,在开放社会亦如是,当然在封闭的社会伤亡率会更高。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教导我尊重个体,尊重那个耕耘和存续自己的思考方式、起身反抗集体思维和集体压力的人,或者那个给予群体必要的安慰、私下存续个体思维和发展的人。
我完全不是在谈论古怪的人,英国人一直对这种人的存在感到大惊小怪。不过我的确认为只有在一个僵化和顺服的社会,才会产生“古怪的人”这个概念。古怪的人倾向于喜欢不同于别人的图景,而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古怪,纯粹因为古怪本身而成了古怪的人。不,我谈论的是那些关心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人,那些尝试吸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行为与运转中的信息的人——那些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人。
我相信,一个智能的、高瞻远瞩的社会应该尽全力培养这样的个体,而不是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打压他们。但是如果政府,如果文化不鼓励个体价值的生产,那么个体和群体可以也应该鼓励。
我们回到精英这个概念,在这个语境下谈及它,我可以接受。我们无法期望一个政府对孩子说:“你们会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宗教类和政治类群众运动、大众意识和大众文化的世界。每时每刻你们都会被淹没在批量生产和反刍的意识与观点里,这些意识与观点的真正活力来自群氓、口号与模式化思维。你的一生都会受到压力从而参与群众运动,而如果你胆敢反抗,那你每天都会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群体的压力,通常来自最亲密的朋友,以使你顺从他们。
“在你人生中的许多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坚持对抗这些压力,你会觉得自己没那么坚强。
“但是你会受到教导:如何审视这些大众意识,如何审视这些显然无法抗拒的压力,如何为自己思考,为自己做出选择。
“你会被教导阅读历史,也会学到那些短命的意识是什么样的,以及那些最无力抗拒和极具说服力的意识可以也一定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你会被教导阅读文学,这是一门研究人性的学科,也会去理解世界人民及各民族的发展。文学是人类学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而且我们会确保你学会如何从人类的长期记忆角度来评判某种观念。因为文学和历史都是人类记忆的分支,它们记录记忆。
“这些研究将被加入那些信息的新分支,即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新学科,由此你就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及群体的行为;终其一生,这群体都会既是你的安慰,又是你的敌人,既是你的支撑,也是你最大的诱惑,因为对你的朋友说“不”,是痛苦的——你可是群体性动物啊。
“你会被教导无论在外部你不得不表现得多么顺从——因为你即将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通常会以处死的方式对待不顺从者——也应该保存自身内部的独立,保存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思想……”
不会,我们无法期望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在推行的课程中讲述这些话语。但家长可以谈论和教授这些东西,学校当然也可以。受到国家通行教育或者私立教育夹击,并且还存留着完整的批判性思维并希望在既定的教育内容之外有所突破的年轻人群体,可以教导自己和别人这些话语。
这样的人,这样的个体,会成为极具生产性的发酵剂,拥有大量这样个体的社会是幸运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我们以此为傲,这是没问题的。一个开放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政府不会对其公民隐瞒信息,政府必须允许思想观念的传播。我们拥有这一切,却太想当然了;我们曾经珍惜的价值,已不再受人关注。数代先烈为思想自由而战,我们才有了如今的一切。我们只需要与住在铁幕背后的人交流一番,就会记起自己是多么幸运,即便我们的社会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与从苏联来的人交流,因为在那里,思想无法传播,信息被压制,处处弥漫闭塞、恐怖、压抑的氛围。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学校教育有缺陷,我们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教导,而且可以伸手去触及任何我们觉得有价值的思想观念。
我认为,我们应该比目前更多地利用这些自由。

为了搜寻例子来佐证我对独立意识、打破规矩者能影响历史事件的信念,我偶然发现了公元前1400年登上王位统治埃及的法老埃赫那吞(Akhnaton)。彼时埃及的国家宗教是阴郁暗淡、受死亡掌控的,存在不可胜数的神祇、半动物和半人类。埃赫那吞不喜欢这种信仰,所以他摆脱了阴郁、压抑的祭司,以及那些同样阴郁的半动物神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宗教,以爱为基调,崇拜唯一的神。埃赫那吞的统治仅持续了数年,他被人赶下王位;旧的信仰和旧的祭司体系卷土重来。后来者如果提及埃赫那吞,会把他称作异教分子或者大叛徒,按照今天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从历史中消失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人发现。从那时起,埃赫那吞就对各式各样的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摩西正是从被压制的阿吞信仰,即埃赫那吞创作的信仰中学习到了一神论的观念。更近一些,托马斯·曼把这位埃赫那吞放进了自己那本伟大的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ethren)。最近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要写一部关于他的歌剧。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位3500年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法老,以令人惊叹的能力点亮了我们的想象之光。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推翻了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并强加一套崭新的,也更简洁的观念。一个孤单的、勇敢的个体,向一个大型的祭司机器以及国家发起挑战;一个人,建立了一套关于爱与光明的信仰,来抵抗关于死亡的信仰……
很可能当埃赫那吞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也问过自己,为了对抗这种丑陋、沉重、强大、压抑的统治,连同它那些祭司和令人惊恐的神祇,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又何必尝试呢?
当我说到要好好利用我们的自由,我不是说仅仅加入游行队伍、政党,或者其他种种,这些东西不过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说要检验种种思想观念,无论它们来自何处,看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居住的社会产生帮助。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画地为牢》的第五篇《社会变革实验室》,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