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张之琪
1991年伍迪·艾伦主演的话痨电影《商场即事》(Scenes from a Mall)讲述了一对各自心怀鬼胎的中年夫妇琐碎婚姻生活中的平凡一天,这整整一天,他们都是在一个购物中心里度过的,仿佛这个无穷无尽的购物中心才是影片的主角。的确,没有什么是”买买买“不能解决的,购物中心拥有你一生中所有需求和难题的答案:
“你可以在这里买礼物,无论是书、冲浪板还是银相框;可以吃饭,无论是日料、汉堡还是墨西哥风味,如果你突感不适,还可以买到止痛片或者阿司匹林。你可以去看场电影或者去酒吧喝一杯,在酒吧幽暗的灯光下与恋人相拥跳舞,甚至在影院黑暗的角落里做爱。如果你厌倦了自己或者伴侣,可以去买一身新衣服,然后在一部电梯上和自己的伴侣吵架,在另一部电梯上发现新的艳遇。”(剧中台词)
如果说购物中心是上个世纪消费景观的地标,那么随着电子商务的繁荣,亚马逊和淘宝则成了本世纪“剁手族”的天堂,相比于实体的购物中心,人们在网络上能够获得更加匿名、更加高效、更加无缝(seamless)的购物体验,购买行为被简化为指尖的轻轻一击,我们看不到钱从账户上划走,东西却会如期出现在家门口。2019年“双十一”1分356秒内天猫成交总额突破一百亿,或许也只是我们社会不可估量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的流水线上隆隆驶下第一辆汽车的一刻,标志着以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的伊始。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存在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根本态度。在这一个世纪间,不少学者试图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揭示消费带来的深刻变革,自由主义者认为消费捍卫了个体实现需求和欲望的权利,批判理论家则视消费为新的控制和支配形式,人类学家认为消费是现代社会确立秩序和意义的仪式,而社会史家则通过消费窥视一个时代的生活变迁。
在双十一这一天,界面文化挑选了八本关于消费的经典著作,与你共勉。

《消费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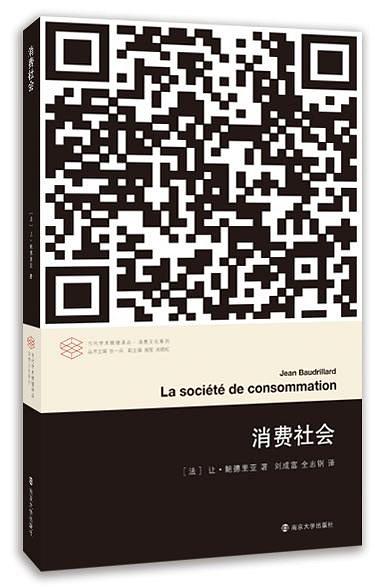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青年时期的代表作。“消费社会”并非鲍德里亚的原创,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均有涉及当代生活中俯拾皆是的炫耀型消费景观,然而鲍德里亚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铺天盖地的商品构成的符号网络和意义链条是如何不动声色地控制和支配着我们的欲望。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头就指出,不断丰富的商品、服务和物质财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富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不断迭代的节奏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不仅如此,这些不可量数的物还是以全套的形式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都指向一系列与之相互对应、相互补充的商品,每一件商品都是具有清晰指示性的,它可以诱导消费者的购物冲动,使之从一件商品走向另一件商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拥有了一条项链,就会想要一条与之相配的裙子,然后就是一个宽敞的衣帽间,一栋豪宅,一座海岛,全世界……我们似乎在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困住并强迫消费,而这种强制性却恰恰表现为一种被幻象引诱的自愿。
《工作、消费、新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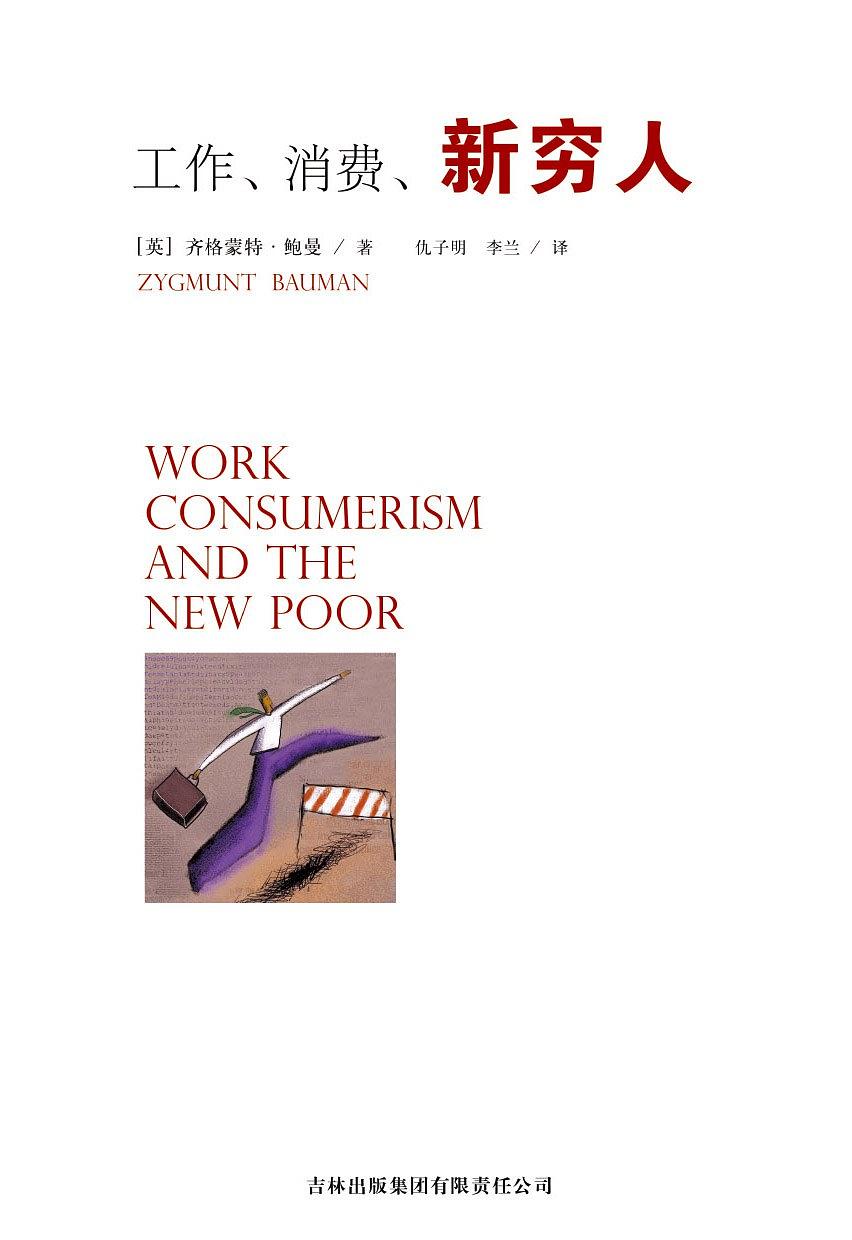
三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已经提出,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传统的生产主人公传奇已经让位给消费主人公;有意义的生活,已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实现。那么没有消费能力的穷人怎么办呢?
刚刚去世的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在鲍曼看来,每个社会都在依据不同的范式建构穷人的形象,“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而消费社会中出现的“新穷人”,就等于“不合格的消费者”,他们被迫生活在为富人设计的消费空间内,却被排除在频繁的购买活动之外,因为缺乏“购买力”,他们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无望,第一次沦为一无所有、一无所用的废料。
而作为消费社会的合格公民、中流砥柱的“月光族”,疯狂地花着明天的钱的“负债化主体”,却随时面临沦为“新穷人”的危险。换言之,消费社会不仅是一个抛弃了穷人的社会,也是一个在大量生产着穷人的社会,无节制的消费正在将中等收入群体拖入贫困的泥沼。看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里,月薪不菲却举债度日的中产,和二三线城市里为了一支唇膏“裸贷”的年轻女孩,就知道鲍曼所言不虚,居高不下的房价、竞相攀比的名牌,将他们变成了光鲜外表下的“新穷人”。
《时尚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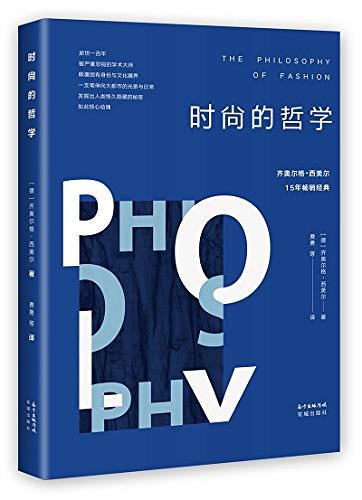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2017
在这本碎片化的文集中,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讨论社交、饮食、宗教等广泛的话题,而其中的一章则着重分析了时尚的逻辑。在齐美尔看来,时尚存在于人类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难追求之中,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冲动,同时也有融入整体的愿望,时尚不仅反映了,而且调节了这种对立。
一方面,时尚是对既定范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规训的需要,提供了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集体样板的普遍性规则;另一方面,时尚又满足了个体对差异性的要求,因为时尚本身就具有阶级属性,社会较高阶层通过时尚将自己与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他们时,他们便会立即抛弃旧的时尚,重新塑造新的时尚——这也是为什么时尚如此依赖快速的更新迭代。
因此,齐美尔将时尚视作一种积极的社会机制,它同时具有分界功能和模仿功能,满足着分化与同化的双重目标,既使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共处,又维护了他们之间的界限和分野。因此,在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时尚的更新速度往往也更快,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欲望总是格外强烈;反之,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潮流也趋于稳定。
《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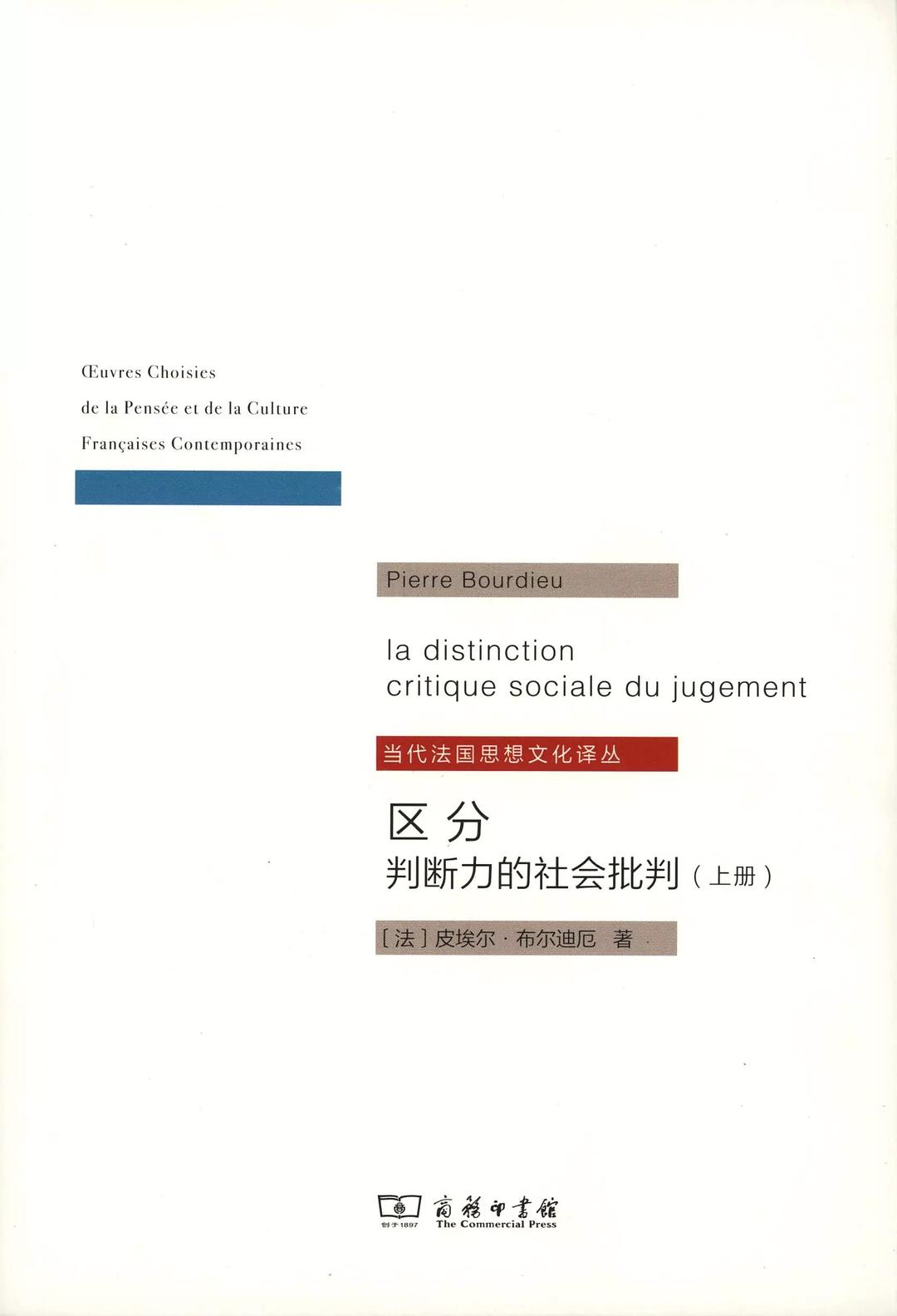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2015
布尔迪厄近千页的巨作《区分》曾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著作之一,它的副标题叫做“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是针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作,在布尔迪厄看来,人的审美趣味并非如康德所言,源于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它是后天的、习得的,是社会区隔的标志。无论是欣赏音乐、阅读经典这类高雅趣味,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穿衣打扮,都透露着符号空间内的趣味等级和现实空间内的社会等级之间牢固的对应关系。
然而,布尔迪尔对这种对应关系的描述,却没有落入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他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惯习”(habitus)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并借助这两个概念阐述了审美趣味和社会等级之间复杂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个体的审美趣味是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和铭写的结果;另一方面,代表不同阶级的审美趣味也是在微观层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文化实践中塑造出来的。
布尔迪厄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的界限,取消了康德以来“感官审美”(taste of sense)和“反思审美”(taste of refection)之间的分野。在布尔迪厄看来,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样受到消费主体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制约,同样有其物质和身体基础,也同样是在主体积极的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的。
《物品的世界:消费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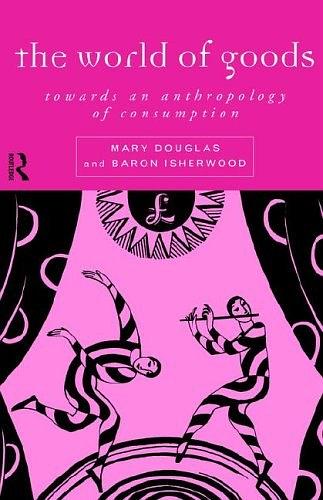
Douglas Profess 1996
由著名英国人类学家、《清洁与危险》的作者玛丽·道格拉斯与计量经济学家拜伦·伊舍伍德于1978年合著的《物品的世界》,可以算是经济人类学的开先河之作。道格拉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消费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她指出,我们要丢弃消费的功利作用,要忘记“东西好吃、穿起来漂亮、住起来舒服”,只有充分剔除了物品的使用价值,我们才能认识到,消费的实质功能在于它可以产生意义。
道格拉斯认为,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限定和明确意义,从而建立社会共识。涂尔干早就指出,拜物教在原始部落中起到了维系和巩固社会关系的作用;道格拉斯在这里则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是通过对物的比较、分类、使用,来建立秩序和组织社会关系的。从这一角度讲,道格拉斯赋予了消费一种近乎仪式的意义,尤其是使用有形物品的仪式,是所有仪式中最具效力的,而且“物品包装越奢华,想通过消费把意义固定下来的意图就越强烈”。因为物的秩序直接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秩序,例如食物就常常被当做识别等级的媒介,社会等级越复杂,需要的食物种类也就越多。
从这一角度讲,消费行为实际上比消费对象更为重要,因为物品只是仪式的道具,而消费行为才是仪式本身。
《物的社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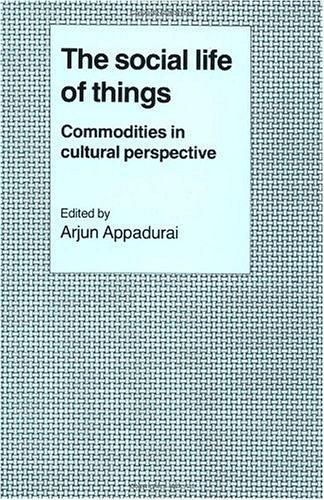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类学家阿帕杜莱主编的这本文集汇集了来自社会史、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探讨了物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流通、消费、使用的历程,并试图回答,物品的价值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变化和消亡的。在阿帕杜莱开来,“商品”并非一种本质属性,而只是物品漫长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当一个物品可以和越来越多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件商品,但任何这种“商品化”都是有期限的。
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莫过于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的《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科普托夫用一种传记的写作手法,回溯了物品“一生”的用途和价值变迁: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苏库族中,棚屋的寿命预期大约是十年,一间典型棚屋的一生是这样的,最初它是多妻制家庭中一位妻子与她的孩子的卧室,随着年龄的增长,棚屋逐渐变成会客室、寡妇的房间或者长子的房间,后来又变成厨房、羊圈或鸡舍——直到最后被白蚁侵蚀,被风霜摧毁。根据不同时期的物理状态,棚屋的用途和价值也不同。
科普托夫还观察到,几乎每个社会都会公开地把一些物品排除在商品化的过程之外,如公共土地、古迹、国家艺术收藏、政治权力象征物、礼器等等。这种对商品化的抵制是通过将物品神圣化,或者特殊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比如非洲的酋长对野猫的皮毛和牙齿拥有特权,泰国国王垄断了白象,英国的君主则对冲上岸的死鲸享有特权等等。
《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凯在《制造中国》开头引用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中的一段:国民党当局以爱国为由出台“封存东洋货”的政策,令小商人林先生苦不堪言,不得不拿自家的金项圈兑换了四百块大洋给党部行贿,才获得了“把东洋标签撕去了就行”的特许。作者从“国货运动”出发,探讨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舶来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先后滋长并互相纠葛的复杂历史。
葛凯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初中国爆发的历次消费抵制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在运动初期,学界和商界往往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短暂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也引发民众不满,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旨在抵制帝国主义的运动,最后大多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
当然,抵制活动也并非一无是处,葛凯认为,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弹性平台”,而历次抵制运动的政治遗产,也渗入到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当中,以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消费行为依然时常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而随着特朗普的就职和全球化的新一轮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和用消费选择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行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集中爆发,这本书或许可能提供一些回应当下问题的思路。
《中国都市消费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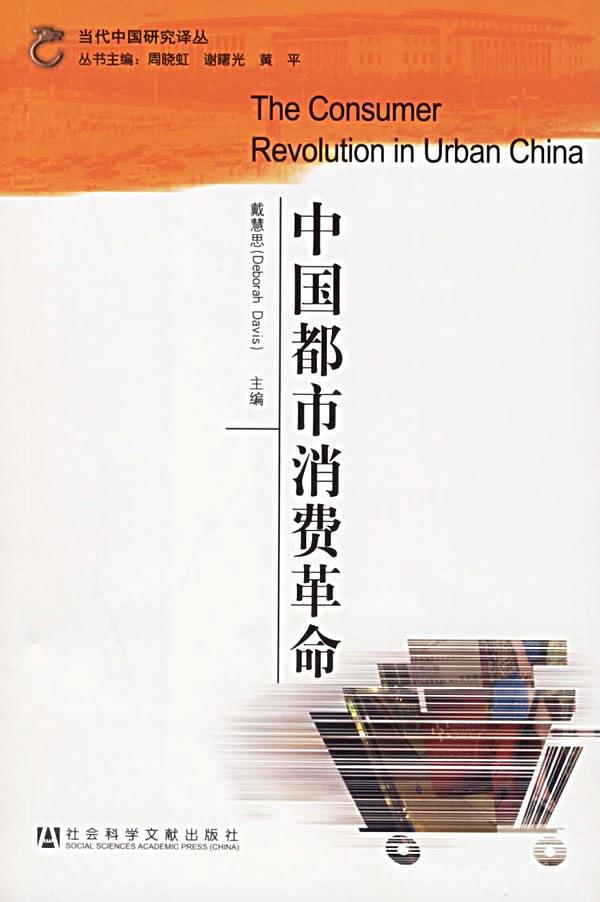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本书是1997年耶鲁大学“当代中国城市的消费者与消费革命”研讨会论文集,由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戴慧思主编。与会的学者从商品房的发展与房地产广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商业化童年,保龄球的友谊之道,生意场上的香烟支配,都市情感咨询热线等日常生活的微观变化,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用主编戴慧思的话说,中国经历了“第二次解放”。
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在《汉堡包与社会空间》一文中对最早进入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厅进行了研究。快餐厅在美国被看作是忙碌者的快速“加油站”,低收入人群的家庭餐馆,以效率和经济实惠获得成功,而当90年代的中国消费者在快餐厅逗留数小时,休息、聊天、读书看报或者庆祝生日,并花掉月收入的1/6的时候,快餐厅显然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和现代化的象征,这种体验对消费者来说太有价值,以至于不能赶时间。
今天看来,这些研究关注的社会现象已经过时,但它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值得思考,那就是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是否产生出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国家-社会,或者国家-个人关系,是否带来了各个层面上的国退民进,物质的丰富、消费的自由又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市民之间的横向连结,从而挑战过去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亦或者,消费产生的自由只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逃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