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朱洁树
《陈涉世家》《荆轲刺秦王》《廉颇与蔺相如》……几乎每个人都从中学课本上读到过《史记》里的篇章,也有不少历史爱好者对《史记》中的故事如数家珍。但在台湾作家杨照看来,读《史记》只读故事是不够的,因为一般读者只选择好看的部分、讲述人物故事的部分来读,而忽略了司马迁写作的用意和整本书结构的完整性。这样,《史记》就变成了半本故事书。杨照2017年在“看理想”平台制作了一套120集的音频节目《史记百讲》,整理了他对《史记》的研究和探索。近日,以音频节目为基础的《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一书也出版了。
在杨照看来,司马迁从来没有要写一本光是“好看”的书,他有着更加广阔深刻的动机和目的。例如,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看到,“天”和命运是不公平的,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常常不一定有坏报,而历史重要的存在理由之一,就是弥补“天”与命运的这种不公,把好坏行为和名声彼此相称地存留下来。又例如,在《吕太后本纪》当中,司马迁看到,吕后掌权的时候是多事之秋,但是她忙于宫斗,反而使得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因祸得福。这样,与当今人们喜爱讨论宫廷的勾心斗角相比,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显示出了他对历史的更高标准和趣味。
这些细节显示出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杨照看到,司马迁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一定会区分“天”和“人”,他讲的“天”指的是庞大的背景,是和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指的是一个人如何思考、选择、作为并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在时间之流当中,司马迁不仅仅会看单一事件,而是看长时段当中人在集体行动里怎样运用权力,这就是“通古今之变”。杨照认为,在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后,方能“成一家之言”。因此,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和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者长远的规律和模式。
在采访中,杨照屡次提到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在杨照成长的年代,恰逢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因此他这一代人阅读了很多教科书以外的相关作品,在治学和讲解的时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也会带有深刻的感情,杨照认为这是台湾知识分子和大陆讲学的差别之处。针对信息爆炸时代的知识焦虑问题,杨照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就像他解读《史记》不注重讲解时间、地点、人物而注重历史解释一样,人们不应该过度关注信息,而是应该关心信息的联结和系统化,将信息转化为真正的知识。

“我觉得我认识了司马迁这个人,而且我真喜欢这个人”
界面文化:关于《史记》的阅读,你曾提到自己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上阮芝生的课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能否谈一谈?
杨照:我们从初中起就会接触到《史记》的选文,一开始是《张释之冯唐列传》,到了高中选得就很多了。高中的时候,我认为一本有价值的书应该从头读到尾,所以第一次动念想要完整地阅读《史记》。但是我碰到的问题是,《史记》很不适合从头读到尾,读得很无聊。我就想,这本书是违背了一本好书的标准吗?到了大学,阮老师每年会选不一样的文章来读,我们当时读的主要是《留侯世家》,期间阮老师一直回头讲《史记》的架构,讲这种架构的用意。
阮老师讲的两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文章笔法,你要了解和想象太史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写而不是用别的方式写,他为什么不啰嗦一点,为什么这里要简省一点,阮老师会不停讲解其中的道理,这也是我后来解读《史记》的时候会用的方法。
《史记》的声音非常灵活,你可以找来任何一篇,算一算句子的长短,你就知道《史记》句子最短一个字,长到十二三个字,而且永远长短错落,可是大部分白话文译者没有这样的美学观念。另外,读《史记》你还能够感受到它文字内部的张力,这很多时候是靠简省产生的。举例来说,白话文是稀释,但是从《史记》中诞生的成语,四个字就会代表好多东西,这样的语言运用起来会有鲜活的感觉。又比如鸿门宴从头到尾只有两三百字,可是却给读的人很深刻的印象,这和司马迁的写作方法是有关系的,这是最有效最精确地运用中文的示范。中国有很多传统经典,有一些是既深又好,读起来很困难,需要看白话文,可是《史记》是既浅又好,只要多花一点点力气,或者看一下白话文作为辅助,千万不要依赖白话文。这样读下来读者都不需要进行分析,就会自然培养出对中文的品味,因为这是太好的中文了。建立了这样的品味,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阮老师讲的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太史公这个人写作的动机和用意。这还经常和文章笔法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留侯世家》的开头,张良暗杀秦始皇失败,流亡的时候在桥上遇到了黄石公。这是很好看的故事,阮老师就会问,张良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只发生了这样的两件事,而且这两件事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非常激烈的行为,一个是莫名其妙碰到的事,为什么司马迁写这一段时间的张良要选这两件事?最后的解答一定会牵涉到太史公写张良的观点或者评价。这是张良人生关键的转折,一开始他想采取的是直接的手段,讨厌秦国就去干掉秦始皇,但是在黄石公的故事之后,张良的思考方式变化了,他认识到目的和手段中间有很多必须考虑的东西。如果是为了直接的目的干嘛要去捡鞋子,可是人生就不是那样简单,这样的思考方式让他避免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避免自我欺骗,认为用鲁莽无效的手段可以达成目标,这样他才从一个韩国贵族成为后来可以帮助刘邦的人。这个故事的背后必须有一个司马迁,有司马迁的道德意识和对人的认知理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并没有每年去上阮老师的课,所以后来他讲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可是就是因为用这种方法读了《留侯世家》,我用大二暑假和大三就把《史记》全部读完了。这样我就有了基本的把握,知道它是一本怎样的书。
界面文化:这是你第一次完整阅读《史记》,那么后来你怎样对《史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杨照:到美国当研究生的时候(注:杨照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我的专业是两汉经学,要读所有汉代相关的史料,这样,我又再读了一次《史记》,也读了《史记会注考证》。我本来是抱着十分功利的想法,想把它也当作史料来读,可是《史记》就不能这样读。《史记》内在有一种光亮,你即使知道某一章和经学没有任何关系,想要读得很快,可你就是做不到,而是会一直被它吸引。当时一大堆汉朝史料我都可以快速看过去,偏偏就在《史记》这样关系不大的书上耗了好久好久。可是第二次读又有了更深的体会,我觉得我认识了司马迁这个人,而且我真喜欢这个人。
尤其是看《报任安书》,知道了司马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任安写回信,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跟我距离有两千年,可是我真的有感动,我会认为我了解司马迁。后来因为做汉代史,接触了很多《史记》相关的史料,我就有一种感觉,比如说我觉得我认识、了解这个人,为什么别人对他的了解和我不一样,是我错了吗?后来我再三看、再三想、再三整理,我只能很骄傲地说,不是我错了,是你们都错了。你们都不了解司马迁,怎么这样看《史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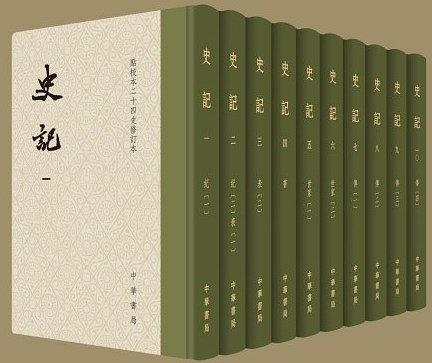
司马迁 著 / 裴骃 集解 / 司马贞 索隐 / 张守节 正义
中华书局 2013-8
界面文化:“你们都错了”指的是什么?
杨照:传统的读法,包括用后来正史纪传体读《史记》,误以为《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或者只写人物的史书,明明就不是。或者用断代史的概念读《史记》,司马迁明明在那么多的文本里告诉我们“究天人之际”这件事,为什么大家都不在意?当然有些书也还是会感动我,像李长之先生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我觉得他很努力地要认识司马迁,也对我有帮助,但他也有一些看法和我从《史记》里看到的依然不一样,这就刺激我去思考。
《史记》里有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太史公自序》每一卷列出了他写什么,读者就可以看清,本纪不是写帝王的,而是借由帝王做断代和纪年来写历史梗概和大事。先有《秦本纪》才有《秦始皇本纪》,两者是分开的,《秦本纪》不是为了要讲秦穆公、秦献公,而是讲秦这个封国的历史。司马迁很明白,光靠写人物很多东西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封禅书》《平准书》这样的“书”,它们是制度史。这些所有加在一起才是《史记》,只有人物,《史记》只是一半。
因为《史记》太庞大,又太好看了,所以大家都选择好看的部分看,这让它实际上变成了半本故事书,它的另外半本被忽略了。这是整本书大的结构,司马迁这个人、他的心理他的精神还在这个大的结构后面。我们不能够读书只读半本。比如说,有人问我,《史记》里最喜欢的是哪一篇,这就是读法上的大问题。《诗经》因为是诗歌总集,是不同来历的放在一起,你可以问喜欢收进来的哪一首,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史记》是完整的结构,“哪一篇你最喜欢”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对我来说任何一篇都必须放在大结构下面才有意义。
界面文化:你还说你对司马迁本人的看法也不一样。
杨照:关于司马迁本人的理解很关键的就是《报任安书》,我们通常就是读它的内容,(知道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和他为写《史记》而忍辱负重的心路),但是了解到《报任安书》的写作背景,明白司马迁到底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才会更加了解司马迁的人格。《报任安书》的来龙去脉是发生了立太子案,宰相叫当时担任太守的任安发兵打太子。如果太子赢了,太子就当皇帝了,那任安不就倒霉了吗?万一把太子打败,皇帝生气了,那也倒霉。所以任安没有发兵。在立太子案解决后,汉武帝把任安下狱,后来判他死刑。审判的过程中,任安写信拜托司马迁帮他。因为司马迁被阉割了,做了中书令,能够进到宫里面,常常在皇帝左右。任安说,你现在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不能因为发达了就忘了老朋友。司马迁把这封信压了快两年,才写了回信。这个时候任安已经要被行刑了,他必须要和任安解释,否则任安就听不到了。他告诉任安,第一,你大错特错,我没有荣华富贵,你以为我现在在皇帝身边,拥有权力,其实我痛苦不堪。第二,我帮不了你,我这个早就该死的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我要把《史记》写完。当年我打抱不平帮李陵说话,实际上已经死过一次了,如果和李陵案一样,皇帝再生气,我就活不下来了,现在《史记》还没有写完,我不得不为了史书而活下去,因此我才选择不救你。
这些内容全部都在《报任安书》的背后,可是我们过去都用传统的读法,不看重、不解释这一部分,只看重本身的内容,没有把相关的背景都放进来。

杨照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1
“没人可以保证没有硬伤,历史解释才是最重要的”
界面文化:除了《史记》,你之前还出过“中国传统经典选读”“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此外你还会开课讲《资本论》《梦的解析》等作品,最近还在讲金庸,你的知识普及涉及了很多面向,这当中会不会遇到出现事实错误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同样也是涉及很多领域的蒋勋就曾经被批评有不少硬伤。
杨照:没有人可以保证没有硬伤。我自己尽可能做到讲到事实的时候不要出问题,但这也很难,比如最近我讲《射雕英雄传》就把贵州讲成了广西,现在已经删掉了。我讲历史的时候没有讲也不爱讲很多人名、地名、时间。这些一般在学校会读到的就是硬伤通常的来源。汉武帝姓什么名什么几岁进宫之类的,很多人倒背如流,我诚实和你讲我背书很不行,但那些不重要。我不愿意这样挑衅,但所谓的“硬伤”到底有多“伤”,这是我们没有好好思考的。事实性的错误因为炫学的关系,人们觉得自己知道这些事情,都记在脑子里了,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搜索,可以查出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有些老师很痛苦,学生上课就拿着手机,上课睡醒过来,看到老师写了一个什么,查一下,就举手给老师说这里那里错了。最后就只学到哪些东西老师讲的和谷歌不一样。What for?
我尽量避免讲的东西查了就有,包括引文这些,我能不讲就不讲,我要讲的是人们在谷歌、百度上查不到的东西。我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交给出版社书稿的每一章都是写着“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第几册第几章”,那个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都在那里。我讲的很多东西是文本上的体会,是联系,是历史解释。历史解释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讲出了荒谬的、不合理的解释才叫作硬伤,可是偏偏这种东西没有人去挑,没有人和我认真讨论。有时候觉得伤心难过,也就接受了。事实的错误是最容易更改的,只要不牵扯到解释。如果犯的错误牵扯到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这才是最麻烦和丢脸的。
解释也是有限度的,最怕的就是过度解释,文章里面没有这个意思,就不要加油添醋,你的解释回到文本之后是要站得住的。我现在在做的中国传统经典,所有文本都在那里,我不是帮大家读书,而是带着你读,告诉你这个本文有点艰难,可以这样理解。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在脑袋里笑自己。讲庄子我有两种方法,讲《说剑》我完全没有讲本文,而是用我的话讲了一次。《逍遥游》《养生主》我会尽力念一段原文,虽然明明知道听众听不懂,但我坚持要念原文,这就是自我的要求,要依照原文,不能够偏离原文作出过度的解释,这是我的态度。
界面文化:不过,即使是批判蒋勋有硬伤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也曾经在采访中谈到,他的总体印象里,港台作家写得比大陆作家优秀。你会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杨照:我不觉得我们水准比较高,而是我们比较有感情。我们当年接触这些内容的时候是有情感的,不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来讲,不是干巴巴的读法。现在很多人在讲“中国人自己的东西”,相当程度上是个口号,是有距离的,还是把它当作知识来看待。可是当年我们去体会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是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所以讲的时候一定会有温度和感情,也许我们(和大陆知识分子)关心和挖掘、彰显的点不大一样。
大部分其他讲《史记》的人很少把司马迁当作那么亲近的人去了解他的情感。对我来说这是有传统的,在我上面有阮老师,他的后面有钱穆,他旁边有我的高中国文老师辛意云。在辛意云的旁边,有你们更加熟悉的蒋勋老师。我们都是同一个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在我们讲文化历史的时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可能这样讲很抽象,但对我来说是真切的感情,如果不能够触碰到那个人,那么讲起来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对庄子的生平知道得非常少,可是通过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孟子也是,我们可以透过孟子这个人去理解他的知识和学问。我会把这种共鸣显现出来。相反的例子是,我知道老子是一个不管在个性还是在思考上都和我有很大差别的人,所以我不会勉强自己去拥抱和解释老子。
界面文化:你曾经说这里有一个“世代”,上至林怀民下至你自己,有点类似大陆198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
杨照:我们成长的基本条件,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我们成长的时候,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中华文化为主的知识的内容突然大爆发。我们这一代相对富裕一点,可以买得起书,但也没有那么有钱,看电影等其他娱乐也没有那么发达,这样的状况下,年轻人想要追寻自我、过不一样的生活,阅读和书一定在选择当中。想要阅读的时候,偏偏又有大量的中国文化的书。那时候虽然我们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但是在1972年以后,又觉得联合国和美国放弃了我们,所以觉得要自立自强,要回到自己的文化根源上,这又带了感情的因素,这和不带感情因素来了解这些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生命上的意义。
我们这一代再往下,到1980年代,经历了原来的中华民族主义到本土化,这个变化是你挡不住的,接下来台湾经济大起飞,这以后虽然还是非常重视教育,可是看待知识的方式改变了,考试的方式改变了,培养我们的知识基础流失了。现在的小孩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读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了,他们的情感就会投射在不同的事物上。所以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代。我还是特例,因为念的又是历史系,所以保留得久一点。

“正因为你那么焦虑,你不能急”
界面文化:你做课堂也做广播,后来做知识付费,有什么不一样吗?
杨照:没有太大不一样,相当一部分是我过去做的事情的合理延伸,我做的音频节目基本上都是我曾经讲过课的。我先为了讲课努力备课,备课到可以讲课的程度,化为讲稿,现在再把讲稿进行整理,化为音频节目。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音频节目和免费的广播节目相比,必须要更能够在内容上说服人家是值得购买的。讲课比较自由,可以咿啊呀啊,突然想到哪里可以跑一匹野马,然后等一下再回来或者不回来了。音频不能这样,音频是非常有结构的,工作人员会一直不断和我检讨结构,这样压力稍微大一些。我比较喜欢讲课,讲课比较自由,而且是对着真人讲话,做音频是对着机器讲话,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
界面文化:知识付费有个问题是买课的人真正从头到尾听完的很少,你会在意有多少人实际上听完了课吗?
杨照:我完全不在意多少人听我讲课,向来我尊重专业和专业分工。我努力负责把节目做出来,平台负责卖,彼此不干扰。平台了解市场,他们给我意见但是不干预我的内容。可是倒过来我一定更了解《史记》。我很少问现在卖得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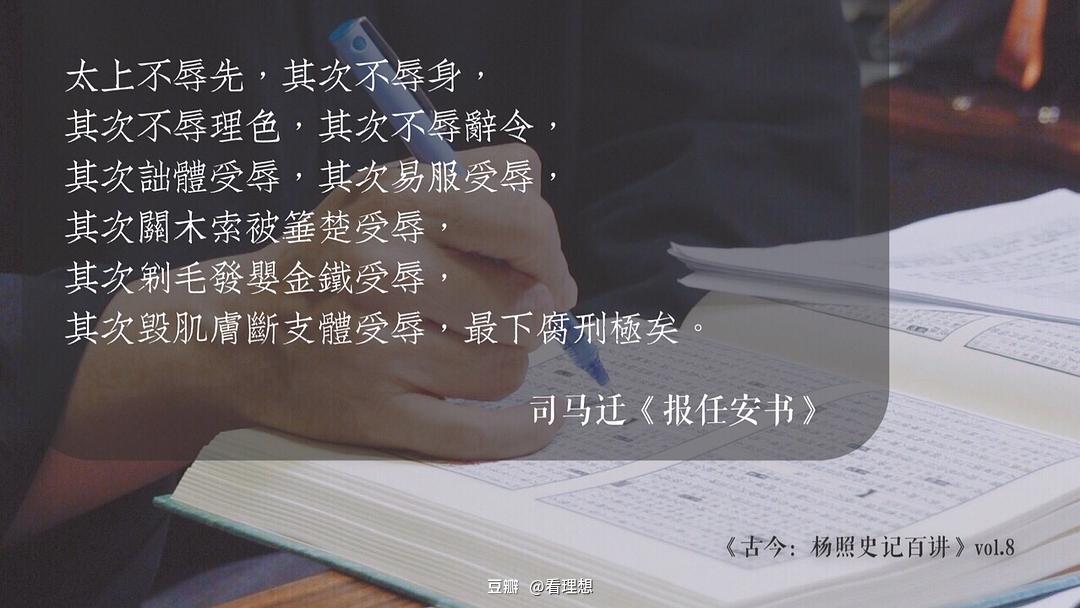
界面文化:你会在意读者是为了获取谈资还是真正为了读懂一本书来买课吗?
杨照:都很好,都无所谓,我最大的目标是让原来不认识司马迁的人认识司马迁,原来不可能接触《史记》的人接触《史记》,出于任何目的都可以。
界面文化:很多知识付费是“X小时教你读完X本书”这种类型的,很多人发现知识付费号称可以缓解知识焦虑,可是实际上越付费越焦虑。你怎么看?
杨照:如果你真的那么焦虑,就应该问自己,这真的可以帮我解决焦虑吗?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信息爆炸,解决这件事,一种方法是帮你把信息浓缩,一本书原来要读三天,现在告诉你说读2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没有办法解决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分类信息。分类信息最基本的问题是你需要什么信息。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不需要信息,尤其是在当下,需要的信息大部分都可以查得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进入到脑子里不需要去查就知道的事情。这个标准要先弄清楚。也就是说,你到底要往自己的脑袋里装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不要往自己脑子里装,比如说在认识中国历史的时候,不要装这么多的年代,年代重点就是帮你解释事件发生的前后,不要前后颠倒因果错乱就行。我们的教育让孩子背诵这么多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个,要往脑袋里装的是让我们能够判别的。一是分类,用怎样分类的架构去理解这个世界。更关键的是品味,同样的领域里有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要听音乐的时候,以前我们要么打开电视听邓丽君、凤飞飞,要么到唱片行里找披头士,这时候我需要判别是邓丽君比较好还是披头士比较好。听什么,这就是品味决定的。那个时代选择有限,现在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品味是什么就更重要了。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真的要解决焦虑,必须要把品味建立起来,可是,建立品味最难用速成的方法。人家告诉你,可是你没有真实的感受,还是要靠自己感受和体验。
我常常说,从目的和手段去思考,我们常常会得到一个悖论,那就是正因为你那么焦虑,你不能急。因为焦虑,人家说什么能够帮助你,你就乱抓。其实,越焦虑越需要慢下来,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犯错,你要慢下来把一些根本的道理弄清楚,培养自己更加深刻的认知和思考的能力。这时候你需要那些讲根本道理的人或者知识。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方法。
界面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怎么才能够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呢?
杨照:要知道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和我原来知道的那些事情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结。如果每一样东西都独立存在,那就是信息。信息要经过系统化,联结在一起才能够变成知识。你认识这里一只猫,那里一只猫,那是信息,你必须把猫给联系在一起成为猫的分类,然后去了解猫这种动物,才变成了你对猫的知识。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依循着这样的逻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