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公共厕所如厕的感受对一些人而言堪称惊心动魄,此处并非指高级商场里的洗手间——地板光洁如镜、灯光亮度恰到好处,甚至会播放音乐遮掩如厕的尴尬声音——而是高速公路边休息区的厕所。进门前要深吸一口气憋好,小心翼翼避开瓷砖地上的不明液体,万分紧张拉开隔间门之时,唯恐坑位上乍现未冲的排泄物或肆意丢弃的垃圾。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周星在他的新书《道在屎溺》中就提到,刺激他开始做厕所研究的诱因,正是在他博士后期间的一次经历。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陌生瑞典留学生穿过大半个北京,就为和他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厕所为什么那么脏?”周星去日本任教后,需要带日本大学生回中国做田野调查,这个问题更加频繁而尖锐地从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口中向他抛出,无从逃避,多少让他有一种羞辱感。
人们倾向于用“素质”解释中国公共厕所的环境问题,但周星认为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也太过归咎于个人因素。他指出,厕所问题反映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历史及文化问题,它投影出了中国在近百年以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高速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粪便以及污秽/洁净的观念经历的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外国旅客的凝视下主动开始“厕所革命,”并且随着中国经济飞跃,将其转化为了服务于人民的运动。厕所的卫生状况在其中成为多方竞逐的意义,它代表了文明阶序的高低,既可能作为殖民者确立自身优越位置的符号,也可能变成后进国家展现国力的手段。
尽管《道在屎溺》一书游离在对厕所系统化与历史化的研究,以及对厕所文明化的倡导性宣言之间,但它还是向读者们提出了难以忽视且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设定为不可言说? 为什么它又在某个时刻一跃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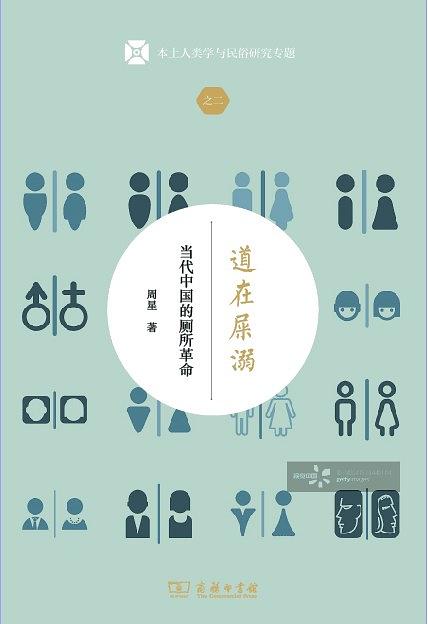
周星 著
商务印书馆 2019-11
在厕所问题上,中国人是别人笔下的“他者”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里,你提到厕所文化是你“宿命般的课题”,你为什么对厕所的研究那么感兴趣?
周星:人类学关心“他者”,同时我们也是别人的“他者“。比如说厕所的问题上,我们就是“他者”。从19世纪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书写,到后来人类学家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要不就不说,只要说到厕所,都是贬低的笔调,普遍认为环境非常肮脏恶劣。哪怕这是如实写,你也会觉得是在贬低。在厕所问题上,我们是别人笔下的“他者”。
在很多年前,我就被这个问题刺激过。记得有一年,北京大学有一个瑞典的留学生,他到中国后受到很大冲击:中国是文明古国,厕所怎么这么脏!他不理解,但是周围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九八几年的时候,中国当时还没有人学人类学。他打听到在社科院有一个学民族学的,就从北大跑过来找我。我不认识他,但他非得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是博士生,就开始思考厕所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讲了几个可能的解释——类似是自我辩护——例如因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能够被再利用,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人们就不会觉得厕所有多脏,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循环的过程。我记得我当时还提了好几个解释。
界面文化:他满意你的解释吗?
周星:他似乎满意,但好像还是不能说服他。我们对海外留学生宣传自己是文明古国,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旅行碰到厕所时,又很难解释。你要说别人特意羞辱你,确实也有这个因素,但你又无法强有力地自我辩护。
作为一个在日本任教的中国学者,我也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经常要向日本的同学或者同事介绍中国、解释中国的现状。刚好日本是一个洁癖国家,日本在厕所革命上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观察中国的时候,厕所问题就特别尖锐。最刺激我的是在日本筑波大学我做博士后那一年,校长在元旦时把各国到筑波大学访问的学生聚在一起举行新年会,会上有一位日本的教授看我是中国人,特意过来跟我说:你们中国厕所特别脏。在元旦酒会上我能怎么办?我只能不卑不亢地说是,这是事实,我不能说不是。再比如我带我的学生到中国实习,我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这些同学解决厕所的问题,不然他们每天都不舒服、不自在,在宾馆不愿出去。他们是过于娇气,或者是故意歧视?也不是,对于他们而言,厕所的环境确实是个困扰。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厕所问题实际上需要在城市化、工业化下系统性地解决,而不是归咎于个人的文明素质或者谁不讲卫生的问题,它需要社会体系的成长。中国在1964年前后,北京胡同里还需要掏粪工,这是我们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落后的或者坏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优劣。随着都市化的成长,国家才能通过程式化的方式大规模建立有效率、合理的、经济的下水道系统,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当然比较先行。
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相当于三四十年前的日本,日本与中国的厕所革命进程非常相似,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在60年代以前,日本的厕所跟中国基本上一样,比如说农村的农民会把城市居民的粪便拿回去做肥料,一开始得拿点农副产品,拿着蔬菜和城里人换,形成固定的交易关系。但是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农民开始用化肥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掏粪了,就一下颠倒过来,城市居民巴不得你赶紧来,甚至我付你钱,让你把粪便运走。而日本的高度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是在60年代才慢慢建立起来,到70年代才完善,但依然还有很多偏僻的地方没有建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结果。从厕所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到了这个时候,厕所革命现在成为一个问题,也成为了我们的使命。只有让人们拥有文明的、有尊严的、舒适的排泄的环境,你才能说现在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
关键是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优雅的部分,对上半身关注的多,对下半身关注少,几乎没人关注。我的人类学同行和社会学同行里没有人做(相关研究),那把它做出来就是我的责任。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关照。在这本书里,我试图阐释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厕所革命,我基本的判断是,厕所问题是中国人想要更好地获得幸福感绕不开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的书中有很大篇幅在叙述中国厕所革命的进程,你觉得它起步的节点是什么时候?它主要的动力又是什么?
周星:动力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凝视,我们变成外人的他者,我们被讲述。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在变革,中国大陆现在的厕所革命源于一个更宽泛视角下的生活革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连续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极大提升,衣食住行都发生极大变化,所以我用“生活革命”这个词。厕所革命这个词最早还不是人类学家提出,而是当时中国建设部搞建筑设计的人提出的。中国老百姓家里的厕所原来是在胡同或四合院里,厕所是公用的。现在一个单元房里要怎么配置厕所,多大的面积是合适的,背后有一个复杂的考量。过去的中国搞民间传统建筑的设计师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要设计现代工业化、大批量建造的单元楼建筑,就绕不开厕所的设计。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穷,没有外汇,靠旅游业吸引外国游客消费,挣点外汇,有外汇我们才能维持基本的国际交流。外宾对我们什么都满意,就厕所不满意,你要查那几年的《参考消息》,关于厕所的抱怨特别多。所以旅游局逼着地方政府,把各个景点的厕所搞好,让观光客的旅游体验更好,所以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旅游局在主导中国厕所革命,就因为有这个传统。这个变化确实有一个外因,但是内在的动机还是更根本的。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到了到21世纪初,国家领导人都重视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需要:我们已经不是为了外国人舒服,是为自己舒服。我们动机已经变了,这是中国社会一个跨越式的成长。
当然,如果说最早的起源,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延续到建国后的“爱国卫生运动”,那时候我们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名字,就要把卫生搞好,厕所的管理与清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是为了搞卫生,现在我们认为人在排泄的时候还是需要尊严感与舒适感的,这种感觉跟过去不完全一样。

界面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对于人的生活是更全面管制的,可是那时候没有对公共厕所进行非常有效的现代化改造,为什么到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反而更关心“厕所革命”呢?
周星:我觉得和人口流动有关,过去公共厕所没有那么重要,那时公厕数量少,但流动人口也特别少。虽然人不方便,但是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全面流动起来,过去的公厕就是在公园有一个,去公园的都是周围市民,农民根本就不进城。人口流动也来自体量庞大的国内旅游业和国际旅游业,游客的体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吃、住、行、玩都还不错,最后厕所不好,前面的印象就打折扣,过去是国际游客不满,现在是国内游客在投诉。为什么投诉?我们人民也跟过去不一样,人民知道了好的厕所是什么样子。以前家里是蹲坑,所以公厕也是蹲坑,没什么区别,但现在人家里是抽水马桶!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认知的变化,中国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正在学习管理一个现代的、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
人民的公共性随着公共厕所的开放与增多而成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公共厕所反映的是大众对公共空间的认知,现在厕所革命不断推进,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大众的公共性发生了改变,更愿意共享与维护公共空间?但为什么同时城市存在大量的封闭的小区,你如何看待中间的矛盾?
周星:中国社会在这点上,还不是一个成熟、开放的公民社会。还是以公共厕所作为例子,出于安全或管理的考虑,中国社会很多小区、机关单位和学校都不会开放自己内部的厕所。比如说一个内急的人在长安街上找厕所,他就没办法找到。大家都会谴责随地大小便的人,但社会没有为他提供好的公共厕所。
其实政府在这方面是有规定有标准的,北京市建委的文件规定了你建多少面积的建筑就一定有多少个厕所,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要设置一个厕所。但是往往在建成以后,人们会故意把按照规定建造的厕所不对外开放,我们把这叫作“隐形的围墙社会”。为什么要讲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现在还是呼吁要加大开放。中国社会确实在很多地方都不够开放,表面上看是城市社会,其实是一个个被围墙隔开的、门卫看守着的“城市里的村庄”。互相开放,大家都好,有资源,为什么不开放?社会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换句话说,公共厕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伴随着公共厕所的开放与增多,我们人民的公共性在成长。公共厕所变得好了,政府管理公厕的能力提高了,认知提高了,人民使用公共厕所的习惯也比以前好了,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公共性的成长。现代社会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界面文化:你似乎觉得世界范围内,厕所文明化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今天讨论的厕所文明化,其实还是由欧美厕所文化主导。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会不会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警惕?
周星:我觉得会有点问题,这个比较复杂。我举个小例子,前年我从青海坐巴士到格尔木,沿途的青海高原上的厕所就不可能有水洗,它的环境就是不容许。理论上,你为政府官员做一个(马桶厕所),做完以后再一锁不让用,技术上可以做到,但实际上成本太大。所以实际上一般沿途的休息区基本都是旱厕。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得强调,按西方的标准做个马桶在那不现实,而且也没有道理。我们不需要统一的标准,应该因地制宜。所以不能够简单地说,某一个尺度是唯一正确的。但旱厕也可以做到卫生,达到卫生且具有良好公共性的标准,不一定说旱厕就一定是很脏的。
当然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说彝族的老乡会认为通过沼气做出的饭是不干净,这涉及到一个抽象的污秽的概念。因为沼气是通过粪便变成的,他们认为拿出来待客或敬神的东西一定需要神圣且洁净,所以不能用沼气做。
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不同文化对厕所、对人的排泄的管理方式不一样,但同时人类学揭示的是人类普遍的东西,我们要承认厕所普遍是在文明化,这与是不是欧美主导没有关系。你非得说厕所文化是欧美起源的,这没必要,我们也不要非得搞一个中国特色的厕所。如果不喜欢欧美的这种文化,你能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也行。我还是相信现代性、都市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我不在乎是不是西方文明或者东方文明,我们古代四大文明再辉煌也没有解决厕所问题,所以还是要问人民自己过得是不是更好了。
垃圾付费象征着一个文明进一步的成长
界面文化:在工业社会之前,由于粪便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正面的作用,其实与排泄物共处其实是常见的事情。但到今天,粪便已经成为完全无用的废弃物,通过厕所的设置与公共卫生系统,我们将粪便完全驱逐出了生活,粪便变得完全不可见了,这种巨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周星:我在日本生活时就觉得他们太极端了,日本人甚至不愿意听到自己大便的声音,也不想让别人听见,所以会在厕所里放音乐。在我们文化逻辑中,我们会贬低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和排出物。人类学会揭示这个人所处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贬低它,并把歧视或者偏见不断弱化,使我们能更自然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我们自己的排泄物。但这挺难的,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这是个更深层的思维结构。

现在一个问题是粪便怎么处理。过去处理粪便,如果你是在乡下,在玉米地里方便也就完了,不会污染,你也不会觉得为难,但是在一座有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怎么处理粪便呢?只能通过工业化处理,但工业化之后人们只是装作看不见了。你将它冲到下水道之后,它往哪里去了呢?北京市市民的粪便就在河北什么地方,这其实还解决得不彻底。
但是这就是工业化处理的结果,这才能够保证大面积人口高度密集化的社区的卫生环境。我们现时代的人只能说这样的处理目前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你很难说它完全没问题。
界面文化:听起来,我们好像只是把这种废弃物转移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周星:没错,这跟垃圾问题是一样。在中国农村社会里面,从家里扫出来的垃圾倒到坑里面,跟猪圈里的粪搅在一起,堆肥就消化掉了。但是现在工业时代产生了塑料,你的垃圾变了,垃圾不是原来的垃圾了,自然不能够把它很快地还原掉,垃圾问题就出现了。
生产的全球化让欧美国家把一些废弃物出口到下游的国家,其实就是将垃圾出口。你进口一个二手车觉得赚了便宜,但是二手车废气排放更严重,废气在你的国家积累,这辆车在拆解的时候又在你的国家变成一堆垃圾,所以进口这种二手货就进口一堆垃圾。在日本街上看不到旧车,全是新车,他们通过把旧车卖给发展中国家来处理垃圾,从垃圾处理成本上看这种做法更合算。
全世界的环境——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城市把环境危机转移到农村,垃圾和粪便没有出国,它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只是那个地方没让你看见而已。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现在我们厕所革命还是不彻底,还是要做到每个人愿意为自己的排泄物、为自己的垃圾负责,负责到我可以为之出钱。现在日本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比如我要扔电冰箱,以前我扔了你还能用,还可以拆解零件,你要给我钱;现在倒过来了,你帮我拆垃圾,我要付给你钱。垃圾付费是一个文明的进一步的成长,拥有越多的物质的人,当然要为环境付出得更多,责任也更大。一个比较贫困的人,他消费的物质就少一点,制造的垃圾也就更少,也就不用为此付出更多。关于粪便和垃圾处理的部分还需要继续讨论,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引起一个后续的讨论。
厕所文学来自私密空间里自然性的凸显
界面文化:你在谈马桶的时候,谈到了便溺、性和生育三者的关系。但现在生育与便溺的联系好像就慢慢消失了,但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讲现代厕所这种私密的公共空间中,暗示会有很多跟情色有关的举动。
周星:关于厕所里的涂鸦文化、情色文学也有很多研究。例如画个女性裸体,人会在里面展示动物性的部分,这有专门的研究。但因为我认为那不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太多。我关注的是更大的、关于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简单地说,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假设是,人的成长是压抑自己的自然性,如果人不压抑自然性,你上街随便见个女孩就抱。文明社会都是和禁欲有关,社会要对私人的欲望、内在动物性进行压制、控制与调整。怎么样控制性?用法律的强制、用羞耻观来控制,人类所有的文化都在使人自然的部分与社会关系能够协调,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私密空间中方便的时候,他自己的自然性就会凸显和表达出来,就产生了所谓的厕所文学。李银河老师的研究有谈到这个部分,这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是在文明压抑下的释放,释放完又衣冠楚楚地打好领带出去,洗手间是一个处理动物性的转换空间。我们的身体是文化、社会和自然的一个混合体,充满了内在的张力。我们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和我们对身体的控制,所以,厕所成为使人可以释放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这一点是好的。
但另一方面,公共性的部分又难以管理,进来可以是私密,但还是要考虑这个空间接下来有其他人要用,所以又要你不能乱写乱画,公共空间难于管理,甚至全世界都没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界面文化:你未来还有针对“生活革命”这个主题的写作计划吗?
周星:其实我一直想写衣、食、住、用、行、厕所、垃圾七个部分,这七块是中国老百姓生活幸福感提升最要紧的事情。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七个部分都在互相联动,倒不一定每一部分都写成书,但因为厕所问题有急迫性,所以我把它单独写出来。这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提供给读者们思考。
我已经针对垃圾写过研究报告,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海之前实施了垃圾分类,北京也马上要进行,而且厕所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以沿用到垃圾上,所以我可能把垃圾放在前面写。
日常生活中有很复杂的社会文化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个社会贡献,就是反歧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通过厕所和垃圾问题建构了歧视链,例如西方人把垃圾出口给我们后,反而瞧不起我们,这就是问题。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学术界一定要对歧视提出批判性的声音,这是学者的公共责任。我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政府对社会成长是有责任的,政府自己也要学习成长:既然商场能开放厕所,当然政府也能开放厕所,这并没有那么困难。政府成长,社会与人民才能成长。从厕所革命里,我们能看到中国社会变成更好的社会的方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