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声 江婧怡
最懂女人心的男导演。
这是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给关锦鹏的定位。女性,是关锦鹏电影最重要的命题,也是他成名的起点。
在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期间,关锦鹏恰巧经历了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兴起。这批从电视台走出来的年轻导演前所未有地关注香港城市本身,以新颖的视角表现他们的周围,突破传统香港电影的叙事。这对关锦鹏而言是一次启蒙。
在许鞍华、谭家明等新浪潮导演手下担任副导、积攒了一定经验后,关锦鹏开始独立执导。从处女作即获金像奖最佳影片和导演提名的《女人心》,到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胭脂扣》和《阮玲玉》,关锦鹏的电影以细腻的心理描绘和对女性形象非他者视角的刻画,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市场凭女性主义电影闯出名堂。
梅艳芳、张曼玉、郑秀文、邱淑贞,这些上世纪著名的香港女星都与关锦鹏紧密关联、彼此成就,关锦鹏这个名字也成为人们回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时的一个符号。
在12月3日大师嘉年华与香港影人文隽的对谈上,关锦鹏分享了他与这些女性角色及女性演员的幕后故事,有一些经验传授,也有一些八卦,更多的还是言语之中对那段他曾置身其中的辉煌年代的怀念。

以下由三声根据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文隽与关锦鹏的部分对话整理:
01 | 张曼玉的眉毛
文隽:在关导你的电影里是可以看到命题的。你的片都是跟性别有关的,像刚刚放的VCR,说你是最懂女人的导演。你对女人的了解,对女性细腻心理的掌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关锦鹏:我1996年拍过一个纪录片《男生女相:中国电影之性别》,纪念华语电影100周年,第一章题目叫“缺席的父亲”。我爸爸在我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这个选择某个程度上跟这有关系。我妈妈比较传统,那个时候的观念是长兄为父,我是大哥,所以我妈妈要把我变成父亲的感觉,带着其他小弟妹。她是个很厉害的人,没有改嫁,一天做两份工作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大。
其实我电影里面的很多女性都很坚毅,哪怕像阮玲玉面对绯闻选择了自杀,我个人不觉得她是因为软弱。阮玲玉在非常短的生命里,无论作为一个演员还是对男人情感的付出,强度都蛮高的。所以对女性角色的描写,除了是我自己的选择以外,从小看着我妈妈怎么作为一个女人生活下去的那种坚毅也给我很大的感触。
文隽:《阮玲玉》有一个新闻,这个角色原本是梅艳芳的,但她当时不想回内地拍戏,后来变成张曼玉。我是过来人,张曼玉80年代是港姐出身的,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花瓶,一个在《警察故事》里面走来走去的傻大姐。真到了有演技的时候,是《不脱袜的人》吧?
关锦鹏:是,那是她第一次拿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但张曼玉一定要记住一个导演,就是王家卫(张曼玉1988年出演王家卫处女作《旺角卡门》)。
文隽:把她完全改变过了。那好导演对待女演员的方法是什么呢?把你的妆卸掉,不要把口红涂得那么重?尤其现在新导演,会遇到有些女明星的经纪人,造型都不让你们管。
关锦鹏:张曼玉投入得很厉害。到上海以前,她有整整两个礼拜,每天从中午到傍晚六七个小时,穿着我们已经做好的旗袍,改她眉毛的形状,穿着高跟鞋,在一面大镜子前就看自己的走路、坐姿。
但我们在香港给她试定妆的时候,张曼玉有一点是拒绝我们美术指导的,就是眉毛不肯剃。她说,有人说眉毛一剃有可能长不回来,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胶水把她的眉毛弄得很细。现在我们看很多30年代的电影、电视剧,那个时代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剃了然后再用眉笔画细细的眉毛。
到上海现场看样片的时候,她也过来看,说就看看我的妆怎么样,看完也不出声就走了。回到饭店,我们开会有人敲门,开门看到她把眉毛给剃掉了。后来拍完戏一段时间,我看到她眉毛还是长回来了,但她说不一样,长回来之后眉毛没那么柔软了。

《阮玲玉》在上海开机前,张曼玉还发生了一个事情。她拍陈可辛《双城故事》的时候,在美国跟一个制片人谈恋爱,后来分手了,但那个男生的现任女朋友找到很多她给那个男生的情书,就勒索张曼玉,你要不给我什么利益,我就把这些信全都丢给娱乐周刊。那时候张曼玉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今天我可以坦白承认这个事情,所以我更同情阮玲玉那个时候。”
一个演员信自己穿上这个服装是那个人,那个很重要。我常常觉得演员是很脆弱的一个职业。导演一切工夫做尽了你还要的是什么?演员在镜头前面给你最好的。当一个演员走入一个角色,她里里外外的感受,包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能放进角色,我觉得张曼玉演的阮玲玉做到了。
02 | 女演员的小纸条
文隽:同样是在上海,拍30年代的女人,《长恨歌》可能是不太成功的例子。《长恨歌》是王安忆的原著改编,还请到郑秀文,她当时在香港是天后了,但这部片的票房不怎么样,郑秀文后来也得忧郁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关锦鹏:你说她是天后是对的,甚至也是票房的保证,她都是跟刘德华、梁朝伟、郑伊健演那种爱情小品。我觉得一个导演碰到一个想改变自己的演员有好也有坏。《长恨歌》就算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因为我没办法让她更放松,这是我的问题。
文隽:我想一个演员能交到关锦鹏手上,不是说商业的保证,不是说就能拿奖、走红地毯,或者是改变她以前给观众的印象。
另外一个例子是邱淑贞的《愈快乐愈堕落》,听说是我的好朋友王晶手把手把她牵到你面前,然后让你帮他改造她的。《愈快乐愈堕落》对很多人来说是1997年回归时挺重要的一部片,我们看着是很有感觉的,还放了王菲的歌。你觉得对邱淑贞的改造成不成功?
关锦鹏:邱淑贞在里面一人分饰两角,都很爱讲电话。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厅,邱淑贞不知道接了谁的电话,在我面前讲了半个小时。其实那时我有点不高兴,问她你经常讲电话?她说“是,我跟叶玉卿好朋友,我们可以一个晚上通宵讲电话。”
其实讲电话的戏不容易演的,《有时跳舞》的时候,梁汉文就因为有一场讲电话的戏演得不好被我换掉了。我觉得邱淑贞聊天的时候就在整合这个角色,她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她自己对香港的感受,都很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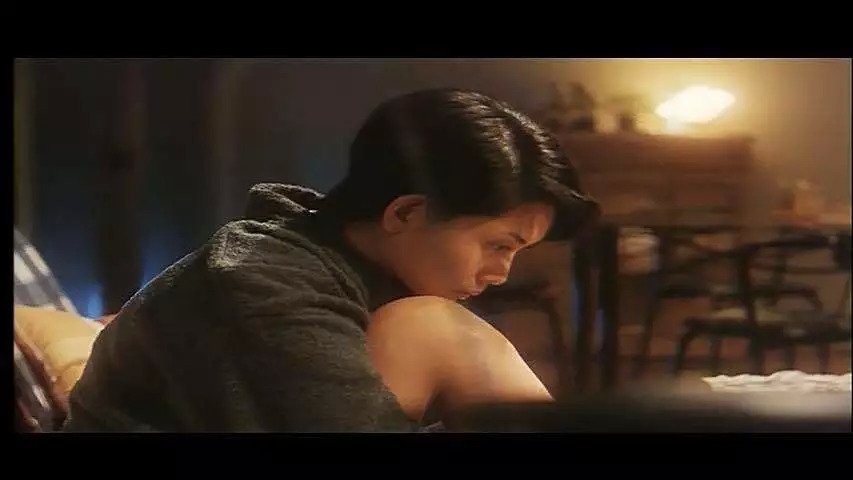
看电影也好,搞剧本、看演员、与演员沟通也好,人物对我来说是最先的。剧本框架有了以后,人物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要先摸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跟演员沟通往往不完全针对剧本,或者这场戏怎么样,到现场,有某一场戏要是突然间卡在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按照剧本里面如花的样子继续。
我会把很多自己的经验很坦白地告诉他,与此同时,梅艳芳也好,张曼玉也好,我说你们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写小纸条让我知道。
文隽:传纸条新导演也学一下,有女演员递纸条,不一定是告诉你房间号。
以前学编剧的时候,师傅说写剧本最重要三个元素,说第一是人物,第二是人物,第三还是人物。一个好的剧本其实都是从人物出发,不是情节来铺垫的。
关锦鹏:人物角色很重要。作为一个导演,你要知道你透过电影最想说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我就是演员》里我跟李冰冰合作,她带来一个剧本,是改编自《双食记》的。这场戏是太太和第三者两个女人吵架,刚开始李冰冰没有拿捏好,我就跟她调整了这个戏。
这个剧本给我的感觉七个字,“哀大莫过于心死”,像《胭脂扣》里面如花对十二少不肯陪她自杀,多年后回来把盒子还他,然后头也不回的那个感觉类似。怎么吵嘴对我来讲不是最好看的戏剧,而是你对这个男人失望,甚至你在第三者身上看到年轻的自己,看到她未来也会碰到这种事,重点不在吵架,而是女人对那个男人心死、悲凉、彻底失望。到头来李冰冰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导演调教一个演员的时候也应该明确。
文隽:现在新导演会遇到强势的演员,那当你不一定认同演员的想法的时候,第一应该是很透彻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第二是要说服演员。现在很多流量,他们永远在演自己,不是在演角色,你要告诉他,现在你在戏里面,你必须要演你的角色,而不是你有多少粉丝。或许你像关导一样学会在他耳边说悄悄话有可能要好一点。
关锦鹏:我还有一个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我碰到的邱刚健也好,林奕华也好,这几位编剧都很细,特别是在对白的处理上。我们都太了解那个人物了,所以很容易发现这句话能不能是这个人物说的。
文隽:要说“人话”。
关锦鹏:对。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留白。现在观众都很聪明,不需要用台词把一部戏铺得满满的。香港人说电视剧我们是吃晚饭的时候看。
文隽:对,电视剧是用来听的。我们写剧本,电视剧是能写的全写出来,电影是能不写就不写出来。人家说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有什么好看的?它就是告诉你留白的学问。你怎么去看梁朝伟跟章子怡的关系?不是我们印象中戏剧里的谈情说爱,都是留白,你去想象。这是现在我们很多电影里没有的。大家看电影看几十年了,还怕他们不明白吗?一点含蓄感也是需要的。
03 | 香港电影的辉煌年代
文隽:刚才介绍你的那个VCR让我回忆起我们香港电影最辉煌的那个年代,当然香港电影融入到我们华语片里面继续辉煌。我们知道香港电影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浪潮,有严浩、许鞍华、徐克一堆这些导演,当时关导还不在这个名单里面,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副导演。
关锦鹏:我在香港念的培正中学,它那时候有剧团,有一年暑假我就参加了,觉得自己好像还蛮喜欢演戏的。小时候看歌舞电影、武侠电影,常常觉得电影里面演得好的演员很打动我,我就想我能不能有一天也当演员,于是报名参加了无线电视的训练班。周润发是我的师兄,他是第三届我是第五届。
我觉得无线电视是给新浪潮导演的一个摇篮。当时无线电视聘了很多在外国读完电影的导演,包括许鞍华、谭家明、严浩、徐克等等。我们那一年在训练班作为电视观众,看到了这一批跟我们小时候看的邵氏、嘉禾那种全都在片场里拍的电影很不一样的片子,那就是新浪潮的前身。
他们那时还是拍电视单元剧,但是是用16厘米来拍,题材上对香港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关注,捕捉到很多香港的城市面貌,有别于我们那时候所看到的邵氏歌舞电影、武侠电影。
文隽:关导跟我们香港另外一个导演王家卫最厉害,什么演员都可以找得到。新导演都很羡慕关导,出道《女人心》就用了最火的周润发。
关锦鹏:你别说我跟王家卫了,其实许鞍华、谭家明他们也是用大演员。因为香港电影工业还是挺商业趋向的,嘉禾、邵氏、新艺城,都允许导演多元化,可以在有些剧本里呈现个人风格,不走一般的商业套路,但指定动作是你要用大演员,哪怕你是拍第一部,也别想用素人。
文隽:我们刚才在后台还在聊,80年代之后香港电影很蓬勃,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最坏是因为有一些黑一点的势力进入了电影圈,那时的演员都在找一些能保护自己的大公司。熟悉香港片的人都知道,成龙洪金宝是嘉禾的,就不会在新艺城看到他们,新艺城的周润发也很少会出现在嘉禾的电影里面。
你最重要的一个片子就是80年代末的《胭脂扣》,梅艳芳跟张国荣一起演的。当时张国荣其实是在新艺城的,与嘉禾的梅艳芳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配搭。

关锦鹏:《胭脂扣》是我签给嘉禾公司以后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胭脂扣》其实原来是香港另外一位新浪潮导演唐基明的,因为剧本拖了很久,原来定的梅艳芳、刘德华、钟楚红,最后只有梅艳芳还留着等这个戏,其他人的档期都没有了。当时十二少的人选,还想过吴启华和刚刚出道的郑伊健。
几乎要决定是吴启华了,有一天梅艳芳跟我说:“阿关要不这样子,我去新艺城拍一个电影,换张国荣过来拍《胭脂扣》。”梅艳芳有一个判断,十二少和如花就应该是张国荣跟她的搭配,所以成就了《胭脂扣》。
文隽: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以前香港电影那么好看?因为八九十年代我们金主是台湾的市场,后来台湾原本靠港片收入的八大院线老板都跑去进好莱坞影片,我们没有了最主要的金主。
香港只有750多万人,市场很小,去年2018年,我们全香港票房只有19个亿,都比不上内地春节档两天的票房。香港全年的票房83%是好莱坞片,华语片只有17%。没有钱当然要退而求其次,有很多的人跑到横店拍电视剧。2001年开始,内地允许我们香港人回去投资电影、拍电影,所以我们香港电影人跑来帮内地的国产片、类型片开放,慢慢变成一年600多个亿的票房。
去年崔永元掀起风暴之后,我们现在很多人日子都不好过,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把一些没本事的、不入流的给淘汰掉。只要你真的有实力的话,你想想,现在5万多个屏幕不放电影放什么?
关锦鹏:我注意到很多香港导演继续和大陆合拍的时候,还是拍很多大型的类型电影。这种电影其实我是没有太大兴趣拍的。《无双》我拍不过庄文强,《扫毒》我拍不过陈木胜。同时我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年轻导演拍的电影,我觉得他们有新浪潮那个时候的感觉,他们真的开始关注这个社会,但这个生活体会始终我hold不住。
《八个女人一台戏》是正好是有投资人找我,我说可以合拍,但是可不可以让我整个电影在香港拍。因为前几年香港政府准备拆掉香港的地标中环大会堂。这个建筑物装载了太多我们香港人的记忆,我们可以一天四部电影待在大会堂里面。这个戏是因为这个初衷。

文隽:对于我们看几十年港片,看着关锦鹏导演过来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关导给自己的一个礼物。里面有很多符号,比如说《胭脂扣》的电车,甘国亮演的戏剧导演就是许鞍华。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认认真真拍一个关锦鹏风格的片了。这部戏里面有一些舞台剧里面跟外面的情节,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关锦鹏:很多人看我的电影说,你老爱用镜子,你老爱用反光的东西,搞不好就是在美学上面下判断说,我的电影没有那么实在。
我个人喜欢的电影不是那种老老实实去讲故事的,我觉得拍电影做导演最有趣、最过瘾的地方就是虚实。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