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精是一种什么精?”
这是一个来自 2018 年的问题。当时,歪楼的王二啧写了一篇文章,全方位解析了一种潜伏于互联网的神秘生物:杠精。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有些无聊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已经见识到了这种生物的威力。以至于当微博推出“全平台禁言三天”这样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策略时,不少用户为之鼓掌,并认为这将是整治评论区杠精的有效手段。
天下苦杠精久矣。
在这样的论调中,杠精成功化身为互联网世界的过街老鼠,成为人人喊打的存在。在网络上,《如何气死杠精》、《如何远离杠精》、《如何鉴别杠精》这样的文章层出不穷,将杠精这个群体描述为一群无礼、无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他人增添不痛快的人。
在这种想象,或者说夸张中,情绪很自然地就会被调动起来。一轮又一轮地反杠精运动,把杠精变成了一个聚光灯下的一个小丑,人们手中的臭鸡蛋有了去处,看着杠精被鸡蛋摔花的脸,每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

杠精必须死。
那么,这一切有什么问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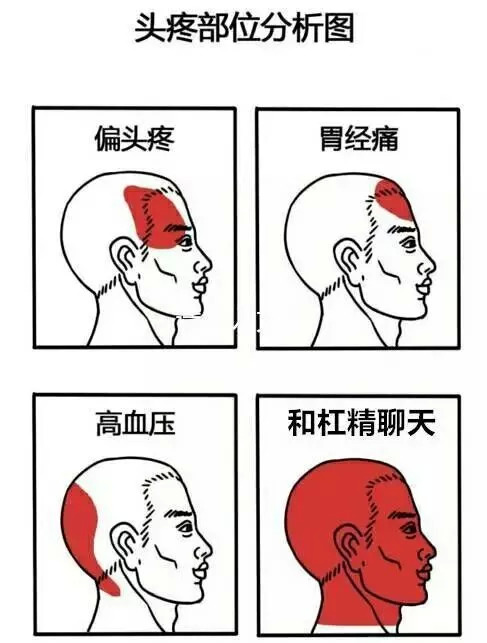
1593 年,在一个德国小镇诺德林根,一位名为玛丽亚·霍尔的妇女被他人指控为“使用巫术的女巫”,随即被教廷逮捕。之后,玛丽亚·霍尔经历了 62 轮的审讯,在每次审讯中,她都坚持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妇女,平日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营她的旅馆。最后,控告者只好选择放弃,放走了玛丽亚·霍尔。
玛丽亚·霍尔活了下来,她是幸运的,比起 15 世纪到 18 世纪期间,另外 35000 名以“猎巫运动”之名被活活烧死的人而言,她的幸运近乎是个奇迹。
对现代人而言,煞有介事地审判女巫,并将人活活烧死这种事情,显得十分荒唐愚昧。但对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件事相当有意义。在中世纪当权者的手中,猎巫是糅合了宗教和政治色彩的一种镇压异见的武器,但在当时的普罗大众心里,更广泛的认知不过是:女巫必须死。
这便是我的担心。

我当然不是说人们会严重到将“杠精”们抓起来烤掉,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对于“杠精”的情感,似乎正在转变为人们对“女巫”的情感。
在舆论场中,人们对“杠精”没有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这使得“杠精”一词很容易被泛化和滥用。如果“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算杠精言论,“我就不是这样”是否也应该算杠精言论?那么,“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况”这样的发言呢?
在一个人看来属于杠精言论的发言,在另一个人心里可能并不算杠精,但依赖于“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样的准绳,则一切异议就都有了落入“杠精”骂名的风险。接下来事态就会发展到当下这一步:发言者在发言前必须小心翼翼地打上“非杠”,以努力撇清自己与“杠精”的关系。
事到如今,杠精这个词汇的内涵已经逐渐偏离了最初时的语境,因为词汇无法孤立存在,“杠精”一词同样包含了一整套叙事,它描绘出了一个不讲理、认知有限而又渴望寻求存在感的形象,代表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和一种偏隘的世界观,它带上了天然的“恶”的光环,成为讨论中不可出现的禁忌。
一旦在讨论中,一方给另一方扣上“杠精”的名号,一切对话就会迅速转向对“杠精”身份的辩解,前者会带有天然的正义感和审判视角,而后者,则需要拼尽全力来洗脱“杠精”的罪名。至于原本讨论的事件本身,则会迅速淡出为一个模糊的背景板,整个对话因为“杠精”一词的介入,演变为了一场微型的“猎巫审判”——哦不,是“猎杠审判”。

这是在为杠精洗地?
如果你此时冒出这样的念头,或许你就落入了另一个陷阱。毕竟,这就是杠精话语滥用后的结果之一,一种新的对立。这种对立将整个言论空间划分为两种潜在的发言者:杠精和非杠精,在这种前提下,发言者因害怕被划入“杠精”行列而产生的自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议事空间的隐性压迫。
当下的网络言论空间正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它看似能容下所有的观点,但事实上,它的尖锐和冲突要远多于共识和包容。如果“杠精”一词成为讨论中战无不胜的武器,那么言论的分裂只会被进一步加剧,无差别地对异见者贴上“杠精”的标签,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议事,不相信中间地带,事实上就是一种“杠精”思维。

杠精阻碍议事,破坏讨论,不具备叙事逻辑,“杠精言论”不利于公共议事空间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另一边在面对异议时拒绝倾听,不去考量发言者的认知局限,否定一切追问,否定复杂,将“杠精”发展为一个无差别攻击的标签,显然不是减少杠精言论的有效方法。这就和“全平台禁言三天”一样,它看似痛快,也确实是一种严惩,但推崇这种带有暴力和绝对色彩的惩治,既无法让“杠精”直到自己错在哪里,更无法让他们服气,问题自然就无法解决。
“杠精”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议事的一种消极姿态,而这个词汇,原本应该用以抵御无逻辑的、无意义的、单纯以宣泄为目的的言论出现在公共议事空间中,并最终让整个言论氛围向善。但若是把它推向另一个极端,把所有讨论的可能都否定掉,变成一种对不同意见的彻底拒绝,公共议事空间只会被逐渐瓦解,到那时,所有人都只能困在闭合的山洞里,一遍遍听着自己的回音。

当代著名的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启蒙》里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做一些关于“语言、心智和人性”的公开演讲,在某一次演讲中,他解释了关于“精神”的问题,他说当今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精神生活是由大脑组织的活动方式建构而成的。随后,听众席上有人举手发问,发问者是一位年轻的女生。
接过话筒,这位女生问到:“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史蒂芬·平克在书中写道:“这个学生提问的语气十分真诚,这表明她没有自杀倾向,也不是在讽刺挖苦,而是真心想要了解:当科学的发展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仰尽悉破除之后,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他说:“这个世界只有愚蠢的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
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互联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将这位女生的问题视为“杠精言论”。假如在网络世界,在无法注视对方的双眼,也无法聆听对方的口气的对话中,在面对异议和质疑时,人们不再诉诸理智和逻辑,而是争先恐后地用“杠精”相互攻讦,那么那些真正好奇而真诚的发问,也将在语言暴力中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最终,那便是“杠精”的胜利。
不要把世界让给“杠精”。

来源:界面歪研社
原标题:你凭什么说我是杠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