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玩《模拟人生》是在一个通宵派对上。那是在我朋友汉娜的家里,午夜时分,我们三个11岁的孩子蜷缩在老旧笨重的电脑显示器前,凝视着屏幕里的小房子,里面住着一群小人儿,在游戏世界的日常工作中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轮流送他们去上班,更换房间壁纸,命令他们把脏盘子放进洗碗机。我们贪婪地翻阅着游戏的家具目录,给他们买了一台电视机、一个漂亮的沙发、一个搅拌机。最让人兴奋的是,我们发现可以让《模拟人生》中的角色“接吻”(我们很失望地发现他们并不能进一步深入——这要在《模拟人生2》才能实现)。
许多人都玩过《模拟人生》。这款游戏如今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包括各种资料片和衍生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销量超过2亿,能与之匹敌的或许只有俄罗斯方块了。《模拟人生》的游戏制作人威尔·莱特(Will Wright)很早就意识到这款游戏吸引了大量女性玩家。在过去,“大量女性玩家”指的是大约5%的用户群,而在《模拟人生》中,女性真正占到了大多数。我有一个朋友的母亲非常沉迷于《模拟人生》,以至于会几个星期都忘记打扫房间。

颇为窘迫的是,我与小伙伴曾经将精心设计的《哈利·波特》和《吸血鬼猎人巴菲》同人剧情塞进了《模拟人生2》里面。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经模仿《老友记》的演员阵容,并用这些游戏角色演绎了比原作最后一季更加完美的剧情。我个人对《模拟人生》系列游戏非常痴迷,以至于当2009年《模拟人生3》问世时,我不得不远离游戏,以防止学位考试不及格。在后来的一次课堂上,一位讲师看到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了《模拟人生》,他与我分享了《模拟人生》里一个非常常见的恶趣味:删除泳池的梯子,把游戏中的角色溺死在水池里。
电子游戏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其控制力——不仅仅是控制角色的动作,更重要的是理解其内在的系统和规则,并让它们服从你的意志。《模拟人生》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控制生活本身的幻想,包括所有在现实世界中难以预测的东西——房屋装修、职业、家庭和人际关系。《模拟人生》的游戏规则本质上是说,如果你努力工作,做你应该做的每件事——找工作、买房子、通过晋升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幸福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一种诱人的资本主义幻想——即使事情进展不顺利,你也可以输入作弊码“motherlode”,让自己大赚一笔。
在《模拟人生》问世的20年里,它分散了我们对家庭作业和家务(包括虚拟家庭作业和家务)的注意力。在这20年中,《模拟人生》系列不断发展壮大,其底层的人工智能代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初的角色只是简单的机器人,后来他们有了对食物、厕所和金钱的基本需求,甚至还发展出了个性、抱负和弱点。他们甚至还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从《模拟人生2》开始,你可以按下一个按钮,接下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模拟角色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发展,自己决定诸如要和谁约会,要花多长时间泡澡等各种选择。


《模拟人生》中我最喜欢的便是让游戏中的角色自由发展,有时这种发展会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把人吓一跳。当我还是个青少年时,我在《模拟人生》中模拟了自己的家庭,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结果相当真实——爸爸冲我那邋遢的弟弟大喊大叫,让他从沙发上下来,我在厨房里和妈妈吵架,之后疯狂写日记直到深夜——我开始怀疑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场别人的电子游戏。
《模拟人生》能模拟的东西越来越多,可以庆祝生日,可以订婚,可以举办新年派对,也可以拥有宠物,建造房子,甚至接触美人鱼。你能想到《模拟人生》的粉丝都在做什么吗?庞大的《模拟人生》社区包罗万象,有人会在游戏中建造完美的豪宅,也有人在YouTube上通过《模拟人生》导演生活肥皂剧——甚至包括各种各样露骨的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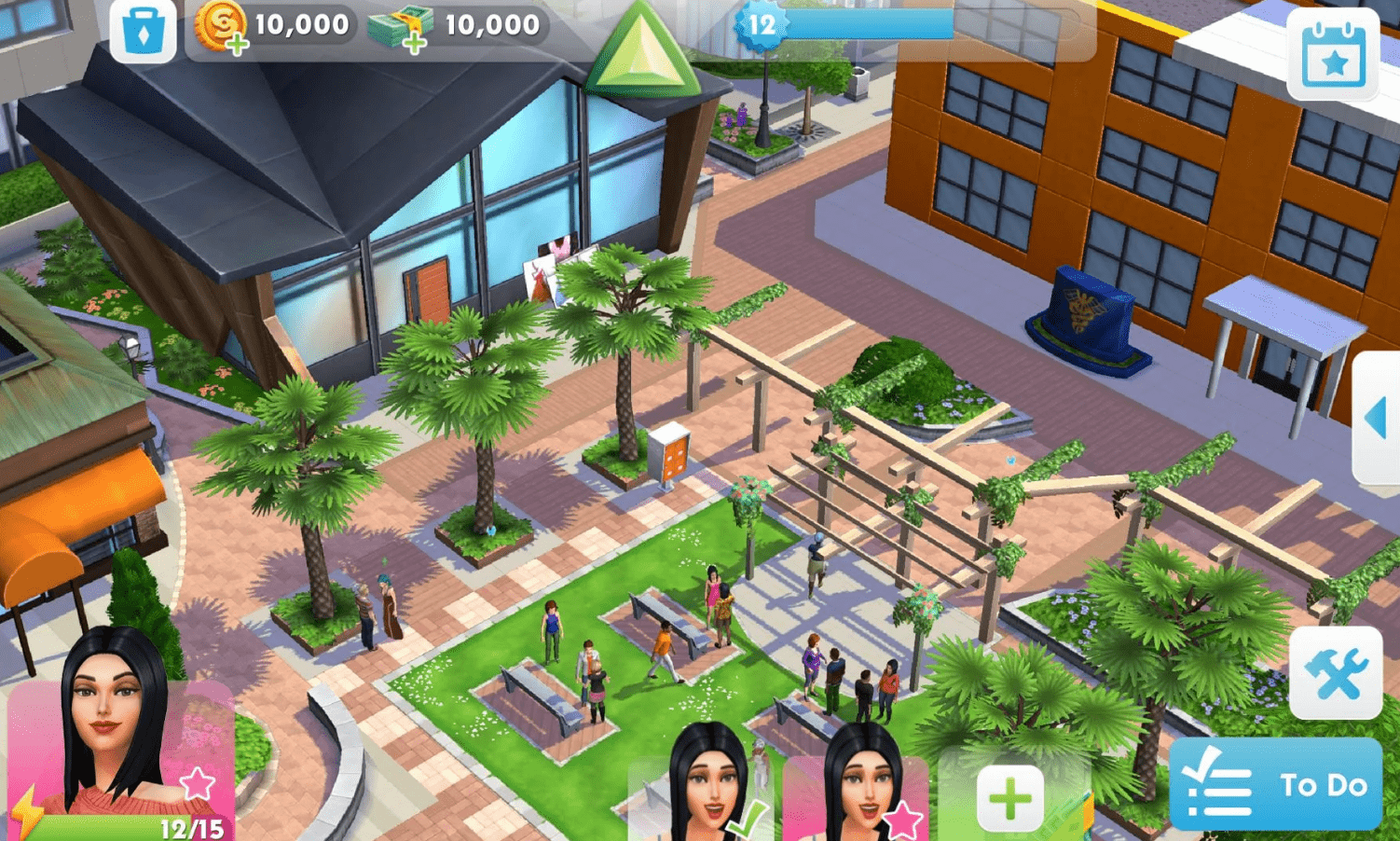
《模拟人生》不仅是数字时代的玩偶屋。在很多方面,《模拟人生》也是一个后文化时代,由爱和金钱驱动,没有种族偏见,没有性别和薪酬差距的乌托邦。《模拟人生》的同性婚姻要比现实世界早好些年。随着《模拟人生》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智能化,玩家不仅可以在其中体验时尚和家居装饰,还能见识人性与动机。从自身的性别身份,到复杂的家庭动态,甚至还可以把所有的希腊诸神放在一间房子里举办派对——玩家可以用《模拟人生》探索一切他们想到的东西。
有时我会想,《模拟人生》如果更加接近现实生活——背负沉重的助学贷款,没有梦想的家,只有昂贵租金的小公寓,倾心的爱人永远不会爱你,工作多年却得不到应有的晋升——会怎样?但是这种现实版《模拟人生》玩起来肯定会很郁闷,因为现在的《模拟人生》让生活中的日常考验、劳动和仪式变得有趣,变得充满了可能性,这难道不是一款电子游戏应有的价值吗?
本文作者Keza MacDonald是《卫报》游戏编辑。
(翻译:张海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