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二战结束已逾七十载,纳粹罪行早已得到盖棺定论,但大屠杀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影依然游荡于人世间,在强调自主担责、不游则沉(swim or sink)的当下社会中尤为如此。英国社会理论学家齐格蒙·鲍曼警告我们,犹太人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步入歧途的必然产物,这种为了某个目标而牺牲掉部分群体的观念与做法是很有可能重现的。
鲍曼所言的“宏大社会设计”,是如何一方面向上承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方面向下呼应了现代官僚体系的?借由梳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变与其在不同时代的应用,我们试图在社会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上揭开这一话题的冰山一角。
“适者生存”:达尔文进化论的不当挪用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20世纪思想史》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叙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史。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作者查尔斯·达尔文从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于1831年12月前往南美洲从事自然调查研究,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后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了“物竞天择”的概念,正式开创了演化生物学的学科。

达尔文或许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理论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领域掀起巨浪。作为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首个重要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知识界都获得大批拥趸,人类社会的等级划分和冷酷战争仿佛得到了科学论证,这为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无疑是这股浪潮下最为灾难性的后果。
《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的思想首先在美国社科学界引起了注意。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等社会学家都以达尔文提出的“生存竞争”概念为出发点激辩过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等级制的问题。
萨姆纳认为,达尔文为人类社会的深层逻辑提供了一种一锤定音的解释,即自由放任经济是客观规律使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观点更是被封为圭臬),另一些学者则指出达尔文的思想论证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合法性。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理论,主要还是拜英国政治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赐。事实上,“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如雷贯耳的词,不是达尔文的原话,而是斯宾塞的发明,后者敏锐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可以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在斯宾塞看来,穷人理应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他在《社会学研究》中阐述了这一理论,而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帮助社会学建立起了独立学科的地位——沃森认为,这或许是因为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基础让社会学更像是一门“科学”了。
沃森指出,当进化论被用来阐释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它看起来就和尼采的哲学思想非常相似了。尼采认为,所有历史都是作为文明基石的领导集团和被领导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斗争。前者被他称为“雅利安人”(Aryans),他们生来高贵,注定要成为征服者,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下层社会,对其生杀予夺。“不管这对某些个体的影响如何恶劣,它听上去与进化、丛林法则以及为了人类整体利益而以‘适者生存’为准则的自然选择是非常相似的,”沃森写道,“但领导能力、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这些本身并不是进化论对‘适者’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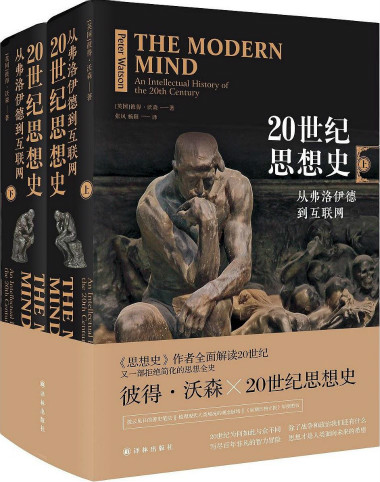
【英】彼得·沃森 著 张凤、杨阳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在达尔文的论述中,“适者”仅仅指的是那些繁殖能力最强、后代最多的种群;但当进化论进入社科领域,它却以“科学”为名为人为决定的种族差异、阶级区隔和社会不公提供了借口。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迅速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支持强大的国家政权、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这让他得到了纳粹主义者的评价。法国社会学家克莱芒丝·奥古斯特·罗耶(Clemence August Royer)在其著作《人类与社会起源》中也采取了强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他坚信“雅利安人”是优于其他种族的群体,为了本族利益,与其他低等种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特别是优生学的发展。法国人类学家、优生学理论家乔治·瓦谢·德·拉普热(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将欧洲人分为三大种族群体:欧洲人身材高大,皮肤苍白,头颅较长(长头);阿尔卑斯人身材较矮,皮肤颜色较深,头颅较短(短头);地中海人虽然有较长的头颅,但身材矮于阿尔卑斯人,肤色也更深。拉普热认为民主就是灾难,长头人种在欧洲的比例不断下降,短头人种将统治世界。它还主张应该向劣等种族免费提供酒,这样他们就能纵欲无度,自相残杀。
持类似激进观点的学者在大西洋两岸还有很多,而优生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则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Rancis Galton)。他于1904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优生学的本质在于“劣等”和“高等”是有客观衡量标准的。当时欧洲人口的下降(部分是因为移民美国)、犯罪率的升高和无法忽视的残疾群体无疑放大了某种社会危机感,让人们求助于优生学来提高“适者”(或许应该直接了当地说身心健全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比例。
于是从1905年到1912年,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成立优生学相关研究机构,一些当时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在当下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比如牛津大学教授F.H.布拉德利曾建议,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处死,他们的孩子也不例外;美国印第安纳州于190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州立监狱内“精神错乱的、愚蠢的和低能的”犯人或“被定罪的强奸犯”实行绝育手术。
沃森指出,欧洲范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奥地利得到了最为热烈的欢迎,且在政治层面得到了贯彻实践。该国政治家一方面煽动民粹主义,主张将权力交给远离腐败城市的“纯洁”农民;另一方面推行反犹主义,把犹太人定位为堕落的化身。鉴于阿道夫·希特勒在1907年前往维也纳就读艺术学院,奥地利这种恶毒的时代氛围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轻的希特勒,并为他日后掌权德国,发动犹太人大屠杀奠定了智识基础。
当人成为数字,我们失去了什么?
二战结束已逾七十载,纳粹罪行早已得到盖棺定论,但齐格蒙·鲍曼警告我们不应将犹太人大屠杀仅仅视作一个德国问题,或一个已经翻篇的历史教训。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理性社会失衡的结果,它本身就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

【英】齐格蒙·鲍曼 著 杨渝东、史建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历史学者萨拉·戈尔顿(Sarah Gordon)在《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一书中提出犹太人大屠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之所以会出现,取决于这样四个因素:纳粹分子激进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变成了一个强大集权国家的实际政策;这个国家有着庞大高效的官僚机器;以及国家构建的“紧急状态”叙事允许这个国家所控制的政府和官僚体系越过一些在和平时代不可能越过的障碍。鲍曼认为,如果说纳粹分子的上台及其激进的反犹主义是个历史的偶然,那剩下的两个因素则是完全“正常”,恒久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他这样描述现代社会大屠杀发生的要素:宏伟的社会设计、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以及社会瘫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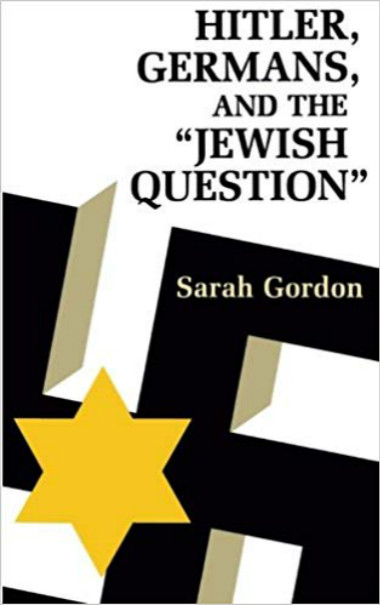
Sarah Gor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之所以说大屠杀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是因为它是按照现代社会标准——理性、有计划、科学信息化、专门化、被有效管理、协调一致——所推动的。鲍曼认为,现代大屠杀的标志性特点是其绝对的规模性,而这基于某种绝对理性的计算。它不仅仅只是激情式地除去异类或敌人,也就是说大屠杀不是目的,而是社会工程的手段,“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宏伟设计。”鲍曼将现代文化比作一种园艺文化,它对自生自发性有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人工的秩序天然是更优越、更值得追求的,是获得理想生活和最佳人类生存环境的必要前提。为此,人类可以且应该改造社会,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则势必要对社会中的一切人事做出分类,将“无用者”当作杂草般除去。
“大屠杀的一个、但可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构成因素:典型现代的、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制度化、产生、维持和再生产的心态。”鲍曼认为,现代官僚体系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建立在受工具理性支配的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之上。这其中有两个过程至关重要:一个是细致的劳动分工;另一个是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
在现代官僚体系中,每个层级的官员都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从事各不相同的具体工作,这拉开了每个人手头的任务和一个整体机构的任务之间的距离,导致大多数人对他们行动的后果至多只有抽象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官员只能通过自身的行动、技术的有效性来判断某个任务是否成功,“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官僚体系的管理对象被极大地非人化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简化为了一个数字,以一种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被呈现。
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分子自然是现代史上最恶劣的现代国家官僚体系失序案例之一,然而技术官僚的弊端在当代全球政治也比比皆是。美国政治学家、宾夕法尼亚州莱康明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指出,在乎数字而非人民是技术官僚的巨大弱点,他们往往期待通过较小的投入来迅速获得想要的结果,却很少关心人在此过程中将付出什么。而疏离人民的官员的决策,哪怕是聪明者做出的高明经济决策,也不会被群众所理解。
在法国,几个世纪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岗位被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把持的局面让民众厌倦,这些有着优秀出身的公务员往往被认为是缺乏常识和人文精神的技术官僚,他们倾向于提出陈旧的国家主义的解决措施,一如他们从国家那里受到的训练一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希拉克的第一任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优秀毕业生因冷酷而技术官僚的领导风格成为当代法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理,也成了其政党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遭受挫败的最大原因。罗斯金举的另一个案例是欧盟宪法在2005年和2008年两度失败。他认为,欧盟宪法由政治和法律精英起草,成稿的复杂性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因此从民众那里获得的只有愤怒、拒绝和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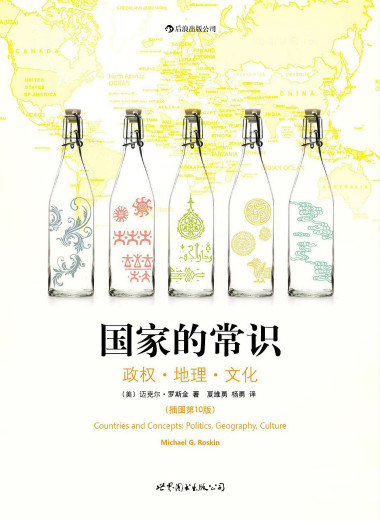
【美】迈克尔·罗斯金 著 夏维勇、杨勇 译
后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年4月
推动大屠杀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瘫痪,即“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国家显著地凌驾于社会之上”。鲍曼认为,现代的条件允许国家用政治命令和管理代替全部的社会和经济控制网络,这隐隐为大屠杀埋下伏笔:“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消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谐睦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回顾历史,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谓一份黑暗遗产,是后世对达尔文生物学发现的不当挪用;而这一概念至今仍时不时在公共舆论中重现的现实警告我们,将之视作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某个历史教训还为时尚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此并非没有反思。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看来,“基本的道德平等”——即“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无论他们在种族、性别和居住地等方面会有哪些差异”——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种道德进步,它为反抗不平等提供了一种与尼采和社达主义者截然相反的,且值得我们所有人牢记在心的论据:社会中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有控制权,这是不可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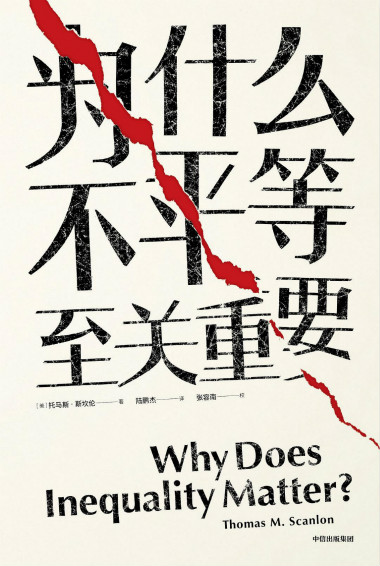
【美】托马斯·斯坎伦 著 陆鹏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