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那样对毒品的看法前后发生巨变。赫胥黎于1894年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家庭,目睹了20世纪初的“禁毒战争”。当时数年内禁止了两种极为流行的麻醉品:可卡因——德国制药公司Merck曾用其治疗吗啡成瘾;海洛因——由德国Bayer制药公司出于相同治疗目的出售。
双重禁令的发生并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客和报纸极力渲染“毒品朋友”(瘾君子)的负面形象,据称“他们”因使用可卡因、海洛因和某些安非他命而被“德国的发明所奴役”,这波舆论风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汤姆·麦泽(Thom Metzer)的著作《海洛因的诞生和被妖魔化的毒品朋友》。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优生学”言论盛行(既来自阿道夫·希特勒,也来自赫胥黎的哥哥朱利安,后者是臭名昭著的优生主义者),阿道司·赫胥黎想象政府机构使用毒品作为独裁控制的邪恶手段。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的毒品“苏麻”被发放给民众,使他们高兴和满足(“完美地综合了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优点。”),该书还多次提到墨斯卡灵(迷幻药,当时赫胥黎并没有亲自尝试过,但显然不赞成),使他的角色“琳达”变得愚蠢且易于呕吐。
赫胥黎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写道,“明天的专政将剥夺人们的自由,但作为交换,仍会带给他们一种真实的、主观经验式的幸福,那是一种化学作用……追求幸福是人类的传统权利之一,不幸的是,实现幸福可能与人类的另一项权利相矛盾,即自由。”在赫胥黎年轻时,成瘾性毒品与政治紧密关联,而在政客和主流媒体看来,对可卡因或海洛因的提倡在很多方面与德国纳粹相关。
后来,在1955年的平安夜,即《美丽新世界》出版23年之后,赫胥黎第一次服用了LSD致幻剂。一切都变了,他爱上了它。这启发他创作了《知觉之门》,并把这种药物介绍给蒂莫西·利里,后者极力提倡精神致幻药物。最终,赫胥黎和利里的嬉皮政治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和越南战争),很大原因也是他使用此类毒品的美妙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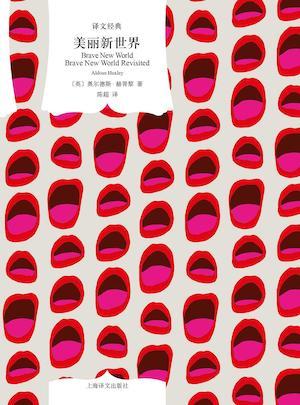
[英]赫胥黎 著 陈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6
在赫胥黎的小说《岛》中,人们居住在一个乌托邦(而不是《美丽新世界》中的反乌托邦)理想社会,通过服用精神药物来获得宁静和相互理解。在《美丽新世界》中,毒品是政治控制的手段,而在《岛》中,毒品是“良药”。
赫胥黎起初视毒品为独裁控制的手段,后来视之为逃脱政治文化压制的方式,如何解释这种转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为何毒品一度被普遍鄙视,后来又为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权威所推崇?为何诸如可卡因等毒品曾流行近十年,而后销声匿迹,直到几十年后重又出现?特别是,药物和毒品如何被用以强调或打破文化边界?其答案影响到了现代历史的几乎各个方面。
药物和毒品为观察我们所处的文化提供了有效的窗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流行的药物和毒品在不断变化,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可卡因和海洛因、到五六十年代的LSD和巴比妥酸盐、到八十年代的摇头丸和(再一次的)可卡因,再到当今诸如阿德拉、莫达非尼和更厉害的类似药物。人们在特定时期服用的药物和毒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或者说,人们发明并服用符合当时文化需求的药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药物和毒品的选择部分反映了每一代人最大的欲望与缺失。因此,药品史指向了有待回答的文化问题,无论那是对精神极限的渴求,还是为了生产力、娱乐、追求标新立异或自由。
需要明确,这项历史性的调研主要关注精神药物。它包括LSD、可卡因、海洛因、摇头丸、巴比妥酸盐、抗焦虑药物、鸦片类药物、阿德拉等,但不包括例如布洛芬等抗炎药、或扑热息痛等止痛药,后两种药物并不改变人的心智,因此在进行社会文化分析时作用不大。
在此讨论的毒品也触及了法律(尽管某些毒品是非法的,但不排除它们成为了某些文化现象的核心)和阶级(下层阶级所使用的药品对文化的影响并不亚于上层阶级青睐的药品,尽管后者往往得到了更好的记载并被后世认为“更具文化影响力”)的界限。最后,此处讨论的毒品及药物类别涉及疗愈、医学和娱乐用途。
要了解我们如何创造和普及毒品以适应我们的文化,请想一想可卡因。可卡因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又在英国1920年通过的《危险药品法案》中被宣告非法(以及1922年美国的《麻醉药品进出口法案》)。据“沉醉毒品的理论家”、《被忽略的嗑药文化史》(Out of It: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toxication)一书作者斯图尔特·沃尔顿称,可卡因在19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很大原因是“它强烈的欣快感”。沃尔顿告诉我,“(可卡因)曾推进对维多利亚时代规范的抵制文化,抛弃了严格的礼节,转向一种‘新艺术运动’时代新兴的‘怎样都好’的社会自由主义(态度),并推动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兴起。”
二战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被抛弃,社会自由主义风行,可卡因就在欧美的白人文化中过时了。直到1980年代,可卡因由于新的文化问题再次出现。沃尔顿解释道,“它在1980年代的回归,恰恰是基于相反的社会趋势:对金融资本和股票交易支配地位的顺应,突显出里根和撒切尔时期企业自利的卷土重来。”
药品回应文化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50年代美国郊区沉迷于巴比妥酸盐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毫无希望、遭受文化压迫。正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写,人们期望这类女性“完全献身于家庭”,并且“只在性被动、男性支配和育儿的母爱中找到满足感”。沮丧、压抑而神经质,她们用巴比妥酸盐麻木自己,以顺应尚未被明文反对的规范。在杰奎琳·苏珊的小说《纯真告别》中,三位女主角危险地依赖着兴奋剂、镇静剂和安眠药(她们的“玩具”),以顺应人生选择、尤其是社会文化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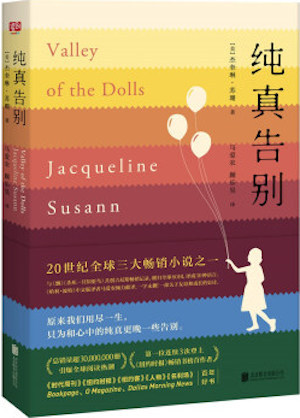
[美] 杰奎琳·苏珊 著 马爱农/蒯乐昊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但是,处方药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药物无法完全解决眼前的文化问题(就像美国郊区的妇女仍然无法摆脱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黯然无望),替代药物(哪怕看上去与眼前的状况并不相干)往往为人们提供了潜在的解决办法。
美国影星朱迪·巴拉班于1950年代在医生指导下开始服用LSD,当时她才20多岁。她的生活看上去很完美:她是派拉蒙影业富裕而广受尊敬的总裁的女儿,育有两女,有一处位于洛杉矶的豪宅,还有一位成功的电影经纪人丈夫(他是马龙·白兰度、格利高里·派克和玛丽莲·梦露的经纪人,并与他们结为朋友)。朱迪·巴拉班是摩纳哥王妃、美国女影星格蕾丝·凯莉的密友,并在后者的王室婚礼上成为伴娘。让她承认这一点似乎很疯狂,但在一切光鲜之下——朱迪·巴拉班对自己的生活深感不满。她同样养尊处优的朋友也有同感。波莉·贝尔根、琳达·劳森、麦瑞恩·马歇尔——所有嫁给了著名电影经纪人或导演的女演员,都对生活有着类似的、隐藏的不满。
由于获得满足感的选择有限,以及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无望生活,巴拉班、贝尔根、劳森和马歇尔都开始了LSD治疗方案。贝尔根在2010年的一篇《名利场》报道中对巴拉班说,“我想成为我自己,而不是一种人设。”巴拉班则写道,LSD就像“一支魔杖”,相比抗抑郁药物,它更能有效地解决眼前问题。很多和巴拉班一样受到文化压抑的同类人群也有相同感觉,在1950年至1965年间,据报道有4万人曾接受LSD疗法。当时它是合法的,但并不规范,而几乎所有尝试过该疗法的人都对其功效大加肯定。
LSD不仅受到郊区家庭主妇的青睐,也填补了同性恋或性困惑者内心的缺失。演员加里·格兰特有数年曾是帅气的演员兰道夫·斯科特的室友,同时又与五位不同女性结过婚(婚姻平均长度为五年,期间他时常和斯科特住在一起),他同样在LSD疗法中获得释放。如果当时格兰特被公认是同性恋,他的电影事业将被毁掉。和那个时代许多郊区妇女一样,格兰特将LSD视作急需的“逃生阀”,是升华痛苦的一种方式。在1959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隐晦地说,“我想摆脱自己所有的虚伪。”在精神病医师指导下的十几次LSD治疗之后,格兰特承认:“我终于接近幸福了。”

不过有时候,并非是人们寻求药物和毒品以解决文化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被故意制造出来,以销售本已存在的药物或毒品。
例如当今应对多动症最流行的药物利他能和阿德拉,它们被大量普及,又导致对多动症的诊断显著增加:在2003至2011年间,美国中小学生被诊断患有多动症的人数上升了43%。这不太像是一种巧合。
“21世纪,对抑郁症的诊断急剧增加,正如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多动症的诊断,”美国精神治疗师劳伦·斯莱特在《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写道,“某些诊断率的上升或下降取决于公众观念,但也因为给病人贴上这些标签的医生可能很少考虑该领域规定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标准。”
这也就是说,当今的制药商催生了一种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认为不那么专注且更加沮丧,以便销售药物去解决他们“制造”出来的问题。
激素替代疗法也是相似情况,它被用于缓解妇女更年期的不适感,以注射雌激素,有时还有黄体酮,来人为提高女性荷尔蒙水平。之后该疗法又被扩展,包括针对跨性别者和男性雄激素的疗法,理论上可以通过激素疗法延缓男性的衰老。这种不断扩张药物使用量和需求性的欲望,反映了当今药物所创造(和鼓励)的文化。
显然,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文化问题可以导致某些药物流行;但有时流行的药物又会反过来造就我们的文化。锐舞亚文化(Rave Culture)随摇头丸而来,而起初旨在帮助治疗认知和注意力障碍的药物又催生了超高生产力文化……化学药品与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显而易见。

但是,尽管毒品既可以回应、又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却没法简单地解释,为什么一种现象(而不是另一种)产生了。如果锐舞文化是由摇头丸创造出来的,那么摇头丸是否也正在“回答”某一文化问题;或是,摇头丸只是存在着,而锐舞文化围绕它兴起?我们常常看不清因果关系。
耶鲁大学医学史助理教授亨利·考尔斯表示,“每发明一种会与使用者大脑和心智相互作用的药物,都会改变研究的对象——药物使用者。”
以沉迷于巴比妥酸盐的美国家庭主妇为例:她们在文化上受到压制、几乎没有自由,因此寻求药物以迫使自己循规蹈矩。LSD和后来的抗抑郁药物是对严格的文化规范的“回答”,也是自我治疗情绪痛苦的手段。但考尔斯辩称,同样可以说,“这些药物就是为这种人群而设计的,最终催生了一种新型家庭主妇或职业女性,她们用药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简而言之,考尔斯说,“只因为有可能接受药物治疗,才催生了绝望主妇的形象。”
这种解释将药物和毒品置于上世纪文化历史的中心:如果药物可以创造并强调文化边界,那么药物及其制造者就可以设计整个社会文化的人口形象(例如“绝望的家庭主妇”或“享乐主义的、吸食可卡因的华尔街交易员”)。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类别的创造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即使不使用该时代中普及药物的人群,也会受到身处文化的影响。因果关系并不清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药物和毒品既可以“回答”文化问题,又可以使文化围绕它们而生长。
纵观当下文化,药物所回答的最大问题也许是“专注”和“生产力”,这是现代“注意力经济”的结果。对于莫达非尼(用于治疗发作性嗜睡病等症状以保持清醒和增长工作时间)的使用,以及出于类似原因对于其他兴奋类药物(例如阿德拉和利他能)的滥用,正是药物在试图回答这些文化问题。
在2008年《自然》杂志的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曾经使用过认知增强型药物。据2015年大学生新闻网站The Tab的一项非正式投票显示,最高的药物滥用率存在于最知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学生滥用认知增强型药物的人数比英国其他任何大学都要多。
这些增强认知能力的药物“在双重意义上掩盖了工作中的平庸”,沃尔顿说,“它们刺激用药者处于一种精神涣散的高度兴奋状态,同时又让他相信,一定是他在工作中的成功高效才导致了这种亢奋感。”如此一来,现代药物选择不仅使人们持续工作并提高生产力,还使他们将更多的情感价值和幸福感寄托于工作中。

提高生产力的另一面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更高便利性和享乐性的需求,这种渴望被类似于毒品的体验(例如ASMR,和其他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得的“精神毒品”)所满足。但是,如果当今的药物和毒品主要满足了“注意力经济”的文化需求(如:专注力、生产力、休闲、便利等),它们也就改变了“成为自己”的意义。
至关重要的是,正是如今我们用药的方式反映了“自我”观念的转变。所谓的“魔术子弹药物”(治疗针对性问题的一次性或有限疗程用药)已被“维持性药物”(必须持续服用的药物)所取代。
“相比旧的模式,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考尔斯说:“过去是,‘我是亨利,我有点儿小病。但一颗药丸可以帮助我做回亨利,然后就不必吃药了。’而现在是,‘我只有在吃药后才能做回亨利。’”从1980到2000年,直到现在,使用这类维持性药物且停药无望的人口比例只会继续上涨。
那么,维持性药物是否会成为“后人类”(精神)状态的第一步?尽管药物未必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是谁”,但总有某种阴郁或迟钝的感觉会重新定义用药者的基本经历:“成为自己”就是“按时服药”。药品的未来走向很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延伸。
在此,让我们来冷静地看一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化与药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人类曾想要前进的文化方向——无论那是叛逆、屈从,还是完全脱离所有的系统和约束。那么仔细研究我们今天和未来想要使用的药品,就可以了解未来需要解决的文化问题。当然,这种可能性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发生——药品使人得以完全逃离自我,随之而来,我们又会看到新的文化问题出现,而解答办法仍可能是,药物和毒品。
过去的一个世纪,用药和毒品的模式令人惊讶地为我们提供了对文化历史的准确洞察,从华尔街的银行家、绝望的家庭主妇,到大学生、文学家,很多人都曾服用药物或毒品,这些行为反映出他们的欲望、其所处文化的问题。
药物和毒品还反映出一种更简单、持久的老生常谈:有时我们想要逃离自己,有时想逃离社会,有时想逃离无聊或贫穷……我们想要“逃离”。在过去,这种渴望是暂时性的——给自己重新充电,找一块净土,远离日常压力……然而,在最近的时代,用药或毒品已变为寻求持久、长期、关于“存在”的逃离——这种渴望非常接近于“无我”(自我消融)。
本文作者Cody Delistraty是一名作家和历史学家,作品见于《纽约时报》《纽约客》《大西洋》等刊物。
(翻译:西楠)
来源:Aeon
原标题:Drugs du jour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