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联网指北指北BB组 洪咸
编辑|蒲凡
“姓”其实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人类学话题,“如何称呼一个人”这件事能够反映出很多社会现实,比如人类学的开山鼻祖拉德克里夫·布朗就认为,人类通过亲属称谓来定位自身的社会关联,而“姓名”则是人类文明里最常见的“亲属称谓”标定方式。
比如在德云社,你叫“X鹤X”,甭管认不认识,就一定要管叫“X云X”的叫声师兄。原因无他,家谱就是按照“云鹤九霄,龙腾四海”这样排辈分的,对应着相声体系中的第八、第九、第十代传承人。
而这仅仅是“姓”使用方式的一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日趋复杂,姓又被赋予了几种不同的新含义:
-标记归属。人们对“姓(或者氏)”的使用方式,很直观地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比如远古社会,人们需要“姓”帮助人们标记亲属血缘,从而一方面避免乱伦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旗帜鲜明地指导人们实施外婚制,扩大家族规模,以顺利渡过不断迁徙、狩猎的苦日子。
直到生产力逐渐提高之后,人们有了剩余的生产资料,于是开始想着把财产固定在自己手里,于是姓逐渐演化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标志。比如《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作为家奴进入华府后需要改名为“华安”,就是这种使用方式的典型代表之一,与之类似的是各种X家庄、X家村。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新的使用方式,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重男轻女”思想的诞生。
简单来说,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耕地劳作的生计方式必然使得壮丁男性一般是家庭粮食的主要来源,这决定了当时主要施行的是从夫居(双方结成婚姻后,女子到丈夫家居住)、从父居(婚生子女跟随父亲居住)的婚姻形式。也决定了男性更有作为“生产资料”来用“姓”来标定家族归属的价值。
-标记社会分工。中国的司马、司徒、太史,西方世界里的Mason、Carter、Smith,都是这类用法的代表——当然中国的体系更加复杂,实际上司马司徒更符合“氏”的概念,用来标记家族的身份、出生地、官职等,到后世才逐渐和姓合为一体,这里不做过多阐述。
总之你可以将这种使用方式,理解为“更高级的继承权”,即获得“姓”的人不仅仅获得的是财产、生产资料的继承权,更获得了“生存技能”的继承权——这对于抗风险能力更弱的古人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当然部分也来自于统治者的需要,比如太史氏的世袭,是为了保证监督权的相对独立。在战国前,人们也会可以随着避祸或迁徙到别的封地而改掉自己的姓,与土地分封制有很强的关联。
-标记赏惩。最典型的用法就是赐姓和责令改姓。比如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贵族杨玄感趁农民起义之机造反,兵败身亡,被敕令改姓为枭——这就是要告诉世人:这个人,当过逆贼——再譬如马三保,就是因为航海外交有功,才有机会获得赐姓“郑”,改名正和的。
民间也有类似的用法,比如最著名的“家法”——逐出家门——最硬核的做法就是将其逐出家谱,不得冠以本族姓氏。
或许也正是借鉴了这种用法,历史上也有不少通过“改姓”来表忠心、纳投名状的故事。比如日本战国名将丰臣秀吉,就是为了向朝廷索取“关白”称号,主动认前关白近卫前久为义父,争取到的“改姓”。

正如上文开头所说,“姓氏文化”的兴起与演变,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直观投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姓氏文化”有着破灭的必然。
开始于清末的中国大家族制度的瓦解,就拥有这样的内因。在新时代的社会体系里,人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分工协作,以及以分工协作为基础建立的新型组织,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以“姓氏”为纽带的家族不再是唯一的“抗风险”策略。再考虑到家族制过多的“道德约束”,以及家族制中必然存在着的“利益相关”、“利益垄断”,早期革命者也往往将“姓”作为革命目标,通过“改姓”的方式来象征着旧体制的打破。最不济,也象征着自己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决心。
新中国对于“姓氏文化”的打破更加彻底,最典型的例子是《我爱我家》里1945年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官至局级的老干部傅明老人,说出的那句颇具时代感的口号——“亲不亲,阶级分,怎么能按姓氏分呢”——这种群体思潮促成了对“冠姓权”里程碑式的解放,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现行的《婚姻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人民群众对于那场解放运动也是喜闻乐见的,并给予不亚于“援朝”、“抗美”、“卫国”的热情。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国人,不少都选择随母姓,比如性社会学家李银河。
当然也有比较“温和”的策略。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到 2018 年底,有110 万人的姓名中同时包含父姓和母姓。在 2017 年出生的新生儿里,尝试用新复姓取名的孩子已经超过了4%。
孙杨、秦牛正威、蔡徐坤都是一种例子,而《2019 姓名全景报告》指出,这背后可能意味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个体意识觉醒,同时也带来的家庭和经济地位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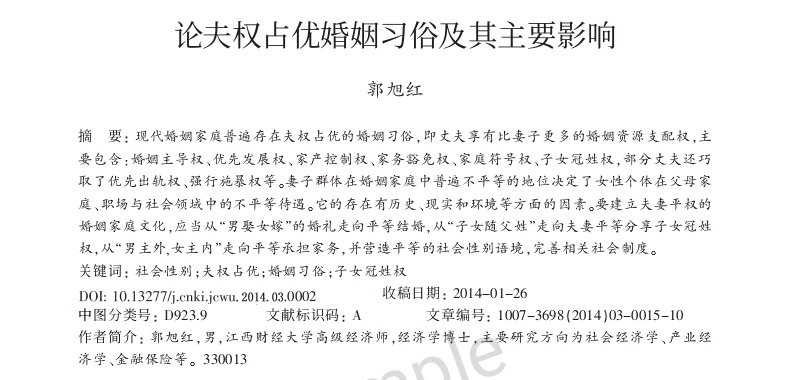
(这篇写于2014年的论文至今仍不过时)
西方围绕着“姓”的解放运动,尤其是围绕着“冠姓权”的解放运动就相对复杂很多。
一方面,早在19世纪中叶,女性平权运动就选择了以“夫姓”为突破口,号召女性姓氏与丈夫姓氏进行解绑,进而获得更加独立的公民权、财产权、继承权等等。
到今天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西方女性选择婚后保留姓氏,并这种权利也开始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支持(包括美国的不少“保守州”),也在子女冠姓问题上形成了“Hyphenated Last Names”(连字符姓法)等有建设性的选择方案。
但受到宗教等传统思潮的影响,“冠姓权”的解放并没有伴随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发展同步进行,而是出现了反复。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就曾经通过调查发现,在马萨诸塞州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有23%的人在婚后仍保留自己原来的姓氏,到2000年,下降到17%。
因此当我们回看西方以“冠姓权”为主题的平权运动,很容易品出很多“实验性”、“解构性”、“反宗教”的色彩在里面,比如2005年左右由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里格萨发起的“新姓运动”,就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分享姓”的概念。
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在以“姓氏”为主题的平权运动中,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对“姓氏”解放是冲击父权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但它更像是一个突破口——是一系列复杂议题所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一系列复杂议题的主因。
而基于这个共识,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形成许多“看上去三观极歪”的新策略形成,比如“放弃父权”。
在一份2016年瑞典提交的立法审议中,有人提议在女人被允许堕胎的孕期内(也就是孕期18周),胎儿的生理父亲可以通过签署法律文件的形式,分割自己与这个胎儿的一切法律关系,其中就包括“冠姓权”,当然也包括“抚养权”以及子女未来对其的“赡养义务”。

平权运动是有必要的,对于“姓氏文化”的消解也必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参与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对于papi酱事件产生巨大反感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是不允许你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谩骂嘲讽,看起来都不是推动正向结果产生的有效参与方式。
换句话说,那些在高喊着反对的人,大概率也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很难说这种现象到底是谁的错。毕竟在papi酱之前,类似的谩骂(包括“驴”这样的称呼)就已经出现在了泛女权话题当中,即使“营销”真的存在,其作用也更倾向于“开发利用”而不是“创造”,单纯地甩锅给papi酱并不比那些叫骂着的“拳师们”高明到哪里去。
“互联网的普及”可能是更现实的答案。
当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不断打破原本由地域、气候、财富、教育等因素构建起来的群体边界,人类开始完成大量的第一次接触,也开始形成一轮大规模的集体误解:
将“旁观”的权利,与“参与”的能力互相混淆了。
于是本来应该由教育程度更高、认识更深刻、执行更效率、规划更科学的人群所完成的“平权运动”,开始被普通网民们“主动接手”,发展成为一个低参与门槛的公众话题,从而形成一种“错位关注”的假象。
与“真实关注”相比,这种“错位关注”带来热度很难转化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像民间会传说皇帝用的是“金锄头”,缺乏理论体系系统支撑的参与者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基于自己已有认知的“逻辑自洽”,并将这个“逻辑自洽”的结果看做是事件本身的内核。
再回到开头我们所说的几个热点,就很容易看出问题的真正所在了:所谓的争议更像是一次巨大的集体浪费,一方面消耗了公众对于原议题的耐心与潜在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快速将原议题快消品化,错位地兑现了原本应有的价值。
最后再补充一个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探讨了原始人的心智结构后提出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人脑中是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分类结构,比如“天/地”“水/火”“我/他者”等,分类是秩序的起源。而人类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改变先验的东西,而反直觉的思考才会带来思维的进步和启发。这个意思也许是说,对任何极端的、二元思维都保持警惕,才能有反抗和理解的清醒。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