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纳森·弗兰岑的第五部小说《纯洁》(Purity)中,汤姆·阿贝兰特(Tom Aberant)和故事中出现的其他角色一样有些不欲与外人道的家丑:精神失常的前妻安娜贝尔·莱尔德(Anabel Laird)。现实生活中,弗兰岑与结婚14年的作家太太瓦莱丽·康奈尔(Valerie Cornell)之间的关系也如同小说里那样充斥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息。他在个人回忆录《不安地带》(The Discomfort Zone)中描述到:即使是非常琐碎的口角之争,最后都会发展成两个人“趴在各自房间的地板上长达数小时,等待承认伤害已经造成”的结局。对于小说中他放在阿贝兰特和莱尔德身上的幽闭恐惧症,弗兰岑自己一定不会陌生;而小说中这些最骇人听闻、最诙谐而引人入胜的部分说明弗兰岑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个人的生活经验。
在弗兰岑最早期的两本小说《第二十七座城市》(The Twenty-Seventh City, 1988)和《强震》(Strong Motion, 1992)中,他曾刻意避免将“个人凌乱的私生活”写入小说中。《第二十七座城市》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孟买的女警官在美国圣路易斯卷入政治阴谋的故事,《强震》则是写一对年轻夫妻探索一家公司的不当操作与波士顿地震之间的因果联系。按照弗兰岑接受学术期刊《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时的说法,在那两本小说中,即使使用了有自传性质的素材,也是以“巧妙掩饰的形式”呈现的。掩饰得太过巧妙,以至于弗兰岑曾在其他场合说这两本小说是“在技术上反自传体”的。
但到了不惑之年的弗兰岑并没有吸引到他所希望的读者群,彼时他正在为第三本小说《纠正》的创作苦苦挣扎。这时的弗兰岑意识到:“前进的唯一方式是追本溯源,重新去体会自己早年生活中那些尚未释怀的时刻。”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塑造出与我相距甚远的人物来肩负我的人生重担,但又不让小说淹没在与我太过相似的人物角色之中”。
何必呢?
在弗兰岑更加有意识地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灵感后,他终于写出了一部通过与读者产生广泛共鸣的方式连接起个人与社会的小说。
他曾在1996年写过一篇随笔。这篇随笔后来改名为《何苦呢?》(Why Bother?),收录于弗兰岑2002年出版的随笔集《如何独处》(How to Be Alone)。他叹惋自己作为一名思想小说家,却生活在一个电视占据人们闲暇时光的时代。弗兰岑的这种叹息被许多人误读,以为他的下一个作品会是一部复兴文学世界、像一部伟大的19世纪小说那样连接个人和社会的小说,与其说这是一种年少轻狂而不切实际的野心,不如说这是一篇墓志铭。“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承诺要写一部鸿篇巨制的社会小说来给主流文化注入新鲜内容,而是借机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抱负。”弗兰岑在随笔集《如何独处》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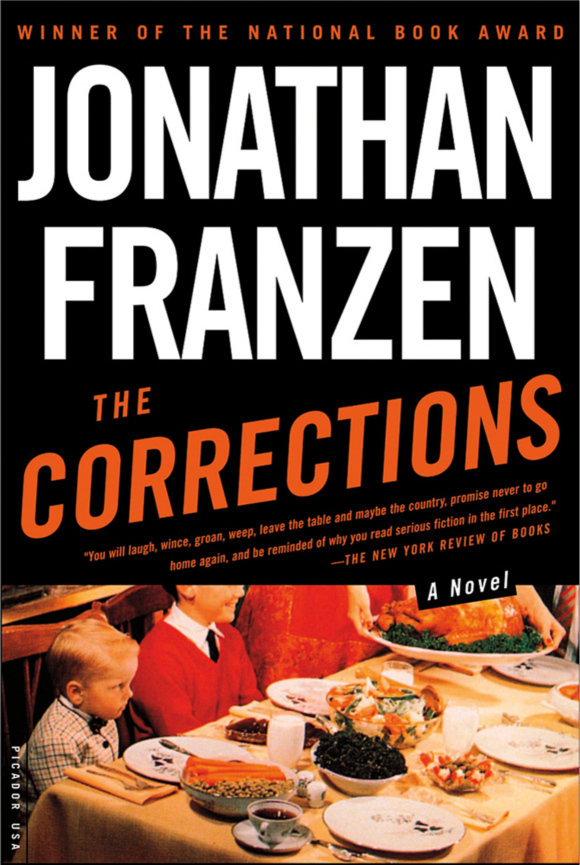
但这时惊喜出现了。弗兰岑的第三部小说《纠正》(也就是他在随笔集中所说的那部问题小说)恰好完成了那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纠正》讲述的是美国中西部兰伯特一家的生活,女主人希望在丈夫被帕金森症夺走生命前全家能有一次最后的圣诞节聚会。这是一部大手笔的社会小说,向来以“难以取悦”著称的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形容该小说“滑稽而具有侵蚀性、感人而具有预言性”, “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家庭里的两代人如何竭力赋予生活意义,也敲开了一条裂缝,让我们看到一个蹒跚走向新千年的忧郁的国家。”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销量超过了三百万册。
自命不凡的文学品味?
弗兰岑的声名鹊起未能逃过随之而来的争议。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曾将《纠正》选入她的读书俱乐部,但弗兰岑据称怀疑奥普拉的阅读品味,按照大卫∙盖茨(David Gates)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书评里的说法是弗兰岑担心自己变成“烂大街”的知识分子,最终奥普拉取消了节目的录制。

作为白人男子特权的捍卫者,“弗兰岑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象征白人男性霸权的文化标志,多过他作家的身份”,大卫∙L∙乌林(David L Ulin)在《洛杉矶时报》的撰文中说。弗兰岑还经常被指责称有性别歧视,或者说他不支持女性作家的作品。乐观地来看,新作《纯洁》中呈现了诸多迷人而有缺陷、强大而复杂的女性形象,这可能会平息一部分对他性别观念的指责。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最近弗兰岑在接受《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的言辞就又为讨厌他的人提供了新的吐槽点。在《卫报》的采访中,他承认曾经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接近年轻人”的时候不太认真地考虑过领养一个伊拉克战争孤儿,他的编辑最后警告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成为了一个笑柄,然而就在一天之后,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直言斥责网络平台“积极地回报不负责任的言论”,原本欢乐的气氛演变成了群情激奋。
“那些成为小说家的人”,弗兰岑接着说,“是会花好几年时间琢磨怎么写才对的人,而那些发推特的人根本就不在意对或不对,并且愿意在连写一个从句都不够的有限空间里鲁莽成文。”
这样的言论必然会在他所攻击的那些社交媒体上引起一阵愤愤不平的反攻,而且这些“以牙还牙”的人大多能言善辩,从而证明弗兰岑在这件事情上是错的。如果我们不提弗兰岑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心胸狭窄对他是不公平的,“我对(网络上的)言论有一种偏执的厌恶”, 他直言不讳,证明自己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但伤害已经造成,和之前的奥普拉事件一样,人们只看了一个在文学品味上自命不凡的人。
畅销作家
除去这些勾勒出其公众形象的抨击网络“点击诱饵”的采访摘录之外,弗兰岑写作的魔力在于他成功地将严肃题材小说的写作与对大众市场的吸引力结合在了一起。2011年弗兰岑出版了他的第四本小说《自由》(Freedom),毫无保留地细腻刻画了一个身处麻烦不断的21世纪的美国家庭。《自由》上市后受欢迎的程度证明了《纠正》的成功并不只是一时侥幸。英国作家布莱克∙莫里森在《卫报》上发表了《自由》的书评,认为家庭是弗兰岑“真正的主题”;角谷美智子再一次被折服,称弗兰岑的第四部小说完全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刻画”;《每日电讯报》更是将《自由》称为“后奥巴马时代第一本伟大的美国小说”——巧的是,奥巴马总统本人据称真的曾在假日里阅读这本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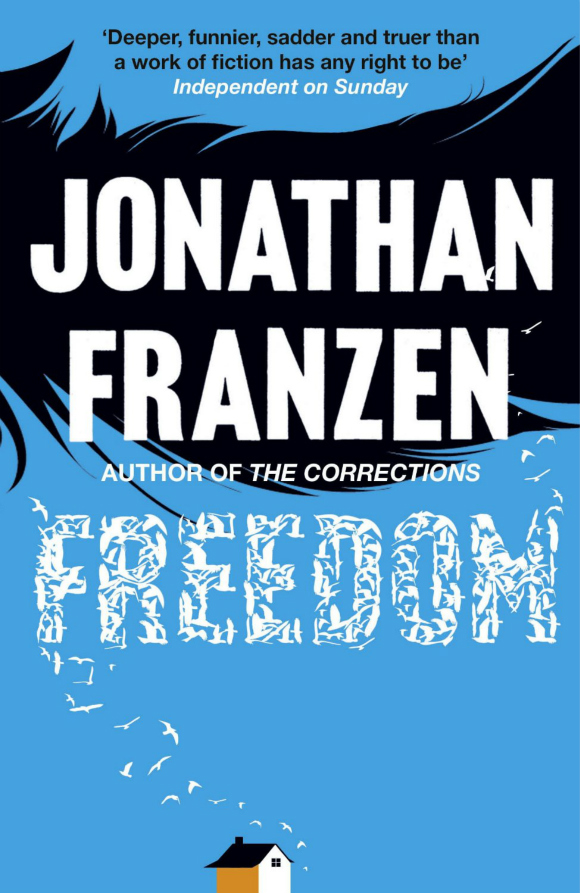
美国作家约翰∙威廉∙德福雷斯特(John William De Forest)在1868年将小说的成就定义为“捕捉平凡情感与美国生存方式的画面”,从此人们都在寻找这样一部难得的作品。就在小说《自由》出版之际,弗兰岑被冠以“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名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他是十多年来第一位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的作家。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能说明弗兰岑已经达到了德福雷斯特所定义的那项最受追崇的文学成就。

现在这位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出版了布克奖(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对美国作品开放以来的第一部小说,但《纯洁》却出人意料地没能入围。有一种倾向是说这个奖项倾向于“冷落”知名作家的作品,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冷落”这个词夸张到无聊,但对于《纯洁》此番的遭遇,倒是挺合适。《纯洁》是我今年读到的最优秀的新小说,小说延续了作者一如既往的繁复而巧妙的叙事风格,却又语调轻盈、触感鲜活。早前发布在文学网站N+1上的一篇精彩书评出奇地将《纯洁》与儿童文学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小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进行了比较,书评的作者内尔∙辛克(Neil Zink)认为,不同于弗兰岑过往“对于令人失望的人物浓郁而令人难堪的刻画”,《纯洁》是一本“有趣”的书。
“没有人是纯洁的。”
“有趣”不代表《纯洁》就不是一本探讨严肃主题的严肃小说了,只是说里面有很多幽默的成分。弗兰岑将人物关系的设定铺开到几个大洲,贯穿几十年的时间,小说从本质上来说对每一个人类互动层面上秘密与谎言的测试,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整个社会间的不同境遇,都有涉及。在这本小说中,弗兰岑可谓得到了“巧合”大师狄更斯的真传,而小说主人公普丽蒂(Purity)的昵称Pip与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里的英雄同名,可就不是巧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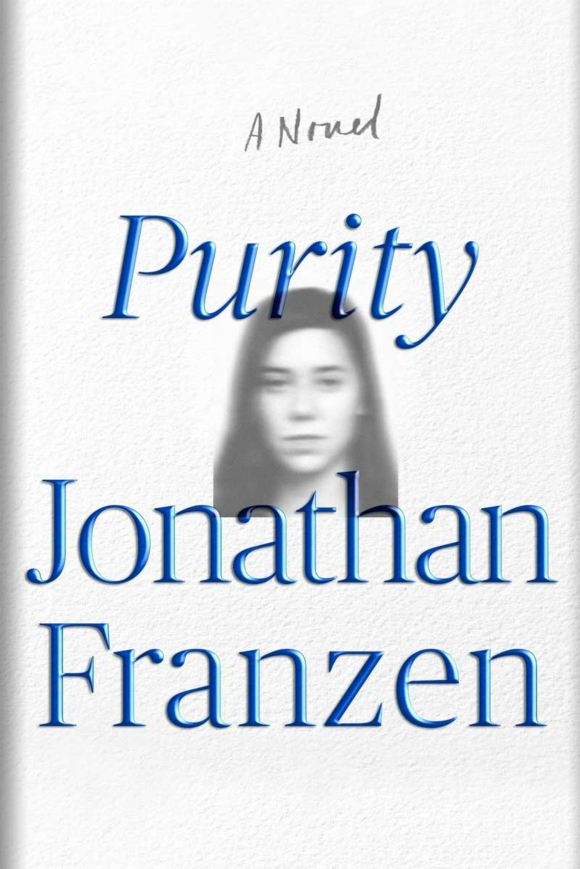
在小说的开头,23岁的Pip住在位于奥克兰的一个废弃屋里,欠着大学学费贷款的她日子过得很艰难。Pip幻想着如果她能找到自己的父亲,或许父亲就能帮她还掉那些贷款。所以当一个年轻的德国激进主义分子建议她参加一个叫做“阳光项目”的实习时,她跃跃欲试。这个“阳光项目”是一个类似于维基解密的机构,运营者安德里亚斯∙沃尔夫(Andreas Wolf)则是一个和阿桑奇、斯诺登一样富有魅力的人,Pip可以利用这个团队的软件来搜索她个人需要的信息。
《纯洁》这本小说的所有人物都有着隐秘的动机,没有人是纯洁的。就像在《自由》里,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纯洁》是一部跨越几代人的叙事史诗,故事的发生地也横跨了当代美国、南美洲玻利维亚的隐秘山谷以及柏林墙倒塌前的西德,因此不难理解有人说比起完整的单本小说,《纯洁》更像是连环小说的一部分。确实,《纯洁》读起来有一种拼图玩具般充满乐趣的质感,故事线索恰逢时宜的揭露凸显了这部作品在结构设计上与《纠正》和《自由》的不同。
尽管弗兰岑一直在证明着自己过去对于文学的一些担忧是错的,但弗兰岑《何必呢?》中的许多内容今天看来仍旧犀利。一部小说要与许多其他作品竞争、与越来越容易通过指尖即可获得的娱乐内容竞争就已经是一种成就了;而作为作家,获得像弗兰岑那般规模的读者群,是令人惊叹的。在小说《纯洁》快结尾的时候,弗兰岑认识到“秘密是一种力量,金枪是一种力量,被需要也是一种力量。力量,力量,力量”。而如果说弗兰岑的职业生涯也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那一定是:小说也可以很有力量。
翻译:黄珠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