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美国当下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抗议浪潮中,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字被人们不断提起。金或是作为上世纪民权运动偶像被抗议者尊崇和呼应,或是被反对派搬出非暴力理论来,作为对当下抗议运动过火的指责。金的传记作者之一戴维·刘易斯(David L. Lewis)曾经说过,“在整个国家将马丁·路德·金追封为圣人的风潮中……我们试图通过忘记他来记住他。”如今,当他再次被频繁提起,作为历史的对照和先知,作为圣人或圣人的反面,我们或许有机会一窥他在上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中所真正扮演的角色、呼喊的价值、捍卫的纲领。

在美国记者、民权运动忠实记录者马歇尔·弗拉迪(Marshall Frady)的马丁·路德·金传记中,金被描述为一位“奋不顾身地与他所处的整个时代开战”的人。马歇尔观察到,到最后,金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进击任务,不仅要为黑人张目,还要为西班牙裔、美洲原住民、白人中的穷人,以及美国社会所有被剥夺、被抛弃和被忘却的人发声,以彻底重整整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权力体系。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对他的咒骂是,“他上足了发条,是美国最危险的颠覆分子。”而马歇尔在《马丁·路德·金》一书中写道,“最终令他鞠躬尽瘁的是一种宏伟的甘地式的雄心:通过改变南方的那种非暴力群众性对抗运动,重塑和救赎美国本身。”
而在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撰写与编辑过多部美国民权运动著作的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这里,因坚持非暴力策略而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倡导的“黑人权力运动”指摘为软弱的金获得了另一种声音。金对使用“黑人权力”这一口号持保留意见,因为他感到这样的字眼做口号并不恰当,而且“我看到它在游行参与者中造成了分裂”。当新闻报道集中于民权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当“黑人权力”成了全美范围内热议的一个专门术语,金对这一口号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分析,也对“黑人权力”四个字所可能带来的改变与造成的分裂、核心的无力与虚无的愿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一方面,金认为“黑人权力”这一口号并非从某个哲学先知的头脑中凭空产生,而是从绝望和失望的伤口中诞生的;这个口号是呼吁黑人们积聚政治和经济力量,以实现他们正当的合法目标。事实上,黑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权力。而另一方面,“黑人权力”在倡导暴力这一问题上,其实就模仿了最败坏、最残酷、最野蛮的美国生活的价值观,“黑人权力”究其实质是一种认为黑人根本无法赢得胜利的虚无主义哲学,这个口号仍然带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问题,注定要失败。
在历史书写中被封神的马丁·路德·金究竟如何看待黑人反对歧视的运动?他对待暴力的态度是怎样的?他是如何作为领袖“被利用”而同时又清醒地不被共识所裹挟的?克莱伯恩·卡森的《马丁·路德·金自传》——卡森于1985年受金的家人之邀,主持 “马丁·路德·金博士文稿项目”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他用马丁·路德·金自己的语言,为他编纂成了这部历史性自传——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一二。
《黑人权力》(节选)
文 | 克莱伯恩·卡森 译 | 徐菡
01 “黑人权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只是我们经过沿途的每个城镇,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往往会冲淡一些争论和分歧的气氛。经过格纳达(Grenada)前往格林伍德(Greenwood)的路,我们大约走了十天,斯托克利越来越难以掩饰他渴望到达格林伍德的迫切心情。在1964年那个不平静的夏天,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在格林伍德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那里算得上是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势力范围。

游行队伍快到格林伍德时,大批民众走出来欢迎我们,其中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当晚,我们在一个城市公园中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斯托克利登上讲台演讲,他大力抨击了密西西比州的种族歧视,听众群情激昂。然后,他宣布道:“我们需要的是黑人权力。”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中有一个富有鼓动力的演说家,叫威利·里克斯(Willie Ricks)。他闻言跳上讲台,喊道:“你们要什么?”人群怒吼:“黑人权力(Black Power)!”里克斯一次又一次地高呼:“你们要什么?”应答声越来越响亮:“黑人权力!”气氛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就这样,格林伍德成了民权运动中“黑人权力”这一口号的诞生地。理查德·怀特和其他人原来曾经用过这个术语,但直到那一夜,它才首次作为民权运动的口号被正式提了出来。这个口号对长久以来遭受白人欺压、低人一等的黑人来讲,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然而,我对使用这个口号持保留意见。我强烈感觉到,用这样的字眼做口号并不恰当,而且我看到它在游行参与者中造成了分裂。有那么一两天,那些支持“黑人权力”的人与那些支持“现在就要自由”的人展开了竞争,双方的演说家都拼命鼓动人群,让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自己的口号,看谁的声音更响亮。
现在,我只相信具体的、切实的黑人权力。我不相信黑人分离主义,也不相信任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人权力。然而,如果黑人权力指的是为了实现我们公正合法的目标而去累积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我们都会相信这样的权力,我认为,所有心怀善意的白人也都相信这样的权力。
黑人人口只占全美国总人口的10%,如果我对你们说,黑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那么我就是愚不可及的。我们必须与心存良知的人们组成联盟。在美国,白人只有同情和理解了我们的事业,明白了种族隔离不仅侮辱了黑人也贬损了白人自己,黑人才能真正在密西西比和美国其他地方获得自由。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依靠暴力赢得自由,那么我就是在误导你。即便想一想也能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暴力革命一旦爆发,必然导致许多人无谓地丧命。当然,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很多人也都准备好要献出生命。如果你对某个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念,如果你全心全意信仰它,你就会心甘情愿为它而献出生命。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主张无谓的牺牲。
我意识到队伍中的分歧正在不断扩大,于是邀请了斯托克利和弗洛伊德来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带领各自的助手,在亚祖市(Yazoo City)的一个小天主教堂会面了。我整整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想要说服他们不再使用“黑人权力”这个口号。我认为,一个领袖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辞表达。每个词语都有它的指示意义,这个意义明确清晰,广为认可;同时,它还有一个隐含意义,也就是它所暗示的意义。虽然“黑人权力”这个词的法律含义清晰明了,但作为口号的“黑人权力”所蕴含的意义却容易引起误解。我提到,媒体报道已经给这个概念赋予了暴力的含义,而一些游行参与者的草率言论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
斯托克利回答说,暴力还是非暴力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黑人要积累起政治和经济资源,来获取权力。他说:“这个世界只尊重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力,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权力。”然后,他紧紧地盯着我说:“马丁,你我都知道,事实上,几乎所有美国的其他族裔都这样做,犹太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他们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回答说,“没人听说过犹太裔公开高呼过‘犹太权力’,但是他们有权力。他们通过自身的团结、坚定的决心和创造性的努力,获得了权力。对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来讲也是同样,这两个群体都没有使用‘爱尔兰权力’或‘意大利权力’这样的口号,但是,通过努力,他们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正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我接着说:“我们必须通过建设性的手段,来积累黑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种合法的权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努力建立黑人的种族自豪感,驳斥黑人生来邪恶、丑陋这些说法。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依靠实际的行动,而不只是一句口号。”
斯托克利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口号本身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口号,怎么能把人们团结到一起呢?难道工人运动没有口号吗?在我们争取自由的各种运动中,难道不是一直都有口号吗?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口号,只不过加上了‘黑人’二字而已。”
我承认我们需要口号,但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样一个引起盟友误解的口号呢?这个口号不仅把黑人孤立起来,而且让原本就心存偏见的白人找到了一个自我辩护的借口。如果没有这个口号,他们也许还会对自己的反黑人思想感到羞愧呢。
经过冗长的辩论,斯托克利和弗洛伊德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斯托克利坦率地说:“马丁,我是特意决定在这次游行中提出这个口号的,其实就是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一场讨论,并且迫使你支持‘黑人权力’这个口号。”
我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我以前就被利用过,”我对斯托克利说,“再多一次也无妨。”
会议结束时,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成员仍然同意我的看法,认为“黑人权力”这个口号并不适宜,它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控诉密西西比种族罪恶上转移开去。而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斯托克利和弗洛伊德的主张,坚持认为应该把这个口号在全美范围内推广。为了维护团结,最后我建议双方都做出让步,在接下来的游行中,我们既不高呼“黑人权力”的口号,也不用“现在就要自由”的口号。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新闻界,都不会被这种明显的分歧搞糊涂,工作人员也不用相持不下了。最后,大家都同意了这一折中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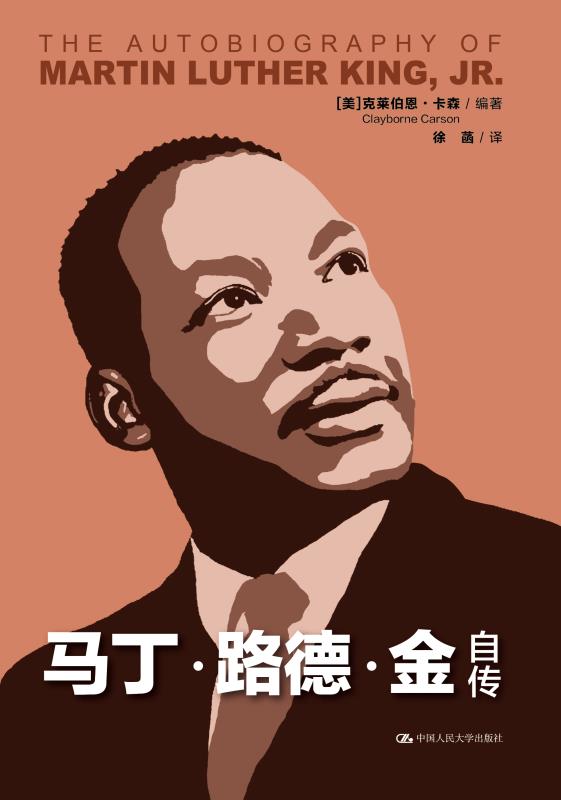
克莱伯恩·卡森 著 徐菡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4
02 “失望的呐喊”
虽然游行队伍里不再有口号之争,但新闻界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新闻报道的热点不再围绕着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弊端,而是集中在民权运动中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要经历团结一致的高潮期和内部分歧的低谷期。这场辩论只不过是正常的内部意见不一致,但是,新闻界一向喜欢小题大做,唯恐不把这个问题吵得尽人皆知。在他们看来,在每场戏剧性冲突中,都必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对抗角色,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制造一个出来。
因此,“黑人权力”成了全美范围内热议的一个专门术语。有些人觉得这个口号让人心生厌恶,但另一些人觉得它充满了活力;有些人对它深恶痛绝,而另一些人认为它令人振奋;有些人说它饱含破坏性,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个口号很有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不同的人对“黑人权力”这个口号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概念,它甚至可能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承载着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层面上定义其最终含义。我们必须超越任何个人喜好、华丽辞藻和大众媒体的歇斯底里,来诚实地评估这个口号的价值、意义,以及它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黑人权力”是表达失望的呐喊声。这一口号并非从某个哲学先知的头脑中凭空产生,而是从绝望和失望的伤口中诞生的。它沉淀着经年累月伤心痛苦的呼声。几个世纪以来,白人权力的阴影笼罩着黑人。许多黑人已经失去了对大多数白人的信心,因为就是白人一手遮天的权力使得黑人们两手空空。因此,在现实中,呼唤“黑人权力”,其实就是对不能给黑人带来任何利好的白人权力的反抗。
许多今天赞成“黑人权力”的年轻人,其实昨天还是黑人与白人合作,以及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拥有极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怀揣着对未来执着的信念,勇敢地在南方开展工作。他们即便身受拳打脚踢,也绝不以牙还牙;即便身陷阴暗肮脏、臭气熏天的监狱,也没有放弃为人的尊严。他们坚定勇敢,蔑视危险,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直面南方各州的吉姆·克拉克和“公牛”·康纳之流,无情地揭露出美国政治机体中的种族主义的弊病。如果说他们是今天美国国土上愤怒的孩子,那么他们并非生性如此暴躁。这只是对绝望的回应,而这种绝望是因为当权者屡屡言而无信、顽固不化和懦弱无能,使得实现自由和平等变得遥遥无期。现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说非暴力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民权斗士,他目睹过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和白人民权战士犯下的种种暴力罪行,他也目睹了犯罪者如何逍遥法外。

更让他们倍感挫折的是,如果白人和黑人同样为了争取正义而献出生命,白人的牺牲往往会比黑人的牺牲得到更多的关注,引起更大的反响。当勇敢的黑人小伙儿吉米·李·杰克逊惨遭杀害,以及虔诚的一位论派一位论派(Unitarianism)又称神体一位论、唯一神论、独一神论、独神主义等,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此派别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并不接受传统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由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组成的理论。白人牧师詹姆斯·里布被殴打致死时,斯托克利和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同事们与我们一起,都在亚拉巴马州。他们记得,约翰逊总统给勇敢的里布夫人送花表示慰问,在他雄辩的演讲《我们必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中停了下来,提到一个人——詹姆斯·里布——为战斗捐躯了。不知怎的,总统忘了提吉米·李·杰克逊的名字,而他才是那个先牺牲的人。吉米的父母和姐妹也没有收到总统的花。学生们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詹姆斯·里布的死不值得痛惜,而是总统没有提到吉米·李·杰克逊的名字,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白人认为黑人的生命微不足道、一文不值”这一印象。
03 “从毫无权力到拥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权力”
其次,从广义而积极的角度去看,“黑人权力”这个口号是呼吁黑人们积聚政治和经济力量,以实现他们正当的合法目标。无人能否认,黑人迫切需要这种合法的权力。事实上,黑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权力。从南方的老种植园到北方的贫民窟,黑人们一直都无职无权,默默忍受奴役。他们被剥夺了决定自己生活和命运的权利,只能服从于白人权力机构的淫威以及偶尔异想天开的裁定。手握重权的那些人创造出种植园和贫民窟,目的就是控制那些无权的人,并且让他们永远无权。因此,改造贫民窟其实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问题,是要求权力变革的力量和竭力维持现状的力量之间的正面对抗。
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权力应当指实现目标的能力,是实现社会、政治或经济变革所需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实现爱与公正,权力不仅值得去争取,而且是必要的。历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通常将爱与权力这两个概念完全对立起来,似乎爱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权力则代表着对爱的否定。现在,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没有爱的权力,无情而残暴;而没有权力的爱,无力而脆弱。最好的权力,是用爱来落实公正的要求;最好的公正,是用爱来纠正任何与爱对立的做法。
权力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当前美国的问题是,权力分配不均。这造成了美国黑人过去只能利用没有权力的爱和道德规劝,来追求他们的理想;而美国白人则通过缺乏爱和良知的权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状况的后果就是,一些极端主义分子鼓动黑人从白人手中夺取权力,而这泯灭良知、破坏性强的权力正是目前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正是缺乏道德的权力和缺乏权力的道德之间的碰撞,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
04 “一句无法指导实际行动的口号”
尽管“黑人权力”这一口号蕴含着诸多的积极因素,能够与民权运动的某些宗旨相呼应,但是我认为,“黑人权力”的弱点在于它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的行动指导能力,因而不能成为民权运动的基本战略。
从表面上看,“黑人权力”是一句令人心动的口号,但究其实质,其根源在于一种认为黑人根本无法赢得胜利的虚无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讲,它认为美国社会已经腐败堕落,罪孽深重,无可救药,根本没有希望从内部得到救赎。当然,这种想法情有可原,因为白人权力机构从来不曾真正致力于实现黑人的平等,并且秉持着一种关门闭户的顽固保守心态。但是,“黑人权力”这个口号仍然带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问题,注定要失败。
在20世纪之前,几乎所有革命的源头都是希望和仇恨。而所谓的希望,表现为人们日益渴望实现自由与公正。印度圣雄甘地所领导的运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革命运动的基础是希望与爱,是希望与非暴力。从1956年的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到1965年的塞尔玛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也体现出了这个革新特点。我们心怀希望,将传统革命的仇恨转化为积极的非暴力力量。对一般人而言,只要他们的希望转化为现实,就很少有人去质疑非暴力的效果;但是,一旦希望破灭,或者情况虽有改进但仍不尽如人意,或者他们看到更深重的贫困、更多的种族隔离学校以及更龌龊的贫民窟,绝望就会蔓延开来。

只是,革命虽然源于绝望情绪的爆发,却不能靠绝望情绪维持下去。这就是“黑人权力”运动的最终无法解决的矛盾。“黑人权力”运动号称美国最具革命性的社会变革风潮,然而,它却拒绝了一个让革命之火熊熊不息的元素:永恒的希望之光。如果希望消亡了,一场革命就只能退化为一个毫无特征的闹剧,迅速被遗忘,于现实徒然无益。黑人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只在绝望中汲取营养的哲学,交给一句无法指导实际行动的口号。
我经常在亚特兰大的家里以及我在芝加哥的公寓里,与“黑人权力”的拥护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展开辩论。他们热衷于为暴力和骚乱辩护。他们从来不会引用甘地的思想,也不会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他们的圣经是弗朗茨·法农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属马提尼克的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与革命家。他是20世纪研究非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近代最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评家之一。他从黑人的角度探索黑色非洲,并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他在阿尔及利亚完成了《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深度反映和探讨了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殖民者剥削的痛苦。所著的《大地上的受苦者》。这位来自马提尼克的黑人精神病学家曾前往阿尔及利亚,与“祖国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并肩斗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这是一本很好的书,里面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法农在书中声称,被压迫者的暴力倾向不但是心理健康的表现,而且在战略上也毫无瑕疵。因此,那些支持“黑人权力”运动的美国年轻黑人,意识到自己也是“大地上的受苦者”中的一分子,经常引用法农的思想,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带来自由。
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美国,黑人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压迫者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不需要约翰逊总统告诉我们这一点,只要记住暴动的黑人只有对手人数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当然,我们也有过一些勇敢起义的兄弟,如丹马克·威瑟(Denmark Vesey)和奈特·特纳(Nat Turner),但是,他们的行动恰恰应该给我们敲响警钟,说明暴力叛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任何想要发动和领导暴乱的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一举动可能造成的伤亡。这是一场少数人面对武器精良、后备充足的大多数人的较量,是一场狂热的右翼分子求之不得的借机消灭成千上万黑人男女和儿童的战斗。
黑人们有时候认为,1965年的瓦茨暴乱和其他城市发生的一些骚乱,是争取公民权利的有效行动。但是,一旦你追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这些举动到底取得了什么具体成果时,他们就结结巴巴无话可说了。这些暴乱充其量就是获得了一点额外的脱贫资金——这是那些受了惊吓的政府官员调拨给他们的,或者是政府多派来几辆洒水车,给贫民窟的孩子们降温。暴乱行动在任何方面,都不曾像有组织的抗议示威那样取得过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让暴力倡导者说出哪种反抗方式有效时,他们的回答又显然不合逻辑。有时,他们会说推翻种族主义国家和地方政府。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除非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武装部队的忠诚,失去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否则试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国内革命,从来没有一例取得过成功。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非暴力也是一种权力,但它是对权力正确而良性的使用。它富有建设性,既可以拯救黑人,又可以拯救白人。主张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其实是受到了一些非理性恐惧的控制,比如,害怕丧失经济特权,害怕社会地位改变,害怕不同种族间通婚,或者害怕不得不适应新情况。数不清的白人被这些恐惧折磨着,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于是,有些人选择逃避,无视种族关系的问题,对所涉事件也视而不见;另外一些人寄希望于法律操作,号召大规模抵制;还有一些人则采取卑鄙暴力的行为打击黑人兄弟,希望以此来消除内心的恐惧。然而,这些方法都根本不起作用!他们这么做,非但消除不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反而使他们在恐惧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白人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教育和善意,通过寻找良知,通过直面种族融合这一事实,让自己从这种恐惧中脱身出来。同时,为了克服恐惧,白人也要借助于黑人运动对他产生的精神冲击,而这只有通过黑人坚持非暴力才能够实现,因为非暴力意味着强大而凌驾于一切的爱,也只有非暴力才能最终减轻白人社会的恐惧。

05 “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一个追随共识的人”
有人问我:“现在暴力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你不与时俱进,还坚持自己的非暴力观点,会不会失去黑人们的支持,变得落伍?”
我的回答永远不会变。我坚信,绝大多数黑人是反对暴力的,即使他们不反对,我也没有兴趣去做一个人云亦云的领袖。我不会按照盖洛普盖洛普(Gallup)是一家以调查为主营业务的全球著名的绩效管理咨询公司,于1935年由乔治·盖洛普所创立。民意调查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猜想,在当时的德国,一定也有一些领袖坚决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所做的那些事情,但他们接受了民意调查的结果,发现反犹主义是普遍的趋势。于是,为了“与时俱进”,为了“不落伍”,这些人向迄今历史上最卑劣的邪恶势力屈服了。
总而言之,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一个追随共识的人,而是一个长于斡旋、促成共识的人。即便所有的美国黑人都转而支持暴力,我仍将坚持自己孤独的声音,宣称那是错误的。这么说听起来似乎很傲慢,但我的本意只是说明,我立志做一个坚守信念的人,而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有时候,一个人会在生活中寻觅到一个意义非凡的信念,对它爱若珍宝,能为它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我在非暴力思想中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信念。
我无法相信,上帝要我去憎恨。目睹过太多的暴力后,我已经厌倦了暴力。我在南方警察的脸上,也看到过太多的仇恨。我不想让曾经压迫过我的人,指导我该用什么方法去反抗。他们对我们使用暴力,用仇恨,用步枪,用手枪,我不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层次,我想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是自制燃烧瓶所不具备的。
“黑人权力”运动最大的悖论之一是,它一直宣称不会效仿白人社会的价值观,但在倡导暴力这一问题上,它其实就模仿了最败坏、最残酷、最野蛮的美国生活的价值观。美国黑人从来不是大屠杀的刽子手。他们不曾在主日学校谋杀过孩童,也没有把白人像果实一样吊在树上。他们从来不是帽兜蒙头的暴力滋事者,不会随意对人处以死刑,更不会随意把谁溺死在水里。
我关切的是黑人在美国实现完全的公民身份,然而,我也同样关注我们的道德的正直和灵魂的健康。因此,我坚决反对以任何恶意、仇恨和暴力的方法去获得自由,因为这就是压迫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方式。仇恨不仅伤害被憎恨的人,也挫伤仇恨者自己。仇恨就像猖獗的癌症,不仅腐蚀一个人的性情,而且蚕食他的生命。我们内心的许多冲突都植根于仇恨,因此,精神科医生说:“或者爱,或者灭亡。”仇恨是一副重担,一旦背上就让人不堪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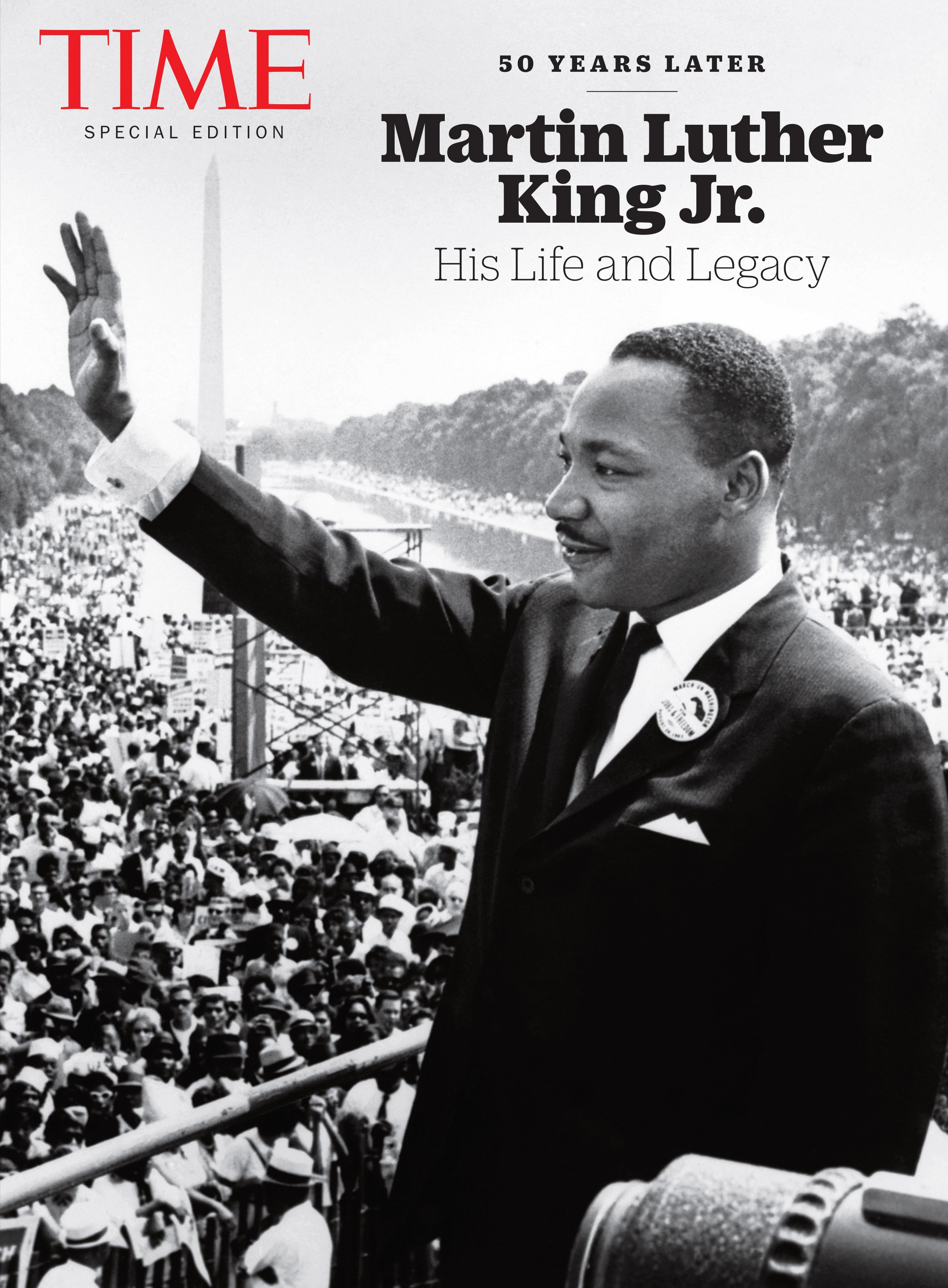
人性总是在期待某些新的东西,而不只是盲目地效仿过去。如果我们真诚希望社会前进一步,如果我们有翻开一页新篇章的诚意,如果我们真心渴望人类焕发出一种新姿态,那么,我们就必须让人类远离漫长而凄凉的暴力黑夜。难道这个世界需要的新人不是主张非暴力的人吗?朗费罗(Longfellow)曾经说过:“这个世上的人若非砧板即为铁锤。”我们必须成为塑造新社会的铁锤,而不是听任旧时代摆布的砧板。这不仅会让我们成为新型人类,而且会赋予我们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阿克顿勋爵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全名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常简称为阿克顿勋爵,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他对美国政治非常感兴趣。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完全支持美利坚邦联(即南方阵营)。他认为,在美利坚邦联里,州的权力高于中央集权政府;而所有历史都证明,中央集权必然导致暴政。他的态度使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转而支持南方。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或者绝对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种力量将是充满爱和正义的力量,能把黑暗的过去转变成光明的未来,能把我们从疲惫的绝望带到升腾的希望。这个黑暗绝望、罪孽深重的令人困惑的世界,正翘首期盼着这种新型的人类,这种新生的权力。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马丁·路德·金自传》一书第29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