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3年的一个夏日夜晚,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经历了一场“男式说教”(Mansplaining)。在阿斯彭郊外森林的派对上,一位男士邀请索尔尼特谈谈自己写的书,但他从未想过要认真聆听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只是在等待一个插话、自我展示的契机。他打断了索尔尼特的发言,开始对着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近期出版的一本“重要图书”的看法,直到别人三番五次地提醒他,眼前的这名女性就是这本“重要图书”的作者,他方才从自鸣得意的长篇大论中暂停片刻。
在索尔尼特与所有女性的一生中,还有无数个被“男式说教”轻视、打断的时刻。当她们公开言说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时,总有被挑动神经的男人(当然,也有一些爱“男式说教”的女人)来质疑她们故事中所说的一切,哪怕最不相干的细枝末节也会被这些居高临下的神探挑出来,进行一番演绎推理以证明女性的讲述充满漏洞,她们的情绪、经历、记忆根本不值得相信。
“如果一个男人的行为准则是你无权说话,无权定义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可以是在餐桌前和会议上打断你的发言,也可以是告诉你让你闭嘴,或者在你开口说话的时候威胁你,或者因为你发声而殴打你,或者为了让你永远沉默而杀了你。”在《爱说教的男人》一书中,索尔尼特指出,在“男式说教”、厌女语言、家庭暴力、强奸的背后,是女性声音经年累月遭受的压抑。男性长期占据“真理”,他们告诉女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应该被感受的,她们对日常言说没有权利,因而也就对自身的经历、观点乃至身体没有权利。从“男式说教”到强奸凶杀,是一场不断下坠的“沉默滑坡”。
神话中的卡桑德拉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遭到诅咒,她能预言真相,却被看成是疯子。卡桑德拉式的诅咒不仅在于所说之事无人相惜,还在于由自我压抑、怀疑、困惑、羞愧以及外部暴力组成的同心圆对女性“叙述”能力的否定和破坏。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从《爱说教的男人》中摘编了关于“卡桑德拉诅咒”的影响以及女性主义对其回击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美] 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 张晨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5
《与狼共舞的卡桑德拉》(节选)
文 |[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译 | 张晨晨

卡桑德拉是那个说出真相却无人相信的女人。在我们的文化中,她的故事远没有“狼来了”的故事——就是那个不断说同样的谎言直到不再被人相信的男孩——那么广为流传。也许更多人应该知道她。作为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卡桑德拉受到这样的诅咒:她拥有准确预言未来的能力却无人相信。她的人民认为她是一个疯子和骗子,在一些版本的故事中,人们甚至将她囚禁起来,直到阿伽门农将她作为战利品掳走。她最终和他一起被随意地杀害。
当我们在性别战争的汹涌波涛中航行时,我总是想起卡桑德拉。因为在那些战争中,可信度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根本权力,而女人总是被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些决定性欠缺。
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位于现存秩序中心的男人,尤其如果这件事和性有关,那么常见的回应往往不光是质疑她指控的事实,连她说话的能力以及权利也会被质疑。一代又一代的女人被告知,她们要么在做梦,要么太糊涂,要么在设局下套、阴谋陷害,要么撒谎成性,要么是以上全部。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拒绝把女人的话当真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如何频频陷入自相矛盾和歇斯底里之中——这些恰好是女人总会被指控的特质。
“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源自希腊语的“子宫”(uterus),因为人们曾经认为这个词所指示的情感状态来自不稳定的子宫,男人自然而然可以免于这样的诊断。现在这个词一般指自相矛盾、过度紧张或者困惑不解。在 19 世纪晚期,歇斯底里是一种常常被诊断出的病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老师让—马丁·沙河(Jean-Martin Charcot)曾公开展示“患有歇斯底里的女人”的痛苦。某些情况下,这些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的女人还会经受虐待、由虐待引起的心理创伤,以及无法表达创伤缘由的无力。
年轻的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一些病人,她们的问题似乎源自童年时期遭受的性虐待。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诉说的是不可言说之事:即使在今天,战争和家庭生活中那些最残忍的创伤是如此违背社会道德观念,对受害者的灵魂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仅仅讲述它们就是一种折磨。性侵就像酷刑,是对受害者身体完整性的权利、自决权和自我表达权的攻击。它试图完全抹去受害者的声音和权利,而她必须从湮灭中站起来才能发声。
讲述一个故事,拥有一个故事,令讲述者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战胜创伤的最好的办法之一。令人惊奇的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曾经能够说出她们的不幸遭遇,而他最开始听到了。他在 1896 年写道:“我因此论证,每一例歇斯底里症的背后都存一起或数起孩童时期性经验。”但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转而写道,如果他选择相信他的病人的话,那么“在所有情况下,你就得指控父亲,不排除我自己的父亲,是变态”。
女权主义精神科医师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她的著作《创伤与恢复》(Trauma and Recovery)中写道,“他的通信很清楚地表明,他的假说重大的潜在社会影响越来越让他不安……因为这样的困境,他不再倾听他的女性病人。”如果她们说的是真的,他就得挑战整个父权权威的结构体系来支持她们。赫曼又补充道,“一种顽固的坚持让他执着于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他坚称那些女人其实是在幻想,并且渴望那些她们控诉的性虐待经历。”对所有逾越法规的权威和侵害女性的男性罪犯来说,这就像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来就是她想要的。她想象出来的。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沉默,就像但丁的地狱一样,由若干同心圆组成。首先是内在的压抑、自我怀疑、抑制、困惑和羞耻,这一切都让发声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然后是恐惧,担心由于发声而被惩罚和排斥的恐惧。苏珊·布里森(Susan Brison)现任达特茅斯学院哲学系主任,曾经在 1990 年被一个陌生男人强奸。他骂她“婊子”,让她闭嘴,然后掐住她的脖子,用石头砸她的头,最后把她扔在路边等死。后来她发现自己难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下定决心讲述和书写我经历的强奸是一回事,可是找到讲述的声音是另一回事。即使在我破裂的气管痊愈之后,我还是有说话的困难。我从来未曾完全失声,可是会常常犯我的朋友叫做‘破碎言说’(fractured speech)的毛病。犯病的时候我会口吃结巴,无法把词语串成一个简单的句子,那些词语就像破碎的项链一样散落一地。”
在这个圆环之外是那些外部力量,它们试图通过羞辱、霸凌或者彻底的暴力,包括致死的暴力,令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发声的人噤声。如今,这个圆环在威胁很多高中和大学里的强奸受害者。这些年轻的女人们常常因为发声而被骚扰或威胁;有些人因此而变得有自杀倾向;很多潜在的罪行未被调查或起诉;很多美国大学继续让无数未被惩罚的强奸犯顺利毕业。
最后,最外面的沉默同心圆是当故事终于被讲述,当讲述者没有被直接噤声,故事和讲述者的可信度却遭到质疑。这个领域的敌意如此强烈,你大概可以把弗洛伊德选择相信他的病人的短暂时光称为虚假的黎明。尤其是当女人发声讲述性犯罪的时候,她们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就会遭到攻击。到今天这种反应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有一种清晰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历史悠久。
这种模式最早受到全面挑战是在 1980 年代。关于 1960 年代的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而 1980 年代发声的那些革命性变化却时常被忽视和遗忘——不光是世界各地被推翻的政权,变化还发生在卧室里、课堂上、工作场所、街头,甚至是政治的组织形式中(开始采用女权主义影响下的合意原则以及其他反等级制、反威权主义的组织技巧)。那是一个爆炸性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如今常常被认为是冷酷的反性主义,因为女权主义指出性是一个权力场,而权力倾向于滥用和虐待,还因为它描述了这种滥用的性质。
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推动了立法,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她们还定义和命名了很多在此之前从未得到承认的违法行为的类别本身。通过定义和命名,她们以此宣布权力的滥用是个严重的问题,男人、老板、丈夫、父亲——以及普遍的成年人——的权威需要被质疑。她们为乱伦、儿童性侵、强奸和家暴的故事创造了一个讲述框架和支援网络。这些故事才能够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叙事的引爆点,因为太多太多曾经沉默的人决定讲出自己的经历。
1991 年 10 月 11 日,一名法学教授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传唤作证。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 布什提名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当时的场合是任命大法官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confirmation hearing)。作证的人叫做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之前的私人采访中以及在听证会上,希尔讲述了托马斯担任她的上司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强迫希尔听他谈论他看过的色情电影和他的性幻想,还给她施压试图和她约会。当她拒绝后,希尔说“他不能接受我的解释的有效性”,就好像“不行”本身不是一个有效的回答。
虽然她因为当时没有采取行动而受到批评,我们得记住,女权主义者直到最近才发明了“性骚扰”这个词并界定其概念。直到 1986 年,在她描述的经历发生之后,最高法院才认可工作场所的此类行为是违法行为。当 1991 年希尔终于开口发声的时候,她受到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攻击。质询她的人全都是男人,共和党议员的问题尤其滑稽,极尽怀疑和揶揄之能事。参议员艾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or)询问了一个证人,这个人根据一些短暂的会面作证称希尔对他抱有性幻想。斯柏科特问:“你觉得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希尔教授想象出或者幻想出了她指控托马斯的那些事?”又是弗洛伊德式的框架:如果她声称发生了一些恶心的事情,那么其实是她希望它发生了,或者她根本不能将二者分开。
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喧嚣、一种内战,因为很多女人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性骚扰是什么样子,太知道举报这种事情会有很多不愉快的后果,但是很多男人并不知道。短期来看,希尔遭受了种种羞辱的考验,而托马斯最终仍然被任命为大法官。最严苛的指控来自保守派记者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他先是发表了一篇文章,继而又发表了一整本书来诋毁希尔。十年后,布洛克懊悔他对希尔的攻击和他的右派立场,他写道:“我为了毁掉希尔的信誉不择手段,采取了一种漫无目标的攻击方式。我把来自托马斯阵营的几乎所有毁谤她的指控——这些指控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搜集混合起来,然后一股脑儿砸向她…… 用我当时的话说,她‘有点疯癫又有点放荡’。”

从长期来看,“我相信你,阿妮塔”成了一句女权主义口号,而希尔则被认为开启了一场承认并回应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革命。听证会一个月后,国会通过了《1991 年民权法》,其中规定了性骚扰受害者可以起诉她们的雇主以获得损失补偿和欠付工资。当人们终于有渠道起诉工作场所性骚扰后,相关案件数量激增。1992 年大选年又被戏称为“女性之年”,这一年卡罗尔·莫斯利·布朗(Carol Mosley Braun)成为第一位入选参议院的黑人女性,参议院和国会的女性议员数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女人说出让人不舒服的有关男性不端行为的话时,她仍然会被说成胡言乱语,阴谋算计,撒谎成性,一个认识不到那不过是风流韵事的怨妇,或者以上全部。这些变本加厉的回应让人想起弗洛伊德讲的那个关于破水壶的笑话。一个男人向他的邻居归还他借的水壶,邻居指控他把水壶打破了,男人回答说他完全没有打破,水壶借给他的时候就已经破了,而且他根本就没有用过。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和他的维护者的反击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她最后成了破水壶。
就在今年,当迪伦·法罗(Dylan Farrow)一再指控她的养父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猥亵她时,她成了最破的那只水壶。攻击者蜂拥而至。艾伦发表了一篇长篇檄文,声称他绝无可能在阁楼猥亵养女,因为他一直讨厌那间阁楼,迪伦一定是受到了她母亲米娅(Mia)的指导和“洗脑”,米娅可能是迪伦发表的指控文章背后的影子写手,而且米娅“毫无疑问”是因为一首关于阁楼的歌想出了这个点子。这里又存在着性别区分,很多女性觉得这个年轻女人是可信的,因为她们全都听过类似的事情,而很多男人却好像只看到了不实指控的例子并夸大其普遍性。麦克马丁托儿所的幽灵再次浮现,提起它的人却好像对这场审判及其结果有着错误的回忆。
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探讨了强奸、猥亵儿童和战争创伤,她写:
掩盖和噤声是侵犯者的首选防御手段。 如果掩盖不管用, 侵犯者就会攻击受害人的信誉。 如果他不能让她永远噤声, 他就会想方设法确保没有人相信她……每一桩暴行过后,人们总是会听到这样预料之中的维护:这事儿没发生过;受害者在撒谎;受害者言过其实;受害者自作自受;无论如何,是时候忘记过去向前看了。侵犯者的权力越大,他就越有能力命名和定义现实,他的说辞就会赢得越彻底。
在我们的时代他们并不总是会赢。我们仍然在一个战斗的年代,一场关于谁拥有说话的权利、谁拥有被相信的权利的战斗,压力来自双方。男性权利运动和广为流传的错误信息创造了这样一种观念:毫无根据的性侵指控极为普遍。“女人作为整体是不可信任的”,“强奸案误判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些推断被用来让女性个体噤声,用来避免讨论性暴力,甚至把男性塑造成首要受害者。这样的逻辑就像讨论美国的选举欺诈——其本身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罪行,长期以来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重要影响。但是保守派近年来声称选举欺诈无处不在,并以此为借口剥夺那些很可能投他们反对票的人群的投票权:穷人,非白人,学生。
我并不是说女人和孩子不会撒谎。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会撒谎,但后两种人并不会不合比例地更容易撒谎,而男人——这个群体包含了二手车销售员,闵希豪森男爵(Baron von Munchhausen)a 和理查德·尼克松 ——并不会特别诚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女人爱撒谎爱头脑不清的古老话术仍然被经常使用,我们应该看清它的真面目。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所著名大学做关于性骚扰的培训,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在学校的商学院做演讲,一名年纪较大的男教授问她:“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仅仅一个女人的举报就要展开调查?”她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他故事则是关于女人——包括学生、职工、教授、研究员——争取信任有多艰难,尤其当她们的证言是针对地位很高的侵犯者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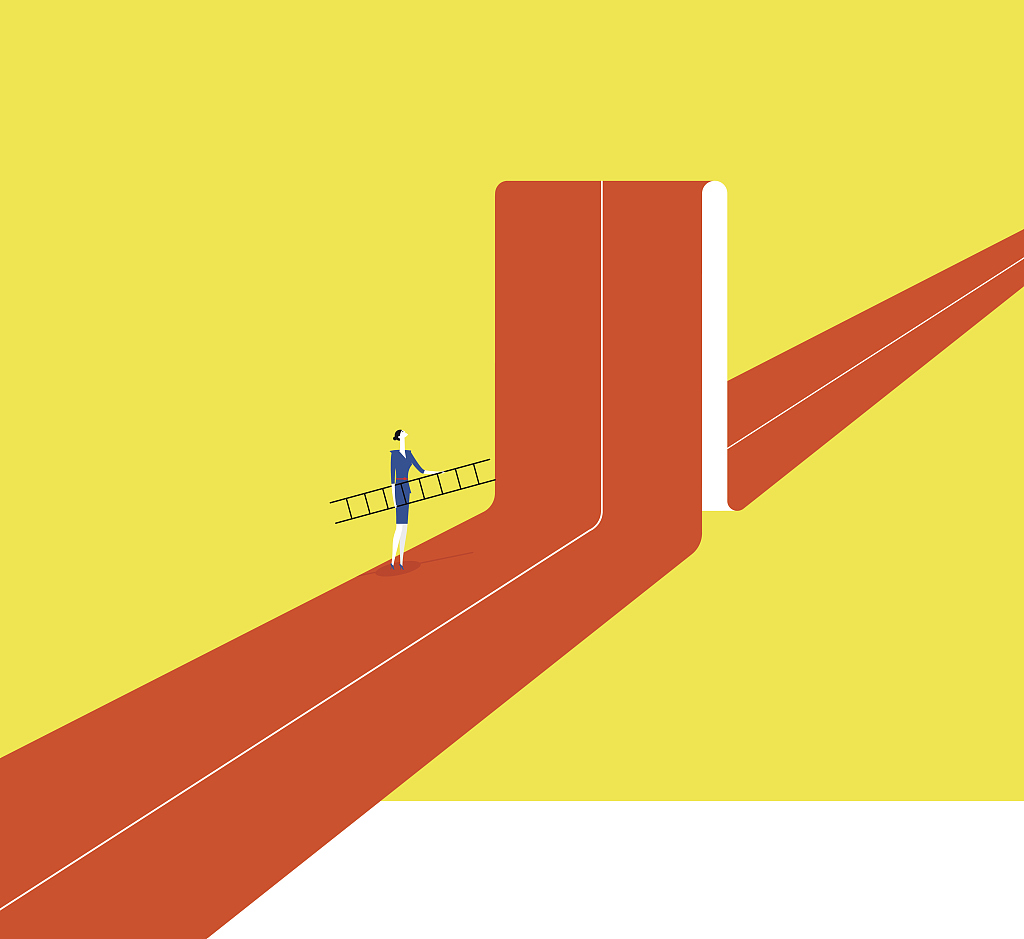
今年夏天,老古董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声称世界上只有“想象出来的校园强奸泛滥”,他说当大学或者女权主义者或者自由派把受害者变成一种可以带来特权的、让人觊觎的身份,受害者就会层出不穷。年轻女性在推特上创造了 #survivorprivilege(幸存者特权)这个标签来回应他:“我以前倒没意识到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严重焦虑和抑郁中生活是一种特权”,“# 我应该保持沉默吗——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我在撒谎”,她们的推文写道。威尔的专栏文章其实完全没什么新鲜的,不过是“女人天生不可信任,这些强奸指控其实都没什么好关注的,我们应该往前看”的老一套罢了。
今年早些时候我自己也体验了这种经历的缩微版。我在社交媒体上贴了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那篇文章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1970年代,那两段话讲述了我当时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嬉皮成年人挑逗刚刚步入青少年的我)。一个陌生人——一个有钱有文化的男人——立刻在脸书回帖抨击我。他的愤怒和毫无依据的自信,那种他有能力对这件事做出判断的自信,都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你在夸大事实,你给的‘证据’还不如一个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记者给得多。你‘觉得’这是真的所以你就是说是真的,呵呵,我把这叫做‘扯淡’。”我必须得提供证据,好像你真的有可能为好几十年前发生的这些事提供证据一样。我是歪曲事实的坏人。我觉得自己很客观,可其实很主观;我把我“觉得”当成我“认为”或者“知道”。这些都是太熟悉不过的指责和太熟悉的愤怒。
如果我们能承认甚至命名这种攻击信誉的套路,那么每一次当一个女人发声的时候,我们就能跳过一次又一次探讨女人的可信度这个环节。关于卡桑德拉的另一件事:在这个神话最有名的版本中,她的预言之所以无人相信是因为她拒绝和阿波罗发生性关系,这位神祇对她施加的咒语所致。试图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就会导致失去信誉,这个线索早就在那里了。但是现实中的卡桑德拉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决定相信谁和为什么,我们就能祛除这个咒语。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爱说教的男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