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0年代的伯蒙塞,小青年席德·柯瑟靠偷拿市场篮子里的水果充饥;路易·斯特莱德在历史名城巴斯的贫民窟长大,早已习惯在阴沟里觅食;德比郡的约瑟夫·夏普穷得只能“光着腿脚”,依靠“茶渣和面糊”度日。柯瑟、斯特莱德和夏普三人,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穷苦儿童的冰山一角。女孩们蜷缩在围巾里,男孩们飘忽不定的眼神里充满了疲惫,维多利亚时期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人何以如此贫困?英国已经富得流油了。19世纪末,柏油马路、收割机、卫生间和电报等伟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英国几乎就等于进步和繁荣的代名词,但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亨利·朗特里(Henry Rowntree)等社会观察家却发现,英国工人家庭日益深陷于哥特式梦魇一般的贫苦生活,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玛·格里芬(Emma Griffin)的新作《养家之人》(Bread Winner)就旨在探讨这一问题,该书既有精到的论述,又不乏真挚的感情。她没有向曲线图或直方图寻求答案,而是选择直接走向人们,走向那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里过着贫穷生活的“反常”之人。她的原始资料是662份生活史,来自工人阶级的男性与女性,大多写成于1970至1980年代,存放在地方档案馆或者由社会主义者的小型出版社出版。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不在于格里芬认为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能提供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宏观经济的剖析,甚至也不在于他们可以交出清晰而完整的家庭账目。她追问的是家庭财务状况引发的一系列感受及其构成:父亲如何把挣来的钱藏在袜子里;母亲接到别人交付的一大堆缝补工作之后表现得如何烦躁;刚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姐回家如何对新衣赞不绝口。这一切都不是单纯的奇闻趣事,格里芬主张,恰是这一类证据令我们窥知到“经济生活具有深刻的人文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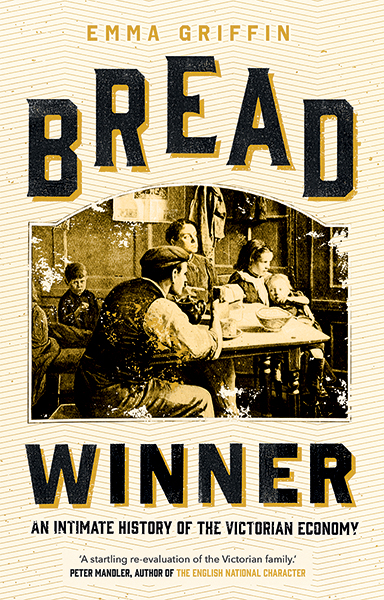
乍看之下,格里芬究竟要怎样从这堆杂音里提炼出一套融贯的模式,是不太明了的,每个故事似乎都自成一体:有在兰开夏郡挖矿的,有在剑桥郡种田的,还有在伦敦当裁缝的——但这一团乱麻也逐渐浮现出了某种体系性。结论表明,有20%的回忆录作者称,父亲的薪酬在这一时期其实开始有所提高。然而,与其说涨薪令家庭处境得到广泛改善,不如说它成了埋葬天伦之乐的先声。例如,约翰·墨菲回忆称,1890年代父亲拿到的加班工资“并没有给我家带来多少利好”。相反,周末酗酒和手忙脚乱地偿还旧债倒成了常态。约瑟夫·夏普略带苦涩地提到,父亲新增的收入都拿去喂养宠物狗了,孩子们并没得到什么好处。
假如母亲能够左右局面,在不断增多的国家财富里分得自己应有的那一份,那不负责的父亲也不至于把事情彻底弄砸。但格里芬却屡次发现,女性的工资不过是男性的九牛一毛。无论你缝补了多少衣服,打扫了多少屋子,赚到的工钱都是不够用的,更别说养家糊口了。离开丈夫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处境将举步维艰,你的抚养资格可能会被剥夺。

格里芬的要点并不在于妖魔化工人阶级男性,而在于表明“养家糊口”者这一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一种压迫男性的渠道,对依赖他的人而言也类似。许多回忆录作者称,父亲在面临巨大压力——孩子夭折,工作事故或当地经济的衰退——时会变本加厉地酗酒。格里芬还敏锐地觉察到,回忆录作者或许并不在乎提到父亲酗酒的经历,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各种变故,却仍旧会有羞耻之感。而那些前往或被送到庇护所、或与房客有私生子的母亲,则连分享经历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更别说出现在孙辈们写下的动人故事里了。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