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美东时间11月16日凌晨,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我赢了大选”,他的这条推文随后被推特官方贴上标签“与官方消息源对这场选举判定的结果不同”。据美国媒体7日测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重要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胜出,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然而特朗普本人及他的支持者似乎都无意接受这一结果。当地时间14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MAGA万人大游行”,喊出的口号是反对“选举舞弊”,呼吁特朗普“再干四年”。
在新冠疫情横行肆虐之际,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折射出了美国国内民意分裂严重的现状。今年7月,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特别是如果未来出现某种极端戏剧化的场面,特朗普声称自己成就非凡但遭受迫害,而不是接受败局下台。”她的判断非常符合现实情况。
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将政治极化的源头追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指出,彼时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刺激保守派找到新的同盟力量,谋求反击;与此同时,占上风的自由派却在政策和实践中出现失误,逐渐远离了他们最庞大的选民基础——工人和中产。与此同时,共和党吸纳了传统主义保守派,将“文化战争”引入选举辩论中。两党之争越来越围绕“议题”而非“问题”展开,造成了两派越来越无法理解彼此的局面,然而“议题”在很多情况下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例如阶级流动性丧失、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平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本首次出版于1991年的著作中的许多论述至今依然有效。

自2016年特朗普一跃成为政坛黑马并意外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反思“自由主义的溃败”究竟是为何。霍赫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一书中分析认为,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在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拉大的时期感到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她呼吁自由派去理解保守派的忧虑与关切,去讲述自己的愿景,去重建社会共识。
也有越来越多学者看出,自由派政党应当从“文化战争”中抽身,直面普通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即经济。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积极声援伯尼·桑德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抨击特朗普偏向维持现状、保护富人利益的经济政策。2017年特朗普政府履新之际,萨克斯的专栏文集《重塑美国经济》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三个关键点”的改革方针——以基础设施升级为核心,推动智能、公平、可持续的改革,重建新型美国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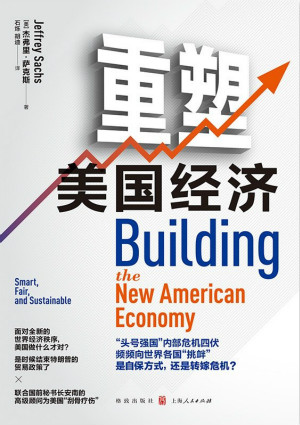
[美] 杰弗里·萨克斯 著 石烁 胡迪 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5
在大选结果揭晓之际,界面文化采访了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政治评论专栏作家徐曦白,就本届大选政治极化愈发严重的原因、下一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根据徐曦白的观察,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依然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其重大失误是忽视了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内部的复杂性,未能进行有效动员。他认为,特朗普虽然连任失败,但他的支持者依然众多,这意味着共和党阵营的“特朗普主义”依然势力强大,共和党将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并有可能在四年后推出一位更有煽动性的总统候选人。
在徐曦白看来,对于左翼式微的现状,自由派内部难辞其咎。自由派一直没有找到和特朗普支持者有效沟通的方式,反而对他们态度轻蔑,“但稳固的政治联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应该争取的对象,以及空谈理论和秀优越感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左翼应当尽快走出文化战争的泥沼,回归左翼政治的本源——工人的权益、就业、收入、住房、贫困问题、公共医疗。唯有这样,自由主义才能洗刷掉“无道德”的污名,重拾合法性。
01 政治极化愈发严重,民主党“虽胜尤败”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新冠疫情对本届大选的影响,这是“特朗普基本盘出现松动”的主要原因吗?此前阿莉·霍赫希尔德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认为,虽然郊区“轻微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拜登,但特朗普的票仓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
徐曦白:美联社的选前民调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些人中73%支持拜登;与之相比,2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更重要,他们当中81%支持特朗普。由此可见,两党支持者对新冠疫情的看法截然相反。民主党支持者自然认为特朗普不负责任,草菅人命,要在他的诸多罪状之上罪加一等;但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眼中,他是在努力拼经济、拼就业,使人民生活不受疫情影响。如果你已经信任特朗普,那么这种宣传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这些支持者拒绝戴口罩,参加各种反对隔离的示威,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会觉得自己也在拼经济,救美国,认同感得到强化。一些底层选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私营业者,没有城市精英那样的积蓄和缓冲,是否取消隔离政策,重开经济,对他们来说是最基本的生计问题,因此他们也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我赞同霍赫希尔德的看法,美国的政治极化更严重了,双方阵营的支持者更偏执了,新冠疫情也是加剧这种极化的因素之一。它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老年白人、高学历白人和温和共和党人小幅转向拜登的趋势。但从有限的选后数据来看,在全美新冠死亡率最高的100个县中,有68个县的特朗普得票率出现了上升,这些县大多位于农村。新冠疫情可能强化了这些地区的特朗普支持率。当然,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界面文化:和上一届大选相比,本届大选呈现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徐曦白:这次大选是多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双方都视其为生死决战,进行了极限动员,投票率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高的。由于疫情影响,提前投票(包括邮寄选票)的选民超过1亿,再创历史新高。邮寄选票中支持拜登的比例接近七成,而几个重要的摇摆州都规定选举日结束后才开始清点邮寄选票,因此媒体报道呈现出特朗普开盘领先、拜登后半程绝地反攻的节奏,甚至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因此怀疑后期邮寄选票的计票有假。实际上这完全是开票顺序造成的假象,倘若这些州先开邮寄票,后开现场票,那么媒体报道很可能会变成“拜登开盘领先,特朗普逆袭失败”。
根据出口民调的数据,拜登的全国得票率与希拉里相比约有1.5%的增长,主要来自城郊(近郊)的白人和高学历白人选民,其支持率提高了超过10%。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共和党大幅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和特朗普本人都颇有微词,他们的转向是民主党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朗普仅在高收入(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中支持率小幅上升,这得益于他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同时,拜登作为宾夕法尼亚“蓝领”出身的候选人,稳固了锈带地区威斯康辛、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的低收入低学历白人票源,这几个州的大城市投票率推高后形成的人口优势,也对民主党有利。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拜登最终在这几个州险胜,保住了希拉里当年丢失的“蓝墙”,成为本次大选胜选的关键因素。
这次选举在城乡和教育维度上的极化更严重了。城市选民比以前更支持民主党,农村选民也比以前更支持共和党。近郊选民的投票意向开始靠近城市选民,而远郊选民则向农村选民靠拢。从地图上看,就是蓝的地区更蓝,红的地区更红。
在种族维度上,极化反而减轻了。尽管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整体大幅下降,但在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却大幅上升。其中,拉丁裔选民的支持率增幅在10%左右,大多来自低收入低学历人群,在亚裔和非裔中也有2%-5%的增长。
拜登虽然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人们事先期待的“蓝潮”并没有出现,在几个摇摆州都只是险胜,可以说“虽胜尤败”。民主党在国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表现都非常不理想。众议院选举本来预期可以趁着2018年的气势继续攻城略地,结果反而丢失了不少席位,优势从超过30席锐减到10席左右。参议院的形势更加严峻,虽然增加了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两个席位,但丢失了深红州阿拉巴马的席位,此消彼长,只增加了一个席位,不足以获得参议院多数。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在选前砸下血本猛攻特朗普的重要盟友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Mitch McConnell),针对每位投入的选举经费都接近一亿美元,呈碾压态势,但最终这两位仍以超过20%的优势获胜。
民主党国会选举失利的原因之一是选票分离(ticket-splitting)现象大大减少,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总统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和参议员、众议员、州议会候选人的名字印在同一张选票上,一次投票即可完成多个选举。选民有时会选择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但把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国会议员或州议员候选人——这种选票分离现象在过去十分常见。尽管总统候选人对同党派的议员候选人有一定“加持”作用,但地方因素占主导。在一些深红州,深耕基层的民主党候选人依然有机会凭借个人能力当选。但最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政治取向极化,地方选举中全国性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重,选民越来越不愿意挑选不同党派的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使得选票呈现出高度的党派一致性,也意味着民主党在深红州获得国会议员席位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反之亦然。

界面文化:鉴于今年“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如火如荼,我们很容易认为种族会是影响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有趣的是,今年西裔和非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都比四年前高,拜登相比四年前的希拉里获得的额外支持反而是来自白人选民。这是为什么呢?
徐曦白:民主党人一直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迁,白人人口逐渐减少,少数族裔人口逐渐增加,后者又是天然的民主党支持者,仅靠这一点就足以“躺赢”共和党。2020年的大选表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少数族裔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具有相当的多样性,不同族群之间也存在“鄙视链”。亚裔和拉丁裔虽然同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对非裔的境遇普遍缺乏同情,甚至因为治安和积极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等问题对非裔抱有强烈的排斥。即使在同一族群内部,情况也很复杂。比如拉丁裔来自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十几个社会和文化状况迥异的国家,其中有白人,有原住民,有混血,也有被贩运至此的黑奴后代。这些人中既有笃信天主教的保守主义者,也有年轻的自由派选民;既有第一代移民,也有早已在美国落叶归根、更认同美国人身份的老移民;既有知识精英,也有低学历的蓝领工人,后者在诸如治安、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看法与低学历白人不无相似,因此很容易被特朗普的话语吸引。这种复杂的成分构成和经济议题、文化心理的叠加,使得预测拉丁裔的投票意向变得十分困难。
实际上,拉丁裔选民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的重点争取对象,小布什在这方面就颇有建树。和2012年相比,2016年大选中的拉丁裔和非裔选民已经开始转向共和党,只是当时的转向幅度较小。到了2018年,这个趋势就相当明显了。在2018年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选举中,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尼尔森(Bill Nelson)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提高了2%-3%,但因为流失了大量拉丁裔选票而败选。特朗普此次在佛罗里达州胜选的原因之一,就是迈阿密地区的古巴裔选民中超过10%转投共和党——特朗普团队将拜登和民主党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这种恐吓宣传对逃离古巴的“反共”移民效果明显。10%的翻转足以抵消拜登在佛州其他地区的郊区和老年白人中的票数增长。
另一个特朗普大幅收获拉丁裔选票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南部与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地区。在这里的几个县,有多达30%的墨西哥裔选民改投特朗普,这与民主党长期以来忽视这里的选情,较少进行基层动员有关。特朗普团队在这里十分积极,“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打击体制精英的口号颇具吸引力,因为当地常有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后因腐败落马。墨西哥裔选民又普遍认为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来到美国的,或者已经成为“美国人”了,担心新移民会和他们形成竞争,反而会认同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最大的就业部门是执法机关,这些人本来就有反非裔情绪。BLM运动提出“削减警察经费”,令很多温和或偏保守的选民难以接受。而在全国层面上,当BLM进一步演变为暴力示威后,特朗普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口号更符合小企业主和商户对于稳定的需求。可以说,BLM运动虽然提高了一部分(特别是白人)对种族正义问题的关注,但同时也严重撕裂了少数族裔群体,把不少人推到了特朗普阵营中。

02 共和党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民主党未来十年将十分被动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大选后美国政局的走向?
徐曦白:首先,特朗普不可能认输。以他的性格,大概这辈子都不会承认败选。他不会甘于被遗忘,会继续鼓吹民主党大规模有组织作弊的阴谋论,将自己树立成受到体制和政治精英迫害的草根英雄。法律诉讼也会继续下去,虽然这些诉讼只是走过场,但这种姿态对稳固铁票仓十分重要。特朗普虽然败选,但他仍然获得了7100万张选票,在共和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铁票仓甚至比四年前更加稳固,这说明特朗普主义依然盛行,甚至更加盛行。在短时间内,他依然会是党内民意号召力最高的人物,可能到了2024年,他还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即使他本人不再参选,他也可能成为挑选下任参选者的“造王者”。共和党在他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毕竟获得特朗普铁票仓支持的诱惑实在太大。下一位总统候选人不会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只可能是更聪明、更极端、更有煽动性的人物。对民主党而言,他(我很确定不会是她)将是更难战胜的对手。
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总体上更偏向农村和低学历白人为主的州,这些州所占的总统选举人团权重更大、人均参议员数量更多,这对共和党来说是明显的制度性优势,民主党在最近几次大选中流失的也正是这部分选票。如果不能取得参议院控制权,通过新的法律重新划定选区、增加州的数量(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数量以解决制度性劣势,那么民主党将在未来十年中面临非常严峻和被动的局面。
短期而言,人们关注的焦点将是2021年1月的佐治亚州第二轮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必须同时赢得这两个席位才能在参议院中取到50比50的均势,并依靠副总统的一票获得微弱优势,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共和党主导参议院,那么拜登将成为跛脚总统。他固然可以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比如重返巴黎协定、重返世卫组织、修补与北约盟友的关系——但在国内政治中将面临严重掣肘,人事任命首先就会被参议院“卡脖子”,民主党提出的改革类法案也会被共和党批量否决。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统所在的党派在中期选举的表现一向欠佳。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可能会进一步丢失参议院席位,甚至丧失众议院多数,如果两院由共和党控制,那么无论拜登有多么大的雄心壮志,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可以参考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全面运用拖延和阻挠战术,所有人事和法官任命都被长期拖延,立法几乎陷入停滞。到2024年,民主党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失败。
界面文化:大选结果揭晓以前,许多观察者发现美国政见不同的选民之间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双方都视对方为邪恶化身而非政治对手。下一届美国政府要如何应对如此严重的党派分歧?
徐曦白:没办法应对。“国家团结”是拜登的主要竞选口号,但我们没有看到有效缓和党派冲突、走向和解的措施。他的当选或许能够为加速冲向选民极化、社会撕裂、甚至暴力冲突的美国踩一脚刹车,但恐怕很难逆转这一大趋势。美国政治近几十年来越来越不遵循“阶级”路线,逐渐演化成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双方阵营的支持者开始沉浸在各自阵营的媒体,活在各自的“回音室”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对“自由派”,或者说文化上的左翼精英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倡导的平权理念破坏了传统的美国精神,压制了白人的文化优势和生存空间,甚至构成了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这种仇恨如此刻骨,以至于他们宁可接受品格上有缺陷的总统候选人,只要这个领袖能够有效地打击自由派的气焰。在他们看来,这次大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善恶之争,“让自由派再次哭泣”(make liberals cry again)成了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响亮的口号。北卡罗莱纳州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考索恩获胜后发出的第一条推文就是“接着哭吧,自由派”(cry more, libs)。这种在政见分歧之上滋生出的部族仇恨近年来在特朗普的鼓动下愈演愈烈,呈现出加速暴力化的倾向,出现了“骄傲男孩”(Proud Boys)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民调也显示,双方阵营都越来越认同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

反观自由派,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得多,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态度自然也是轻蔑的,认为这些人要么智商低下、见识浅薄,才会被特朗普轻易蒙骗,要么就是赤裸裸的男权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场正邪之争,没有妥协余地。自由派一直没有找到与特朗普支持者进行有效沟通的方式,更谈不上说服。自由派媒体有两个爱好,一是派记者混入特朗普竞选集会,向支持者提问,让他们说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以显示这些人的不可理喻,但这种“智商羞辱”并不能使对方诚服;另一个爱好是“核查事实”(fact-checking),这对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样是无效的,因为承认事实错误就等于承认自己搜集信息的能力不如人,这也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自由派以掌握知识、掌握真理的专家精英形象自居,垄断公共话语,形成对底层民众的实质统治,这本来就是特朗普支持者最反感和强力反抗的,“核查事实”只会加剧这种反感。
正如霍赫希尔德所说,政治是关乎情感的。在这个后真相时代,特朗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某种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他们能找回失落已久的自尊和优越感。但在自由派看来,这是在留恋基于种族和性别压迫的的特权,他们断然无法赞同。杨安泽(Andrew Yang)等民主党人士提出自由派在胜选后应当更关注与特朗普支持者之间的共情,努力去理解这个群体愤怒和被剥夺感的来源。他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以“全民基本收入”为主要政见,大谈经济和就业问题,避谈文化问题。桑德斯2016年针对锈带区工人的竞选口号也限于经济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在2020年开始大谈文化问题后,支持率反而有所下降。但这一点在自由派内部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杨安泽在疫情期间表达的种族立场被左派广为诟病。他们也指出民主党能够翻转佐治亚州这样的共和党堡垒,靠的是基层工作者挖出了那些以前被压制、没有机会投票的选民,但挖票的潜力最终还是有限的。

[美]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著 夏凡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5
自由派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远远比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偏左,他们可以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泡泡里,但稳固的政治联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应该争取的对象以及空谈理论和秀优越感的基础之上。自由派在BLM运动后期展现出的那种无节制的愤怒、敌意、侵略性和暴力倾向恰恰是右派所乐见的,越是如此,底层民众越会投向右翼民粹的怀抱。右翼同样乐见左派沉浸在文化议题中,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去关注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矛盾了。因此,左派需要回到左翼政治的起点:工人的权益、就业、收入、住房、贫困问题、公共医疗。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文化左派必须自我改造,要与改良左派结合,要与工会接触,要大谈特谈钱的问题,为此不惜尽量少谈屈辱的问题。
03 当下左翼最迫切的任务不是改革,而是形成政治联盟获得执政权
界面文化:霍赫希尔德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失利,当下的美国左翼正沉湎于悲伤中;而在全球范围来看,自由主义似乎都在经历一个被打压、被质疑的时期。很多人批评自由主义不过是牟利政客的幌子,失去了普世正当性的主张。至少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开始,人们就在不断讨论为什么会这样。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徐曦白:确实,自由主义同时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双方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右翼的批评集中在文化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世俗化和个人选择权消解了宗教和家庭等传统权威,使个人陷入自私自利、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和道德沦丧。这类批评继承了几百年来天主教对自由主义的各种攻击。自由派在性解放、堕胎、生育权、LGBT权利、控枪、大麻合法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完全超出了保守主义者能容忍的极限;而种族正义、对少数族裔的积极平权和支持移民的态度,也使白人保守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指责自由派做着世界大同、文化多元的黄粱美梦,却不关心周围白人同胞的境遇,实则是引狼入室,以外来文化毁灭原有的美国主流文化。为此,他们不得不重新高举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自保。
左派的批评集中在经济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正当性的丧失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英美政府开始对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服务功能进行私有化,减少公共福利,降低富人赋税,减少市场监管,放开资本流动。在这种“新自由主义”中,市场的逻辑一跃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最终准则,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成了市场中的交易关系,所谓的自由,只剩下市场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不再有制度化的互助,原子化的个人面对强大的资本时毫无招架之力。这种偏向资本和富人的体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也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左派的批评与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立场紧密相关,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资本主义的这种侵害,才使自由主义为人们带来自由、平等、繁荣的许诺无法得到实现。
大多数西方的左派批评家既不反自由,也不反民主。相反,他们认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比如个人自由,他们思考的是如何从资本主义中挽救自由主义。首要的措施就是对资本加以限制,通过赋税等手段防止超级富豪积累过多的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影响政策,然后推进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实现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并争取更多的工人权利。因此,美国的左派大多支持桑德斯,虽然他的理念放在欧洲并不算很左,但在美国的语境中,已经是少有的明确指向以更社会化、更公平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尽管这个过程将会相当漫长,终点也不甚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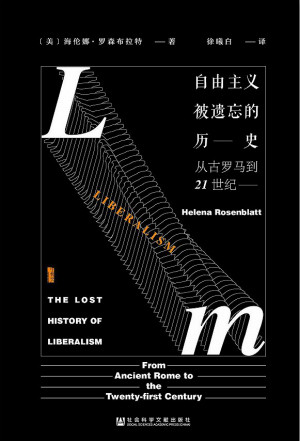
[美]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 著 徐曦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10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仿佛如钟摆一般循环往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进步主义者不满对市场自由放任的旧自由主义,提出了融入社会主义理念,强调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这个新自由主义传统后来成为欧美的主流,特别是在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中得到了实践,以至于反对国家干预的右派在20世纪后半叶又重新发明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自由主义当下的危机同时也是机会,左派可能需要重新夺回“新”字,发展出一套“新新自由主义”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尝试,比如效仿罗斯福新政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旨在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获得了不少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支持。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即使左翼有意进行改革,它也已经无法以国家为单位来进行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它造成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全球体系的问题,这可能是和19世纪最大的不同。当国家面对全球精英力有不逮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难以想象一个自由主义回归的未来?
徐曦白:是的。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全球化使资本和人力具有了高度流动性,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很难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当左派提出加强监管和更严的税收政策时,反对者会说,这样做会导致资本和人才外流,对国家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类政策有赖于跨国协调,像欧盟这样的机构就能发挥重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一些资本家急于支持脱欧,因为他们不希望受制于欧盟更严苛的政策监管。
但是,这不是左派当下最急迫的问题。想要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执政,想要执政就必须赢得选举,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形成占据多数的政治联盟,而英美的左翼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中左翼政党的两大核心票源:城市精英和劳工阶层在价值观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如何将这两大群体粘合在一起才是最大的难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