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生机的宇宙里,再无他物能够比爱更必然、绝对、势不可挡地进入我们的身体。”
与老师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情感,始终是我们在今天回望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一生的角度之一。这段爱情深深地吸引着当代读者,人们试图从二人的信件中发掘哲学和爱情的光芒,背叛与谎言的痕迹,以及两人在后来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上出现重大分歧的蛛丝马迹。
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陪伴了阿伦特整个一生,她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论奥古斯丁爱的观点》:“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是其所是地存在”也正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对自由的定义。在这种自由中,信任将会愈发地牢固,爱情于此得到了肯定。
1941年,阿伦特迫于战争,跟着德国流亡哲学家布吕赫,带着口袋里仅有的二十五美元登上了逃往美国的船只,将她“孩子般的恐惧”和海德格尔那只“狡猾狐狸”丢在了身后。此时,在她眼中,他已是一个整日被粉丝俱乐部的女同学和一个可怕的老婆包围着的“隐形杀手”。而在汉娜再次返回欧洲、与马丁·海德格尔第一次重逢时,虽然海德格尔彼时就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窘迫的狗”,但汉娜昔日的爱意却再次被点燃,曾经的不安全感也再次被唤醒。于是,她开始了对于忠诚、不忠与遗忘的重要思考……在一封写于1960年但从未寄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她向他坦白道,自己对他“一直都保持着忠诚与不忠,并且从未停止爱他”。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在纽约离世。值此纪念日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新近出版的《哲学家与爱》一书中节选了相关章节,以飨读者。
《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厄洛斯之翼的振颤》
文 | [法] 奥德·朗瑟兰 译 | 郑万玲
马丁·海德格尔不是爱情的思考者。所以卡尔·雅斯贝尔斯才在某天这么写道,这位哲学家“不仅没有爱情,他的态度也不友好”。也就是说,爱情在此并不受宠。1927年,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出版,在马堡(Marbourg)最主要的创作期间,他与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之间发生了一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但与这段故事相比,海德格尔在爱情话题里的沉默态度似乎更引人争议。他本人曾公开谈论过这段感情,并在后来表示那段日子是生命中最兴奋激动的时光。至于阿伦特,海德格尔承认她曾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并激发了他“激情的思考”。尽管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扯上了关联,这段发生在“没有国籍的犹太女人”和“一只黑森林的鸟”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最后依然转化成了一种友谊;尽管这段爱情深深地吸引着当代读者,也丝毫不能改变最后结局。我们也肯定无法仅根据这段故事,哪怕它几乎成了一段神话,去宣称这位探讨新型本体论的思想家就是一位与柏拉图或卢梭并列的情感哲学家。
若想弄明白其中这一切,不妨看一下《存在与时间》:“存在”,“此在(Dasein)”,时间,死亡。没有爱情。或许还是有的,在书中的一处批注里,它只出现了这么一次,还是在书页的最下方。批注位于书中第29页。批注中作者没有留下任何字句,只有引用的两句话。第一句出自帕斯卡尔:“当人类在讨论尘世之事时往往会说,在爱人之前,必须要先了解这人,这句话已是人尽皆知的俗语;而圣人则与人类不同,在谈论神圣之事时他们会说,想要了解人,必须要先去爱这人,只有仁慈的爱德才能走进真相,圣人们将这句话奉为最有意义的训言之一。”第二句引用出自于圣·奥古斯丁:“倘若不通过爱,我们无法走进真相。”或者说,爱情是走向真相的开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句格言一致强调,从本体论的角度讲,爱情是最重要的事物,它通向了真相。现在让我们再放大研究范围。整体而言,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所有著作、他们互通的信件以及双方与各自伴侣来往的信件,形成了一个极其宝贵并不断更新的文本库。鉴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并肯定地说,爱情在这两人的思想中占据着最中心的位置。

[法] 奥德·朗瑟兰 著 郑万玲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01
爱情中的“此在”

让我们再来看在这本曾经震撼了整个二十世纪哲学的著作中所找到的两处引用。海德格尔在1928年马堡大学夏季学期的最后几节课中同样也提到了这些引用。他再次思考并且赞同了马克斯·舍勒的观点,后者很早就认为爱与恨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同样地,舍勒在自己的论证中也引用了帕斯卡尔和奥古斯丁的观点。在《爱的秩序》中,舍勒写道:“人,在成为会思考的人或有意愿的人之前,先是一个会爱的人。”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海德格尔的导师胡塞尔(Husserl)提出了意志性,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形成的是一种认识,而一心想超越导师这一概念的海德格尔提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此在”,即一种生存方式,它永远处在“在世”的状态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此在”本身就系统性地具备了超验性的能力,从而得以与所有事物以及其他存在产生关系。在所有的认知范围或主体性的构造范围内,存在总是开放性地面对整个世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认识的本身已提前存在于某个在世的存在之中。”乔治·阿甘本在一篇简短精彩的散文中对海德格尔表示赞同,他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引用了奥古斯丁和舍勒的观点,是因为对他来说,爱情超越了所有认识,它以一种更具先天性的开放模式存在。从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说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问题”。或许读到这里,这一切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但请继续看下文。
在1936年关于尼采思想的课程中,海德格尔建立了一套关于激情的理论。首先,他将激情或者各种情感定义为——“人用来证明自己‘此时此刻’(Da)的存在以及用来证明人在‘是其所是’的存在者里的敞开状态和遮蔽状态的最基本方式”。然后,海德格尔又将爱和恨定义为激情,与其他简单情感区分开。他认为,这两种情感永远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并以“一种更加原初的方式贯穿于我们整个存在”。于此的证据是:我们可以说“滋生仇恨”,却从不说“滋生愤怒”。“恨和爱,不仅是持续最久的,并且只有它们能持续地、稳定地停留在我们的存在之中。”只有在激情里,“情感的束缚才会渐行渐远和自我开放”。海德格尔解释道,此时情感束缚不仅会将我们带到超出本身范围外的状态中,还会“将我们的存在都集中到这种情感本身里”。激情会释放被集中搁置的我们,“所以,就是通过激情,就是在激情里,我们将自己的存在踩在了脚下,我们清醒地成为了主人,掌控着我们以及在我们身上的存在”。在爱与恨的情感里,人类获得了各种偶然,起初他在偶然里迷失,在最后又会回归到自我。总而言之,这两种激情,都是让人类在存在本身带有的混沌里去体验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08
1953年,尽管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存在差异,汉娜·阿伦特也写下了相似的话:“在充满生机的宇宙里,再无他物能够比爱更必然、绝对、势不可挡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爱是一股能量,它会尽一切可能地存在。此外,1925年5月13日,在《存在与时间》出版的两年前,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写道:“你可知在万物之中,人最容易承受之物,实为最难之物?因为其他所剩之物,总会有办法和援助,总有帮助人找回自我的栅栏,而当被爱俘获时,便等于被扔在了最“属于自己”的存在里。爱(拉丁语,Amor),意为“我想存在”(拉丁语,voloutsis),于是圣奥古斯丁这么说:我爱你——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这话阐尽或差不多阐尽了一切。在爱中存在,就是去简单、纯粹地体验那份最“属于自己”的存在,就是与所爱之人一起,去明白被“扔在”自己的存在里也意味着同时渴望他人的存在。这种渴望又是如此的热烈。“你完完全全地‘如你所是’地存在,现在和未来,就是这样,我爱着你”,海德格尔对自己的学生阿伦特说道。
爱的责任
在爱情中,当我们回到自身的存在时,也得到了另一个存在,它有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可能性和自己的世界。当这个存在被赐予给我们时永远都充满着神秘,因为于我们而言,另一个存在永远都既亲近又陌生,否则它就不是另外的一种存在。人们看着自己的恋人,感受着他(她)显而易见的存在,甚至将其视为自己存在的外延,却仍不明白他(她)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他(她)的感受是什么,他(她)到底是谁。而无论这个无法表明一切的存在是什么模样,它永远都独立存在、保持着陌生性,这一切之中必定存在着一份馈赠。“在这样的命运里,另一人会将自己交付于您。”倘若另一人如洪水般突然涌进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拦截这股激流的”。
1925年初,在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彼此表明心意后没多久便开始有了这种交付。当时的情况显然十分复杂又痛苦。他们秘密地展开恋情。海德格尔比阿伦特年长17岁,已为人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阿伦特刚满18岁。鉴于恋情的不合法性,阿伦特自然会对这段感情的未来感到担心。相反,于海德格尔而言,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段爱情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别的选择,他们只能“互相接受,并且以是其所是的姿态去存在”。“是其所是地存在”,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对自由的定义。爱的唯一方式,或许就是让每个人以自己的存在方式自由地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陪伴了阿伦特整个一生,她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论奥古斯丁爱的观点》:“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在这种自由中,信任将会愈发地牢固,爱情于此得到了肯定。“只有对本质的信任,”海德格尔补充道,“即信任对方的爱情,才能真正地留住那个‘你’。”爱,是让对方是其所是地存在,然后“留住那个你”,而不是试图占据他。我们处在可掌控的范围之外,无法完全地、彻底地占据这份馈赠,哪怕它被特意赐予我们,我们只能接受。“无论爱情成了什么模样,赐予给存在的幸福的负担将会一直存在,从而使得每个存在都能够去存在。”爱情或许可以调节每一个存在。或许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不是友好的”,但爱却在其中占据了极其突出的角色。
阿伦特在《思想日记》中是如何说的?“爱首先是一股生命的力量;在世之人都知道一个事实,这股力量控制着我们。没有在这股力量中经历磨炼的人不算活着,他不属于在世之人。”但对于接受了这份馈赠并希望在不让爱情“毁容”的前提下去真真切切地体验爱情的人来说,这其中必定存在着一种负担、一个任务和一份责任。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它为中心让自己成长”。我们对所爱之人必定会心怀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使我们获得了爱的恩泽,这种感激也必须要升华为“对自己的忠诚”。投入于绝对纯粹的爱情,就意味着要“永远保持第一天时强烈鲜活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许,这也是忠诚的第一层意思?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思想,给当时的阿伦特——一位花季少女,带来了多大的吸引力和混沌。阿伦特在寄给海德格尔的《阴影》——一部充满了少女忧愁的自传小说——中写道,想要为他“忠贞地专注于一人”。但这终究是不可能的爱情。如果海德格尔真的爱她,如果海德格尔真的鼓励她去是其所是地存在,同时又帮助她肯定自己,那么他就不会在后来又斩钉截铁地拒绝为她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肯定有过属于自己的二人世界,但它只短暂地存在于某些时刻。在这些像是“五点至七点”的短暂时光,阿伦特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些时光对海德格尔来说有多惬意,对阿伦特就有多痛苦。那时的她,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想过自己的生活。而海德格尔却自私地希望她可以一直是属于自己的幸福,希望她能够继续激发自己的理论创作。让海德格尔离开自己的妻子是不可能的。所以离开的人便是汉娜。即便不愿让汉娜仅成为一颗“流星”,海德格尔也没有挽留她,但却一直抱着再次获得她的希望。

1929年,在柏林,汉娜嫁给了曾于1925年在某次海德格尔的研讨课上所认识的同学君特·施特恩,但她却从未真正地爱上这个男人。甚至在新婚之夜,她给旧情人写了一封请求书:“请不要忘记我。”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才中断,那年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在海德格尔于弗莱堡大学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讲”的四个月后,汉娜从德国逃到了巴黎,在法国创建了一个犹太复国组织“阿利亚”。1936年,她在组织中结识了日后被她称为“真爱”的男人——参加过与共产党联系密切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德国流亡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1941年,汉娜迫于战争,跟着布吕赫,带着口袋里仅有的二十五美元登上了逃往美国的船只,将她“孩子般的恐惧”和海德格尔那只“狡猾狐狸”丢在了身后。此时,在她眼中,他已是一个整日被粉丝俱乐部的女同学和一个可怕的老婆包围着的“隐形杀手”。
一身两头的制度
同样地,也是在1950年左右,汉娜·阿伦特开始思考忠诚这一棘手问题。事实上,现实的一切都将她推向了这个问题。1941年逃到美国之后,当汉娜再次返回欧洲,与马丁·海德格尔第一次重逢时,就像她所说,当时的海德格尔就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窘迫的狗”。而对汉娜而言,昔日的爱意却再次被点燃,曾经的不安全感也再次被唤醒。此外,她现有的家庭也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事实上,汉娜得知丈夫与一位名叫罗斯·费戴尔松的女作家有染。这位拥有俄罗斯血统的年轻犹太人,活力四射、妩媚性感,还是她们共同的友人圈——流亡“部落”里的一员。尽管性情极其敏感,阿伦特最终还是选择了理解,并且与丈夫达成一致,承诺以后两人之间不保留任何秘密。因此他们发明了“一身两头”的规则,就像作家兰德尔·贾雷尔1954年在《制度的作品》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规则不存在任何控制关系,双方都会考虑彼此生活的幸福和独立性。在“生活的重要事情”上,夫妻二人保持一致,对彼此的欣赏和赞同将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哪怕是在家庭争吵时,他们都保持着“哲学家小市民”的身份生活。此外,作家艾尔弗雷德·卡齐在《纽约的犹太人》一书中也回忆到了“这对夫妻面对某个意外的哲学发现时共同的激动。她对吕布赫冷着脸,哪怕心里是赞同他的,我这辈子听到过最有激情的研讨会,就是这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讨论”。理所应当地,她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献给了吕布赫,并称之为“我们的书”,甚至是他们“思想的孩子”。当然,他们之间也绝对不是知识分子间的纯洁友谊。“任何友谊都无法承担起婚姻所要求的责任,”汉娜·阿伦特写道,“当作为制度的婚姻被两人的自由决定缩减为一团虚无时,爱情,它本身,就可以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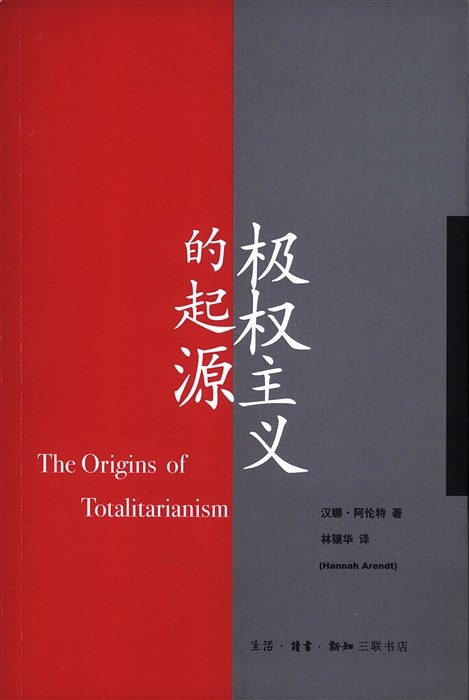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06
嫉妒心,汉娜似乎已经完全战胜了它。布吕赫鼓励她再次与马堡的老师取得联系,她也将每次的书信一一汇报给布吕赫听,甚至在此过程中还对他说想念海德格尔。当她担心“马丁夫人”——她和布吕赫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埃尔福丽德——怒火倍增时,布吕赫会想尽办法安抚她:“让那些人嫉妒这里的一切,你就待在家里,等着属于你的那位‘从不嫉妒的先生’,这位先生正以自己的方式深深地爱着你。”“好,我的挚爱,”汉娜回应道,“我们的心已经向着彼此成长了一次,我们步调一致地向前走。这种默契不会受到任何阻断,哪怕生活紧紧跟着它。疯子们自认为放弃充满活力的生活,前仆后继地,一个踩着一个,成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就是忠诚,这些人不仅无法体验共同的生活,常常也根本没有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当在某一天告诉所有人,婚姻到底是什么。”风波的最后,汉娜·阿伦特最害怕的背叛不是丈夫的通奸,而是他的抛弃,他抛弃了曾在1936年将他们的逃亡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爱情,那是在惨淡灰暗的日子里包围着他们的“四面墙”。这也是为什么当她四处奔走、解说平庸之恶的根源时,她曾“随身携带的丈夫”迟迟不给她写信的原因,这位在外界看来独立自信、备受呵护的女人实际上又再次沦落到了以前那般脆弱可怜的境地。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她给丈夫写道,自己无法承受“像个脱离车身的轮胎一样从人群的高地里往下滚,与自己的存在已毫无联系,没有一人、一物可以去依靠”。布吕赫忠心地爱着她,却无法成为她忠诚的情人,他安慰他的这位“康德的女粉丝”:“你的家在这里,它在等你回来。那里一切静好。”
不忠之罪
在哲学实验室——《思想集》里,汉娜总结了自己近年来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最后,她区分了“无辜的不忠”和“不忠的重罪”,前者以“生活和生活者继续向前走”为征兆而发生,后者则是“谋杀所有过去真实发生的故事”,并将我们带给世间的一切统统删除。后者是真正令被欺骗之人感到万箭穿心的一次“彻底的消除”。因为“在并且只有在”忠诚里,我们才能掌控过去,它能保证我们的故事在过去和现在,就像我们切实经历的那样存在。忠诚与否完全取决于我们,它如此取决于我们,以至于世界里的事实并不一定存在。而倘若事实和“曾为事实”的可能性不存在,阿伦特强调道,那么忠诚说到底或许就是愚蠢的“固执”。反过来,倘若忠诚不存在,事实便更不可能存在,它不持久,也不永恒,它是“完完全全的不真实”。准确来说,鉴于忠诚和事实间的关系,“所有执念”应该从忠诚的定义中剔除。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强行要求做到忠诚,就像我们无法要求那些现在不是、过去也从不曾是真实的事物变得真实。因此,由于嫉妒而对“人们习惯性以为的不忠”进行辩解,实际上是对忠诚的歪解。将事情僵硬化,或“清除人类的生机活力”,都是病态的企图,这种旺盛的活力往往会转变为炙热的愤怒,它与认为生活换个地、换个人就能继续的想法形成对立。最严重的不忠,在阿伦特看来,即“唯一真正的罪行,是抹灭了事实、否认了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实的罪行”,是“遗忘”,对过去的遗忘。
当时的汉娜·阿伦特清楚地意识到,“伟大的爱情就像伟大的作品一样罕见”,她将巴尔扎克的名言改写成了这么一句。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她深深恐惧马丁·海德格尔追随纳粹,但还是选择了在这段感情里保全他的性命。这不仅仅是原谅,从另一方面而言,是否真的原谅他已不是重点,此时更应该看到的是,这是对过去的经历、对发生过的爱情“事件”的难舍之情。在一封写于1960年但从未寄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她向他坦白道,自己对他“一直都保持着忠诚与不忠,并且从未停止爱他”。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故事,肯定不是一场忠心的爱情故事,却是一场忠于爱情的故事。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哲学家与爱:从苏格拉底到波伏娃》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