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赵兰溪 顾嘉琪 杨舒鸿吉
编辑| 刘素楠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尹雪出国读书的计划。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她忽然觉得已经没有很强的意愿去做什么事了,生活陷入了死循环。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力气,但又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干点什么事,她感到自我唾弃,而且逐渐失去食欲,心跳无缘无故加速,有时候还喘不过气。
8月,尹雪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倾向”。在遵循医嘱坚持服药后,她的抑郁倾向仍未能改善,直到开学后又有新的学习任务,她才慢慢恢复了行动力。
尹雪就读于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类专业。她的专业课排名稳定在年级前30%,但她仍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同宿舍的其他三人,分别获得国家奖学金和一等奖学金,而她只获得了三等奖学金。有的同学四个学期每门课的绩点都是满绩,还拥有国家级立项科研。 “每个人都是削尖脑袋去拼”。
周一到周五全天近乎满课,她会提前完成作业,并参加课外竞赛项目。没课时她就在图书馆自习直到闭馆,还自学了Python计算机语言。“一旦闲下来不做正事而去放松娱乐的话,就会有很强的负罪感。”她说。
尹雪希望通过紧张的学习节奏来躲避负面的情绪困扰。夜晚来临,她仍然会失眠,越是提醒自己入睡,越是睡不着。她开始有些社交恐惧,遇到人多的情况便会莫名的紧张,也不愿去结识新的朋友。朋友建议她前往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她总以没有时间回绝。
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24日曾在微博上发起针对大学生抑郁症的调查,在超过30万人次的投票中,超两成大学生认为自己存在严重的抑郁倾向。而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曾表示,大学生的抑郁症高发与社会的内卷化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高校学生用“内卷化”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内卷化现象在重点高校及热门专业里尤甚。
究竟什么样的状况算是抑郁症,又如何寻求心理咨询或医疗机构的帮助?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大学生。
子桦:“他们说这个病是矫情,是故意说自己心情不好”
“爸,妈,你们快来救救我!”摔落在地板上的子桦发出了一条消息。
2016年10月,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把衣服拧成绳子,试图上吊自杀。进行到一半时,她突然不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及时抓住衣柜的门把手,发出求救消息。
当时子桦刚上大二,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在脑海里徘徊了两三个礼拜。周围的世界似乎都跟她没有关系。每天晚上睡不着,她便花上几个小时盯着天花板,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找不到答案,她想到了死,不停在网上搜索哪种死亡方式的痛苦最小。
子桦来自浙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望女成凤,家庭氛围严肃。子桦曾问过父母,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读书”。
高中时,子桦曾获全国生物竞赛二等奖,而后通过自主招生,于2015年9月进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生物科学精英班。生物是她最喜欢和擅长的学科,但是没想到,大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完美。除了生物,子桦还要上数学、物理、化学等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即便是生物课上,也有很多实验内容她并不感兴趣。重新审视学科兴趣,她发现自己其实只喜欢解剖课。
她没有想过换专业。面对生物精英班高难度高强度的课程,达不到想要的成绩时,她感到特别难受。她说自己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
“我也缺乏学习以外的兴趣爱好,”子桦说,“如果有兴趣爱好的话,也许就会多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慢慢地她开始失眠。夜里睡不好,白天上课犯困,更加听不进去。学习成绩下降,又导致失眠更严重——如此往复,形成了恶性循环。就连吃饭也受到了影响。她感到胃痛吃不下饭,进食就像是完成一种仪式,吃一点就会吐出来,两个礼拜体重暴跌十几斤。还有莫名其妙的反胃,一想到要回学校就开始呕吐。
那时候,她眼中的世界是黑色的,黑色的抑郁沉沉笼罩着整个世界。
2015年深秋,子桦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想开点就好了。”父母这样劝子桦。
她不是家族中首位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子桦说,在父母眼中,抑郁症不是一个大事情,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病是矫情,是故意说自己心情不好”。
很长一段时间里,子桦不敢也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抑郁症病人。听说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病”,她说:“小时候我们说别人是‘精神病’,不就是骂人的话吗?”
学术文献一般使用“抑郁障碍”这个词。《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抑郁障碍的一种典型状况。
抑郁症患者自身的病耻感,以及人们对抑郁症以及相关精神疾病的轻视或污名化,使很多患者抗拒寻求专业帮助,也就耽误了治疗时间。
王超是上海某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他告诉记者,有些学生到了心理咨询处后,坚称自己各方面都好,或者表示,只是为某件事心里不舒服,最终在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引导和共情下,才发现背后严重的心理问题。还有部分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不会主动来找心理医生,直到出现了躯体病症,如胃疼、头疼,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问题,才想到可能是心理问题引发的疾病,才来求助心理咨询师。
40次心理咨询
子桦迈出了这一步,她曾向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然而,心理咨询老师随后将她的情况告知了辅导员。辅导员担心她想不开,就将患病情况告诉了班委和她的室友,让他们多看着子桦。
从此室友渐渐疏远她,她患抑郁症的事情也成为班上公开的秘密。随后,在她参加转专业考试时,填报专业的老师均以抑郁症为由,拒绝了申请。“他们可能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源吧。”子桦猜测。
确诊抑郁症后,子桦办理了休学手续,回到老家休息。但是,她吃了一个月的药以后就自行停药了,家人也不知道抗抑药需要长期服用。
2016年初,大一下学期,子桦回到了学校。她疯狂购物,渴望出去玩,想跟人聊天,情绪高涨,动不动就哭。当时家里人都以为这是病情好转的表现,却不知道子桦已经发展为双相情感障碍,正从抑郁转到躁狂。双相情感障碍,通常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同年秋天,刚上大二的子桦又由躁狂期转到了抑郁期,情况比之前更加严重。很长一段时间里,自杀念头萦绕在她头脑中。她决定去死。幸好,求生的念头阻止了这次自杀。
在接受第八次心理咨询时,子桦哭了出来,当时觉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去外面吃早饭的时候,忽然感觉黑色的天空仿佛有了一点色彩,我能够听得清楚鸟叫,并且觉得鸟叫很好听。感觉稍微有一点情绪的起伏了。”
休学期间,子桦接受了40次的心理咨询疗程。她认为,虽然心理咨询看起来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长时间的交流让她有一个可以不停倾吐负能量的空间,就像一个接纳情绪的黑洞,潜移默化中帮助她化解了抑郁情绪。
父母也终于同意对子桦“完美”的人生松绑。在意识到她有自杀行为后,父母只希望女儿健康平安。他们明确地告诉子桦可以不用去学校,就算退学也没有关系。子桦也放下了对学业的担忧。
虽然病程多次反复,但总体向好的趋势发展。子桦意识到,当她对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以后,她的病就慢慢好起来了。抑郁症并没有吞噬她,她暂时战胜了抑郁症。
经历两次休学治疗后,她换了一个专业方向,于2017年9月顺利转入社会工作专业。
为了帮助有抑郁情绪的同学预防抑郁症,她还结合自己的社工专业背景,创立了一个干预小组,取名为“黑狗消失大作战”。通过小组的方式,子桦向人们分享关于情绪的理论知识,告诉大家抑郁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控制。
在医院做实习社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倾听被消极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时会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她打算以后继续从事相关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青少年消极情绪的研究。
“在我生病以前,我一直想做一个优秀的人,生病之后我就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我现在觉得,活着的意义就是去体验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美好。感觉自己冲劲儿少了很多,但是对平凡的认同也多了很多。”子桦说。
文音:“他人的关怀成了我必须承受的负担”
“我已经和抑郁症相处了五年了,我只把它当成脚气一样,它确实在困扰我的生活,但它也就那么回事儿。”文音说。一般人得了“脚气”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担心别人知道,但文音有很强烈的表达欲,她不认为这是一种羞耻,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群体的真实状况。
2016年,文音在高一期末时头痛到不能思考,去了医院各个科室都没有查出问题,她悄悄地盼望自己是得了癌症。之后,她在精神卫生中心被测定为中度强迫、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
文音幼时和母亲被生父赶出家门。父母离婚之后,父亲每个月支付300块钱抚养费给她们。其实,文音父亲的家族有精神类疾病病史,比她大六岁的表哥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已放弃他了。因此文音父亲那边的亲戚认为,得了精神疾病就意味着“完了”。
回忆起当年老师和亲人对自己的“帮助”,文音却用了“抓”、 “逮” 、“拖”、“押送”这样的词。高中的某一天,她感到头痛手抖,父母忽然冲进教室,把她直接拖走,还把桌子里的东西全部掏空带回家,班主任则直接给她开了一周的假条。这是她生活的常态。
2019年,文音来到上海念大学。由于在一次聊天中不小心告诉了辅导员自己有抑郁症,并已经断药,辅导员就停了她周五的课,并将她带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插队就诊。
上大学后,为了消耗每天过剩的精力,文音买了毛线学织造,排满阅读书单。难过时,她会去看黄片,不是为了感受刺激,而是为了感受人生的虚无。“他们好像是很快乐,但也就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所以一切(快乐)都会过去的是吧。”
每次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晒幸福生活,文音都会觉得他们太单纯,“他们被保护得太好了,没有实打实地见过苦难,所有对穷人的想象都来自书本。”文音想不通,为什么身边的人都能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生活,而她一想到世界上有些人连生存都很困难,就会充满负疚感。每个月,文音都会省出一部分饭钱捐给公益机构。偶尔点了几十块钱的外卖,她会非常后悔。“我在干什么?把这些钱拿给他们的话,他们就能吃上饭。”甚至在看到轻奢广告时,她会当场崩溃大哭。“为什么会有人把钱花在这种地方?有人都活不下去了,竟然还有人浪费这么多钱来干这种事!虽然钱是他们的,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拿去捐款不好吗?”
在课堂上,文音是“捧哏”。周围人都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老师还将她视作正能量的典范。只有她自己知道同时感到极度亢奋和极度疲惫是怎样一种生活:“早上计划满满,晚上就想立遗书。”
文音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筹划自杀。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顶望着楼下的时候,她在考虑跳到哪个地方不会太影响到楼下的人。她有时候会想当然的规划人生:年轻时挣一大笔钱,然后英年早逝;如果挣不到钱,就买一份巨额保险,再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担心和别人产生较深的情感后,就舍不得离开了。一旦察觉到自己和某个人的关系还不错,她就会很害怕,想要逃离。她有两位关系很好的朋友,每次三人聚会后,那两个朋友还会单独聚会。文音很珍惜这样的友谊结构。“我哪天突然死掉了,她们两个也不会怎样。”
2019年11月的一个周末,文音独自在宿舍,动了轻生的念头。她给好友发微信:“你半个小时过后帮我收一下尸。”之后就用腰带在床头试图自缢。她感到视线逐渐缩小,像电影里的雪花一样逐渐缩小,感官逐渐消失。
突然,腰带的扣子崩坏了。摔倒在地的文音大哭着又给好友发微信:“靠,死不掉了。”
文音说,活过来就不想死了,下周还要和两个同学组队考口语。“要死也不能耽误别人。”
文音曾向心理咨询师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自杀计划,心理咨询师建议她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后来她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
辅导员拿到她的转诊通知,说自己没见过这种情况,就告知了学院书记。书记随后邀请文音去她的办公室,拉着文音嘘寒问暖。文音想找借口离开时,书记一把抓住文音的手问道:“有人爱你吗?”文音吓了一跳,猛得把手抽回去。书记又一次抓住她的手说:“有人抱过你吗?我们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文音感到非常不适,不想和书记聊。她认为这种关怀方式“非常糟糕”,“但凡有点心理学知识的老师,都不会这个样子”。
文音希望老师不要太把她的病当回事儿,然而老师的关怀却成了她生活中必须承受的“负担”。温度骤降时,辅导员关心她“天气凉了,我怕你难过。”辅导员还常常以“给我看看你们家的猫吧”,“这两天雾霾重”为开场白,跟她聊了两句便直奔主题:“你在吃药吗?”
后来文音的抑郁症更加严重了。2020年秋天,她被送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学业也被迫中止。
在精神卫生中心,文音遇到了几位聊得来的高学历伙伴,也遇到了一些难以沟通的患者,他们都是被家人送进来的。她觉得,这次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
2020年只剩下最后十几天,她刚刚出院回到老家,打算先找一份实习,等拿到康复证明后再回到学校。
她知道,双相情感障碍很难根治,自己即便拿到“好转”证明,没有得到“临床痊愈”证明,明年新学期能否返校,仍是一个问题。
从高校到医院:心理咨询就像走钢丝
一旦有学生在大学自杀,社会舆论通常一边倒地责怪学校,家长也责备校方,学校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直接反应就是:校内的心理健康中心没有把工作做好。在巨大压力传导下,给抑郁大学生做心理咨询,就像一份走钢丝的工作。
如何把握隐私的边界,就是一个头疼的问题。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就强调了“保密”原则,要求建立心理健康数据安全保护机制,保护学生隐私,杜绝信息泄露。
但是对待具体个案时,咨询师往往面临两难。上海某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询师王超告诉记者,一方面,根据咨询伦理,当来访者出现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倾向时,咨询师可以突破隐私保密原则,告知周边人员,这样才能保障学生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学生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心理问题被家长知道,很多时候家长其实就是导致这个心理问题的原因,告诉家长后反而会加大学生的压力,并导致咨访关系破裂。
另一个问题是,有就诊需求的学生太多,而高校心理咨询师的数量远远不够。
《纲要》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要具有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学历和专业资质,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每校至少配备2名。按照上海市规定,高校心理咨询师与全校学生的配备量是1:3000。“要做到这个比例其实很难,学校固定的专职咨询师数量不足,只能通过向校外聘用兼职咨询师来弥补缺口。”王超透露。
2017年,我国正式取消心理咨询师国考。这项存在了15年的制度,累计为国内培养了150万持证心理咨询师。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考之后,新监管政策几年之内未能出台,导致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出现断档。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校外可以一小时赚几百元起步,但是在学校往往只能拿到一小时一百元,学校只能通过免费的心理培训、督导来吸引他们,但是部分骨干还是会向外流失。”王超认为,薪酬不高也是导致高校心理专业队伍储备不足的原因之一。
一边是学校心理咨询师严重短缺,一边是来就诊的学生数量连年攀升。这给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实际上,不光高校心理咨询师人力不足,我国整体精神科医师数量也不多。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3.34万人。“其中,部分精神科医生来自其他科室,经过短期的转岗培训之后转至精神科。纯粹科班出身的精神科医生在每10万人口当中的占比,我国在全球是倒数的。”陈俊指出。他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环太平洋精神病学家学会(PRCP)杰出会士、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CSP)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俊认为,“当下关注的主要是保护患者隐私。而从长远看,消除歧视才是根本。”在他看来,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病耻感,高校抑郁症防治如果不能消除歧视,则会助长患者隐瞒、逃避病情的现实,影响病情判断和质量。
关于大学生患者的特殊之处,陈俊还指出两处亟需改善的地方。
首先,学生患者有学业要求,一些治疗中的学生往往需要在治病和尽快复学之间进行选择。“为了身体康复,要不要考虑留级?另外,康复后回到学校,随着心态变化,患者能否适应新环境、新同学和新老师?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引发新的心理问题。”陈俊指出,大学生抑郁症的治疗与追踪是动态的,不能简单以一般生理疾病的治疗周期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当学生的心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以回到熟悉的环境进行恢复性治疗时,一些学校却要求家属和医院提供治愈康复证明,这样才批准回校。“其实医疗机构无法从医学角度提供这类证明。所以,这反映了学校对精神心理治疗的认识不足,也违背了治疗的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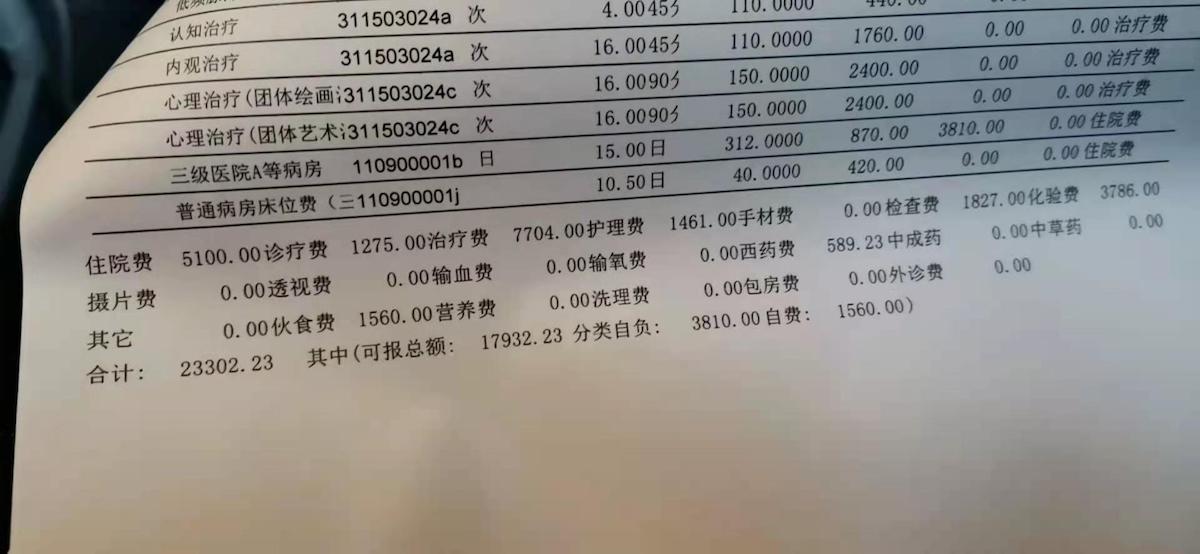
(文中子桦、尹雪、文音、王超均为化名。)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