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你知道,在非洲不存在黑人。”当美国普利策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听到一位尼日利亚剧作家如此说时,她明白自己永远也不会忘了这句话。只有来到新大陆的非洲人才会成为黑人,此前他们是埃维人、阿坎人、伊博人……而白人在抵达之前,也只是波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当黑与白站定光谱的两端后,其余的人夹在中间,成为黄种人、红种人和棕种人。
我们用种族主义来谴责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奴役,一种肤色对另一种肤色的压迫,但它同时也释放了危险的暗示:种族是天然的群体,它自古便是如此,黑的不能变成白的,白的不会变成黑的。但当我们凝视自己的皮肤时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用肤色、语言、血统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的种族,不过是为了把人框进等级制的框架,好让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就像印度的四大种姓之于达利特,纳粹之于犹太。在种族主义批判力度日益衰弱的时代,威尔克森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用种姓来思考种族主义问题,因为区隔人的是等级,生理或者文化特征不过被随意截取为工具,用以完成种姓的任务。
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
人人都知道种族主义,但几乎没有人会在镜头前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一些刚刚施行了种族歧视的人可能会在众目下羞恼,极力辩解自己一点种族主义也没有,声称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个黑人,还有一些人会明目张胆地使用“白人至上”(或者其他什么XX至上),但他们绝对不会公然大喊“种族主义万岁”——大家心里都清楚,种族主义不是什么好词。
美国《纽约时报》的非裔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深知自己活在这种既嚣张又叫人缄默的种族主义中。每次开门取东西都有人问她主人是否在家,坐在头等舱一定会引来旁边白人的抱怨,翘首以待《纽约时报》上门采访的零售商再三拒绝相信她就是记者本人,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她恰好有一身深色的皮肤。没有当事人肯为种族主义道歉,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就是种族主义。这个词正在失去刺痛现实的效力,它无法指向言说者自身。

在一次次与印度的种姓制度遭遇之后,威尔克森像半世纪前的马丁·路德·金一样震惊地意识到,种姓比种族更能直指事情的本质——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种姓等级制度,黑人就是美国的“贱民”。威尔克森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中写道:“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种姓设置了一个巨大的等级框架,把每个人按一定的标准塞进事先规定好的位置,不容置疑,不容更改。在美国,肤色就是用来判定一个人所在位置的记号,这个记号也可以是其他的,例如印度种姓制度用姓名来给人做标记,纳粹则沉迷于测量血统。黑人可以成为中产一员、NBA大明星或是总统,但他永远不能摆脱黑人身份,就连最底层的白人也觉得自己本该凌驾其上,与阶层相比,种姓才是牢最不可破的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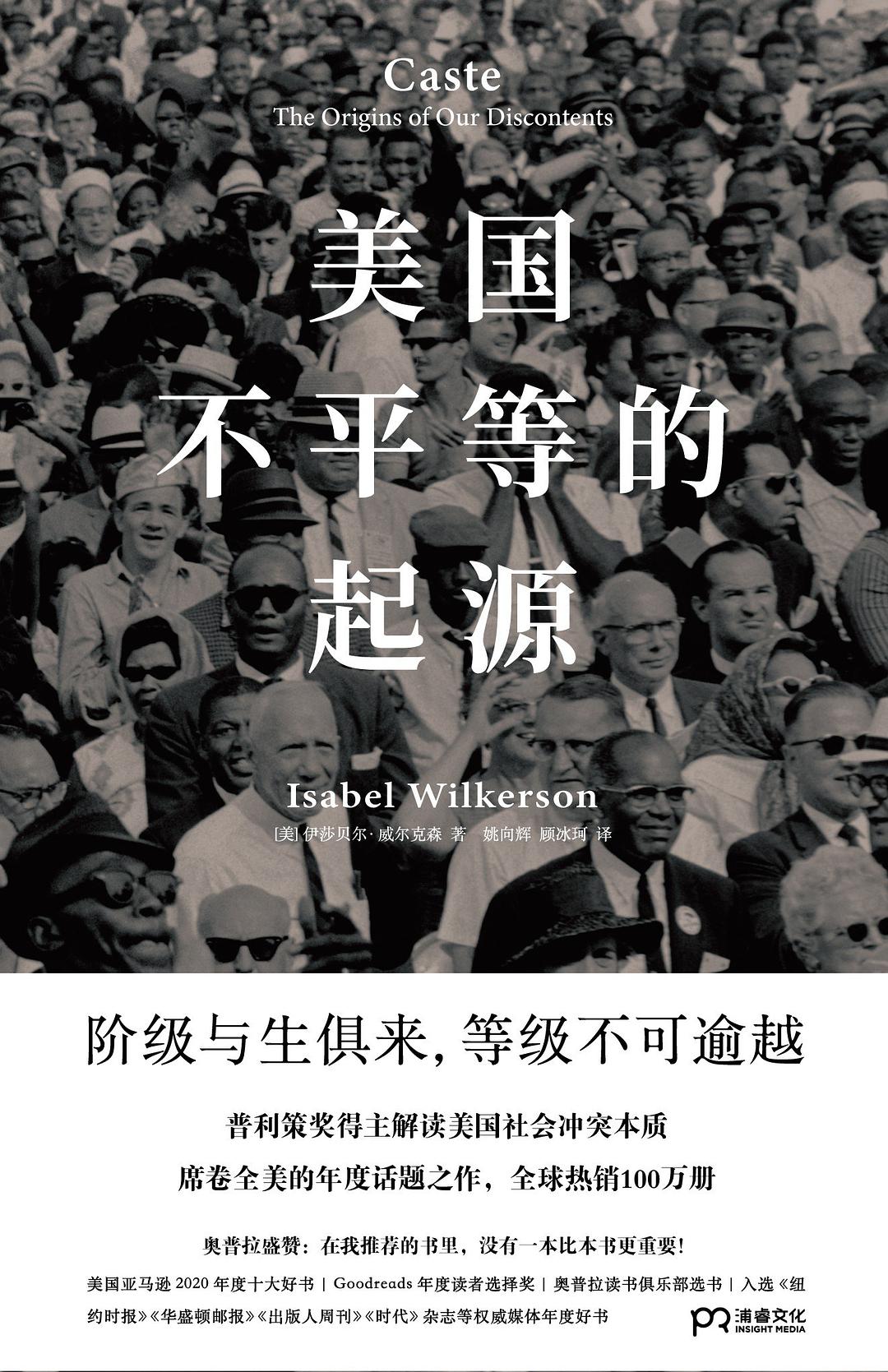
[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著 姚向辉、顾冰珂
译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2
“种族主义”这个词遮掩了等级制的真相,此外,它还误导人们去相信种族是一个天然而稳定的实体,白人永远是白人,黑人永远是黑人。然而,深色皮肤的非洲人在被运抵新大陆之前,世人还不知道有叫作“黑人”的人,欧洲人在登陆美洲前也不以白人自居。种族的缔造者是给人类定等归类的种姓制力量,前者按照后者的要求来修订边界。早期的美国以盎格鲁-萨克逊血统为尊,东欧和南欧移民直到20世纪初还遭受法律性的排挤,1903年,路易斯安那州曾尝试将意大利选民排除在白人之外,1922年,一对同居的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本来要被判处违法跨种族通婚法,但当法官得知这位女性是西西里人时,便以她“不够白”为由释放了两人。如果像纳粹那般严格地进行血统溯源,现在的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或许会因为自己的祖籍而被开除“白籍”。
讽刺的是,美国为上世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了庇护,而纳粹却是从美国的经验里寻找种族清洗灵感的。1934年,纳粹分子在讨论如何把雅利安人种族纯洁性写进法律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美国的种族隔离和外来移民法。美国种族主义优生学家洛斯罗普·斯托达德的著作被当作第三帝国的教科书,希特勒把《伟大种族的逝去》称为“我的《圣经》”,这本鼓吹剔除某些群体基因的著作出自另一位美国种族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之手。
可见,一个人是否会被凌辱虐待,与他原来所在的群体无关,而是看他所在的新社会选择把他纳入上等种姓的种族,还是抛入下等种姓的种族。
摇摆的模范:“黑-白”光谱下的中间种姓
把种姓制度完全看成别人家的事或许会让人好受些,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人类外貌差别不那么显著的地区,不存在以貌取人的种族主义,但我们无法欺骗自己不存在等级这一事实,种姓还可以通过语言、举止、打扮、职业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区隔。威尔克森在接触印度学者一段时间后,她无需打听对方的姓名来处,就可以判断其种姓,因为高姓者永远昂首阔步,低种姓者则表现得礼貌谦卑。
而我们更不愿意承认的另一层事实是,尽管我们努力把种族主义(或者改口说种姓主义)当作美国人、黑人和白人的事,但身为亚洲人的我们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黄种人处于白人和黑人之间。
每当黑人走上街头维权时,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质问:黑人为什么不能学学模范亚裔,好好遵守规则,靠自己的勤劳努力获得好生活,融入社会?但问题是,位于等级制底端的黑人有机会融入吗?南北战争之后,刚从奴隶制中解脱出来的黑人就落入了吉姆·克劳主义的恐怖统治,种族隔离使得黑人无法获得和白人相同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有的州招募黑人老师的标准甚至是“挑其中最差的一个”,等级绝不允许被颠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也没有将黑人计入其内,联邦住房管理制度明显地向白人倾斜,黑人家庭想要在两三代人以内累积到和白人家庭相同的财富近乎天方夜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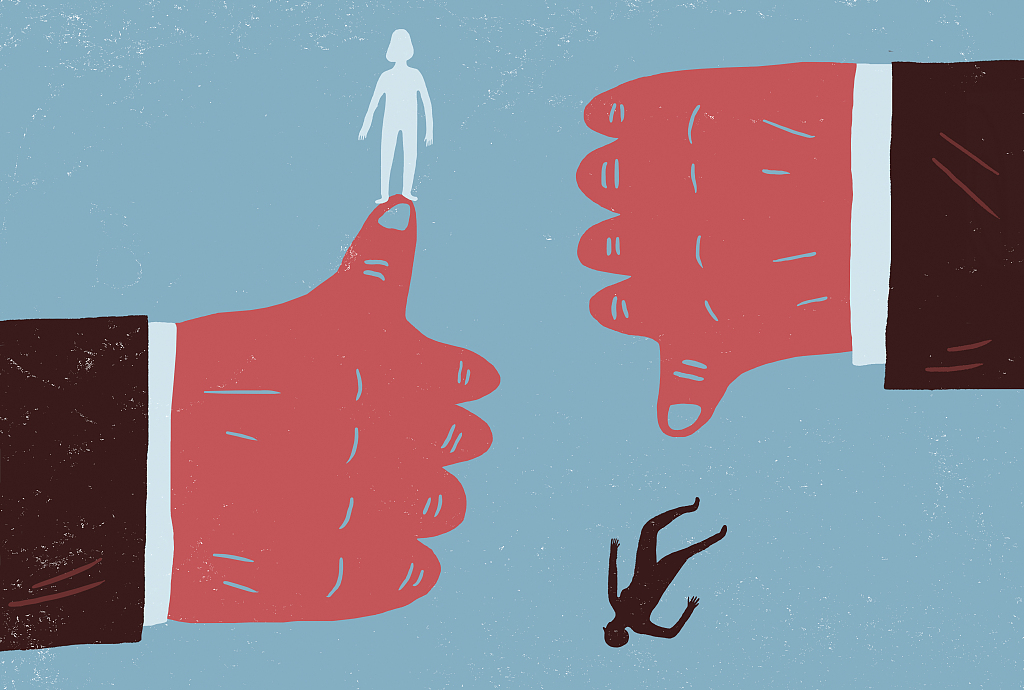
第三种肤色走进这片新世界后,很快便掌握了种姓制度的规则:白人在上,黑人在下,新来者为了生存要向上等种姓靠拢,争取其认可,与下等种姓保持距离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如今,一些非洲移民也会极力划清自己和美国非裔人的界限,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肤色,先祖来自同一片大陆。
在种族隔离时代,一群古巴人在弗洛里达州伊博尔市的电车上不知该坐在哪个区域,当他们被获准落座白人区时,不禁松了一口气,感到欣喜若狂。威尔克森称之为一场“中等种姓钻入白人阵营的竞赛”,她认为上等种姓偶尔的褒奖和特权施与 “实则源自对种姓秩序的维护”。这种奖励的脆弱和虚幻在2020新冠之年再好理解不过——昨天还是黑人衬托之下的模范亚裔,明天就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一句“中国病毒”遭人白眼、担惊受怕。
历史学者罗新在《世上本无黄种人》一文中指出,色彩是非中性的,它带有文化所赋予的情感和价值,西方人最开始时并不觉得东方人皮肤黄,是在工业革命发展后,才将东方人从象征着圣洁智慧的白色中剔除,归入病态、低俗、恐怖的黄色。随着基因研究与社会科学认知的进步,“黄种人”“蒙古人种”等带有种族色彩的描述已经在淡出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而我们自己却还在用西方人陈旧的观念来测量自身,无形之中也嵌入了“黑-白”的光谱。即使是在东亚街头,人们对一个白人投注的大多是好奇、好感甚至畏惧,而对黑人则是漠然和避之不及。
人人都可以欺压最低种姓,哪怕是他们自己
有等级制的地方人人都不想当末位,即使是被安排在最低等级的人也想踩在同类的背上,好靠向窗边喘口气。统治者鼓励告密和揭发,利用权力和荣誉的稀缺把底层人困在内斗中,任其相互消耗。黑奴工头可以对其他朝夕相处的黑人施以暴行,一方面是为了换取微末的好处,另一方面则如威尔克森所说的,他们不必为背叛负责,“因为那些被背叛与忽视的是低种姓的人。”
2015年,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因被押前往巴尔的摩警察局,他双手被铐,但没有人为他系上安全带,在颠簸中他因无法掌握平衡撞在了汽车内壁上,脊椎受伤,最终导致死亡。涉事的6名警察要么被宣告无罪,要么被撤销指控,其中3人同样是非裔,包括开车的司机。威尔克森指出,即使不属于统治种姓的人也可以对低种姓者发号施令,他们是种姓制度在各个等级设置的哨兵,依赖这一层身份,他们的暴行免受刑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帮助维持种姓制度的运转”。

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社 2013-6
还有一种底层人之间的内耗与之相反,即被留下来的人会想方设法拖垮那些试图向上走的人,这种现象被称为“螃蟹心理”。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老祖母贝比·萨格斯的儿子为她赎了身,成为一名自由黑人,虽然七个孩子都被夺走,但儿媳和孙儿孙女们回到了她的身边。她们家的生活食物充足,心灵饱满,贝比在林间空地训众,赠与他们食物,教他们爱自己黑色的身体,让男人、女人和孩子跳舞、大哭大笑。但贝比的大方和快乐很快引来了妒忌,她在空中闻到一股不属于白人的“肆意飘荡的嫌恶”——那嫌恶来自黑人——她走得太远,施与得太多,“由于不知节制而惹恼了他们。”
地狱夺走了人类互相祝福的能力,那些得到贝比·萨格斯物质与心灵馈赠的人因为在长期的奴役中被消磨了人性,转而厌恨她的热情和富足——在非人的折磨下,她怎么敢保有健全,怎么可以活出“人”味?我们坚信自己不会如此小肚鸡肠,就像发誓自己不会去残害同类的性命一样,但事实就放在眼前,人人都知道杀人是邪恶的罪过,但每天都有人因为等级的压迫而丧命。我们说在那些最糟糕的时代,人们陷入了疯狂,而这疯狂的逻辑还在我们之中延续。
参考资料:
《美国不平等的起源》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著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罗新 著
《宠儿》 托妮·莫里森 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