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1766年2月13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他的父亲在子女教育方面不拘一格,在家亲自教育他。1784年,马尔萨斯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两年后当选耶稣学院院士。1805年,马尔萨斯在新建的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兼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可能是世界上首位拥有该头衔的教授)。东印度学院是东印度公司训练职员的教学机构,在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东印度公司是该国在印度的主要机构。
马尔萨斯一生著作颇丰,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首次发表于1798年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它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人口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尔萨斯也因人口以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理论而被称为“人口马尔萨斯”。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对人类社会的预测已被证明并未成真,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论》的提出与当时欧洲人口高速增长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回望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它促进了欧洲的移民潮,因此间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悲观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理论,工人阶级在遭遇越来越严峻的贫困、失业和疾病问题时难以获得国家援助。
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与移民潮

“法国革命的到来以及革命后的激烈影响使人们专注于似乎各处可见的政治不稳定,马尔萨斯认为他至少有了一个答案,就算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人性法则是可以发现的。但是就他而言,他相信进步是有限制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在《思想史》一书中,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如此写道。马尔萨斯眼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他首先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学原理,因为它影响社会的未来进步》,然后又于1803年出版了第二版,继续扩展自己的论述。
在很大程度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环境的回应——除了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引起的政治震动之外,19世纪快速的人口增长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经验,也亟需社会科学学者——大革命后出现的全新学科分支——去理解、去阐释全新的社会运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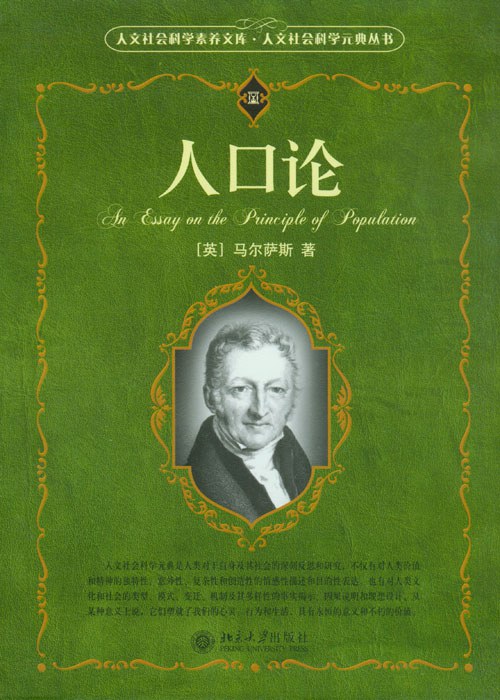
[英]马尔萨斯 著 郭大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1
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法国人口数量从2870万增长到4070万(上升42%);意大利人口从1809万飙升至3297万(上升82%);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75%、86%、130%和181%;在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格兰,人口增长率更是高达246%。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指出,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两大因素驱动:大量的食物供应和运输方式的改进。耕作方法的持续创新,特别是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欧洲人开始获得剩余的粮食、肉类和奶制品;与此同时,针对这些剩余粮食,欧洲开发出了全新的高效存储和运输方式,例如长途运输铁路系统。食品短缺基本不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出生率因此不断上升。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悲观的。他认为,人性的基本法则是人口增长率以几何速度增加,而食物的生产只能以算术速度增加,因此物质匮乏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马尔萨斯继而指出,人口增长会对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人口增长将带来劳动力增加,继而导致工资降低;更严峻的是,人口增长会导致粮食短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一旦达到临界点,前者就不再能够满足后者的需要。鉴于此,人类应当有所节制,避免增加人口。
马尔萨斯指出,阻止人口增长有几种方式。战争、瘟疫和饥荒是自然方式,但它造成的社会破坏和痛苦也是巨大的;一种不太痛苦的方式是控制生育(比如单身或延迟婚龄);另外一种替代性方式就是移民。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Julio Crespo MacLennan)在《欧洲》一书中提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后果的理论对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英国和其他正在经历人口快速增长的欧洲国家影响很大,这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在19世纪大都积极推动移民。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 著 黄锦桂 译
中信出版社 2020-08
“事实上,由于环境所迫,底层群体不得不移民,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减少,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麦克伦南写道,“即使不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少欧洲人也很清楚人口过剩会引发问题。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食品短缺,因此农村人口会向城市迁移,但许多人的境况并未好转。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暗淡的前景,而19世纪出生的人拥有一个新优势:移民机会更多。”
作为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美国是当时的欧洲移民最喜欢的目的地。1845年的马铃薯枯萎病在爱尔兰引起严重饥荒,导致近1/4人口死亡。在十年的时间里,近200万爱尔兰人远走他乡,其中大部分人移民去了美国。从19世纪中叶起,巨型游轮增多,越洋航程的时间缩短,旅行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这从客观上促进了移民。大量欧洲移民前往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
在麦克伦南看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建立史上最大的帝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坚定地推动移民。16-18世纪,欧洲帝国将文化传播到很多地方,但当时的欧洲没有足够的人口移居到所有领地。这一情况在“人口爆炸”的19世纪出现了根本性扭转。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面貌——比如他们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和在1900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塑造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全球化世界。
马尔萨斯学说视角下的城市病与贫困问题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9世纪的欧洲见证了农业人口的快速下降。1700年,全欧洲70%人口以务农为生,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耕种所需的人手越来越少。在1801年,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只有18%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到1901年,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3.65%。这意味着多出来的人口必须进入城市,在工厂中获得谋生机会。在莫蒂默看来,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剧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人口增长导致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和交通业的增长,工业和交通业的增长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专业化分工等。”
随着劳动者被驱离土地进入城市,工业革命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表明的,劳动人口在1790-1830年间经历了社会地位下降——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者普遍权利的丧失和许多行业的日益贫困。

[英]E.P.汤普森 著 钱乘旦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03
沃森援引霍布斯保姆的观点指出,19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恶化。1800-1840年,伦敦肉类供应不足;手织机织工的平均工资从1805年的23先令下降到1833年的6先令3便士;1840年代甚至在当时被称为“饥饿的四十年代”。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国爆发过数次与食品短缺有关的暴动。以上种种城市化问题促使英国人建立从1851年开始的十年一次的普查机制,其目的是为英国社会各层面提供一个简单但经验性的基础。普查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贫困和住房问题的关切,“贫困问题”(pauperism)一词最早正是在英国出现的。
在沃森看来,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理论加剧了工人阶级的窘境。马尔萨斯的理论在19世纪被理解为“在中长期,大众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这成为反对提供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个有力论据。
在《万物进化》(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一书中,进化生物学家、记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政策简洁明了地总结为“对待人民善良不如残酷”(Better to be cruel to be kind)。这种“掌权者才知道怎样才是对弱势群体好”的信念让马尔萨斯的理论直接干预了法律实践。1601年由伊丽莎白一世批准的《济贫法》(Poor Law)在1834年被《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大幅削弱,因为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帮助穷人只会鼓励他们多生孩子,进而加剧贫困问题。此类观念也影响了英国政府在应对爱尔兰大饥荒时的立场。雷德利注意到,财务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曾声称,饥荒是“减少多余人口的有效机制”。

与此同时,李嘉图认为工业成功的前提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必须高于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如果工资一直保持在“刚好够劳动者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低水平,那么资本的积累永远不会到头,普遍的生产过剩也永远不会发生。因此,“工人注定是贫穷的,任何其他状态都会威胁整个工业社会这座大厦。”沃森指出,秉持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立场的李嘉图是激怒卡尔·马克思的人之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预示了几十年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到来。英国政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社会科学理论,他认为穷人理应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特别是优生学的发展。从1905年到1912年,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成立优生学相关研究机构,一些当时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在当下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比如牛津大学教授F.H.布拉德利曾建议,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处死,他们的孩子也不例外;美国印第安纳州于190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州立监狱内“精神错乱的、愚蠢的和低能的”犯人或“被定罪的强奸犯”实行绝育手术。
贫困问题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引起了欧洲各地和大西洋彼岸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广泛讨论,他们并非在自由放任的问题上都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持相同观点,也有人在目睹工人阶级的惨状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教授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大量证据显示,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地区的自由派认为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并不矛盾。托克维尔曾和许多自由派人士一样担心《济贫法》会使工人丧失工作动力、助长懒惰、犯罪和不道德,但之后,他就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呼吁加强国家干预帮助穷人,他注意到随着工厂主越来越富有,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势,工人越来越士气低落并被不断非人化,因此工人需要“立法者的特别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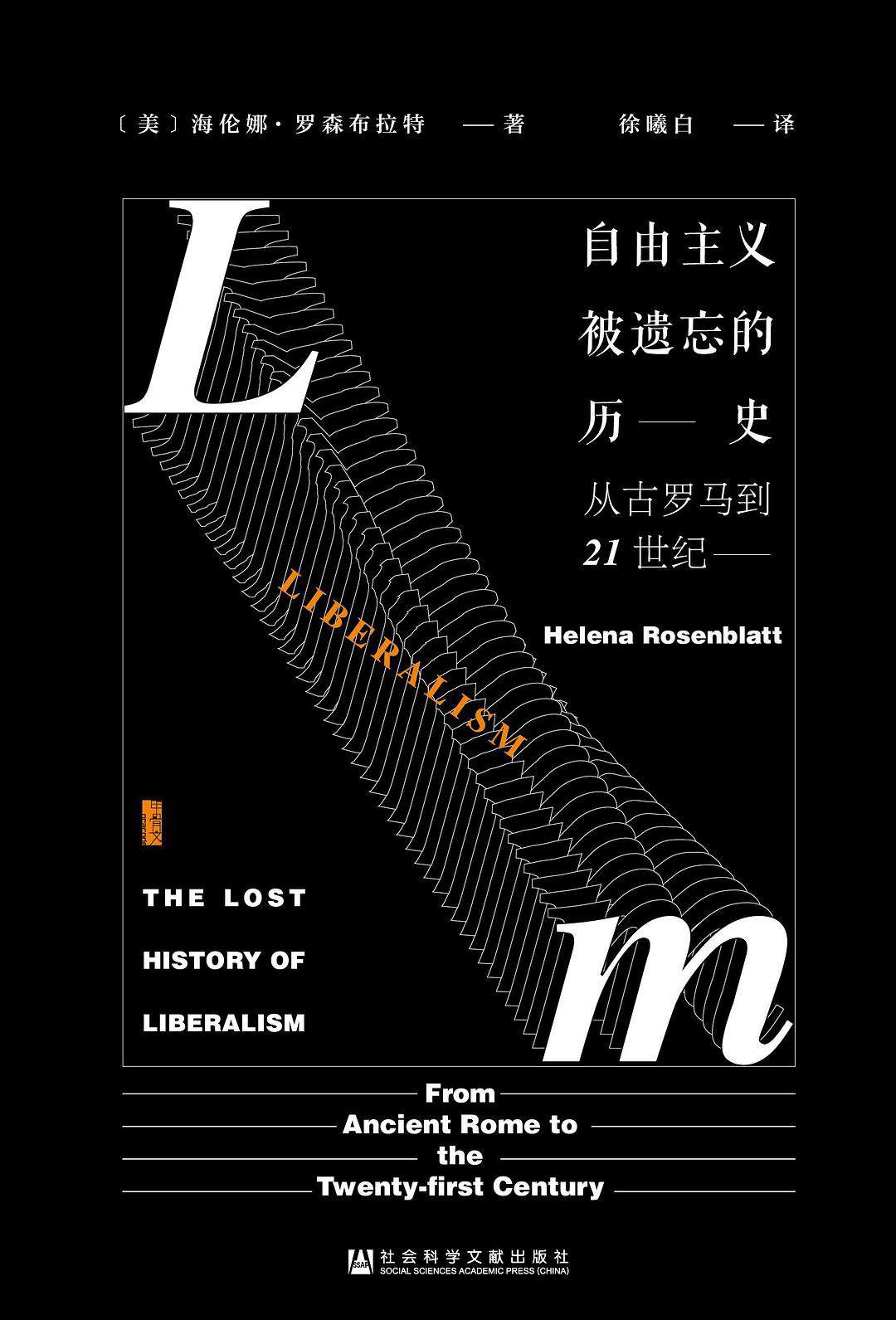
[美]海伦娜·罗森布拉特 著 徐曦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10
“19世纪英法德的大部分自由派不反对政府干预,也不倡导绝对的财产权。他们当然不相信追求个人私利的人会自发地创造健康的财富分配机制或者促进社会和谐。他们借助一切机会声讨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少数倡导绝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自由派受到了其他自由派的严厉批判。”罗森布拉特写道。
尾声
现在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并未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技术进步让许多国家的粮食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生率会下降而非上升;人们对生育的态度出现极大的变化,家长们开始认为,与其多生孩子,更重要的责任是拼尽资源照顾培养好孩子。
在美国科普作家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看来,马尔萨斯学说支持者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放弃一个简单却明显错误的观点,即人类在生育问题上和鹿群是不同的”。人类是一种会思考、会权衡利弊的动物,这导致的结果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截然相反——粮食储备越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育率越低,反倒是最受粮食安全问题困扰的国家拥有最高的生育率。回顾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学家在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上表现出的傲慢,以及未经论证的理论被盲目应用到社会政策中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对于曾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即将进入少子化社会的我们来说,这段历史更加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
“Thomas Malthus (1766-1834),” BBC
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malthus_thomas.shtml
“Why Malthus Is Still Wrong,”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malthus-is-still-wrong/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Explained with Its Criticism,” Economics Discussion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变与实践》,界面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974572.html
[美]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英]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20.
[英] 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英] 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译林出版社.201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