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当地时间2月22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突破了50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总和。
美国疫情失控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公认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医疗系统积重难返。
2月中旬,美国德州遭遇了30年以来最严寒的天气,伴随着大面积的停电,以及许多地区天然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等公共设施被冻坏,近1300多万人供水受到影响。仅哈里斯一个郡就有300多起因取暖而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数十人因为温度和缺乏取暖设施而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德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跟美国医疗系统的争论一样,德州停电引发的争论热点之一也是市场和政府管制问题,因为德州是最强调市场放任自由主义和独立联邦倾向的州之一,左右翼每一个立场的人都能从这场灾难中找到支持自己、指责对方的证据。不过,在这场争议中,有一个事实是不同阵营都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美国社会面临结构性问题,而且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了。
在新冠疫情一年后的2021年,这一看法仿佛成了一种隐喻:美国生病了,需要医治。
奥巴马医疗的争议
在医疗方面,这一隐喻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许多美国人。2021年1月底,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九岁男孩的母亲谢弗(Katie Schieffer)在抖音上哭泣着说,她儿子被诊断患有1型糖尿病,她家是一个双全职家庭,却仍旧无法负担1000元的胰岛素处方费用。她通过媒体问美国公众:“我是唯一这样挣扎的人吗?”
当胰岛素的三位发明人以三美元的价格将发明权转让给多伦多大学,以保证人们可以免费使用它治疗糖尿病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美国的制药厂通过改变一些配方来维持专利权,让患者不得不每月负担近1000美元的费用。这并非最近才出现的偶然的事情。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述了1980年代美国版“药神” 患有艾滋病的伍德鲁夫如何用7年时间和美国药监局、制药公司斗智斗勇,从墨西哥等地帮助美国病友买廉价药的真实故事。而据《美国病》(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作者哈佛医学博士和记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有读者这样告诉她在边境购买糖尿病药品的事情:“每个月购买捷诺维的费用超过300美元,也就是每天6美元,在美国我可买不起这种药。因此,我一年去圣地亚哥两次,然后步行穿越边境……一模一样的药在那里只需要大约40美分——多亏了墨西哥政府对制药公司和药品的管制!”

尽管有为无家可归者和最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慈善医疗机构,但是对更多普通美国人来说,医疗和保险是一项重担,其公共政策也左右着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因为医疗问题是个极为复杂的体系,一篇文章无法涉及到方法面面,下面我们将会围绕奥巴马时期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来讨论美国社会的问题。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平价医疗法案》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拉票的关键议题。特朗普也信誓旦旦要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平价医疗法案》的全称为《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由时任总统的奥巴马在2010年3月签署,以此来推进美国的医疗体系和保险改革,试图在控制医疗成本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该法案覆盖在原先联邦医疗辅助(Medicaid)的基础上扩大了覆盖范围,特别是要求保险公司不能够因为个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拒保,或者对于不同人群(除年龄因素外)进行价格歧视,这使得一些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的人,如具有哮喘病史的人都能够获得有效的保险。《法案》还对人均自费额度规定了上限,例如在2016年是6850美元,以此来保障普通人不会因为生病而导致家庭破产。
尽管这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正如罗森塔尔在《美国病》一书中指出的,由于美国药品协会、医学会等等利益集团的阻止和游说,该法案对失控的医疗支出仍旧无能为力,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妥协的产物。《平价医疗法案》出台后的效果是,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占比从2013年的18%下降到了2016年的11.9%,但是还是有近2000万美国人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而因为平价医疗保险让保险和医疗公司的利润下降,在2016年许多公司已经宣布不再提供或者使用平价医疗保险计划。
在2020年11月特朗普当政期间,《平价医疗法案》仍旧处在飘摇不定中,共和党不断要求废除这项影响数千万人的法案,而美国最高法院暂时表态保留《平价医疗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也让很多支持这项法案的人松了一口气。
维护基本权利还是遵循市场规律?
被共和党人污名化为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平价医疗法案》的强烈提倡者。他的观点是,医疗保健应该是人的一项权利,而不是特权。他反对以人的社会财富来决定受医疗救治。桑德斯提出,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美国,一场大病会让很多家庭面临破产,而整个医疗体系设计的动机却主要是为保险公司、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供应商创造高额的财富。
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一书中有些动情地说,“医疗行业每年将几千亿美金收入囊中,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保障不足,许多人饱受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死亡。”一方面,医疗保健费用的大幅增长,却让更多的普通患者无法负担医疗保险和处方药。另一方面,制药公司的CEO普遍都拿着每年千万的年薪,2015年再生元制药的CEO年薪是4700万,强生的CEO和其他医疗保险行业的CEO也普遍在2000千万美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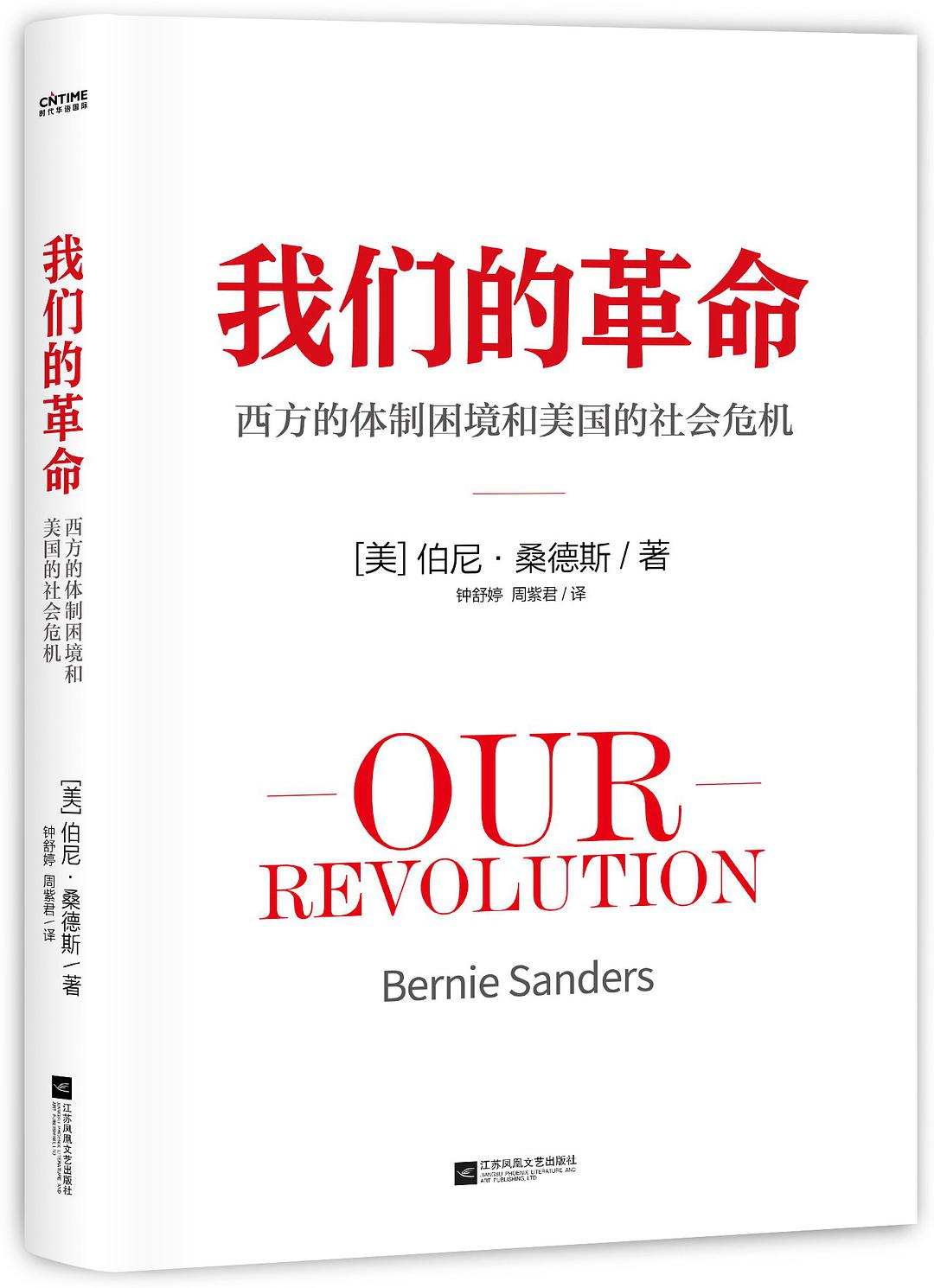
桑德斯引用了权威的研究数据来说明美国本土的处方药价格位居世界首位,例如辉瑞制药治疗风湿等的恩利(伊纳西普)在加拿大售价1646美元,在美国是3000美元(实际上在2020年已经在6000-9000美元之间,目前中国的售价是在单支售价大约700-1000元左右),很多同样的药在美国的价格要高出加拿大近十倍。桑德斯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瓦伦特(Valeant)制药在2015年对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盐酸二甲双胍片(俗称降糖药),在6月份从572美元上调到3432美元,而在一个月后,则再次调价到5148美元。
桑德斯自己在担任参议员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时,发现该系统的事务部(VA)每年在处方药上花费数十亿美金,其中有一项开支是治疗丙肝,因此,联邦出资,有VA雇员参与,由法门塞特(Pharmasset)制药公司研发了治疗丙肝的新药索非布韦片(Sovaldi),在公司被大型药物公司吉利德(Gilead)——在去年年初以瑞德西韦而闻名于世的公司——收购后,对该药的市场定价是12周的疗程约8.4万美金,平均每片药约1000美金。也正是这些原因,桑德斯强调,医疗保险应该是在美国的人都享有的权利,也是为什么他希望能够对全面医疗保险进行系统性改革。
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最近的书《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20)中,其中一章的标题就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他们讨论的并非美国的医疗事故和成瘾性药物滥用这些普遍的问题,而是医疗制度和高额费用对人们生活的间接的影响。

在书中,他们指出,根据2019年Health Affair的研究论文统计,在2017年美国的医疗制度大约耗费了美国GDP的18%,人均10739美元,是国防开支的4倍,教育开支的3倍,但是在高昂的社会成本之下,尽管美国医疗支出远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但是人均寿命却在发达国家中最低。以2017年的数据来看,相比于人均医疗支出排列第二位的瑞士(约占GDP的12.3%)的人均寿命比美国人多5.1年,但人均医疗支出却少了30%。
美国人普遍对医疗体制的不满也通过民意调查表达了出来。在2005-2010年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只有19%的美国人对医疗制度感到满意。高昂的医疗成本最终流入了医生、医疗机构和制药企业的口袋中,比如,在2005年美国收入前1%的人口中,医生占了16%,而在这1%中的前10%,有6%是医生。在美国,患者除了承担高昂的药费外,手术费用也通常是其他国家的4-10倍。相比其他富裕国家,美国的医院和医生也更愿意采取高回报率的治疗手段,而非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党派政治和利益游说团体也卷入其中,通过国会立法来稳固其利益。按照凯斯和迪顿书中整理的各种统计数据,医药行业是美国政治游说支出最大的行业,甚至超出了金融业,例如在2018年的游说支出是5.67亿美金。除此之外,医药行业还斥资1.33亿美元用来支持现任或潜在的国会议员,其中有7600万用来支持民主党,5700万用来支持共和党。本书作者还特别指出,这些游说实际上完全左右了国会的立法,维护了医疗行业的利益。即便《平价医疗法案》在通过时,也不得不向利益集团妥协,不涉及控制医疗成本的措施。
《美国怎么了》这本书中将这些团体的存在和政府的关联形容为一种劫贫济富的行动,就好比“一个店主被人要求支付保护费,于是他威胁对方要报警,结果来收保护费的敲诈者本身就是警察。美国的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医疗本来应该是改善人民健康的行业,而它却在损害我们的健康;国会本应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它却正在支持医疗业对人民进行勒索。”
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
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因为利益集团、游说团体、以及制度本身的漏洞导致人们反对《平价医疗法案》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国内媒体忽视的因素——意识形态团体,特别是美国宗教右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权威、奥地利学者露丝·沃达克在她《恐惧的政治》中提到,在美国,人们反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堕胎。这是共和党和奥巴马时期出现的茶党运动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强烈反对的理由。在沃达克看来,《平价医疗法案》算是第一个成功的全国性医疗保健立法,目标是想覆盖几乎所有美国人,但是因为涉及避孕和堕胎费用而遭到了这些群体的反对。茶党的立场主要是反对这些公共政策:医疗改革、经济刺激计划、联邦资助干细胞研究、联邦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研究、金融改革和对高收入家庭增税、枪支管制、外国援助、堕胎等,沃达克认为“除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更重要的是,种族仇恨和不喜欢奥巴马也有极大影响”,而“反政府立场、新自由主义政策、基督教基要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女性身体规训则是美国茶党的主要组成基础”。而这些在特朗普时代则转变为了他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然而讽刺的是,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一群体的人群里,哪怕有一些人自己也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不能够负担起昂贵的医药费,但还是会坚定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会买“奥巴马健保”,也不会买其他他们认为会负担堕胎费用的保险,“政府在骗我们的钱……” “我不会让人在用我的钱杀人…”。
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改变。这远不是市场和管制、左右意识形态的争论等等非此即彼的争吵,而是如何在一个因利益和权力而产生的巨大沟壑和分裂的社会中进行弥合、施行正义的问题,这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社会分配和团结中,能够先惠及最弱小和最有需要的人。
单纯的自由竞争世界只能够是教科书中的幻想,单纯的管制也只能够在乌托邦中实现,人既不是自由竞争市场中理性的原子或被淘汰的失败者,也不是大企业或权力规制下的螺丝,他们有疼痛、疾病和喜怒哀乐,既是个体也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部分,如那首古老的诗歌所说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相关阅读:
美国国会危机:特朗普运动背后的清教灵知主义和娱乐化丨美国向何处去⑦

美国大选背后的深层危机:选举人团,摇摆州与社会极化丨美国向何处去②
新冠大流行不仅让特朗普检出阳性,也测出了美国的深层思想危机丨美国向何处去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