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国学者、作家伊丽莎白·奥特卡(Elizabeth Outka)在她的《病毒的现代主义》(Viral Modernism)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疾病不同于战争,它很容易从文化和历史记忆中消失。
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病中写道,“我们不再是正义之师中的士兵,我们成了逃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写作中,伍尔夫提到了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对西班牙民族胜利的威胁。流感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移动,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伤害。
这种对疾病的兴趣是伍尔夫个人的。1916-1925年间,她数次感染流感并卧床休养。她记录下了自己得西班牙流感的经历——她在1918年的日记中用置身事外的口吻写道,“根据《泰晤士报》,我们正经历一场自黑死病以来未曾有过的大瘟疫。《泰晤士报》似乎对此感到恐惧,生怕诺斯克利夫子爵(第一代诺思克利夫子爵,英国现代新闻事业奠基人,《泰晤士报》创办人。一战期间曾担任英国对敌宣传总监,主持对德国的战争宣传)染上此病,从而逼我们投降。”
她当时的语气是嘲讽的,但她后来会体会到流感威胁的严重性。但她在这里提出,疾病有望带来的是战争利益的终结,而战争利益助长了诺斯克利夫子爵庞大的大众新闻帝国所搅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伍尔夫逝世80周年之际,在这场疫情之中阅读她的作品,特别是她1925年小说《达洛维夫人》,我们能看到她是如何试图让死亡和疾病重新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的荣耀和力量的国家叙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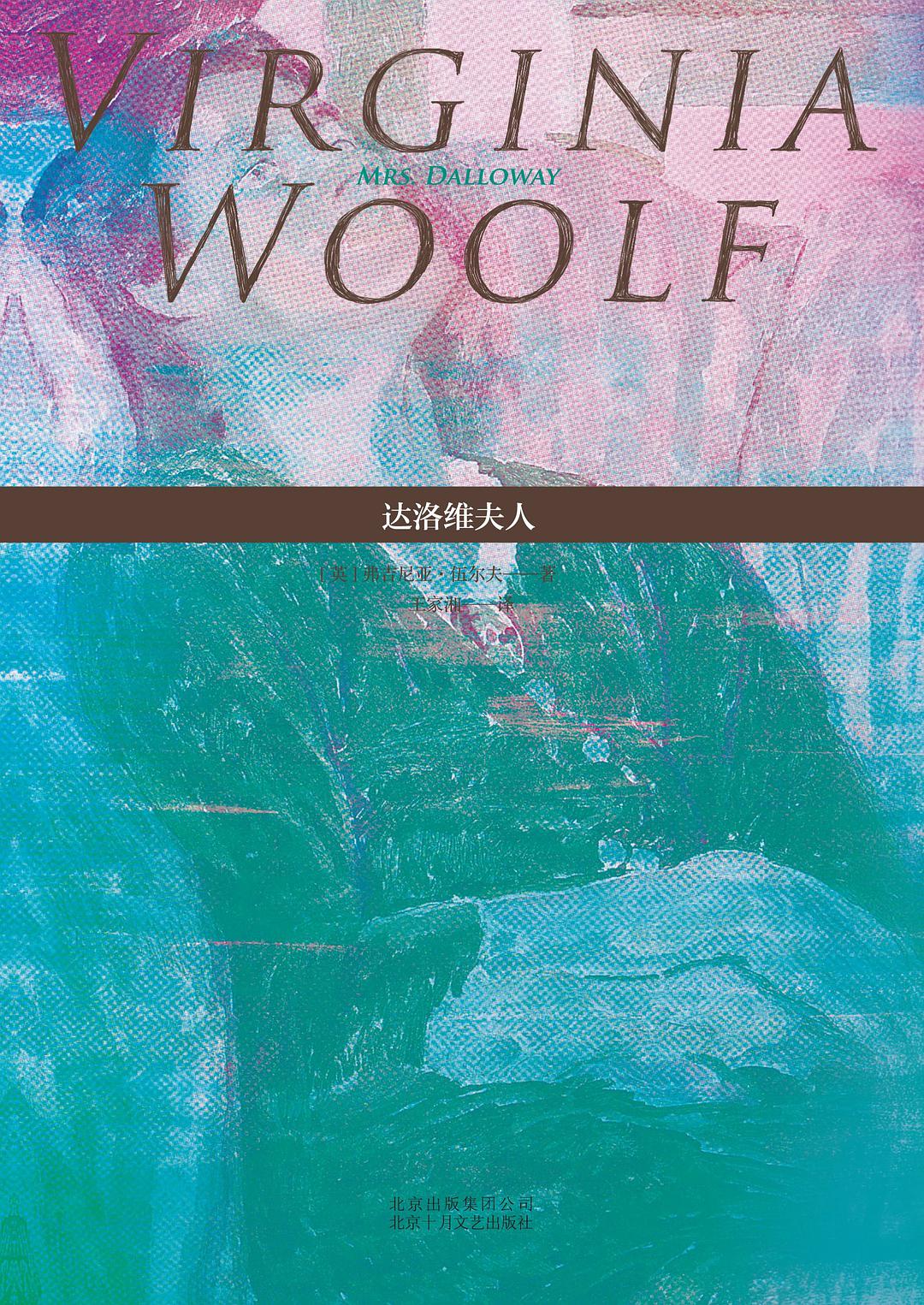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王家湘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3
抽离死亡

我是卡迪夫大学英语系的讲师。在疫情期间,在听者稀稀拉拉的讲堂里教授文学,是一份令人不安的经历。《达洛维夫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让我们得以在新的全国紧急事件在自己身边展开时,也能学习和思考。《达洛维夫人》的主人公是1919年西班牙流感的幸存者,贯穿全文的生命感慨来自于她重新发现生活乐趣的经历。我们认识了达洛维夫人,她在伦敦穿梭。在6月的一个早晨,她体验到了生活的宁静浓烈。
小说的著名开场白——“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在今年引起了新的共鸣,因为疫情使我们的世界变小了。达洛维夫人想自己买花,因为她很高兴能出去——我们也许能体会到这种感受,毕竟我们在室内呆了这么久。
在课堂上,我和学生都在思考,把达洛维夫人看作一个经历过大流行病并从死亡走出来的人物意味着什么。达洛维夫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禁锢之后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这是有代价的。

在小说构建的达洛维夫人的聚会上,传来了年轻的退伍军人塞普蒂默斯·史密斯自杀的消息。在伍尔夫最初的小说计划中,塞普蒂默斯并没有出现,达洛维夫人本来要在聚会上自杀。在创造塞普蒂默斯作为达洛维夫人的替身时,伍尔夫得以把死亡抽离出来——我们都希望能够如此。
伍尔夫通过深刻的向内挖掘来革新人物——她带给我们的不是人物的描述,而是他们的心理地图。我们通过意识流的写作近距离地从内部体验主角的感受,但一系列外围人物也在这部现代主义小说中涌现。
伍尔夫认识到,把人物推向生活的边缘是多么容易。毕竟国家小说都是如此,为主角腾出空间,牺牲那些被推到更远的视野之外的人。战后的英国为战争的荣耀腾出了空间,却没有为西班牙流感腾出空间。

集体记忆
《达洛维夫人》是一部展示记忆和哀悼如何维护大英帝国价值观的文本。它对情感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循环的关注,使我们能够理解国家的感情结构是如何通过报纸、通过符号认同的编排而产生的。
“在所有的帽子店和裁缝店里,陌生人彼此对视,”伍尔夫写道,“并想到死者,想到帝国的旗帜。”伍尔夫有意展示一些难以确定的东西:民族共同体是如何被创造和维持的,以及战争中的死者是如何继续支撑着一种不可阻挡的英国国家身份认同。
伍尔夫看到,要理解死亡如何继续影响一代人的情绪,需要一个主观的视角。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类似时间点意识到的那样,哀悼是持续的、虚幻的工作。关于她的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死亡如何将我们推向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承认自己的生命更脆弱,更依赖于他人的生命。
正如伍尔夫的一个角色在《出航》中所阐述的那样:
“这似乎是如此的莫名其妙,”伊夫林继续说道。“我是说死亡。为什么她会死,而不是你或我?才两个星期前,她还和我们其他人在这里呢?”
伍尔夫表现出了解释死亡的艰苦卓绝,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死亡共存的困难。面对死亡的孤独、死亡的公共形式的日益消亡,以及公共悼念制度的减少,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纪念制度之外的死亡语言。
(翻译:王宁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