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作家余华在八年之后推出了新作长篇小说《文城》,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村庄为背景,书写一位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的男子,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落脚,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结交朋友,日子逐渐过得平静安定,而此时外部世界正在剧烈变迁,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村庄的生活。
《文城》出版问世后,评论称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回来了。小说《活着》的时空背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这部小说的时空设定比《活着》更早。余华说《文城》是他在20世纪的最后两年开始写作的,在写法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与前作相似的特点——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死死,忍受着饥饿、战乱和苦难,也经常陷入彼此斗争之中。
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写法?如果如人所说余华的小说里都是善良的人经受着苦难,那么这种善良和苦情会引领我们去往何处?
一、始于哺乳,内里饥荒
林祥福带着女儿讨母乳是小说开头最为重要的画面。村里人记得他当时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挨家挨户讨奶水,看起来像一个谜,之后才揭示出母亲小美离去的直接后果就是女儿无人喂养,他向父母告别离开家乡,告别辞是“你们的孙女要吃奶”。寻找小美的途中也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像小美一样的女人,一个是正在哺乳的女人,前者可能是女儿的亲妈,而后者能够喂饱女儿。他来到溪镇,感到这里的人们和善,因为这里有人主动上前将他引入哺乳期的女人家中。小说写,他依靠聆听婴儿的啼哭来寻找哺乳的女人,一次次地敲开大门,向女人和他们的男人祈求奶水。

作者在写溪镇的哺乳场面时,沟通了幼儿与主角的生理感受,胸部的温度、触感、都由女儿和父亲同时感应,父女完全感同身受:“他取下胸前的棉兜,将女儿递过去,看到女儿终于达到那些女人温暖的胸怀,他的体内就会出现一股暖流。当女儿的小手在她们胸口移动时,他会眼睛湿润,他知道她抓住了,就像是脚踩在雪地上一样。”这样随机的哺乳生涯终于在林祥福找到了一位稳定的、善解人意的女人后告终,她是工友的妻子,看起来更像一位“母亲”的角色,她以奶水让女儿吃饱了,健康起来,林祥福听到婴儿响亮的吮吸声“不由得泪流而出”,又一次与女儿的感受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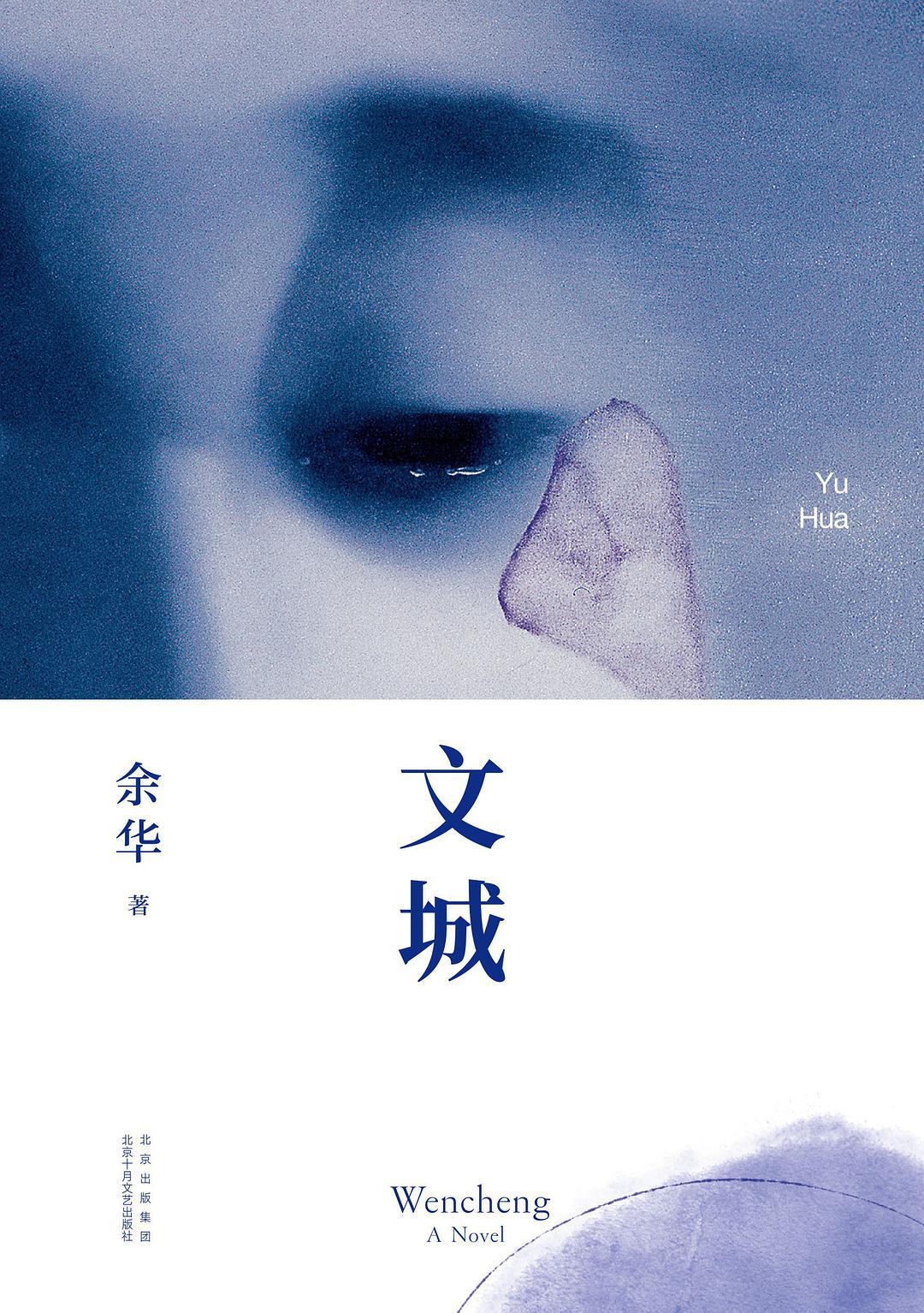
余华 著
新经典/北京出版集团 2021年
因乳汁欠缺开启的寻母之旅,也因为寻到哺乳的“母亲”而结束,小说开头明确无误地萦绕着从婴儿角度出发的饥饿感。林祥福将女儿名字唤作“林百家”,流露出对女人们慷慨解衣的感动,同时也涵盖着父亲在陌生的女人胸前的乞求,慷慨中充满随机与不确定,饱食总以乞求异性为代价,这才是林百家名字的真正意涵。关于哺乳崇拜的描写,可见于更多当代作品,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将惠嫂的乳汁比喻为瑰宝资源“源远流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莫言在写喂奶时也细致地描述“那混合着枣味、糖味、鸡蛋味的乳汁”是“一股伟大瑰丽的液体”。
与这种饥饿感遥相呼应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吃食。在决定前往土匪窝赎回顾会长之前,林祥福吃了一碗酱油炒饭,仅仅是混着猪油、小葱和酱油的炒饭,被写得朴素但具有人情味。在他终于进入土匪窝后,也被招待了一碗炒肝,那是让他感到怪异反胃的一餐。他觉得那味道十分奇怪,既不像猪肝,也不像羊肝牛肝或是鹅肝鸡肝,后被告知那是他们顾会长的人肝——用土匪的话说,叫做生剖取肝。因为这顿饭,林祥福对土匪发起了最后的抗争——他红了眼睛,将碗砸向他们,手持尖刀向土匪头子张一斧扑去。
以众位女性的奶水为食会成为一个婴儿的名字,大人吃下的朴素一餐也能成为荣誉或耻辱的象征。这不禁令人想到余华最早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一幕——还是孩子的“我”被领进了一家面店,因为自尊拒绝点餐,被招待了一碗价目表上最贵的三鲜面。这种写法似乎映证了陈晓卿所说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饥荒基因”,正因饥饿,朴素的餐食也令人记忆深刻,报复性的大吃也再一次佐证了之前的难忍——《文城》中被绑匪释放的少年喝到米粥,发出的声响像是往井里扔石头。《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里都有孩子贪食豆子的描写,前者中“我”弟弟在婚礼上贪吃了一百五十颗蚕豆臭屁滚滚,后者里的苦根因为吃了太多豆子而胀死。
二、竞技一般的酷刑奇观
如果说哺乳和吃食,以满足身体的方式,标志着一个人应当向谁感恩或报复,那么酷刑就以对身体摧残的花样百出,展现出了丧失尊严的可悲与可笑。《文城》里书写匪祸,描绘土匪对村民的摧残自不必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细致地诉诸文本的凌虐有时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游戏。溪镇人被绑票时,各人有各人的虐法,李掌柜的被抽鞭子、张嘴呼喊时被撒进灶灰;唐大眼珠的脸被抽成一团模糊的屁股,屁股被抽花了,还被铁钳烙出两个“眼珠”……齐村村民被集体屠戮是小说中最惨绝人寰的场面,此时书写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体凌虐所构成的奇观种种。
“女人看见前面的女人被砍下肩膀,砍下胳膊,砍下脑袋,仍然视而不见地扑向自己的孩子。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跑来,张一斧上去砍下孩子的头,孩子的鲜血喷涌而出,女人满脸是血,她浑然不觉,抱着无头的孩子仍在奔跑,她以为孩子安然无恙,跑出了村庄。”
读者可以将这些凶恶的行径归罪于乱世土匪丧心病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对于人体的强调和戏弄。人体的器官、内脏和肢体都可以成为暴力奇观本身,唐大眼珠的屁股成为脸,脸再成为屁股——不止是为了行凶,更像是一场狂欢,先是肆无忌惮地毁灭他的脸和屁股,再以荒诞玩笑的方式再造屁股和脸,而将脸和屁股颠倒本身就令人丧失尊严,因此甚至好笑起来,就像小说里写人们杀猪时听到猪的低声呜咽反而会发出阵阵欢笑一样。如果没有丧失尊严的前提,酷刑也就没有意义,这点在溪镇顾会长的土匪窝受虐事件上最为明显,他遭受了“摇电话”(用竹棍插进肛门摇动起来)的酷刑,而他此前被明确地称为“溪镇最有尊严的人”。
小说也顺着有关器官、人体的想象编织出了一些奇幻的场景,这也是余华所擅长的。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爷爷在濒死前讲述自己的魂从口中飞走了,他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只能慢慢等待它降临。在《文城》里,土匪们在释放人票时割去了他们的一只耳朵,失去耳朵的人们不会丧命,但受到了微妙的影响:跑步失去平衡,不会跑直;没有耳朵的先生讲课时倾斜身体,“像是被一根绳子扯住了”,失了威信。割耳并非首先出现在《文城》中的刑罚,《在细雨中呼喊》一样有割左耳的酷刑——父亲骚扰妻子破坏人伦,为妻子报仇的哥哥割去了父亲左边的耳朵。复仇也要朝向人体的同一部位,否则不算真正的以牙还牙,《文城》末尾,工友陈永良为主角林祥福报仇,在意的也是要向敌人的左耳根刺上尖刀,因为他记得,林祥福死时尖刀刺在左侧耳根。

余华 著
新经典/北京出版集团 2018年
还有更多的身体描写,仿佛是不经意地被带出来的——虽然也很严酷,但重要性明显不如前面的例子,更像是一种荡漾于文本内的间奏。比如余华写刚刚被枪毙的连长,他刚刚吃进去的肉食和肠子一起流了出来,而这段描写的前后是负责枪毙连长的年轻副官向往林百家、憧憬恋爱的温馨场面。如是间奏反复出现,以至于到了齐村村民被大规模屠杀之时,读者不再会感到惊讶,虽然这里惨死者空前的多,死法也有着花样百出的残忍。
与上文引用的“砍瓜切菜”相比,余华小说中的性酷刑看起来似乎没那么明显,但也值得一提。妓女遭受官兵性凌虐,妓女们按照官员级别大小服务,先是旅长、排长、营长,接着是排长与班长,到了晚上士兵来时,她们已经承受不住,纷纷哭诉“饶了我们吧”。具体的折磨也体现在她们的身体饱受蹂躏,“她们的乳房被捏肿了,她们的屁股和大腿像是脱了臼的疼痛,”还是“供不应求”。官兵对妓女的折磨来自于性欲的不可控制与性能力的绝对征服,鉴于官兵与妓女的身份,以及以妓女哭诉映证官兵夸张的性能力,这样的凌虐不仅不显得可悲,甚至还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笑谈气氛。似乎对妓女的征服是比较容易写得如闲笔般的段落,小说中写十几岁的少年嫖妓,同样是雄风凛凛无坚不摧、令妓女们避之不及,因为伺候他一夜像是在码头干了一天的活。相比之下,土匪对女子的侵害就是赤裸裸的虐杀。他们洗劫村庄时,因为争夺姑娘而大打出手,他们“每人一枪将那个姑娘打死,然后继续挥刀互斗”,“十多个年轻女子被土匪轮番强奸后,又被土匪用长刀砍落人头”。
余华小说中最有名的酷刑应当是《现实一种》中的狗舔脚心(这与辛格的小说《泰贝利与魔鬼》相通,里面写地狱里最重的刑罚就属呵痒,地狱里被搔挠脚心和咯吱窝痛苦难耐的笑声一直传到了马达加斯加岛)以及《1986》回归的知识分子的疯狂,他高呼着墨、劓、剕、宫,想象着将人们的脸上刻上文字、剜去鼻子、切除膝盖以及实施宫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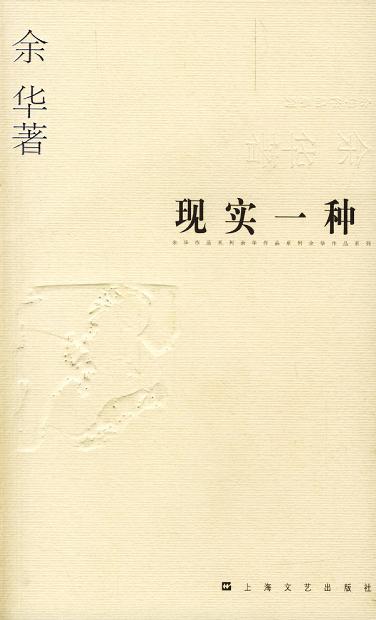
余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
关于酷刑,我们思索的也许不仅仅是是摧残身体哪个部位最具羞辱性、最令人难以承受、最让人心惊胆战,而应当去询问酷刑到底有着怎样的揭示与预言作用,提醒人们看到日常不曾注意的暴力。而绝非沉溺在哭诉求饶和嬉笑狂欢交替中,对施虐者可能报以憎恨,对受虐者怀有更大的轻蔑,最终潦草地归为人性黑暗,毫无耐心探寻其中更大的问题——而这是恰恰是酷刑书写最容易达到的效果。
事实上《1986》中的酷刑想象被表现为一种文革后的精神创伤,已经展现出了分析黑暗和恐怖的可能,小说写人们沐浴在新的世俗空气中,而只有他一人受过去的折磨,被痛苦改变了存在的形态。人们说卡夫卡长于酷刑与恐怖,2020年去世的乔治·斯坦纳在评价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与《审判》时强调了残酷与恐怖书写的预言性质——《在流放地》预言了新型施虐方式,即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可憎的巧妙合作;《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预言了缺乏个性杀手的空虚无聊、极权主义偷偷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这种恐怖的观察眼光,如斯坦纳所说,正根植于他的法律训练以及对阶级关系和经济事实的关注,也来自于他对非人道时代来临的洞见,并非单纯残暴的血腥描写和性虐呈现所能达到。
三、疲惫于苦情人伦
余华将《文城》置于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又以雪灾和匪祸构成艰难的生存环境,其中的人物从林祥福、陈百良、顾益民到被卖作童养媳的小美、天生就失去母亲的林百家,无不面临艰难困苦。如此背景使得林祥福这样愿意救赎的人、陈百良这样始终记得复仇的人,还有顾益民这样感恩图报的人显得尤为难得,就算是那个心存欺诈之意跟了林祥福却两度出走的小美,也有《文城补》的陈述补足了她的悲哀和不得已。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子东所说,余华小说的特点在于其中的人都很苦但很善良,余华自己也认可小说中人物的善良,他说不想将小美写成一个坏人。既然苦是循环回荡的主题,或许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苦与善的关系是怎样的?人们在苦难的反复折磨中,体现出的善究竟会通向何方?
齐村被土匪洗劫,小说达到高潮,村民们被屠杀,被丢入湖中,最终变成了鱼肚子里的指甲,还能有更悲苦的结局吗?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读到了文本中的许多苦,也见识过《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里的死法多样,这样的结果更像是不断的重复后的剩余。一个女人的死可以说是对前一个女人的死的重复,一个人的被杀戮也可以说是对一头猪的被戕害的重复,这样的书写也许确实可以展现生存、死亡的随机与荒谬,证实乱世中个体的微不足道,但也让苦变成了命运仁慈与残忍的随机事件,取消了书写苦对于个人的深层次的震荡与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不同于另一个人,仅仅在于死法的随机性,是眼睛上挂着眼睛,还是屁股变成了脸。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
苦情一方面是由时代、时势决定的,就像许多当代小说书写的那样,个人在历史变迁中起伏不定,另一方面则在于伦理生活的悲剧,这两者在小说中通常呈现出互相交织的状态。林祥福因受了欺诈,有了女儿却没了妻子,投奔寻找的旅程也是追求夫妇人伦圆满的过程;之后找到溪镇终于让女儿有了“母亲”,林自己虽然没有组建家庭,但女儿初长成便许给了顾家的少爷,也算有了延续。而女儿和陈家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悸动也是故事重要线索之一,春夏之交的一个中午,林百家与陈耀武在树下懵懂地彼此触摸、瑟瑟发抖——这个举动被林百家的义母、也就是陈耀武的母亲撞见,她呼喊着作孽啊,所谓的“作孽”指的是两个孩子僭越了道德准则,将要破坏林百家的婚约。遵守道义的工友陈百良携全家搬迁至齐村,正是这次搬迁串联起了齐村和溪镇的关系,最终奠定了齐村村民遭受屠戮的悲剧。
如果回头阅读《在细雨中呼喊》,我们可以发现,两处“作孽”的呼喊对应的场景几乎一致,是不受控制的情欲、出格的性行为对人伦关系的毁灭——一处是父亲捏住了大嫂的短裤以及里面的皮肉,母亲知道后说“作孽啊”;另一处是少年扑向七十几岁的老妇,要扯下她的裤子,老太太说,“畜生,我都可以做你奶奶,”又忏悔般地喊道,“作孽呵。”
“作孽”的呼喊之所以惊心动魄,因为人伦关系在小说中是如此重要,是人物角色的基底,也是故事发展的动力。《文城》中人物的善良并非没有根基,他们的善是一种维持人伦的善,是基于五伦——婚姻、亲子、朋友关系之上的善。如果说所谓苦情主要来自于世事浮沉、不由自主以及这种境况下的人伦破坏,他们的善也就体现在于这样的环境中仍然为了人伦圆满而牺牲自我。
《文城补》中的小美看起来更不像是个坏人,因为她被置于整套家庭关系中,她需要侍奉严格到僵硬的公婆,也会怀念自己抛弃的孩子( 有趣的是,小美被休的情节又一次与《在细雨中呼喊》里“我”奶奶的故事形成了呼应,“我”奶奶也被恪守道德的婆婆休了,在离开前,古板的丈夫一样给予了她最后的温存)。而对这种善的破坏,自然就表现为对人伦关系的滥用。《在细雨中呼喊》里“我”父亲滥用家庭权力、无法控制情欲,是不折不扣的家庭暴君,《现实一种》中同样是兄弟妯娌之间互相倾轧的人伦惨剧。至于村庄或者学校青少年间的残酷与斗争,则是这类人伦关系的放大版本。人们因为最基础的感情关系和最原始的尊严互相厮打,有人通奸、有人施暴、有人疯了、有人死了,而女人经常堕落。这样的故事似乎与任何时代背景都没有关系。或者说,看到这样的村庄故事,更会想起的是胡安·鲁尔福笔下的墨西哥村庄, 毕竟其中有类似的家庭关系、欲望斗争与生生死死。
读者也应当注意到书中人物或者叙事者对于苦难的沉默。《文城》中的“和尚”可能是个例外,他为自己当土匪做出解释,也仅仅停留在慨叹乱世身不由己,“身处这乱世若想种田过日子,必遭土匪劫杀;若做上土匪,不抢劫又活不下去。”人物的遭遇一再让人掉泪,但掉眼泪并不是很高的标准。看到那么多村民浮尸于河中,读者可能会和故事里的人一样,仿佛闻到腐臭,感到情绪被耗尽的疲劳。
四、传奇与良善的陷阱
评论者和余华都认同小说的传奇感,余华说传奇小说的特点在于由情节驱动人物,而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在于用人物驱动情节。也就是说,他承认传奇作品中的人物可能存在情节“工具人”的性质,形象较为简单,情感也更为分明。说起来,传奇的风格并不是从《文城》开始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具有这种俗世传奇的特点,比如《在细雨中呼喊》拆解后几乎看作是“我”的流氓父亲小传、“我”的混账哥哥生平、“我”多情的养父和多病的养母传记,此外还有纯情的姑娘堕落为娼妓、友善的同学死于流行病的插叙。之所以说是俗世传奇,是因为小说更突出这些人物特征的鲜明以及经历的离奇,他们的行动出于饥饿、性欲、天生品性——如同未进入社会却陷入同龄人残酷斗争的青少年,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动机。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
在《文城》里,林祥福和陈百良的合作也有共同谋生的目的,但这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小说他们挣钱的过程充满诗意,二人具有高尚的品德,甚至会修理无人居住的宅屋的门窗,手工艺精湛更像是为林祥福的工匠传奇再增添了一笔传说色彩。如果以巴尔扎克《贝姨》里的雕塑家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后者的工艺更多关联的是一笔笔具体的金钱交易,雕刻谁的塑像,接下什么项目都关系着偿还债务、养家糊口以及在某个社交圈层中立足。
从表现良善的方面来说,《文城》确实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相通,像《三侠五义》那样,这个世界讲究善恶分明、有仇必报,将主持公道的职责赋予英雄(或者包公和鬼魂),崇尚侠义与孝顺。名为“和尚”的土匪也有慈爱的老母,令人想起《水浒传》里的李逵与老母,虽然作恶多端杀人如麻,还是不违背最基本的孝道。作品中的爱憎分明、善恶有报的爽利当然令人称快,但以通俗文学中的道德和道义作为创作范本,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如苏力在以古代戏剧为分析材料的《法律与文学》中所写,传统戏剧诸如《窦娥冤》《赵氏孤儿》都凝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话语:善恶、忠孝和三纲五常等等,而如果将这一点与这些戏剧主要的消费者市民阶层联系起来,就能发现这种道德话语的社会控制功能。苏力推论说,一般来说,俗文学的作者一般比诗歌、散文甚至非话本小说有更少的表达自由,因为后者通常具有更强烈的个人性以及个人的特殊经验及感受,而前者通常会受制于正统意识形态。当然这也有具体的历史背景,苏力说,通俗文学诸如元杂剧中的道德话语之所以强烈,与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关系不大,可能受制于传统社会政治治理能力的不足。
将苏力所说的通俗文本与巴尔扎克的小说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创作自由的推论的道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诸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贝姨》都有强烈的巧合因素,人物也并不复杂——这或许指向了其传奇性,但其中的人物动机、故事发展以及巴尔扎克在字里行间的评论都不可能脱离其时代和经济背景,从家具陈列到婚礼庆典,从经营商铺到剧场娱乐,巴尔扎克都运用了观察以及洞察的能力,于是读者可以清晰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面貌,也得以分辨人类情感的复杂情况:爱情可能混合着虚荣与欺骗,欺骗中又蕴藏道德激情,而不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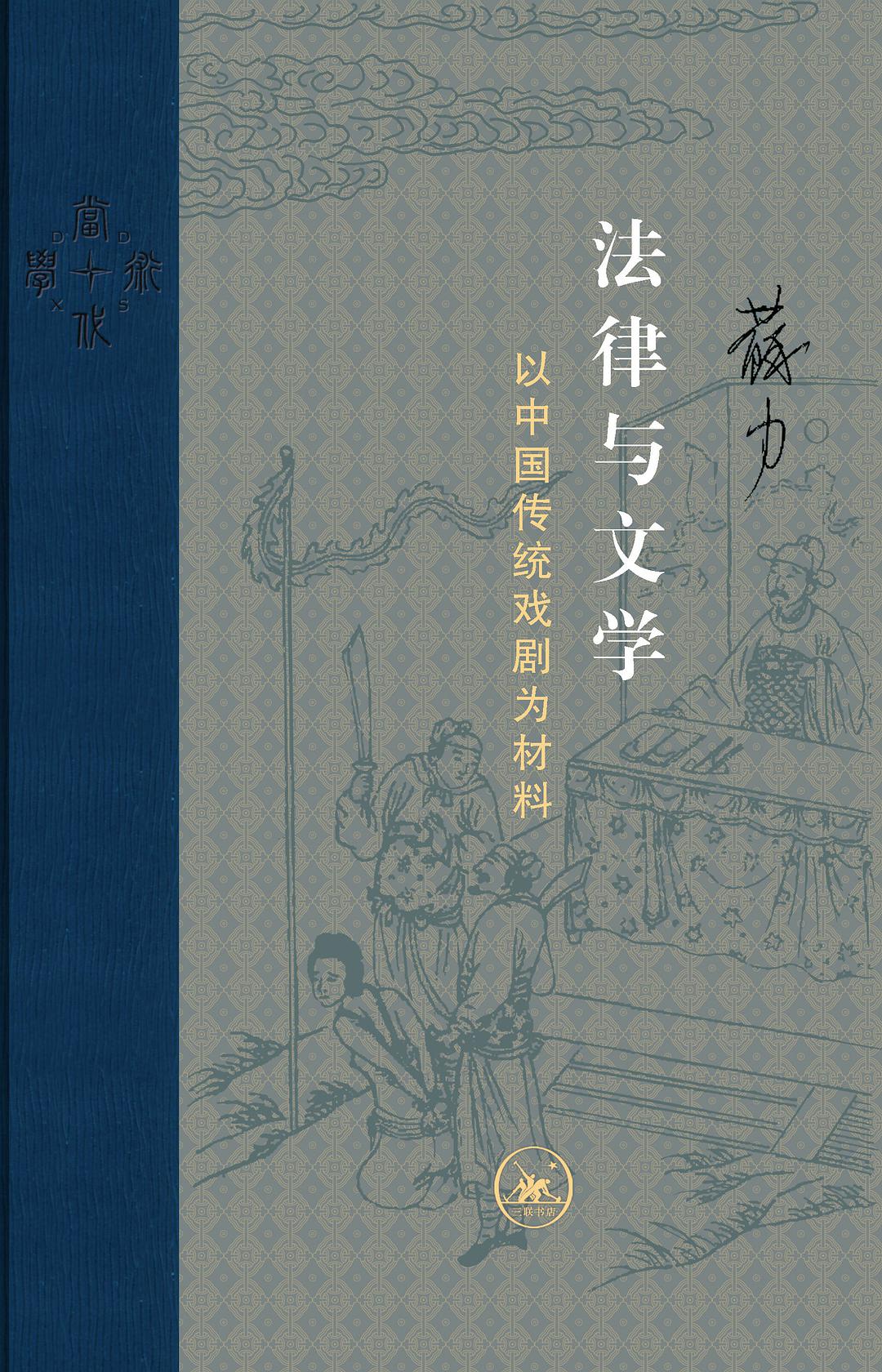
苏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
再进一步分辨这种善的力量,不难联想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的观点。密尔在论证个性的重要性时提示我们,依据大多数人的善恶道德进行判断具有危险——公众将个人的善恶当做适用于整个世界的义务,是人类最普遍的倾向之一,因此道德情感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它谴责怪异、鄙视个性,不鼓励任何与习俗不同的举止,甚至有观念暴政的危险。回到《文城》的文本中来,满足于表现良善可能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基于人伦、忍受苦情的善不足以启迪人心,也在于这样的善的人物,基于更多数人认同的善,最终指向了一种缺乏个性的想象,甚至是有些粗暴的判断。 因此,由善人构成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dystopia),仍是一个问题。
当然,《文城》中依然保留一些光亮与开阔,死去或者疯掉的人最与尘世以上的世界接近。例如,结尾处林祥福由田家兄弟送葬归乡的处理,流露出了仿佛救赎的神性,村庄里傻掉的万福也是最接近神圣世界的人,他们在这时终于离开了残酷的斗争,归于平静,苦情也终于不再变本加厉,抵达了开阔一点的地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