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五一出行,你偏爱偏远郊野还是名胜古迹?假期结束,你将如何记录或讲述这次旅程?古代士人又是如何游山玩水和以景言志的呢?
在日前出版的《玉山丹池》一书中,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学系教授何瞻(James M. Hargett)教授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游记,为我们解读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地理观以及社会空间观。从这些跨越历史长河的游记中,我们看到了从富阳桐庐至桂林七星洞的奇山异水,也看到了从山水审美到旅行娱乐的更迭。
六朝:山水审美的发端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吴均《与朱元思书》
在这封著名的致友人的信件中,吴均没有提到关于自己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提供行程的任何细节,唯一要传达给朋友的信息就是富阳桐庐一带景色优美。在信件的最后,吴均也发表了对景色的回应,“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何瞻写道,《与朱元思书》体现了六朝时期游记的要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景观描写—作者评论(scenic description-author comment)的结构,这在中国诗词中是常见的构造,在近现代中国文学评论中也有表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这一结构称为“景”和“情”——“景”指作者在物理环境中的移动,在路上或者江上行进,而“情”常表现为个人对景观的反应。《与朱元思书》之后的游记都沿用了相似的“主题—评论”结构。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六朝时期另一封以风景书写著称的书信。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骈体写成、以旅途为情境、描写山水景观的书信。在信中,鲍照记录了自己从南京到江西的旅行,登上雷池(今在安徽省)堤岸时,他写道,“途登千里,日踰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与其他的赋一样,何瞻说,写信人对景色的美学欣赏是有限的,原因在于他心事重重,为追求政治前途,他离开家庭前往陌生之地,宦途令他感到悲伤。
六朝山水欣赏的审美兴起,与4世纪晋王朝的覆灭有关。那之后官员与士族迁移至南方长江三角洲一代,而此前在北方,几乎没有什么作者写过游览优美的山水景致。在南方定居后,他们发现了这些清新的山光水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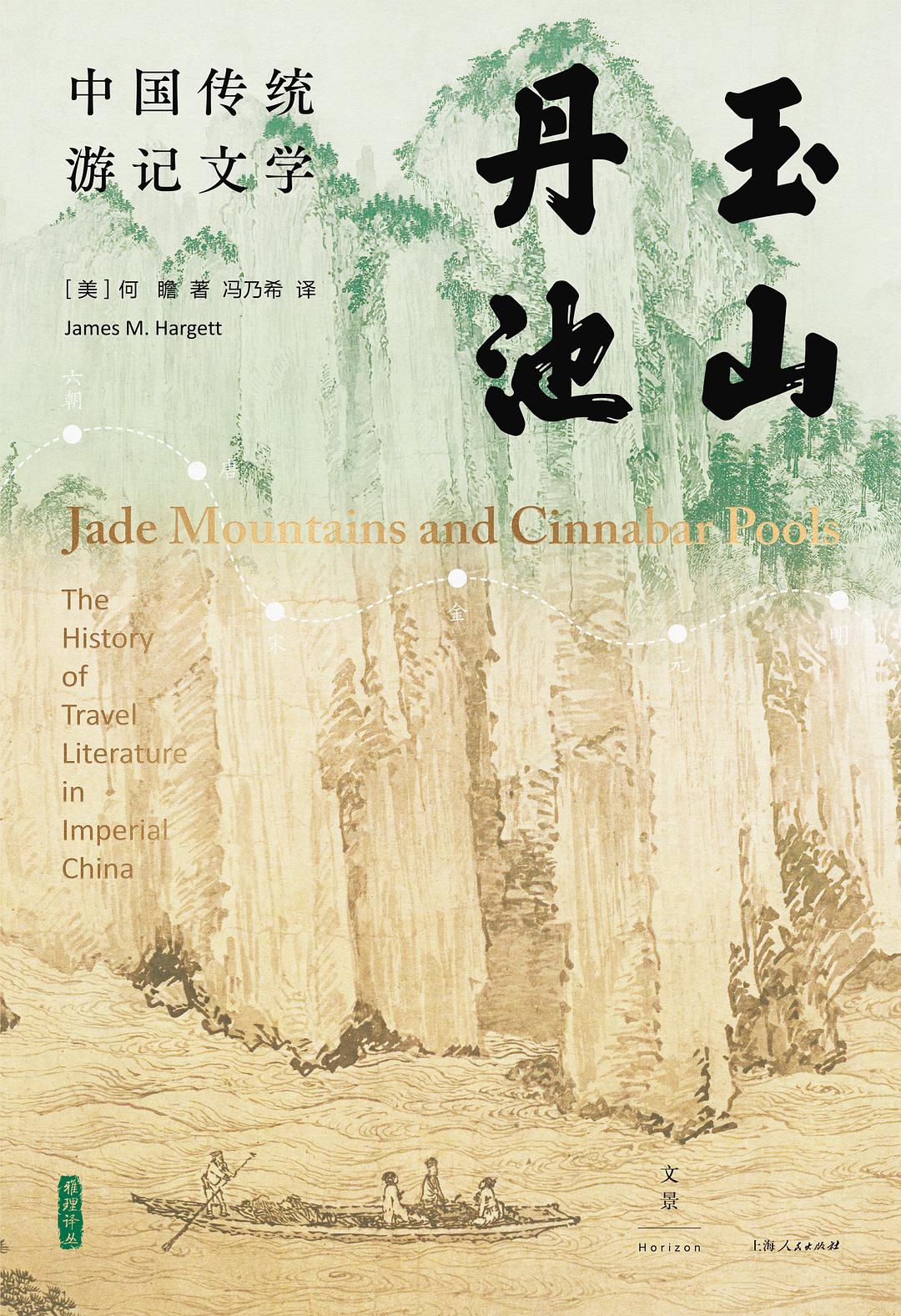
[美]何瞻 著 冯乃希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
唐:个人与山水的统一
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柳宗元《永州八记》
公元805年,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连同其他失败者一起,他被安排到湖南南部的永州。在那里他度过了十年岁月,也创作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永州八记》写作时间跨越四年,在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头,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之后他逐渐发现了此处的“奇”“异”“怪”和“美丽”。何瞻提示道,我们应当意识到永州八记中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柳宗元在这个偏远的、疟疾横行的地方,感到屈辱与尴尬;另一方面,在探索原生态美景的同时,他也获得了短暂的愉悦和解脱。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柳宗元将自己的困境与永州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他在美丽却不被欣赏的山水和被贬谪的自己之间发现了一种类比关系。在《永州八记》最后一篇的末尾,他感慨“造物者”的存在,所谓“造物者”,是一个负责创造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超自然存在。柳宗元试图对流放的生活妥协,直接发问道,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有意识的造物者,为什么要在如此偏僻的蛮夷之地创造优美却无人来赏的环境——以此间接指涉自己的困境:如果造物者创造了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人,为什么要将他发配到这样一个无法报效君王、也无法施展才华之地?

既然是无人欣赏的环境,通过他的抒情状物,人们便可以了解这个地方。柳宗元将《永州八记》的读者定义为“好游者”。9世纪早期,除了被贬谪流放,身居中国北方的士大夫从来没有去往炎热偏僻的南方旅行。这种以山水美景告慰从未去过此地的读者的做法,也为后人所继承,徐霞客便是其中代表。
何瞻也注意到,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将自己和朋友都包含在了叙述中。他积极地参与到描述的场景中,“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他的感官情感也与山色水光互动,“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在游记的最后,他说,“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此时此刻,山水与情感完全交融一体,这样的游也既是物理的远足,又是精神的旅行。
晚明:游览玩乐与科学考察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用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张岱《陶庵梦忆》
晚明以来,旅游繁荣推动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游记创作进入高潮。与之前的游记不同,这时候的游记作者往往喜爱前往一些有名的、舒适的、方便到达的地区。上文这段引文就来自张岱雪夜游览西湖湖心亭的记述。何瞻说,张岱的写法与通常游记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详细地描绘雪景,也没有提到雪天泛舟的危险,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两个无名游客身上,还引用了他们略带称赞色彩的自嘲“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说自己暴雪游湖,实在太痴了,复又引用船夫的话,“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种幽默的自嘲构成了旅行写作中全新的作者回应,属于一种自我再现,而这正是晚明文人生活的一部分。
何瞻引用卜正民关于16世纪以降旅行对文人的意义说明,旅行已经从与朋友共享的活动变成构建文人身份的关键因素;创作游记成为了士大夫文化、自我完善的方法,游记为旅行作家带来了相应的声望。与浪漫的暴雪游湖不同,张岱也去过泰山,但对泰山之旅非常不满。他抱怨道,每一段攀爬途中都会遇到大量乞丐,游人随处题刻亵渎泰山神圣,这也恰恰表明,明代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旅游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游览名胜。
历级而上约三丈,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为七星岩。从其右历级下,又入下洞,是为栖霞洞。其洞宏朗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官职,他出生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是明代最典型的“私人旅行者”。1637年,徐霞客访问桂林,并用两个月的时间记载了这个地区一百多个喀斯特岩洞的状况。在第一次游览桂林七星洞时,他记录了溶洞内部幽黑曲折的空间、描写了导游的服务,最后还总结了旅行的里程数。徐霞客似乎从来没用过指南针,仅仅依靠纸笔观察和标识周边环境,而20世纪的喀斯特专家的研究证明了他书写的精确性。在叙述空间移动方面,他也极富技巧,以动词来展现方位和空间,也赋予了读者某种参与感,譬如他在七星洞游记中写道,“由台北向,洞若两界,西行高台之上,东循深壑之中。”

徐霞客对大部分地理书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引用的不是神话传说,就是过时的记录,大都是简单的代代相传,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通过务实的科学的调查方法,徐霞客想要为一个地方留下准确的记录。正是在1638年的一次贵州之行中,他发现长江的真正发源地并不是《书经·禹贡》所称的四川岷江,而是青海的金沙江水系——虽然以现在的知识看来,徐霞客也没有正确指出长江源的位置,但他已正确地发现长江源位于金沙江水系上游的某处。
徐霞客的地理调查也代表着与传统地理学的决裂。传统地理学主要关注国家管理机构的演进,受到儒家国家秩序和平衡的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各朝的《地理志》都可以作为这样的地理调查的代表,其中呈现的地理信息支持并强化了国家政治管理组织的等级差序。《大明一统志》(明代地理总志)这样的专著并不旨在增加人们的地理知识,而在于搜集和展示能够加强政治控制的信息。明代晚期国家对地理学的控制日渐衰微,而地方或私人的方志作者花费巨大精力,尽量提供给完善和准确的信息,从而促进了晚明旅游事业的繁荣。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