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下午,五位中国作家梁鸿、欧阳江河、李娟、颜歌、余华做客哈佛大学,与特约嘉宾、作家哈金就“如何书写当代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演讲与讨论,主持人为哈佛教授王德威。这是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和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中国文化创新领袖”项目的一部分。
或纪实或虚构,或诗歌或小说,五位作家的书写各有不同。就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经验与困惑。

梁鸿:“我们不能像鲁迅那样写农民”
“当代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断裂”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被局限的生活,相互之间是一个被隔离的状态。乡村与城市,南方与北方,农民与市民,你与我,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你在乡村生活,完全不知道城市怎么样,虽然有网络,所有人都有手机,但我们的心灵、精神都特别隔绝。反过来,城市也不知道乡村,哪怕这个保安就在你身边,你也不知道他的精神状态,也从来不会去关注他。
这样一种巨大的断裂,包括官方与民间,包括政治制度对个体精神的束缚,因此书写当代中国非常难,因为没有“整体性”,精神和生活形态都处于特别四分五裂的形态。但这恰恰为文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空间,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书写。
我原来一直搞文学批评,2008年回到自己的家乡,以我的故乡为原点,写一个村庄的生活,我给它虚拟的名字叫“梁庄”。我也是那时才意识到,虽然你每年都会回家,但当你真的站在故乡的村头,站在你熟悉的那些亲人面前,你才发现他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才发现所谓中国社会确实是断裂的,每个人心灵差异如此之大,也如此难以进入。

所以2008年我在家乡住了五个月,每天在村庄和我的叔叔婶婶堂哥侄子们聊天,最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在梁庄》。当然,谁也不敢代表中国,我只是写了自己村庄的一个故事。我以农民的自述为中心,以我这样一个所谓的归乡的亲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为线索,来带大家进入村庄的现场,来看村庄的老人、妇女、儿童怎么生活,来看村后的河流、自然环境什么样子,当然也包括那些古老的传统,丧葬文化、礼仪等的变化。
2011年,我又沿着我们村庄那些人打工的足迹,跑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写了一本书叫《出梁庄记》。你突然发现中国的农民就像吉普赛人一样,即使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也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农民在城市做的职业。农民走出村庄以后,他面对的不再是农民,而是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国复杂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他们跟城市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一个三轮车夫,他既要跟抽象的制度及代表制度的管理人员、城管打交道,也要与市民、市井打交道,所遭遇的问题也很多面。
这两本书写完之后,我非常苦恼。那样一种尘土飞扬的生活,你试图用真实的文学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当你用真实之名来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后来别人说你的是非虚构的时候,我都说,我写的只是一个文学的、个人的村庄史而已。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主观的村庄生活。所谓的真实只是文学的真实,不是一个社会的真实。
2013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艰难的“重返”》,反思之前五年的书写。知识分子回到故乡,这实际上是一百年前的命题。一百年前,在鲁迅笔下,“故乡”一出场就死了,“没有活气”。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纠结的状态。一百年后的当代作家,比如我,还在写这样的故事。这里边本身就是一个视角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大的问题。
完成一种对中国农民新的书写,敞开他的一种内部的新的空间,这是非常难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渗透到文本之时,在多大程度上遮蔽了作为一个农民的自在性的空间?今天谈农民、谈乡村,我们依然用特别概念化的书写,愚昧、麻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充斥着这样的话语。 “农民”这个词可能是太固化了,需要作家来把它还原成一个社会普通形态的人的存在。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农民成了一种病症,成了社会一个大的问题。
前段时间有人批判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像鲁迅那样写农民”。我不是说鲁迅写得不好,而是说一百年后的作家,当你在面对农民这个群体的时候,如果你还是重复鲁迅,还是那样一个面貌,那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在去年写了一本短篇叫《神圣家族》。为了写小镇的十二个人物,每次回家乡我会待七八天时间。但我不想把小镇本质化,我想把人写在前面,写一个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流浪汉、坐轮椅的妇女等等,一篇一个小故事。他们也是环境下的人,但环境又没有决定这个人,有某些所谓的超越性吧。

欧阳江河:一个盛世和乱世纠缠在一起的时代
在中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现实感,每一种现实感都可能是真的,每一种现实感都是中国,但又全都不是。所以中国真的变得很复杂,又是一个盛世和乱世纠缠在一起的时代。
作为我们诗人,面对的是两重压力,一个来自于不同的现实感构成的中国,另外是诗歌写作者要面对的,诗歌本身带有它自足的、自律的形式发展的历史,得面对它传统的东西、原创性的东西,以及语言本身的一些形式、风格变化的压力。而写作本身又涉及到中文写作和汉语诗歌的差异,这涉及到一个诗歌写作中的原文问题。中文写作里的原文是什么?它可能是多种语言,不光是外来语言的差异,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中文写作也有很多空间、错层。
另外,还面对一种行话的挑战。媒体语言、政治话语、娱乐话语,或是手机语言、微信语言、微博语言等等。这些东西对中文诗歌写作中的“原文性”是一种质疑、剥夺、抵抗。在这样一种混乱的情境中,诗歌写作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应该怎么回应这样一种乱局,尤其涉及到消费政治、资本逻辑之时。
写作经常面临先于写作的阅读建构上的挑战。大家一讲到诗歌,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诗歌的原型,比如说他的出发点是海子,那是一种对诗歌的反应。如果你按照这样一个出发点来面对当代中国的写作,可能就会有“这是不是诗?”这样一种质疑。
所以如果我们不针对文本,很难一下子把这个复杂性呈现出来。写作本身面临怎样一种情况,文本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它一定是在写作、阅读和批评本身同时的开放和挑战下,形成的一种语言的、风格的建构,现实和文字的事实,以构成文本。所以我最近的写作在强调发生意义上的写作,也就是词语的肉身性、物质性,它的消散和内部凝聚的张力,在这样一个层次上进行写作,要反抗它成为纯粹的一种小资情调的、优美的、简单的东西。这是我最近写作的基本考虑。
观众:我来自日本,我也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看你们的作品,你们知道有海外读者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
欧阳江河:对另一种语种的读者,我写的诗歌可能跟抒情诗这些不太一样,不是为优美、忧伤写的,而是用一种更混合的语言形态写作的,带有一种公众的性质,某种意义上讲有一种冒犯的性质。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语言后面的形态,完全超越了词与物的关系。比如树这个概念,不同的语言内部词与词的关系又有一种衔接的、暗示的、隐喻的方向。这里文化差异已经产生了。
在诗人从事创作的时候,他面对的读者是谁,超越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写作的原创性,还要敞开阅读、理解意义上的原创性,这样才是够格的读者。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在为诗歌语言意义上的、原文意义上的读者写作。这样可能有时候很冒犯,不讨喜,让人不喜欢,但是没关系,因为语言一定得保留这种少数性,保留这种复杂性,否则我们的语言要退化。
汉语在形成过程中,除了魏晋的时候佛经的翻译,就没有被外语打扰过,它都是在同化其他语言。但是我们讲到当代诗歌的时候,它受到各种各样的翻译的影响,这个意义上,诗歌写作的原文怎么穿透所有的影响进入深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阅读和写作不在这个意义上相遇,相互理解,相互寻找敞开,就还是在一种比较浅的层次进行交流。而诗歌本身不是交流的产物。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碰到读者,就像荷尔德林碰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样的读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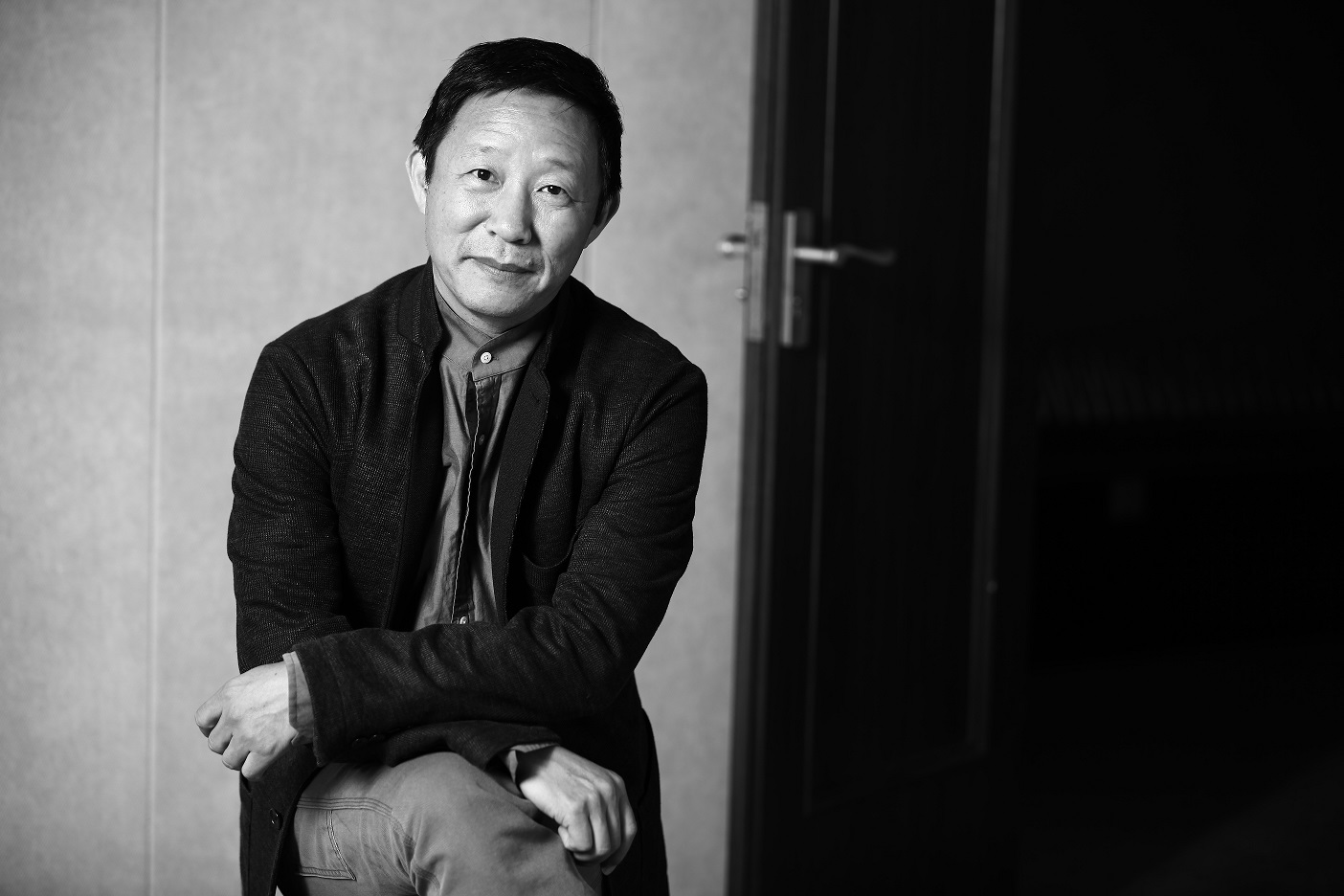
李娟:我渴望写出共有的快乐、希望和痛苦
我的写作大多是围绕我的个人生活展开。我生活在新疆,有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哈萨克游牧地区,我们家就在牧场上做小生意。渡过了几年难忘的少女时期,觉得所见所闻很有趣,就开始写,慢慢越写越多。那里比较偏远,生存景观迥异,一直被外人好奇。关于那里的历史、文化等文字有很多,但是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差异,让人读了仍然一无所知。我渴望写出他们与我们相同的那一部分,相同的快乐,相同的希望和相同的痛苦。
《冬牧场》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作品。冬牧场是位于沙漠腹心,交通不便,又没有手机信号,可谓与世隔绝。在我借居的地方,走一个星期也不能到公路上。居住的条件也很恶劣,就在地上挖的一个地坑里,叫做地窝子。一家人就挤在一起生活,不到十个平方。我决定进去采访之很害怕,但又非常渴望了解牧民的冬季生活。出于种种考虑,我开始了那段生活。
我的性格存在很大缺陷是在那里的最大障碍。和大家的日常相处总是感到艰难,很尴尬。其实无论什么样的采访,难免都会存在某种对立感。当我拿着相机拍摄,拿着笔记录,甚至仅仅是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强调我与大家的不同。都能感觉到对方的防备,尽管这种防备只是出于面对陌生人的本能反应。
记得以前一个朋友给我外婆照相,照片令我大吃一惊,外婆显得特别悲哀特别可怜。可是我给外婆拍的照片总是喜气洋洋。当时我的外婆身体不太好,我这个朋友可能觉得外婆很可怜吧。这种同情心被我外婆察觉到了,顺势表现出弱势形象,流露出乞怜的态度。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不是我真实的外婆,这是她的一种戒备状态。这件事给我了很大的顾忌与启发。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也是自以为是的人。
冬牧场是极度封闭的环境,在那里生活,我与牧人的关系远远复杂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我不但需要被接纳、被关照,更需要展示我的生活和劳动的能力,需要得到大家的尊重与认可。文学上的才华在那毫无用处。如果不能适应当前的生活,自己简直就一无是处。但我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在迎合什么,我觉得我只是在强调我和大家仅有的相同的部分。
我始终努力克制,淡化自己的采访行为。当时很多生活场景非常珍贵,我特想拍照,可却一直忍着。因为我觉得拍照与当前安静的艰辛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是一种打扰,甚至是破坏。而且只要面对镜头,大家就开始微妙地表演起来。只有当大家全放松下来休息的时候,我才开始拍照,然后把照片反复回放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很好玩,就会放下戒备。
在冬牧场的日子里,我小心遵从这个家庭一切的固有习惯,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我就尽量去认识它理解它,直到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接受了它。文化差异不可能消失,但可以去沟通去体谅。因此,到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遇到我真正抵触的事情。大家也感觉到我的真心实意。
我觉得这本书最扎实的根基不是我的思考和我的观察,而是自己流露在文字中的自信和坦然。就这个题材而言,很多人都可以写点什么出来,但我觉得我的文字无可替代。而那段生活对我也非常重要,不仅仅帮助我形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更是我人生一个重要过程,一场重要的修行。我很满意我这样的自己。

观众:我特别想在你的文字里找刻意,因为太没有刻意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作为文字的所有者,真的是在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都没有刻意吗?
李娟:我没有一个文字不是很艰难地写出来的。我很羡慕能一稿而成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很刻意地去写,很刻意地去克服我的不自然的那一部分,我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人。一直渴望改变吧,一直到现在,我快四十岁了,还一直在不停的改变中。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希望的。
颜歌:在都柏林写平乐镇
我从小就开始发表作品,被别人叫做少年作家,“八零后”作家,这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出身。实际上在我作为作家的大多数时间,或者作为一个写作的学徒的时候,我都在试图跟这个“不光彩”的身份对抗,或者试图在回答它。
2011年我来美国,真正开始书写当代中国,在比较天然的状态下写作。我那个时候在杜克大学读博士,学比较文学。但是我在美国的经验并没有给我一个PHD学位,它只教会了我一件事情,就是nostalgia(乡愁)。
在我离开我从小就开始当作家的中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看我自己,甚至很少使用中文的时候,我开始写我的故乡,写四川话,写过去的生活,父老乡亲,一直写到现在。比如我写了不是跟少年作家和八零后作家这个身份来对话或者去回应它的一个小说,《我们家》,基本上写的就是郫县,四川小城镇。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郫县豆瓣厂,里面有许多方言。当然故事不是真实的。
我很讨厌人家讲我写的是方言,因为方言是一个conspiracy(阴谋),你在写方言的时候,实际上你被边缘化了。所以我都说我是写的“有四川地方言语特色的中国话”。
我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用四川话写作的四川本土作家”,但这和我本人的差距很远。我住在都柏林,说中文的时候非常少,但是我写的是我们小镇上的四条街,镇上的那些人日常的故事,我就觉得这样我是不是很虚伪。但是后来,有两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爱尔兰作家的。
第一个是乔伊斯:爱尔兰是一个文学之国,乔伊斯是爱尔兰最重要的文学人。乔伊斯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不在爱尔兰。但他在《尤利西斯》、《都柏林人》里面,非常详细地描绘每一条街,每一个药房,每一个酒吧,他写了都柏林这个城市。到现在这么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所虚构的都柏林在经过快一百年之后替代了真实的都柏林。都柏林人会非常骄傲地告诉你说,这个店是以前布鲁姆去买肥皂的店,这个店是哪个场景转进去喝酒的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可能离我的豆瓣镇很远,但是我虚构的东西在很多年以后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上的真实。
第二个作家是贝克特,他回答的是我的另一个问题:我在写方言,但是在生活里我不用这个语言了,因此我很困惑。贝克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乔伊斯当秘书。而乔伊斯是“the king of portmanteau”,把英文玩得非常绝。贝克特想我该怎么办,英文我已经不想写了,写不过乔伊斯。于是在离开爱尔兰以后,他决定用法文写作。他写的东西变得非常极简,因为他想知道语言从文学里面减去以后,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贝克特的故事对我现在很困惑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观众:在这个纸媒没落的互联网时代里面,作为一个作家,继续用长篇小说、长篇记录文学来试图向社会传达一个信息,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或新的挑战?
颜歌: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年以前开始就有人在说。五六年前就说有影像了,文学要死掉了。现在说互联网来了,文学要怎么办。我觉得文学是一直要死不活的,但是肯定是死不了的。我知道文学以前是非常非常昌盛的,在大家干完田里的活没事干,要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候。但是从那以后它就一直要死不活的,我觉得中间这个dynamic(活力)其实是很重要的。
简短地说,我认为大多数的作家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作家会完全走向非常经典的状态,他会去写更大的部头,去写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的小说。我一直都很爱看乔纳森·弗兰岑,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我要做的就是经典的。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作家,因为现在有网络,有新的表达方式,他们就会把这些新的表达方式融合到写作中来,比如像珍妮弗·伊根。我觉得这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每个作家是不同的材料,你选择合适的方式。所以这种对抗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但它也是文学的一个活力所在吧。
余华:书写当代不容易,因为当代社会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会说你在胡说
书写当代中国不容易,其实,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的作家书写当代也不容易。因为当代社会的人都还活着,他们会说你在胡说。
写长篇小说犯一个错误是很正常的,很难从头到尾都不犯错误。《兄弟》出版后,北师大教授张清华向我指出来,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他说文革时候不会说这样的话。我说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那你为什么再版的时候不再改呢?改它干嘛?五十年后如果有人再读这本书的话,不会有人知道文革时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五十年后没人读了,我改了也是白改。
再比如我写的那个小镇,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改革比较早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在喝可乐了。有人就批评我,他说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乐,因为他是从偏僻地区出来的。中国地域宽广,发展不平衡,各地方区别很大。比如我写的羊是圈养的,他们就说哪有羊这么养,都是放羊的。
所以我就想,虚构是什么?虚构就是一种角度。阅读是什么,阅读也是一种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写,从自己的角度来阅读。和别人聊天,是一个角度同另一个角度在对话,今天是我们很多角度在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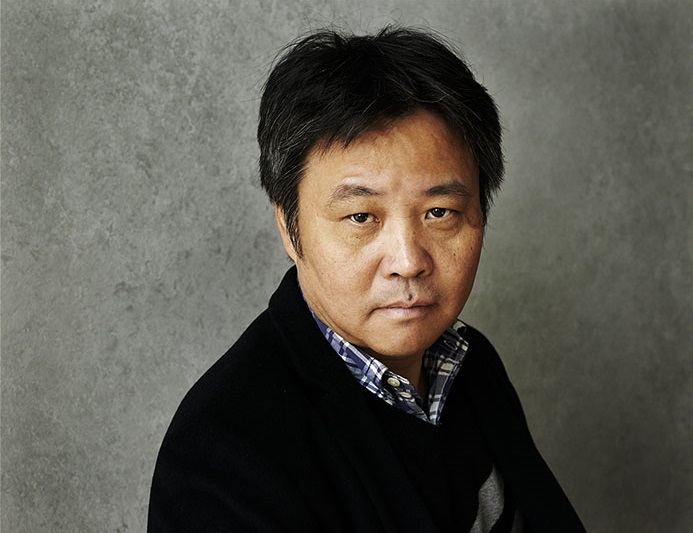
观众:对我来说,从技巧这个角度,《在细雨中呼喊》是最好的。我想请您来确认一下,您真正出于为写而写,特别想写出来,没有任何外在驱使的,我觉得只有《在细雨中呼喊》,其他都有外在的驱使。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我第一次要求自己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我就在北京开始写,初稿是在北京完成的。在写一部书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方向的。
《活着》发表之后,国内有一个批评家叫陈晓明,他说《活着》是为张艺谋写的。《活着》是小说,不是剧本,我当时觉得陈晓明的话很荒谬,后来,我开始理解,这叫因果报应,因为我一直在虚构别人,也该轮到别人来虚构我了。
其实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时,他也会虚构作者。只有他喜欢这个作家,才会去虚构他,他不喜欢这个作家,就不会去虚构。所以被虚构也不错。《活着》是我的幸运之作,如果不是它,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关注,反过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攻击。受关注和受攻击是成正比的,这很正常。
哈金:艺术是你的许可证
作家你写别人,你在运用别人的苦难创造艺术,什么是你的许可?我的回答很简单,你的艺术就是你的许可证。这有一个条件是你必须写得好,在艺术上必须能超越历史。
比如斯坦贝克写《愤怒的葡萄》。他从来没有去过俄克拉荷马,当地人看到他写的那些方言后都愤怒了,说我们不这样说话。拍电影都不让摄影组进。但是他写的那段历史是大萧条以后,灾难的美国移民从“尘区”出来。现在你要是读那段故事,只能去《愤怒的葡萄》。他的艺术把那段历史给保留下来了。
乔伊斯,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按照艺术自己的规律、在自己的结构当中,把这个地方、这些人保留下来了。所以说,一个艺术家真正要负责的是要对自己的艺术负责,你的艺术做好了,就是对所有的对象、题材、人物负责。
李娟现在离开了哈萨克,她写他们,文字和创作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外来的能量,这对中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在那种环境当中形成的感觉、感应、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的体验,都是从那块来的,也是作者自己的一部分。问题就是你怎么运用那些东西,这是你的财富,只有通过自己继承的财富,才能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李娟和颜歌想的问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可能,因为当时我们根本就读不到这些作品。她们并不把国家作为参照的系统,这是很重要的。李娟讲生活的质量,那些人生活的感情,跟他们交往当中产生的感觉,这些感觉是很基本但是很真实的,是有意义的,能体现大的问题。
颜歌提出的问题完全是超越国家之上的,作家在人类流徙当中怎样生存,怎样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说得很明显,你必须离开家乡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我们都有怀乡的感情,但更大的问题是家乡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你的成长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但在多大程度上有阻碍。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