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蔡星卓
“虽然口吃不妨碍我的生存,但它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但这是每一个口吃者的日常。”小郑的这句话让我突然意识到,口吃者不但要克服舌头的难关,还要在他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
英文单词three是小郑心里很大的一个坎儿。不论把舌头放在什么位置,不论重复几遍th的咬舌音,她也无法过渡到接下来的r音。每一次英语口语考试的练习,每当碰到这个高频词,她都会想办法略过,或是用伸出的3根手指代替。后来,因为想到必然的难堪和无力,她逃掉了正式的考试。口语评分中的那项“流利性与连贯性”,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好分数。
全世界成人口吃发生率约为1%,据此推算,中国有超过1000万口吃者。很多口吃者至今也不了解口吃,更不知道如何与它相处。
在小郑看来,口吃是一种残障,“流利讲话的人”和她在两个世界。不论是大学时候谈恋爱,怕被男朋友发现,还是工作时候害怕老板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她总是努力隐藏自己,尽量显得说话顺畅一些。口吃对她的心理打击,到了不可小视的程度。口吃了十几年,她形容,自己早已习惯了口吃出现后的失落。那些为了隐藏口吃而发明出来的小技巧,比如更换词汇,也早就变成了她的日常语言习惯。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明白,口吃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只是一种差异。在专家看来,并不是心理因素导致了口吃,而是口吃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回想我跟几位被采访者的电话聊天,我觉得,下一次碰到有人说话迟钝或重复,我应该像聆听任何一个人讲话那样去聆听他们。英文中,有口吃特征的人被称为“people with stuttering”,意为“说话会口吃的人”,下文以“口吃者”代称。
下面是两位口吃者和一位言语治疗师的自述。
李振宇:口吃并不是“想好了再说”那么简单
我叫李振宇,生活在辽宁沈阳,是一名大学生。我与父母或是熟悉的人说话还算顺畅,自言自语时也完全没有问题。一旦和陌生人说话,不管有没有事先在脑海中演练,我大概率会出现口吃的情况。
我曾经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回听自己说话时哪个地方不足。我发现自己不能一口气说完一句话,卡壳时会重复某些字句,或是在卡壳的地方拖长音。严重的时候,一个词会被我重复好几遍。同时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很不清醒,也想不起来下句话要说什么。严重卡壳时,除了喉咙发紧,我还会脸红和频繁眨眼。有时我会感觉到,听我说话的人很着急。久而久之,我学会了精简用词,尽量少说。
说起来,我大概5岁就开始口吃了。小学时,有个别同学会学我说话的样子,或者笑话我,我很难过,还有些生气。后来这样的同学少了很多,我猜他们应该是习惯了。口吃有时候会让我极其尴尬,有一次我和大学同学去吃烤肉,为了催服务员上菜,我重复了6遍“西红柿炖牛肉”。卡顿的那一分钟时间十分漫长,我感觉自己挺不好意思的,服务员也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口吃也很容易被人误解。小学时,由于我语速很慢,有的老师会感觉我是故意的。高中时,一次上台演讲,虽然准备了一个星期的稿子,我还是很紧张。我清楚记得,我大概卡顿了10句话,但还是把想说的都表达出来了。结束之后,老师说我演讲的时间太长,需要再来一次。看来她并不理解我的状况。其实,以前我父母也不知道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时会提醒我,想好了再说,但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真正认识口吃之前,我只是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想要表达的东西没办法全部说出来,心里觉得有些遗憾。口吃给我带来了不少痛苦,因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口吃者,在生活中也尽量少说话,减少暴露口吃问题。
对我来说,导致口吃的原因,可能大多来自心理层面,比如我的性格容易紧张和着急,在张口说话之前,害怕自己会口吃和被他人嘲笑。口吃也许反过来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自卑,和异性交往也变得小心翼翼。口吃还影响了我的一些人生选择,比如我目前就读的专业并不需要口语能力,这也是当时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再比如我更倾向于在网上交朋友,而常常回避现实交友。
关于治疗口吃这件事,我的出发点是,想和别人变得一样。从十几岁到20岁,我大概去了上海、杭州等地至少7家医院,检查了全身的各个部位,也有医生推荐我去大脑科和耳鼻喉科,但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感觉很无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和很多口吃者一样,看到过很多类似偏方的广告,比如自称7天可以治好口吃的汤药,或是长得像牙套一样的器材。我也认识至少10个“吃友”,他们花了好几千块钱治疗,但没有任何效果。
我有好几个微信好友,都是和我一样的状况,口吃现象十分严重,我们会互相交流口吃的经历,以及如何恢复等等。我曾想过,口吃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有其他原因。我的口吃可能是遗传,因为我的妈妈和姥爷都曾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跟着一个口吃微信群的群主在练习说话,他也是个“吃友”,但他恢复得不错。今年暑假期间,除了每天和父母、朋友聊天,我还会朗读文章,每天光说话就至少7个小时,我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心里也没那么难受了。
虽然口吃是一种无法被彻底治愈的疾病,但我的两位家人都已经恢复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离恢复不远了。
龚嵘:我选择将自己的口吃暴露给陌生人
我叫龚嵘,34岁,目前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记忆里,从我开始学会说话起,口吃就与我形影不离了。小时候,同学和亲戚、朋友会因此笑话我,叫我“结巴”或者“磕巴”,我自然就会有羞耻感,也疑惑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同。
我的口吃并不表现为重复或拖长音,而是明显的卡壳。在一些让我紧张的场合,我甚至很难说出话来。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隐藏自己的口吃。比如在感到自己快要口吃时会避免说话,或者会避免一些容易发生口吃的场合,比如会与他人发生竞争的面试。这种刻意隐藏在口吃者中十分普遍,原因很好理解:当一个口吃者努力地把一个字挤出来的时候,会出现面部肌肉抽搐、眨眼、吐舌头……我们不想把自己丑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
本科毕业之前,没有同学知道我口吃,直到毕业答辩那天,我不仅卡壳,面部也开始抽搐,我的口吃就这样公然暴露了。研究生答辩持续了20分钟,而我几乎没有说出话来。直到读博士时,我还是有隐藏口吃的习惯。直到工作后,我才决定要改变这个习惯,因为经常性的工作会议与报告等让我很难继续隐藏。
几年前,我曾在国内上过一个民间的口吃班,每天练习朗读和发言,学习呼吸方法等等,也学过其他方法,例如打着节拍说话,或是放缓说话节奏等。和很多人一样,回到生活中半个月后,这些效果就逐渐消失了。可能我当时年纪比较小,于是对口吃班抱了很大的希望。后来在法国,我尝试过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变成了一对一的形式。专业的言语治疗师教授的方法更加多样和系统,另外,他们并不会灌输“包治口吃”的想法,即口吃可以被迅速治愈的思想。
刚开始尝试时,口吃治疗并不能达到我的预期,我很自责,产生很多自我疑问。后来我知道,它并不那么容易被解决,我也慢慢接受自己生理上的这个特征。为了让自己说话更轻松,以及心理压力更小,我意识到公开口吃状况的必要性。遇到新的环境和陌生人,我就会跟他们事先说明我的口吃状况,让他们知道即便碰到我卡壳的情况,也不要太惊讶,因为这是正常的行为。与告知他人相比,这更像是给我自己的一种安慰。
决定暴露自己的口吃之后,刚开始我确实经历了一段难受的时期,也伴随着生理上的各种不适——逼着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身体器官和思想准备一开始并不能完全适应,在努力挤出来某个字之后,会感觉身心俱疲。大概过了半年,我感觉自己在这种场合说话才真的放松下来了。虽然不确定这样的方法在其他人身上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但自我暴露对我来说非常有效,放下了心理负担,在以往会令我紧张和想要回避的场合,我反而获得了很多练习说话的机会。
在我生活过的欧洲城市里,口吃者的处境和国内会有所不同。就我的经验而言,在西欧,对口吃的意识和全民教育可能更科学一些。我接触过很多人,他们知道口吃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怎么对待口吃者,并不会表现出诧异、不耐烦,或取笑我。对于这里的很多口吃者来说,他们也更加了解口吃,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口吃者互助组织在欧洲很普遍,口吃者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专门的言语治疗师。我记得在伦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叫做国际演讲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的互助组织,他们还包含了一个给言语障碍者的分支协会。在互助会中,口吃者往往会分享自己的口吃经历和口吃带来的心结,有时也会有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参与其中。这样的互助组织给了很多人安慰,也因此,大概两年前开始,我和几个朋友也自发组织了自己的非盈利互助团体,这不仅为了帮助更多口吃者,其实也是为了帮助自己。
回想起来,那种一早起来没什么精神,时刻在想着怎么避免口吃的生活是很令人疲惫的。言语的流畅究竟重要吗?其实,我觉得达到一定的流畅度,只要自己与他人交流不太受影响,且在其他人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与其更在意别人的反馈,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与质量。
晨佳:口吃者需要学会和它相处
我叫晨佳,是一名公立医院的言语治疗师。2018年毕业,在美国工作一年后,我回国工作至今。
我的本科专业和口吃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对语言学,尤其是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与其中的障碍很感兴趣,因此选择了相关专业进行深造。我学习的专业叫沟通科学与障碍,也就是言语病理学,课程包括儿童语言的发展、成人的语言、语音学、嗓音、吞咽、流利度障碍等内容。尽管存在语言差异性,但大部分知识都可应用于我回国的工作之中。虽然还不能算作一名成熟的言语治疗师,但除了在美国大量的临床经验,我在国内已经接待了30多名口吃者。
言语治疗包括很多种类,比如成人脑卒中(又称“中风”、“脑血管意外”)后出现的失语症,儿童语言发展迟缓或发音障碍等等,口吃只能算作其中很小众的一个分支。口吃,可以被定义成一种言语流畅度障碍。口吃者在说话过程中会体现出一些特征,主要是重复、延长和卡顿三种。除此之外,还有些口吃者会表现出一些次要特征,比如身体或面部的紧张、眨眼、面部肌肉抽动等,甚至会攥拳跺脚。
我接触的第一个口吃者是我读研时的同学,一个非裔美国人。记得这名同学上台讲话,一旦出现超过10秒的卡顿,她就在那里站着,试图使用自己学习过的策略重新开口讲话。出于一个听者的善意,我不去直视她的双眼,觉得看她会让她紧张。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看她才会让她觉得异样。所以,现在面对问诊的口吃者,我再也不会避讳应有的眼神交流,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不正常。
在我从业的这段时间内,我碰到过3岁到35岁不同年龄段的许多患者,有两个口吃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心理压力非常大的口吃者,说话时他用字非常节省,也回避和我眼神交流,非常不愿意表达。另一个口吃者则恰恰相反,他根本不把口吃当一回事,甚至觉得口吃这件事让他在口头上表达不畅,因此给了他更多时间去思考。
口吃的治疗从评估开始。国内学术界目前并没有基于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化评估工具,而我会记录下口吃者口语表达非流利的程度,以此作为治疗的基线,用作其自身对比的依据。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授权引用了美国一个相对主观的评估,评估从口吃者角度如何看待口吃这件事情,比如在排队点餐的情况下,或是在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流时,会不会感到有困难等等。这样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了解对方口吃情境的细节。
就治疗过程来说,儿童和成人的差异较大。对于儿童来讲,一方面是通过行为的方法减少口吃表现,另一方面是指导家长给孩子营造科学的会话环境。而对于成人,我会更注重他们技巧的学习,以及心理层面的科学应对。
民间流传着很多口吃的治疗方法,但靠谱的非常少。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口吃是个体差异非常大的言语障碍,治疗方法应当因人而异。民间的治疗一方面可能没办法满足这样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很多方法并不科学。我曾经碰到一个女孩子,她上过某个口吃治疗班。为了鼓励口吃者开口和陌生人说话,治疗班让他们去大街上要别人的电话号码,这样的行为其实对于非口吃者来说,都有难度呢。
除了一些民间的自助群体,国内针对口吃治疗的机构大多来自各个领域,也有一些公立医院开设了口吃义诊等特别活动,但对于口吃的科普仍需加强。在美国,执业的治疗师拿到的是CCC-SLP执照,也就是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学会认证的临床言语语言治疗师。不过国内并没有专门的言语治疗师认证,而是将其归属于康复技师。在国内,很多医院也并没有为言语治疗单独设置科室,而是更注重比如肢体方面的康复。这可能也是和需求有关系,毕竟,比起肢体上的不便,言语上的障碍就显得没那么紧迫。
人们对口吃有很多误解,常见的一种,就是认为口吃可以被治愈。其实口吃并不能被治愈,但可以被改善。导致口吃的原因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弄清楚,神经、大脑或遗传等多个因素可能都起了作用。在我看来,口吃表现来源于语言产出时各系统之间配合的不协调,是由神经底层原因表现出来的障碍。和其他语言障碍相比,心理因素对口吃来说格外重要——并非是心理因素导致了口吃,而是口吃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比如年纪较小的口吃者可能要面对来自父母的责备。从口吃者的个人体验来说,他们可能明明知道要说什么,但就是无法顺利表达出来,这一点给他们带来很强的挫败感,很容易因此恶性循环。
有些人的口吃不易被察觉,那也许是他们在很努力地隐藏,或是多年间已经形成了换词等习惯来掩饰,但对他们来说,这依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专业性来讲,语言的流利度意味着效率。但从口吃者的角度,这一切只关乎个人感受。他们害怕与别人不一样,但其实说话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正常”的标准,就像方言之于普通话。口吃并不是一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它更像是由大众偏见造成的。
从根本上说,口吃者需要做的是对自己差异性的接受,也就是理解口吃这件事情并不会离自己远去,要学会和它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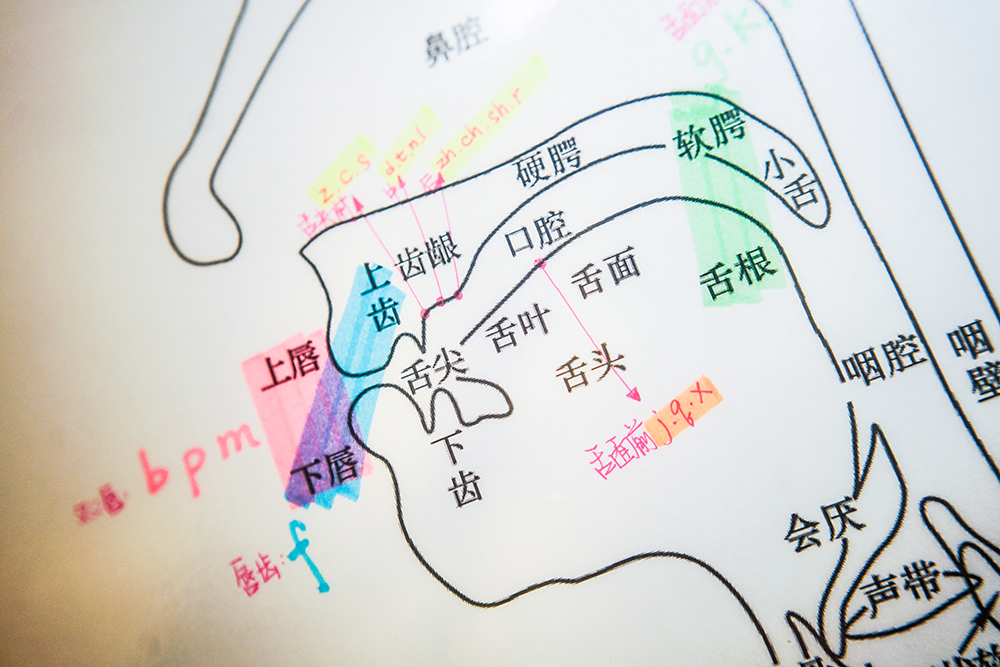





——完——
作者蔡星卓,界面摄影记者,与世界只有一支镜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