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11月16日,距离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正好过去20周年。在系列电影推出20周年之际,HBO Max宣布将在2022年元旦推出特别节目《重返霍格沃兹》,在这档节目里,三位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哈利·波特扮演者)、艾玛·沃森(赫敏·格兰杰扮演者)和鲁伯特·格林特(罗恩·韦斯莱扮演者)和参与过八部电影的众多主创将重聚一堂。
在粉丝欢欣鼓舞的同时,许多人发现这记回忆杀唯独没有邀请的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价值250亿美元IP的创造者J.K.罗琳。HBO Max公布的预告片中也没有提及罗琳是否会参与特别节目的录制。据《好莱坞记者报》(The Hollywood Reporter)报道,熟悉该项目的人士透露称,特别节目将重点关注系列电影的创作及其主创团队,罗琳只会以档案录像的形式出现。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拒绝评论是没有邀请罗琳,还是邀请了罗琳却遭到拒绝。
这使得罗琳近年身陷的与跨性别议题相关的纷争再次进入舆论中心,且在中文互联网内也引起了广泛关注。2018年,罗琳力挺奉行“性别绝对主义”的英国学者Maya Forstater,Forstater因质疑英国政府正在征求意见的性别认同政策而被网民审判为“恐跨性别人士”,并失去了在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工作。自那之后,罗琳的多番言论遭遇了愈演愈烈的批判和网络暴力,她被许多人定性为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2020年6月7日,罗琳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关于呼吁人们在疫情期间和之后持续关注“来月经的人群”(people who menstruate)卫生条件的文章,对文中回避使用“女性”一词提出质疑。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主演、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到与罗琳属同一文学经纪公司的作家,纷纷谴责罗琳的“歧视性言论”。一个月后,美国左翼月刊《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发了由153名自由派文艺界名人联名签署的《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对强迫“异见者”噤声的现状提出批评,罗琳也参与了该公开信的联署。

今年5月,新西兰费瑟斯顿图书节(Featherston Booktown)的哈利·波特主题活动临时取消,主办方表示,在与文学专家的讨论中,人们普遍担心这一活动会给当地社区的特定人士造成困扰,因而决定取消。略显讽刺的是,图书节还设置了一场关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专题研讨会。在人们讨论哈利·波特电影20周年特别节目为何没有邀请罗琳的同时,罗琳在推特上激烈批评了三位极端跨性别活动家在社交媒体上泄露她住所地址的行为。罗琳表示,自去年6月以来,她收到了源源不断的辱骂和威胁信息。
在仅仅三年前,罗琳还是千禧一代心中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她的故事——囊中羞涩的单亲妈妈不得不在哄好孩子后去咖啡馆写作,出乎意料地创作出了红遍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人们艳羡不已的文学偶像。这位文学偶像是如何陷入取消文化漩涡的?在本文中,我们以圆桌讨论的方式解读罗琳争议背后的种种问题。参与圆桌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但汉松和哈里·波特粉丝、微博博主@隆巴顿的记忆球(下称“记忆球”)。但汉松长期关注和研究包括罗琳在内的英美文学和取消文化,记忆球从2003年起成为《哈利·波特》铁杆原著粉丝,对全球哈迷圈层内部动态颇为了解。本文将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罗琳争议与中外舆论场内的不同反应、取消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哈里·波特》系列小说的文学价值。

01 谈跨性别争议:罗琳面对敏感议题不选择明哲保身,警惕“看热闹不嫌事大”
界面文化:罗琳第一次陷入“恐跨性别群体”争议是在2018年,自那时起她的公共发言被密切审视,她对性别议题的相关言论也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弹。最近罗琳再度进入舆论聚光灯下是因为 HBO Max的哈利·波特电影20周年特别节目疑似没有邀请这位原著作者,普遍认为是她的“不恰当言论”所致。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地步的?
记忆球:我认为事态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那是罗琳应得的。其实我不太同意“不恰当言论”这个说法,因为只要做过深入的调查就不难发现,她的观点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那些话在所指的语境中是具备合理性的,它们不应当被剥离上下文单独看待,因此她的相关言论最好能够被描述为“有争议的”,而非“不恰当的”。
在当今性别界限日益模糊化的欧美,提出生理性别的重要性非常需要勇气,因为她就像是在挑战社会的多元和包容,站在了自由选择身份的对立面。她的理念对很多人来说听上去很荒唐甚至落后,连我一开始也产生过质疑。但我比许多网友更愿意多相信罗琳一点,所以我就花时间做了些调查,希望自己至少能了解她的出发点,更希望不要盲目站队。我发现网络上所谓“罗琳支持同性恋电击扭转治疗”的传言纯属臆断,而“她的笔名Robert Galbraith是在致敬Robert G. Heath”这样的说法更是捕风捉影。
说实话,罗琳的言论的确动摇了一部分人存在的根基,伤害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罗琳考虑不足的地方。作为一名顺性别者,她只能通过观察来了解跨性别者的生存环境,很多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她去讨论这个话题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作为一名优秀的作者,她一定有办法把观点传达得更加柔和,但是这么做的代价就是损失其输出力度,她最终选择的方式大概也是造成她目前境遇的原因之一。
但汉松:我觉得这一事件特殊之处在于,罗琳真的胆子非常大,而且特别固执。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她就在反复捅“政治正确”的马蜂窝。2020年,她又因为在推特上批评政府的变性人政策,强调生理性别的重要性,而成为互联网上的众矢之的,但她依旧没有屈服。大多数社会名流其实会对敏感的社会进步议题谨慎发言,或者避而远之,明哲保身。但罗琳没有,她说自己愿意把这件事当作进一步深化公共讨论的契机,思考社会运动中的一些棘手问题。
界面文化:你对中文互联网内关于罗琳争议的相关讨论有怎样的观察?哈利·波特20周年特别节目引起了一种质疑的声音是:如果不是罗琳当初坚持在英国选角,艾玛·沃森、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和鲁伯特·格林特根本不可能拥有现在的财富与名望。他们与罗琳“割席”被认为是一种忘恩负义。你对此怎么看?
记忆球:这个论调成为主流我感到比较意外,这件事上热搜之前我和几个博主朋友就关注到了一些自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渲染。几位主演发表声明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当时我还看到有不少人称赞他们的理性和对少数族群的包容,但是这一次大众却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其实在这期间他们并没有对罗琳的争议发表新的看法,这样的变化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某些自媒体的措辞,什么“割席”、“忘恩负义”、“丢碗骂娘”等等,他们提炼出了这些演员反对罗琳的态度,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们在文章中同样感谢过罗琳的事实。比如伊凡娜(卢娜的饰演者)就因为说了感谢罗琳的话而被网暴到暂时关闭了Instagram社交账户。那些耸人听闻的、容易引起群愤的标题总是传播得最快、最广(例如“在魔法世界里,到最后支持罗琳的只有伏地魔”)。雪球最终越滚越大,几位演员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背叛者。我觉得较为理性的做法是像支持罗琳发声一样,也去包容那些理性反对声音的存在。

但汉松:简中互联网内对这一事件大多有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超然姿态,但我觉得这种看客吃瓜心态其实蛮可悲的。我们要警惕道德上的自以为是,不要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看西方社会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争吵。
界面文化:我们注意到国外最大的两个哈利·波特粉丝网站The Leaky Cauldron和Mugglenet也在把罗琳剥离出去。作为哈利·波特的粉丝,你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哈利·波特粉丝内部现在对罗琳的普遍观感是怎样的?
记忆球:MuggleNet在很早以前就想在从哈迷网站转型到覆盖面更广的欧美亚文化粉丝交流平台了。在《神奇动物》电影系列上映初期,出于对剧情的不满,某些内部的编辑就曾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攻击罗琳,所以这些网站和罗琳正式割席是迟早的事。
和仅持反对意见的演员们不同的是,这些网站除了反对罗琳之外,还发表过不少取消罗琳的言论(虽然网站在最新的声明中表达了对罗琳遭遇的同情,但这和他们以往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发表过的态度有着比较大的出入,我认为这和近期“罗琳地址遭跨性别权益激进分子曝光”的新闻有一定关系)。顺便提一件往事,MuggleNet的主创Emerson Spartz曾因为支持罗琳而被网暴,甚至被要求和自己创立的网站做切割,我认为这件事荒唐至极。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罗琳的性别观念究竟是怎样的?哈利·波特系列中是否包含了多元包容的思考?在我对“哈利·波特”系列的阅读经验里,罗琳是一个强调自由主义和多元包容的作者,比如赫敏发起的家养小精灵平权运动、邓布利多的同性恋设定、对魔法部和乌姆里奇的描述影射压制言论的负面影响等等。
记忆球:从《哈利·波特》中不难感受到罗琳对各种各样角色的包容,你所举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次的事件中,罗琳比较具有争议的核心观点是“生理性别是真实(客观)存在的”(biological sex is real)。许多人认为她是在反多元性别论,其实并不然。得出那样的结论我认为是十分懒惰的。罗琳的对立面(跨性别者权益激进分子)主张的观点是“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transwomen are women),我感到疑惑的是,这些激进分子是如何定义“女性”的呢?具备明显的第二性征?拥有XX染色体?符合刻板印象?还是“只要我觉得我是,我就是”?如果跨性别女性也被归类为女性,这难道不才是贴近性别二元论的一种体现吗(非男即女)?而且,罗琳实际上并不提倡抹去跨性别者,她主张不应当在儿童刚出现性别认知障碍时就将“变性”作为一种便捷的选项提供给他们,她支持先引导儿童探索和了解自己,试着让他们接纳自己。要知道,变性手术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它当然是一部分人和自己的精神自我达到统一的最佳选择,但它也实在不必被随意地建议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
02 谈取消文化:社会行动主义以取消文化为武器,并不能解决真问题
界面文化:从去年开始,关于取消文化的讨论不绝于耳,罗琳是取消文化知名度最高的受害者。为什么西方愈演愈烈的取消文化似乎成为了一个左翼内部党同伐异的风潮?
但汉松:西方知识界对此已有很多反思,标志性事件是《哈泼斯杂志》发表公开信,抗议取消文化伤害了宝贵的言论自由原则。签署人不乏重量级人物,包括史蒂芬·平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诺姆·乔姆斯基以及J.K.罗琳。不难发现,当前在左翼内部存在一种集体焦虑,即:社会行动主义以政治正确为名、以取消文化为武器,但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很多误伤。这种去中心化的大众行动容易变成了一种私自执法(vigilantism),没有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确切证据,却急于进行定罪、围攻、指责。现在看来,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不可小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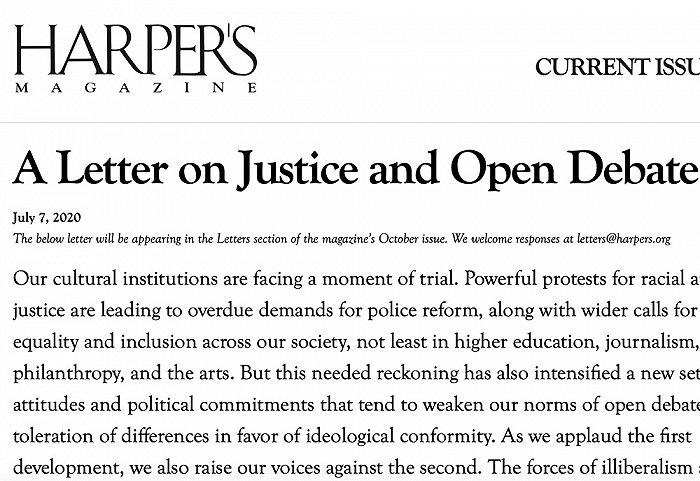
在我看来,罗琳其实属于那些“不可取消”(un-cancellable)的精英人士,她是这个星球上古往今来靠写作赚钱最多的作家,但绝大多数取消文化的受害者没有罗琳这样的财富加持。他们可能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或杂志编辑,在课堂内外或个人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或质疑了一下政治正确的狂热,于是就招致网暴或人肉搜索(doxxing)。反对者直接向其任职的学校或机构施加压力,导致他们丢掉工作。对这些人来说,这份工作可能是养家糊口的全部来源。长此以往,取消文化会让大家噤若寒蝉,因为一种不同观点的表达,可能被网民界定为“仇恨言论”。这对言论自由(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是很大的伤害。
作为社会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大杀器,取消文化天然地反对权威和既得利益者,它意味着一种民主(甚至民粹)的自下而上的对抗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有进步性——在前互联网时代,你无法想象凭借匿名的草根,就可以撼动那些看似不可撼动的人,扳倒原本在司法体系中享有特权的精英。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民主的胜利,也是互联网时代向大众赋权的体现。有了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中哈维·韦恩斯坦的前车之鉴,今后那些想对女同事上下其手的男高管们或许不得不考虑一下后果,因为一旦被曝光,取消文化会以无远弗届的铁拳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或许也意味着,大众除了取消文化,并没有别的武器了。他们在对抗社会公敌或压迫性制度时,除了通过社交网络造势、造成对方“社会声誉雪崩”之外,其实并无它法——他们并不能在经济或政治上去实质性地惩罚特权人士。
界面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影视公司、出版社等机构动辄与陷入舆论争议的作家割席,实质是一种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即表面上做出进步姿态,实质上却无意进行彻底的企业和社会改革。你对此怎么看?
但汉松:“Woke”作为形容词的用法,最早出现于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时期,但后来“wokeness”的语义经历了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转变过程。后来,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非法移民等热门进步话题都可以征用“wokeness”的概念。如果你是一个“觉醒”之人,就意味着更敏感,对制度性不公有更多的反思和警惕。
继“woke”之后,2015年又出现了“woke capitalism”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现象。从好的一面说,商业企业纷纷意识到需要表达对进步事业的支持态度,资本不能置身事外,提升进步的社会意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然是社会风气的良性体现。但另一方面,这个词最近也获得了负面含义。比如,百事可乐拍摄的一则广告中激发了公众不满——金小妹(Kendall Jenner)在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现场给军警送上了一罐百事可乐。这样的觉醒资本主义其实暴露了它的虚伪——口头上是为进步事业背书,其实还是行品牌营销之实,借机与目标客户达成深度的情感认同。

很多人批评这种觉醒资本是在避重就轻,因为算一笔经济账,如果企业既投了商业广告,同时又蹭到了正义的热点,既让品牌和年轻人之间体现强烈的政治认同,同时又增加了销售和市场份额,何乐而不为?比这种觉醒资本主义的品牌营销更难的,其实是另一些企业介入社会议题的做法,比如向少数群体开放更多工作岗位、就业培训、实习机会,增加他们的代表性,或者推出各种在地化的机构变革。这些都是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远不如拍电视广告那么拉风。所以,很多人批评觉醒资本没有真正地去解决问题,只是用广告修辞来占领道德制高点。
归根结底,觉醒资本主义假装自己是参与解决问题的一分子,但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真相: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换句话说,族裔、移民等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生产关系或意识形态导致的,如果不触及制度本身的变革,空谈这些问题是徒劳的。真正敢触及问题本质的,或许还是当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次运动的口号是“我们是99%”。这个口号触及了一个真问题,可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闹腾一段时间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对真正的老左派、新左派来说,真正触及资本主义本质问题的抗议或对抗策略,如今都让位于更虚假、浮夸、伪善的互联网社会行动主义。这些东西被资本主义收编,也在情理之中。
03 谈《哈利·波特》:人性描写、小说元宇宙与哈罗德·布鲁姆的担忧
界面文化: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20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思考:《哈利·波特》是如何成为一个全球最受欢迎的IP之一的?它吸引人的关键是什么?
记忆球:《哈利·波特》问世已经二十几年了,直到现在还不断有人加入哈迷的行列中来。如果它仅仅是因为酷炫的魔法或者刺激的打斗,那么它必然会被新的冒险故事所取代,所以我认为真正令《哈利·波特》长盛不衰的是它对人性的准确描写。我之前在外国论坛上看到过一段话,我认为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合适,翻译过来是:
“人们常说《哈利·波特》教给我们友谊与勇气的意义、爱能战胜邪恶等等。我当然认为这些很重要,但是《哈利·波特》还教会我们这一代人新闻媒体并不总是值得相信;政府时常充满腐败与昏庸;法律制度并非永远正确;当权者不一定把你的利益常放于心;可怕的事情也会降临到好人身上;你心目中的英雄或许没有你想象的完美;好心的人未必总是对的;所有人都会犯错以及做正确的事往往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和代价。我觉得这些和其他积极向上的信息一样重要。”
但汉松:罗琳确实是一位现象级作家,《哈利·波特》系列在当今流行文化中罕有其匹。这种特殊地位可能也有偶然性,或许当时读者刚好渴望读到这类魔法世界的童话故事。但外部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哈利·波特》出现在互联网文化兴起的时候,罗琳的故事通过粉丝在网络上的口口相传,很快获得了全球知名度。我觉得,《哈利·波特》的主要读者群不是幼童,而是青少年,甚至是年轻人。罗琳很好地抓住了这一部分读者的阅读趣味。
当《哈利·波特》成为一个畅销的文化商品时,全球资本主义当仁不让地争相参与对它的营销。试想,如果没有电影改编,《哈利·波特》不可能有现在的知名度,华纳兄弟对它的IP购买、经营,对衍生品的开发(甚至包括主题乐园),大大提高了它的粉丝总量,使之成为了一种当代亚文化。我认为,《哈利·波特》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共同塑造的产物,不独属于罗琳一人。

现在,学术界关于《哈利·波特》也开始出现一些正经的专著,学者开始考察它对英国文学或西方文学的传承。所有玄幻小说背后,都隐藏着古老的文学母题或文类,当代作者只不过对它进行了一种变形或转换。在新的故事外衣下,还是可以看到经典的文学叙事模式(pattern)或原型(prototype)。罗琳、托尔金都不例外,他们的故事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受到狄更斯、夏洛特·勃朗特、欧洲历史或《圣经》的影响。和成长小说一样,《哈利·波特》总是会十分动人地讲述爱、友谊、亲情或背叛,讲述主人公如何在与黑暗的对峙中不断变得更强大。对青少年读者来说,从《哈利·波特》系列中学到的与其说是魔法传奇,不如说是如何凭借友谊、爱、信念或知识,让自己实现成长。这是罗琳写作的重要驱动力。
界面文化:很特殊的一点是,罗琳是一个与其作品关系非常紧密的作者。在《哈利·波特》系列完结后,她还在不断出版衍生作品,不断完善魔法世界的设定。你怎么看这种作者和作品的强关联呢?根据读者反应理论,一部作品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如何评价一个作家在作品完成后依然持续创作衍生作品,改变原作意义或补充原作细节的行为呢?
记忆球:我认为这件事有利有弊,因为罗琳有时对原著细节的了解程度未必会超过那些读了无数遍原著的粉丝,所以她后补的一些设定会和原著有所出入,这让部分比较严谨的哈迷感到不快,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接受并且欢迎这样的补充的,因为可以不断丰富波特宇宙的世界观,让哈迷之间有新鲜的谈资。
但汉松:罗琳其实在构建一个小说的元宇宙,并不断充实它。读者不仅是阅读《哈利·波特》的故事情节,还是借由《哈利·波特》进入这样一个元宇宙,与大大小小各种人物相遇,了解他们的过去。我觉得,任何野心勃勃的小说家都想打造这样的元宇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五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很强的故事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如此,它不仅讲一个戴绿帽的犹太男人一天的故事,而且展现了都柏林为数众多的各色人物,他们在不同的章节反复出场,并勾连出时代和社会的众生相。我很喜欢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开放的作品”的概念,它其实是一切伟大文学的特征。一部文学作品要获得恒远的生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开放,不断激活更多的意义。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哈利·波特》在未来会有持续的生命力,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正典”吗?
记忆球: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哈利·波特》受人喜欢的原因是作者对人性深入的描写,虽然和时代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里面的部分设定用现在的价值观去审视也未必能完美过关,但是我认为不论时代怎么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最终能够感动到我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亲情、友谊、奉献精神等等……在未来,这些品质或许会更加稀缺,而《哈利·波特》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受欢迎也未可知。至于《哈利·波特》是否有资格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正典”,就交给时间去判断吧!
但汉松:罗琳并不是第一次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她上一次陷入笔战,是在2000年。当年,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刚出版了《怎么读,为什么读》,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3500万读者的选择可能是错的吗?是的》(Can 35 Million Book Buyers Be Wrong? Yes)的文章。3500万,是当时《哈利·波特》的销量。作为《西方正典》的作者和文学经典的守护者,布鲁姆坦言自己对罗琳的大红大紫非常担心。他说自己翻了一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发现写得很糟糕,里面到处是陈词滥调。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书中每当罗琳写到谁要出去走走,就会用“stretch one’s legs”。同样的表述在书中中反复出现,他于是有理由怀疑罗琳的写作技巧和语言丰富度是不合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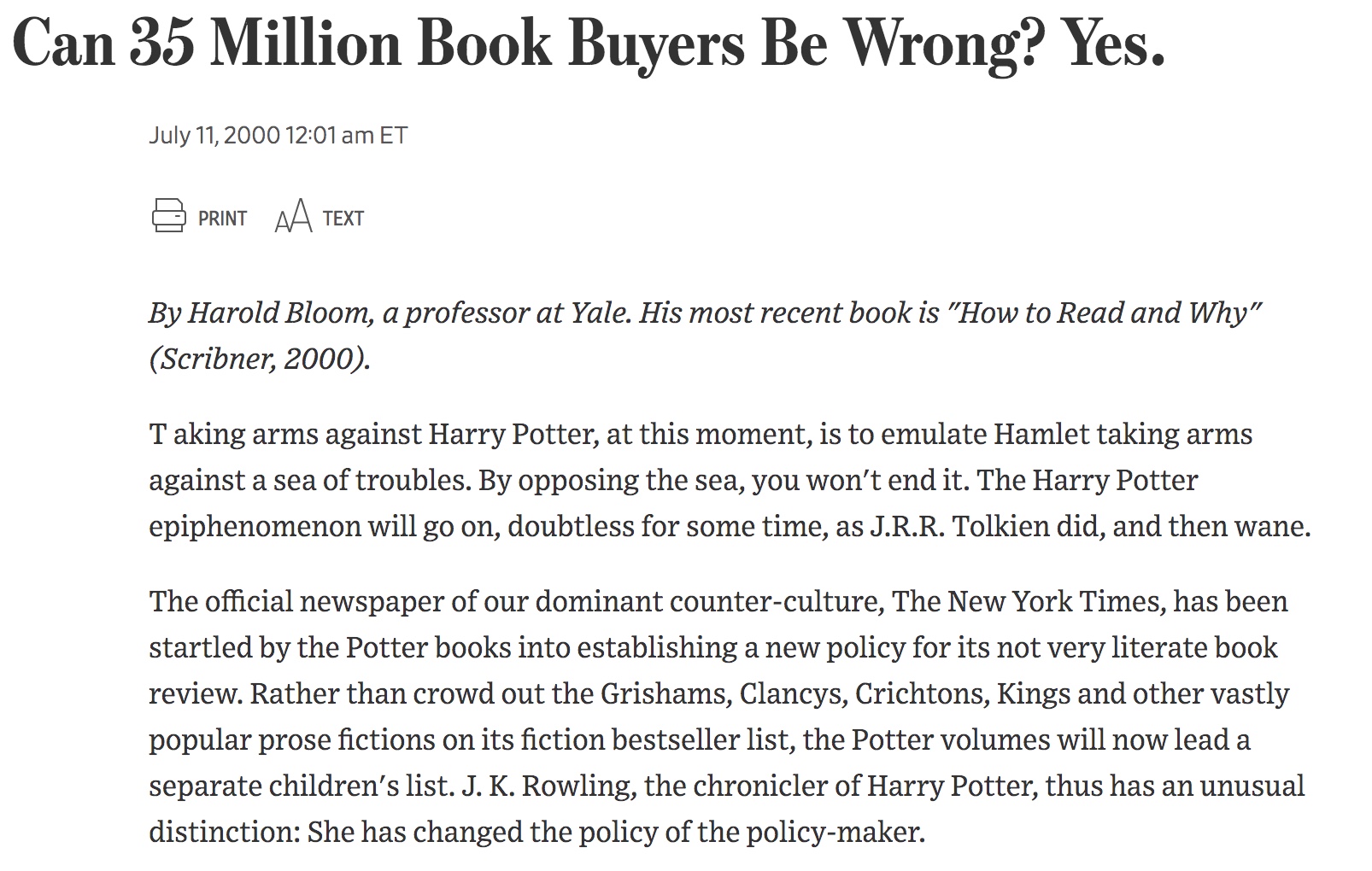
布鲁姆进一步说,《哈利·波特》之所以让人诟病,更是因为它不会激发读者的积极思考。主角进入神秘古堡、与伏地魔作战、最后肯定安然无恙地以胜利者姿态归来,这类故事不激发思考,只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智性的懒惰,长久以往,这类作品会慢慢排挤掉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他推崇的《荷马史诗》、《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卡夫卡、福克纳。布鲁姆断言,如果读者越来越不读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那么最后留在书架上的就只能是“次等的 ”(sub-literary)文学作品。这种文化的堕落,让他忧心忡忡。那一年,布鲁姆单枪匹马指责罗琳以及罗琳的千万名拥趸,在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成为了一起很大的文化事件。罗琳好像没有特别去回应这件事,但她的粉丝和布鲁姆进行了一场隔空骂战,很多人抨击布鲁姆过于文化精英主义。大家觉得,文学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带来愉悦的阅读吗?现在读《哈利·波特》的年轻读者,也许以后就对严肃文学产生兴趣,接下去就会读莎士比亚全集了。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重提布鲁姆和罗琳的笔战,其实是想说这桩陈年旧事或许和罗琳现在的遭遇之间有一些冥冥之中的关联。布鲁姆当时真正批评的对象并不是罗琳,而是痛心于流行文学在互联网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泛滥——它们的极度流行,会让真正的文学正典走向边缘化,其后果是更多的人没有时间与耐心进行严肃阅读。事实上,他当时看似杞人忧天的看法在今天已经应验了。对很多人而言,《哈利·波特》可能就是他们人生的阅读巅峰,然后就耽溺于美剧、动漫、好莱坞带来的视听享受。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严肃文学的地位是可悲且可疑的,当代读者已经愈发习惯了那种不假思索、享乐式的快读或碎片阅读,那些拥有慢读、细读技巧的读者,如今变得愈发稀缺。阅读的退化,也导致了当代读者愈发丧失了全面了解真相、成熟地做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英国作家拜厄特在批评《哈利·波特》过度流行时,也担心罗琳的读者会成为长不大的成年人。

20年前那些读着《哈利·波特》长大的读者,现在正好构成了批评、辱骂、攻击罗琳的主力。他们为什么只能有这样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其实,公允地说,罗琳对相关问题有长期的严肃思考,她说自己做了大量的调研,旗下基金会有项目专门在研究这类问题。罗琳深知推特不是严肃讨论的场合,后来她在个人网站上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详细解释她的立场,阐明她对跨性别问题的忧虑在哪里。那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文章,可是那些在网上攻击她的人们会去读吗?我深表怀疑。他们为什么不去读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深度阅读能力,而这正是布鲁姆20年前警告我们的后果。作为一位教授文学的老师,我不完全赞同布鲁姆的观点——我认为罗琳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她的文笔远不像布鲁姆说的那么差。但想到20年前的那场论战,我还是心有戚戚焉。
最后回到你的问题:《哈利·波特》是不是文学经典?站在文学批评的专业立场来看,我觉得不是。布鲁姆甚至说,不要把它和《白鲸》去比,直接把它和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记》去比,也是相形见绌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记》有很多哲学解读的空间,它看似简单,但耐人寻味,不是那么善恶分明、非黑即白,不是一种简单化的英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在儿童文学这个类别中,《哈利·波特》的艺术价值也并不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一般文学当中,就更称不上是最好的。但在这样的时代,伟大文学的标准和阿诺德式的审美趣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会遭到质疑。现在,大学里把《哈利·波特》当作博士论文课题来写的人也是有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反精英的姿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