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年轻时在一战战场上被炮弹爆炸的破片击中,受了重伤,他在一封家书里表示,“赴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我已经目睹了死亡,有了深切的体会。如果我当时想死,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它是我所做过的最简单的事。”
许多年后,海明威把自己的体验——即灵魂出窍、飞升而后又返回的过程——写进了他的中篇小说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其中讲述了一场陷入绝境的非洲之旅。主角染上了坏疽病,他明白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突然之间,他的病痛消退了,康普顿开着小飞机来救他了。二人同乘飞机升空,穿过一阵猛烈得如同“从一道瀑布中间飞过”的暴风雨,小飞机终于又重见天日:在他们面前,“阳光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方方正正的顶峰。他一下就明白了那正是他想要去的地方。”这一描述与濒死体验的诸多经典元素颇为吻合:黑暗、疼痛的消失、进入光明之中并产生平和的感觉。
难以言喻的平和
身体受钝性创伤、心脏病、窒息以及休克等令人生命垂危的特殊情况,均可能触发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简称NDEs)。在医院环境下,约有十分之一的心脏骤停患者会有此种经历。许多在这种惊心动魄、命悬一线的状况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曾谈到过这样的体验:他们离开受损的身体,进入一个超拔于日常生存状态的领域,冲破了寻常的时空界限之约束。这些经历影响深远且神秘莫测,足以永久性地改变幸存者们的人生。
濒死体验绝非异想天开的产物。它们具有广泛的共性——疼痛消失、看见隧道尽头的亮光以及其它一些视觉现象,离开自己的身体并在其上方悬浮,甚至于飞往外太空(灵魂出窍的体验)。相关的体验还包括与挚爱之人相会、处于生死边缘或遇上天使这类精神性的存在者;对自己的一生来了个普鲁斯特式的全景回顾(“我的一生在眼前闪过”),无论其好坏;或者产生了时空扭曲的感觉。对于这些感知,例如在狭窄隧道中前进的体验,已经有若干种可能的生理学解释。视网膜周边的血流量减少意味着视力的丧失将首先在该处发生。

濒死体验当中的元素可以是积极或消极的。积极的一面包括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感受到某种无所不能的存在,或某种高洁的、神圣的东西。有一种显见的不和谐将巨大的创伤与平和以及与宇宙合二为一的感觉割裂开来。但并非所有濒死体验都是美妙的——它的某些方面可能是可怕的,其特征是强烈的恐惧、痛苦、孤独与绝望。

围绕濒死体验的各种宣传,很可能已经塑造了人们对经历此类事件后应有何种感受的预期。事实上,由于羞耻感、社会的污名化以及迎合“美妙的”濒死体验之原型的压力,那些令人痛苦的濒死体验基本上都被轻描淡写地打发掉了。
任何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都让我们回忆起生命的动荡与脆弱,还能消除厚重的心理压抑,此种压抑让我们不必去直面存在性的湮灭(existential oblivion)这类令人不快的念头。在多数时候,这些事件的鲜活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消退,最终一切如常(尽管它们可能会留下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人们对濒死体验的回忆过了几十年都仍有非同寻常的鲜活性以及清晰性。
一项2017年由弗吉尼亚大学两名学者发表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能否以“异想天开”之说把濒死体验中的认知增强与大脑功能受损之间的悖谬打发掉?研究者向自称有过濒死体验的122人发放了问卷。他们让被试者将自身经历的记忆与一系列真实或想象的事件作比较。结果表明,濒死体验的回忆更鲜活,细节也更丰富,为真实或想象性的境况所不能及。简言之,濒死体验的回忆“比真实本身还要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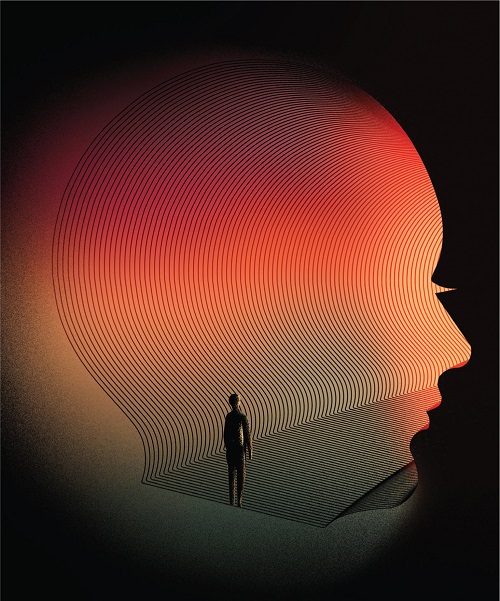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个年头里,经由一群医生与心理学家的论著,公众也开始对濒死体验发生兴趣——尤其是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与布鲁斯·格雷森(Bruce M. Greyson),前者在1975年的畅销书《死后的世界》里首创了“濒死体验”这一术语,而后者则是上文所述的两名研究者之一,他在2009年推出了《濒死体验手册》(The Handbook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学者们留意到,人们所分享的濒死故事在内容上呈现出了一定的模式,这些以往被斥为虚构或狂热幻象(昔日的临终幻觉)的东西就此变成了经验研究的领域。
我(指本文作者Christof Koch)接受这些感受强烈的经验的真实性。它们的本真性不亚于任何其它的主观感受或知觉。不过,身为科学家,我秉持如下的假设来开展工作:我们的一切思想、记忆、知觉和经验,都是大脑的自然因果力量造成的无可避免的结果,与超自然因素无关。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前提对科学及其侍女——亦即技术——做出了莫大的贡献。除非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具备足够说服力以及客观性的反面证据,我不认为有理由放弃这个假设。
接下来的挑战,便是如何在一个自然的框架内解释濒死体验。作为一个身-心问题(mind-body problem)的长期研究者,我关注濒死体验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构成了一类较为罕见的人类意识,以及此种事件就客观时间而言只持续一小时不到,却会在当事人醒来后改变其一生,如同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改宗历程——不再恐惧死亡、不再执着于物质财富并转向了更大的善好。或者与海明威的案例类似,开始密切关注风险与死亡。
经由某类与神经递质血清素相关的致幻剂摄入精神活性物质后,人们也常会产生相似的神秘经验,这些致幻剂包括赛洛西宾(即某些神奇蘑菇里的活性成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二甲基色胺(又称精神分子)以及5-甲氧基二甲基色胺(又称上帝分子),于宗教、灵性以及娱乐活动中均有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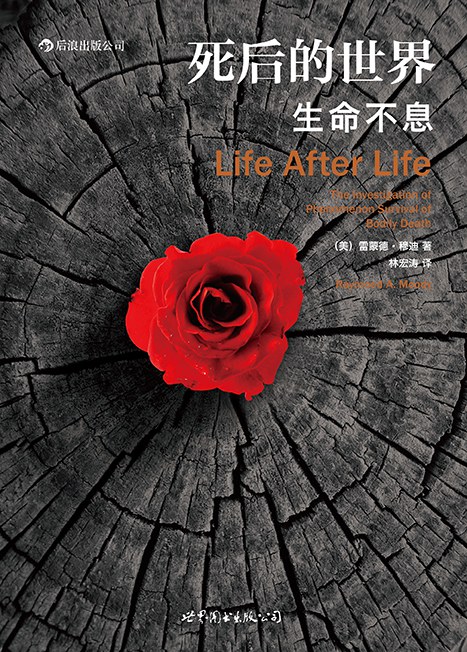
[美]雷蒙德·穆迪 著 林宏涛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4-4
未知的国度
务须牢记,濒死体验乃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时代、文化与人群,不分老少,也无所谓你是虔诚的信徒还是怀疑论者(例如,那本所谓的《西藏度亡经》就描述了生前与死后的精神状态)。对那些成长于宗教传统下的人而言——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它宗教——最明显的解释就是他们被赐予了一种看见天堂或地狱、洞察自身未来之命运的能力。有趣的是,对虔诚的信徒而言,濒死体验的发生几率并不大于世俗主义者或者不参加宗教生活的人群。
取自历史记录的个人化叙事可以为濒死体验增添极为生动的说明,其启发性就算不比那些干瘪的临床病例报告更强,至少也是不亚于它们的。例如,英国将领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国际通用的蒲福风力等级即源自他的名字)在1791年曾有一次接近于溺毙的经历,他对此事件有这样的回忆:
“一种最完美的宁静的平和感压倒了最喧嚣的感受……我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疼痛。相反,我现在的感觉是相当愉快的……此后感官虽然接近于麻木,精神却不然,它的活跃程度似乎超出了言语所能形容的范围。念头在脑海里一个接一个地升起,这对于没有亲历过类似状况的人来说不仅难以形容,甚至也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时至今日我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回忆起那些念头:那件事就像是刚发生过一样……类似于时光倒流,我过去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以逆序掠过我的回忆……我的所有人生经历俨然以一种全景式的样貌呈现在我的面前。”
另一个案例是1900年记载下来的,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奥格斯顿(Alexander Ogston,葡萄球菌的发现者)饱受伤寒的困扰。他是这样形容病况的:
我似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它排除了任何希望或恐惧的存在。思想和身体似乎是双重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我意识到身体是那团在门边笨拙地扭动着的物体,它属于我,但并不是我。我意识到我的精神性自我经常离开身体,然后又被迅速拉回去,带着一股恶心再度加入身体,它变成了我,并被喂饱、交谈和照护……虽然我知道死亡就在不远处徘徊,但既没有想到宗教也没有恐惧终结,只是在阴暗的天空下漫无目的地游荡,内心没有一丝波澜并感到满足,直到有某样东西再次惊扰身体躺卧的地方,我才重又回归身体。
近些年,英国作家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在一名塞浦路斯女性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她1991年曾接受过紧急胃切除术的治疗:
术后第四天,我陷入休克并昏迷了好几个小时……虽说是昏迷,但我多年以后都还记得当时在场的医生和麻醉师谈话的整个过程及其细节。我浮在自己的身体之上,没有一丝痛苦,以同情的眼光打量着痛楚清晰地挂在脸上的自己,我平和地漂浮着。后来……我又到了别的地方,漂向了一片黑暗,但那里并不可怕,是一处像窗帘一样的地方……我感到了一阵完全的平静。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我又被打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并再次感觉到了痛苦。
鉴于大脑受损的状况五花八门,要精确地刻画濒死体验中各个事件在神经上的序列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一个人若是躺在磁性扫描仪中,或头皮被电极网覆盖,濒死体验便不会发生。通过检查心脏骤停(用医院的行话来讲就是患者正在“编程”)即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此时病人并没有死亡,因为我们可以借助心肺复苏术来让心脏重启。
现代的死亡定义里包含“大脑功能不可逆丧失”这一要件。大脑一旦缺乏血流(缺血)以及氧气(缺氧),患者在一分钟内就可能昏倒,其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会变为等电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平直的。这意味着大脑最外层皮层内大规模的电活动已经崩溃。就像一座城镇里按街区顺序依次断电一样,大脑的局部区域也一个接一个下线。但只要神经元保持完好,大脑就会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讲述一个由某人的经验、记忆与文化期望塑造的故事。

鉴于这些“停电”现象,此类经历可能会产生构成濒死体验报告语料库的各类奇闻轶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濒死体验的真实性不亚于大脑在正常清醒状态下产生的任何东西。当整个大脑因完全失去动力而停摆时,精神就与意识一同熄灭了。如果氧气和血流恢复,大脑便会重启,经验的叙事之流也会跟着恢复。
科学家们对一些受过严格训练的个体——美国冷战期间的试飞员与NASA宇航员——的意识丧失及随后的恢复过程进行了录像、分析和拆解(不妨回忆一下2018年的电影《登月第一人》中由瑞恩·高斯林饰演的硬汉尼尔·阿姆斯特朗,他在多轴训练器中不停打转直到昏倒)。当重力五倍于正常值,心血管系统便会停止向大脑输送血液,飞行员就会昏倒。在巨大的重力减弱后约10-20秒,意识就会恢复,并伴随一段时间的迷乱和方向感的丢失(这些测试的参与者显然非常健康,也具备卓越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些人所描述的现象或可纳入“类濒死体验”(NDE lite)的范畴——隧道式的视觉以及亮光;从睡眠中醒来的感觉,包括部分或完全瘫痪;一种平静的漂浮感;灵魂出窍的体验;愉悦甚至欢欣鼓舞的感觉;简短但印象深刻的梦,通常关涉到与家人的谈话,且当事人多年以后对之依旧记忆犹新。这些由特定的生理创伤引发的强烈感受通常不含任何宗教特征(也许是因为参与者们已经提前知道了自己会承受压力直至晕倒)。
就其本质而论,濒死体验的研究与实验室里受控良好的试验暂时无缘,但未来可能会有变化。例如,我们可能会借助实验室里的老鼠来研究它的某些方面——或许老鼠也能在死前体验到一生的记忆或欣快感。
光的消逝
许多神经科学家都留意到,濒死状态在效果上与一类名为复杂部分性发作(complex partial seizures)的癫痫事件具有相似性。发病时,意识会局部受损,并且通常局限于同一半球的特定大脑区域。发病前可能会有先兆,不同的患者各有其个人化的独特体验,可藉此来预测初期的发作。癫痫的发作可能伴有物体尺寸感知的变化;异常的味觉、嗅觉或身体感觉;似曾相识感;人格的解体;或欣喜若狂的感觉。这一清单当中的最后几项状况在临床上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的范畴,这位19世纪晚期的俄国作家在患上严重的颞叶癫痫后即出现了前述的症状。他的小说《白痴》里的主人公梅诗金王子回忆道:
在癫痫发作期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癫痫发作前的一两分钟里,他的整个心灵、思想与身体似乎都变得活力四射、光彩照人;此时他充满了喜悦与希望,所有的焦虑似乎都一扫而空了;而这些时刻不过是他在癫痫发作前最后一秒(永远不会超过一秒)的预感。 当然,那一秒钟是难以言喻的。从发作中恢复过来后,这位王子不时会反思自己的症状,他常常对自己说:……“它不过是一场病,一种大脑的异常紧张,但每当我回想与分析那一刻时,它似乎又表现出了最高程度的和谐与优美——这一瞬间的感受极为深刻,洋溢着无限的愉悦以及狂热而忘我的虔诚,也许还有圆满的生命?……我甘愿为这一刻付出我的一生。
经过了150多年,神经外科医生已能通过用电刺激大脑中植入电极的癫痫患者的皮层部分——名为脑岛——来诱发这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此流程有助于确定癫痫发作的源头,为未来可能的手术切除做好准备。患者通常报告称自己感觉很美妙、幸福感变强、自我意识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得到提升。刺激别处的灰质则可能会引发灵魂出窍的体验或视觉幻象。异常的活动模式(无论它出于自生自发的病程还是外科医生的电极控制)与主观经验之间的这种直截了当的联系,对生物学而非精神性的起源说形成了支持。濒死体验很可能也是如此。
为什么大脑在缺血以及缺氧状况下奋力维持其运转所带来的体验是积极而美妙而非引发恐慌的,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颇有意思的是,人类经验光谱的外部界限还包括其它一些场景,缺氧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活泼感、头晕目眩以及高度的兴奋——如深海潜水、攀登高山、飞行或昏厥游戏,以及性方面的窒息玩法。
也许只要头脑保持清醒、不被鸦片或其他缓解疼痛的药物所迷惑,这种欣喜若狂的体验对多种死亡形式而言就都属于稀松平常。被垂死的身体所束缚的心灵,在踏入哈姆雷特所谓“从无旅者生还的未知国度”之前,已经先去了一趟专属于自己的天堂或地狱。
(作者Christof Koch系艾伦脑科学研究所MindScope项目与小蓝点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为《科学美国人》顾问团成员)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