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与种族主义者辩论》(How to Argue With a Racist)一书里,遗传学家亚当·卢瑟福(Adam Rutherford)清楚明白地解释了为何许多广为接受、具有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的有关种族的观念其实是伪科学,他还在论证过程中稍微勾勒了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以及助长了此类观念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偏见。对于进化的具体运作机制,我们的观点可能还不够成熟——并且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一些18世纪帝国主义者发明的种族范畴,但他也企图借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向我们表明,这一切背后的遗传学可能“高度复杂”。
《控制》(Control)是《如何与种族主义者辩论》的姊妹作。它依旧着眼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对科学的招揽与利用,或者说对此一关系的浅薄认识。如今拜纳粹所赐,“优生学”这个词已经臭名昭著了,以至于它往往会腐蚀它所触及的任何东西。鉴于此,报纸上的恐怖故事经常会拉它做大旗来抨击广义上的种种干预措施与观念。任何胚胎或干细胞实验有关的事都会“引来优生学的阴影”,令读者生出一阵夹杂着愉悦的小小恐惧。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20世纪早期,许多杰出人士无论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为何,都认为优生学肯定是个好东西,有人甚至认为它的好是不证自明的。选择性的育种(selective breeding)——其推进手段或可包括设法让那些被认定具有不可欲特征的人少生孩子——必定能增进普罗大众的智力、健康与繁荣。这一观念并不新颖。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设想过让一个由兼具聪慧与美貌者构成的特权阶级来创造聪慧而美貌的婴孩;而斯巴达人——起码就杜撰的内容而言——则倾向于把瘦弱的婴儿扔下山崖。 在孟德尔与达尔文有关遗传与遗传机制的一系列思想问世后,这种古老的冲动又获得了新的尊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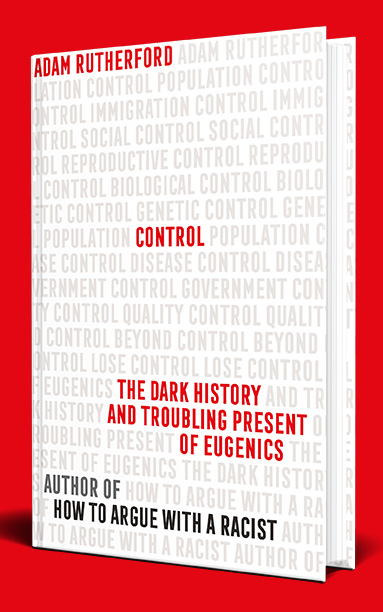
在英国,遗传学的创始人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不仅首次提出遗传学这个术语,还是孪生研究和许多统计学技术的开创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后来都成了诋毁其成就的口实。卢瑟福并没有妖魔化各个优生学的现代先行者,但他还是不介意称这些人为种族主义者。高尔顿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他的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说乃是“证实性偏见的最高级表现”。他的弟子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对科学史的影响是巨大的”, 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Ayler Fisher)则“稳居有史以来最顶尖科学家的行列”,然而这三个人都跌进了优生学的“兔子洞”。
定义——尤其是这种内涵极其庞杂的术语——会惹出麻烦。优生学可否被有效地界定为一本书的主题?为了部落的利益而对瘸腿、无法行动以及精神上处于不利状态者实行安乐死等做法——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这样做,与表面看来是良性的干预措施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又如,我们会在妊娠早期进行唐氏综合症的筛查,许多父母正是据此来决定是否继续妊娠。至少在理论上来讲,在体外选择一个遗传性疾病几率最低的胚胎进行植入是有其可行性的。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在探讨于受孕后立即编辑胚胎基因组,以防其罹患遗传性疾病这一可能。基因编辑技术还为我们带来了新冠疫苗。这一切难道都是“优生学”吗?
卢瑟福在“减轻个人、父母和孩童的痛苦……而非国家强令的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之间做出了区分,我(指本文作者Sam Leith,《旁观者》杂志文学编辑)认为这大体上能成立。换言之,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卢瑟福的意思就是:在人口层面实行干预不好;至于个体层面的干预……行吧,至少还可以讨论一下。

这本书最有力之处就在于它就上述论调提出的解释。如卢瑟福所指出的,在人口层面,有关什么能够“提高”一整个社群的素质的决策,通常都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关系不大。它们暗示了一种人类价值的等级制——哪怕其并不以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波兰东部村庄,纳粹灭绝营所在地——译注)为归宿,也容易把人忽悠到种族主义、残障歧视以及阶级歧视这一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潜藏在这些理论背后的恐惧,是病患、残障、低劣的穷人或种族上的他者将会“吞没”、污染或压倒光明与善良。卢瑟福认为,这种恐惧——他的论述偏简练但说服力尚可,与维多利亚时代面对新兴的工业化世界里数目不断增长且颇为刺眼的下层阶级以及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滋生的焦虑有关。许多人相信罗马灭亡的原因是下层阶级淹没了统治者,这暴露出了他们的文化偏见。高尔顿认为,教父让自己最优秀的神学家们保持单身乃是愚蠢透顶的。
的确有观点认为,优生学支持者与那些声称相信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必然性并鼓动武装革命的人有着同样的毛病。如果你真的相信北欧人种的血统更优秀、更具活力(乃至于相信进化的压力青睐更高的智力),那你还用得着走这么多过场吗?你难道不希望高等种族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自动胜出吗?
话说回来,优生学支持者总的来看并没有这么优哉游哉。相反,就像我们成功为肯德基培育出了肥美的鸡仔一样,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为智人(Hom sap)做类似的事情。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来制定政策规划,其中一些出于善意,另一些则远非如此。正如程序员所言,垃圾进,垃圾出。诸如“低能儿”“白痴”与“蠢货”等操场上的羞辱之语一度还被归为了诊断意义上的范畴——包括智力迟钝或心理疾病与其他形式的残疾再到刑事累犯在内的多种情况,均被笼统地视作遗传退化的标志,被判监禁或绝育。而这只楔子的大头正是所谓的“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与纳粹对所谓Lebensunwerten Lebens的灭绝行径——这个德语词的意思是“没有再活下去的价值的生命”。
但这本书并不满足于做这种志在必得的事,即论证我们都明白某不好的东西是不好的。卢瑟福的公允态度,或者至少是运用科学思维的程度,足以让他关心一些更尖锐的问题,例如:即便我们认定“积极的优生学”是个好东西,它又真的能起效吗?
截至目前,答案都是一个响亮的“不”字。回到以前是没戏的——科学家们基于一些对遗传运作机制的想当然的猜测来构思政策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放到今天也还是不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基因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而这也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所知之稀少。例如,一般智力或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可遗传成分涉及到我们已知的数十或数百个基因,还关系到更多我们一无所知的基因,它们的影响是多元的,呈现为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这段论述可谓是卢瑟福在自家地盘上作战(“当科学家扮演历史学家时,”他略带挖苦地说道,“存在极大的风险”)的一大高光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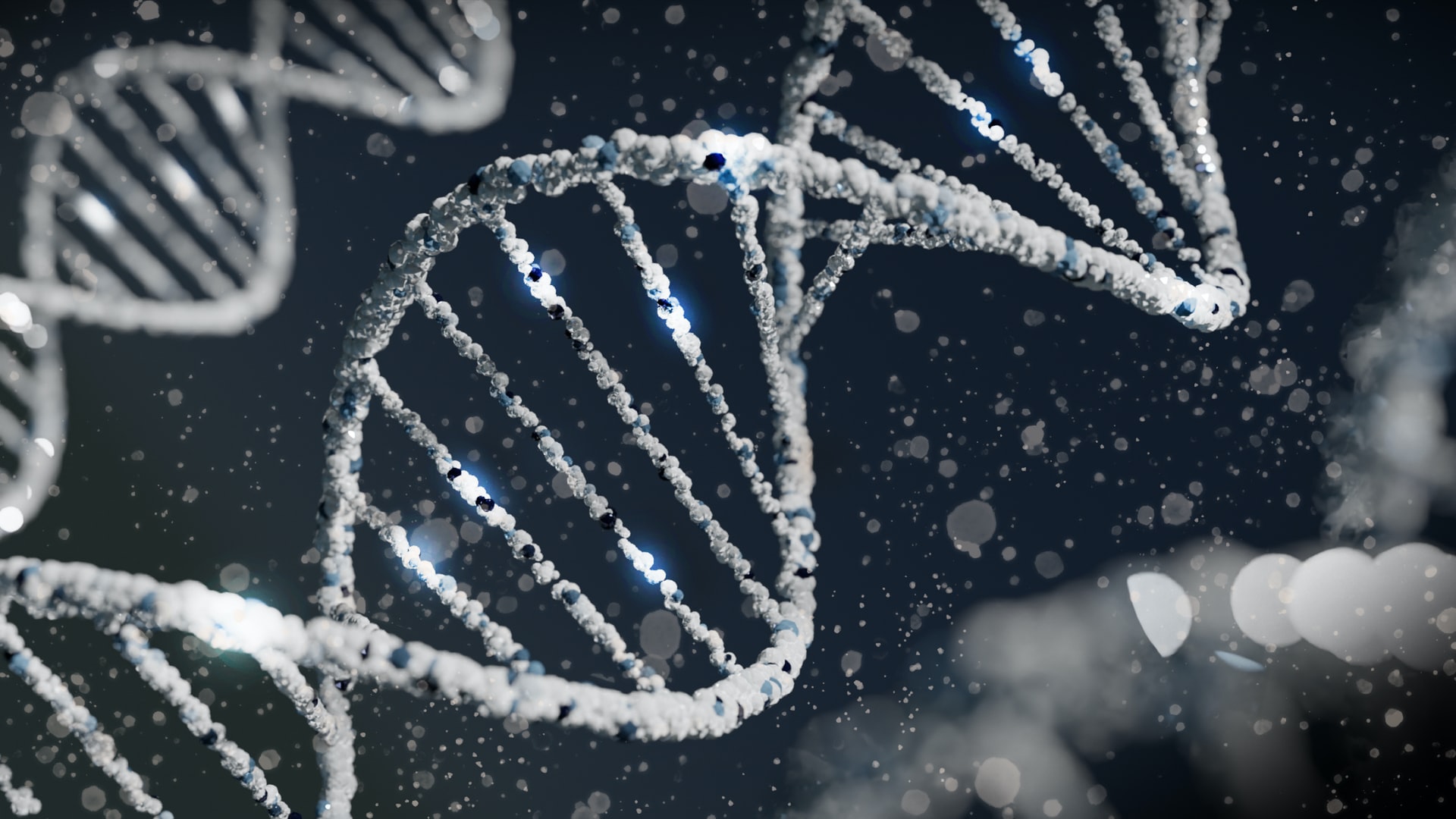
有关遗传的绝大部分流行观点,都源自他所称的“单基因决定论(monogenetic determinism)”:这种观念特别适合于放在头版头条上吸引眼球,即“存在某个导致X的基因”,如果有导致蓝眼睛的“基因”,那么你似乎就可以刻意选择蓝眼睛了。但即便是眼珠的颜色以及发色这种例子——英国中学生学到的则是其简化版——也未必有表面上那么可靠。“这一谬误有三个维度,”卢瑟福写道:
复杂的性状很少有单一的遗传学起因,它们总会涉及到非遗传环境,而遗传也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论的。这是优生学计划始终缺乏坚实根据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在意的弱智、癫痫与酗酒等状况,确实都有遗传成分——人类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当中的几乎所有元素都概莫能外——尽管它们从来就不是单基因的,且这些遗传学起因也很少是决定论的。
卢瑟福认为,那些迷恋技术的未来主义者似乎最热衷于在21世纪复兴某种“美好”版优生学(托比·杨在书中被敲打了一番,多米尼克·卡明斯也被点了名),但他们不过是因为不够了解科学而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设计婴儿”在科学上仍属异想天开。CRISPR基因编辑远非某些人炒作的所谓绝对可靠的“DNA打字机”,那些让我们在通往《变种异煞》(Gattaca)的路上走得更远的实验不仅不切实际和不可靠,而且在各方面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此外,卢瑟福还表示,企图在试管中就开始为广大普通人群“施肥”并不可行,传统的方法更简单也更有意思。如果你想提高人们的一般智力,那么投资教育、营养与洁净的空气和水,让进化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其实是更便宜、更有效以及更人道的——当然也更枯燥。如果我们忽然有能力一举消灭唐氏综合症或亨廷顿病了,我们是否应该立马开干? 卢瑟福在这些问题上持观望态度,你也不好责怪他,我们也尚未碰见过那样的情形。
有趣的论点、历史奇闻、细致的案例研究以及平易近人的笑话在卢瑟福的书里汇聚一堂,你读完它之后想必会再次对真正的科学家的所作所为产生敬重与兴趣。我想这本书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毕竟它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
(翻译:林达)
来源:旁观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