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赫蒂(Sheila Heti)本不打算写一本关于悲悼的书,但在2018年底,在她开始写新小说《纯色》(Pure Colour)大约一年后,她的父亲去世了。“他一直体弱多病,但那总归都是很强烈的冲击。父母离世乃是我成年以后所经历的最为深刻的变化。父母与生活的意义息息相关,而且你一直都明白他们并不是天空与大地——他们只是凡人。但即便你心里明白,你的身体也可能不听指挥,”受这一冲击影响,她书里的故事“突然中断了”。
赫蒂与我(指本文作者Hadley Freeman,《卫报》专栏作家)正坐在多伦多的公寓二楼,这里环境舒适,她和交往了十一年的男友卢克以及一只性格温顺的罗威纳犬费德曼住在一起。外面下着暴风雪,但在我们脚边打盹的费德曼却带来了一丝暖意。一名共同好友告诉我,45岁的赫蒂“在你看来想必很年轻”,加上她少女一般的声音与长袖T恤配棉质蓝色连衣裙这种1990年代的少年装扮,的确乍看并不显老。在写作2010年出版的《人应该怎么过?》(How Should a Person Be?)以及2018年的《母性》(Motherhood)这两部销量俱佳的小说期间,她还留着精灵一般的短刘海,但它现在已经消失(“我只是没这个习惯了”),她有一种经常被评论家所忽视的安静和敏锐,他们把她的原创性误认为了离经叛道。不难想象,正如她以往是个颇有艺术天分的少女,她也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犀利的中年女人。
《纯色》在原创性与尖锐性两方面均属典范,以短短二百来页的篇幅涵括了世界的开端与终结、亚当与夏娃以及女主角米拉的一生。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想必会有马上再读一遍的冲动,以了解作者到底是如何做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我在写其它书的时候曾想到:‘某个朋友可能会读到这个,我希望这本书能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但《纯色》则不包含此类想法。我完全放空了自己,它诉诸直觉的成分也更多,”赫蒂说。结果就是,这本小说有一种梦幻色彩,一些章节读起来像是直接从赫蒂的潜意识当中迸发出来的,例如米拉在哀悼父亲的时候因悲伤过度而变成了一片叶子,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哀悼——倒不是说灵魂出窍,而只是感到离每个人都很远,不是那个富有活力的世界的一部分了,”赫蒂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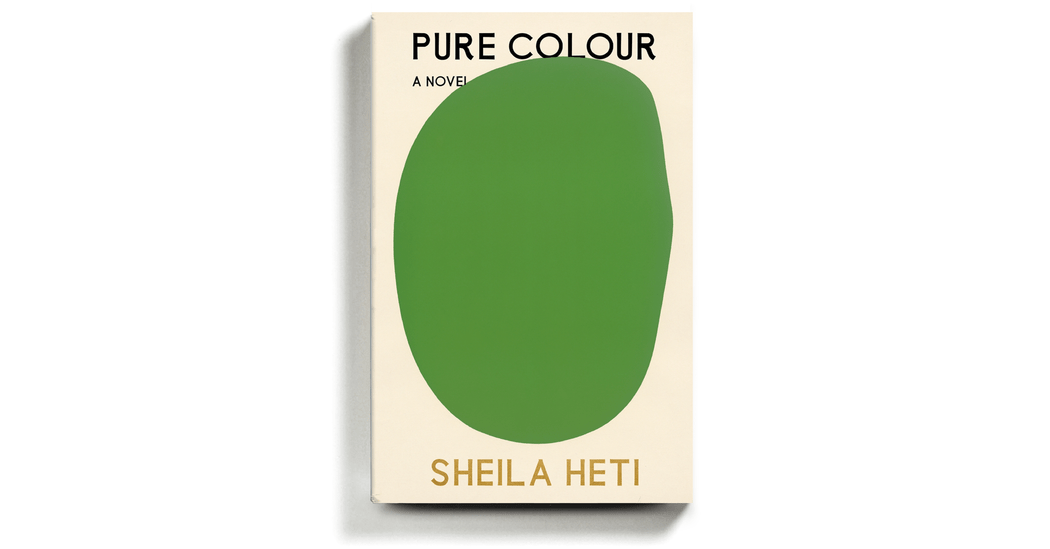
赫蒂在多伦多长大,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移民之家的独女。她非常喜欢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艾德蒙·怀特(Edmund White)以及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等作家的著作。他们给了她一种感觉,使她把小说当做一种没有模板的中介:她可以借它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在有趣而又温和的《人应该怎么过》一书里,一个二十来岁的名叫希拉的女青年游走于多伦多与纽约之间,并与她的朋友们交谈——有时是散文,有时是剧本的形式——她试图回答名字雷同(eponymous)的问题。在更关注内在、偶尔会透出焦虑的《母性》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样名叫希拉的女子依旧在多伦多徘徊,与她的朋友们以及男友迈尔斯展开对话,想要弄清自己是否想要一个孩子。
这些小说听起来很相似,但语气与情绪却截然不同,赫蒂在较早的作品中抓住了二十来岁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怀疑,而后期作品则聚焦某种特定类型的三十多岁的人,挖出了困扰他们的恐慌和焦虑。鉴于书中的浓厚自传色彩,许多评论家将其形容为自我虚构(autofiction),类似于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和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作品。赫蒂一度有些抗拒这个词,但现在已经认同。“它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它与人们对这本书的期望相符。不过我还是会称之为小说。所有作家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当成素材。看一看普鲁斯特即可知——这他妈的全是自传,”她说。
多次运用自己的生平经历,也意味着赫蒂的书之间是相互呼应的:在《母性》里,她表示儿时母亲的严厉批评使她“决心活成一个超越一切批评的人,力图证明我比她眼中的任何一个我都要优秀”,她第一部小说的标题也因此而有了别样的意涵。《母性》主要关注她与母亲的复杂关系,而父亲作为一个特别“会玩”的照料者则只得到阴影里的一瞥。如今,借助于《纯色》一书,赫蒂让父亲也走上了前台。

与前两本书不同,《纯色》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写成的,且它也没有提出什么核心问题:叙事者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读者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人们何以是眼下这般样貌,以及世界何以是其之所是。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赫蒂对自己的反思——“确实,现在的我比以往要自信多了,”她同意这一论断——而这也是因为这部小说关乎中年,在人生的这一时间点“派对已经是关起门来举行了”,正如书里所谈到的,这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问题可问,只有需要着手应对的各种情况。
《纯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惆怅且略带讽刺的,叙述者解释称我们都生活在上帝的“存在的初稿(first draft of existence)”之中。米拉惊叹于自己年少时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耗费的大量时间,以及她所称的“令保持联系变得第一重要的友谊革命”。然而不久后她的父亲突然就去世了,故事变成了某种赫蒂始料未及的样貌。“我从来没想到父亲去世的经验会成为书的一部分,但接着我又想到,‘啊,存在的初稿……’亲人逝世后你就像生活在存在的二稿里,因为这就好比世界已经终结了一回,对吧?我见证了这一切汇聚在一起的全过程,”她说道。

没有作家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小说会令人想起别人的作品,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诉她说《纯色》屡屡让我想起帕特里夏·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同样融合了悲悼与对于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的戏谑式观察、去年入围布克奖的《没人在谈这个》(No One Is Talking About This)一书。她点了点头。“是的,帕特里夏和我是朋友,几年前我们彼此透露过书讯,当时我说,‘这些书的相同点真是不少!’我们还交换了手稿,发现它们在结构上也非常相似,”她说。
在我看来,赫蒂的书更好,它对悲悼的描绘是如此地出人意料与真实,以至于让我有一股窒息感:“她一度以为,某个人的死可能类似于他们步入了另一个房间,”她写道,“她不曾知晓的是,生活本身已经变形为了另一个房间,并且把没有逝者相伴的你困在了里面。”
在上一本书里,赫蒂以同样的真诚谈及了爱与性。写这种个人经验是否显得有些暴露狂?“我从来不觉得有过度暴露的问题,因为我之内的一切都没有不在你之内的。一切写作都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我说了什么超出人类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她说道。
《母性》里的希拉选择不要小孩的理由不外乎自己不想要,但这并非普遍的经验。这本书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赫蒂的推论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我则再进一步,告诉她这本书的某个部分令我很失望,其中希拉相信自己必须在追求自己的艺术事业与生小孩之间做选择。为什么不能让她的伴侣来照顾孩子而她则继续专注艺术?
“你有孩子吗?”她问道,显然是希望在此掌控一下议程。
我告诉她我有。
“我知道很多有小孩的艺术家,所以那不是我为什么没有小孩的理由,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法从事艺术,”她说。赫蒂说,自己没有小孩的理由就是不想要,除此之外无需多说。“但你必须得有个理由,”她苦笑着补充道。
鉴于她将在余生当中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她是否后悔当初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那个决定?她思索了一阵子。“不后悔,因为我喜欢那本书,”她笑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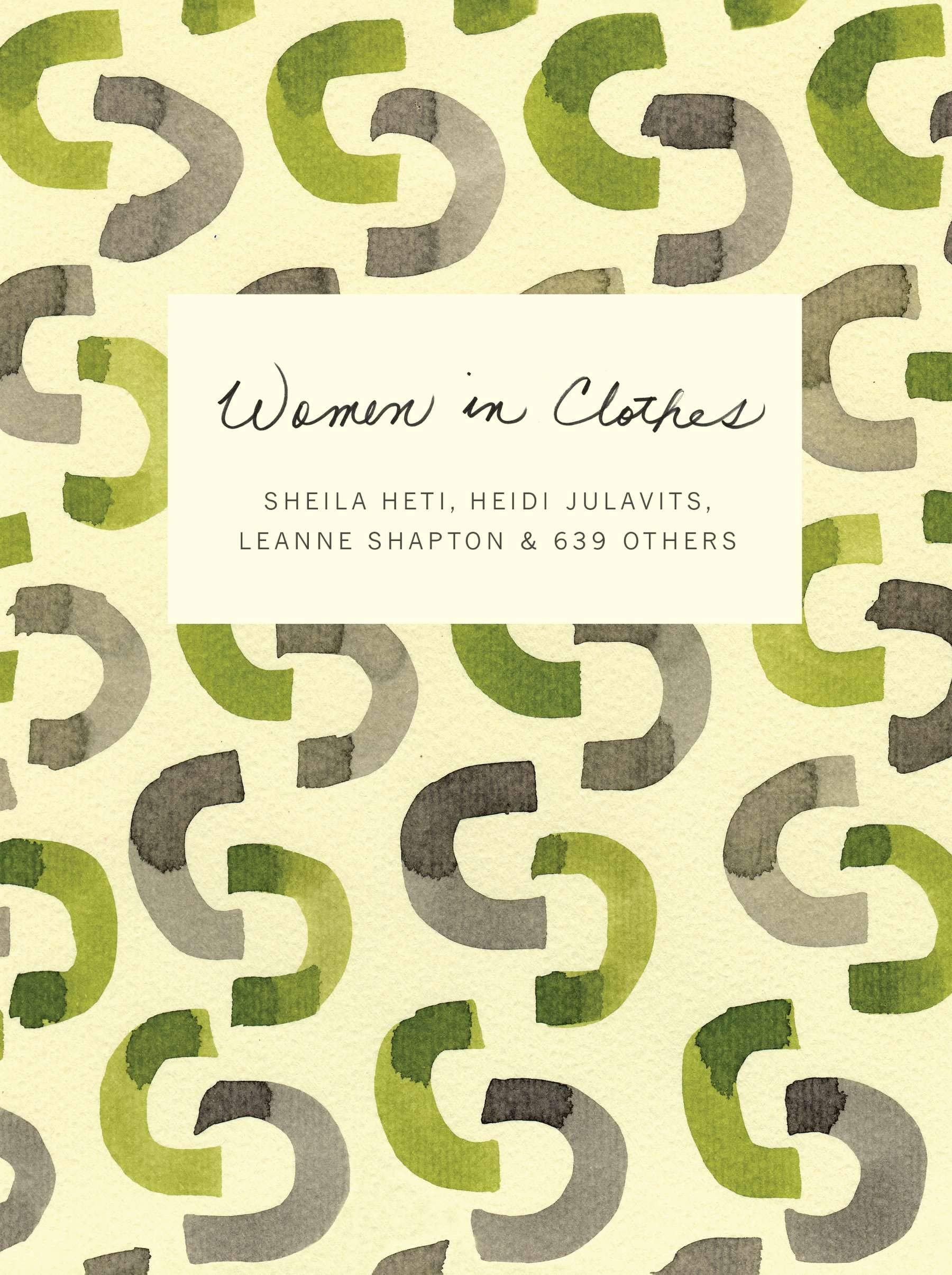
赫蒂年幼时就热爱表演与写作,经常和朋友组织节目以及和父亲一起写故事。她逐渐认定,自己必须在两者之中选取其一,以提高自己在某一方面取得更佳表现的几率。她最早成名是因为给文学杂志《信仰者》(The Believer)撰稿,但后来又专注于与人合写《衣装里的女人》(Women in Clothes),她形容这本书是“数百位女性之间的一场对话”,主题是时尚选择。除了它以及长篇小说外,赫蒂还写过一部戏剧、一部中篇小说、一部小说集、两本童书以及另一部有关哲学的合著。她自称爱书“胜过一切”,而我俩周围的书架上也都摆满了名家经典——纪德、福楼拜以及托尔斯泰。赫蒂在访谈过程中还推荐了几本书:艾黛儿·瓦德曼(Adelle Waldman)2013年的首部小说《纽约文青之恋》;莉莉安·费什曼(Lillian Fishman)同为处女作的《侍奉》(Acts of Service),它将于2022年夏季在英国上市;还有肖恩·索尔·康罗(Sean Thor Conroe)的自传体小说《渣男》(Fuccboi),该书讲述了一名私底下和觉醒完全不搭边的男青年如何拈花惹草以及设法让自己的书出版。“优秀的作家实在是太多了!”她高兴地说道,而她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灵感则是“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十分出色,所以你需要找准你心仪的事”。她最近的一大发现则是1963年初版的一部奥地利反面乌托邦小说《墙》(The Wall),作者是玛莲·豪斯霍弗尔(Marlen Haushofer)。“它现在已经绝版了,给你一种恶心感——因为假如作者不是女性的话那每个人就都会读到它了,就像《鲁滨孙历险记》一样,”赫蒂说。
她是否认为女性写的书所得到的待遇依旧与男子不同?
“完全是这样。把《渣男》的书评和我那本《母性》的书评对照起来看就很有意思。评论家把疑点利益都给了他,假定他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以及他的选择是有意识的。没人会说,‘角色就是作者。’但放到《母性》这边,批评家对角色本身的攻讦便来得很猛烈,这令我有些意外。”
此时此刻,暴风雪已经演变成一场完整规模的雪暴,外面已经没有出租车了。我说你自己忙你的,我出去走一会儿,但赫蒂坚持要我留下来,所以我们又坐下来聊了45分钟的生活。回到家的卢克以一种在十年以上的夫妻当中甚为少见的花样与赫蒂相互调情。我问她卢克是否就是《母性》里的迈尔斯,她迟疑了一阵。“是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和我在一起,”她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她的生活与她的书之间划清界限。
我们又聊了一些有关《母性》的东西,她问我是否后悔要小孩。我说不后悔,因为没有他们我就会倍感失落。看了看她的书架,我又接着说当然我也不时会怀念旧的生活,那时我还可以一个人在家呆一整天,安静地阅读和写作。“那么你的理想自我就是一名没有孩子并且乐意如此的女性,”她说。我表示赞成,并且我可以看出她在脑海里的某张内部索引卡上记下了这一点。她又看了看我,露齿而笑。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