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母亲并不会帮参加选美比赛的女儿黏假睫毛。她们不会像《选美小天后》节目里的妈妈那样,刻意把孩子的腿喷涂成褐色。她们也从未站在观众席上,带着一脸爱意指示孩子们应该怎么去表演,一面挥手,一面高喊:“女儿,拿下它!”和“太棒了,宝贝!”
但她们可能会放任孩子在电视屏幕面前坐太久,面容松弛且精神空虚。让自己被孩子的顽固不化弄得心烦意乱,举起双手,大喊大叫。用巧克力贿赂她们的女儿,让她们穿上一直想穿的裙子来拍复活节照片。为小学单词拼写比赛的成绩而过度投资。
的确,真人秀节目上的母亲一亮相就与其他母亲有所不同:评价她们——而她们也经常及不了格——的标准与在其它领域一样严格。无剧本的节目编排可能会弄巧成拙,令母亲们的失败更加引人注目,但那些所谓的缺陷却是我们早已烂熟于心的。
以真人秀《糊涂妈妈进产房》为例,如剧名所言,它关乎直到快要生孩子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女性。这些女性当中有一部分身体本来就有些小毛病,与妊娠的症状混在了一起;在另一些情况下,怀孕的标志则非常显著——后一群人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嘲笑对象。在2010年的单口专场《拄着拐杖的妓女》(Whores on Crutches)里,凯西·格里芬(Kathy Griffin)以夸张的南方口音形容了一系列怀孕的经典标志(体重增加,早上精神不好),末了却又补充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是怀孕的迹象?!”

我很难把注意力从《糊涂妈妈进产房》上移开,在和其他母亲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得知自己并不是一个人。也许我们能在观察不同于自己的处境时获得一种偷窥的喜悦,我们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这么愚蠢。又如,恐怖电影里那种“它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感觉也许就是我们乐在其中的原因。不过,这档节目能在我的某群朋友当中引发共鸣,也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我们都是当妈的人,而《糊涂妈妈进产房》在内心深处打动了我们。
这部剧的前提违反了社会学家莎朗·海斯(Sharon Hays)所提出的“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即那种认为女性应当只把时间、资源与情感投入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的文化观念。而《糊涂妈妈进产房》里的女性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快要当妈妈了,乃至于到分娩前夕也浑然不觉。

作为一个刻画家长职责的模型,“密集型母职”的定义很狭窄,但流传甚广。从生物学上看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母亲显然应该积极看护自己的孩子,对吧?然而,正如海斯所指出的,那种认为母亲应当持续不断地为孩子提供情感慰藉、随时随地都盯着孩子并且为孩子设计一系列有序的活动的观念,不过是现代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想。即便在美国,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的新英格兰父亲所承担的责任,也主要是培养孩子的纪律性与“道德刚毅性”。历史学者史蒂芬尼·孔茨(Stephanie Coontz)就此谈道,“母亲完全负责带孩子而父亲完全负责在外挣钱这样的分工,在历史上是极端罕见的。”而母亲将大量的爱与情感投注给自家孩子也无疑是个新现象。
且不论其在历史上的新颖性,密集型母职如今似乎已经定义了多数人认为可接受的抚养模式。真人秀节目里的母亲类型也许是多种多样的:名人妈妈、生存狂妈妈、一夫多妻制妈妈、变装妈妈(drag mom,指带领某人接触变装这一艺术形式的人)以及克莉丝·詹纳(卡戴珊姐妹的母亲及背后推手),但归根结底她们还是会被这套严格的标准审视,并且常常被指存在缺陷。

而观众们在提出责备时也相当严厉。在社交媒体上,粉丝们四分五裂,就这些母亲的选择展开争论,话题包括她们的孩子吃什么、她们的着装以及她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本身。各种报道、清单体文章及小报短篇里不乏以“真人秀妈妈的最差育儿时刻”与“荧屏十大不配带孩子的最糟糕妈妈”为题的——这种清单包含了诸如《权力的游戏》里的瑟曦·兰尼斯特这样的虚构人物,也有克莉丝·詹纳。而父亲在其中则几乎没有存在感,或者压根就没登场。例如,2012年的一份题为《真人秀节目里的最糟糕父母》的清单里几乎只有母亲,父母一同上榜的情形仅有两例,分别为《名人换妻》中的史蒂芬·傅勒(Stephen Fowler)与《乔恩、凯特和他们的八个孩子》里的乔恩·戈瑟林(Jon Gosselin)。
就“母亲是小孩福祉的主要责任人”这一广为接受的预设而言,乔恩凯特夫妇可谓是反面典型。这档节目一开始叫《乔恩、凯特和他们的八个孩子》,后来改成了《凯特与八个孩子》,起初它聚焦于这对夫妇与他们蹒跚学步的六胞胎以及年长一些的双胞胎女儿的日常生活。随着婚姻的破裂,乔恩也离开了家。在节目最火的那段时间里,甚至于在稍后的一些年里,凯特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都是各小报常用的“流量密码”。她是否做了整容手术?她在和保镖约会吗?她是否应当继续参加《与星共舞》?这些问题据称都在关注她孩子的福祉,只不过有时候明显一点,有时候隐晦一点。例如,某网站一连登出了15张照片,企图“论证”凯特缺乏做母亲的资格。“凯特·戈瑟林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文中问道,“她是否具备以爱、平静与亲和力来抚育八个孩子的气质?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报道还简略地提到了乔恩,但对他着墨不多。事实上,虽然有报道称他如今与孩子里的至少某几位已有些疏远,但他很大程度上仍被排除在相关的讨论之外。
问题不在于真人秀节目上的母亲都是“糟糕的妈妈”,因为原本就没有普遍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她们。如果以密集型母职模型来判断,那很多母亲更是完全没法及格。从儿童选美节目《选美小天后》里为年仅5岁的孩子修饰睫毛的妈妈到《小妈咪2》里的珍妮尔(Jenelle)被指无视汽车座椅的安全规范,这些女性都在现代母职的“石蕊试纸”上表现不佳——并且通过这样做而揭露出了测试本身的参数设定。观众对她们的回应则凸显出了密集模型的狭隘性及其内在的张力。
母亲被期望有较高的参与度,但又不能太高,譬如不能变成“直升机父母(指过分干预子女生活,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周围的父母)”或者扼杀小孩的天性。无剧本的真人秀节目里经常会浮现出一些有关此类极端情形的警世寓言。如克莉丝·詹纳就被形容为对自家孩子既不上心而又太过于上心。一方面,在《与卡戴珊一家同行》的前几期里,当时还未满13岁的凯莉和年长一些的肯达尔看起来有着大量不受监视的自由时间,单单第一集当中就有凯莉脱衣跳钢管舞以及姐妹二人调制鸡尾酒的场景。另一方面,有着母亲与经纪人双重身份(momager)的克莉丝又会在方方面面插手她们的职业生涯——二人经常在节目上抱怨这类事情。克莉丝这种把负面极端都占全了的能耐,或可部分地解释她缘何成为各种“最糟糕母亲”名单的常客。

探究如何维系这一平衡,是《名人换妻》节目的核心叙事线索,其中两对伴侣(妻子的社会背景通常差异极大)要临时交换妻子。在首期节目里,对调的是曾参演《成长的烦恼》的特里茜·古德(Tracey Gold)与以威尔逊-菲利普斯乐队(Wilson Phillips)而闻名的歌手卡妮·威尔逊(Carnie Wilson)。卡妮显然是两人当中比较悠闲的那一个,她首先分享了自家的座右铭“先讲爱,后讲规则”,并谈到有一群人在帮自己打理小孩和房子,因为她经常在各地举行巡回演出。特里茜则说自己的家庭“秩序井然”,还列出了每天由她亲自完成的一系列家务。在这一集里,节目一直在暗示特里茜为她的孩子做得太多(例如把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衣服翻出来给他穿),而卡妮则做得不够。正如旁白的解释所言,卡妮“不习惯在没有众人帮忙的情况下打理一间房子”。最后,当两人聚在一起畅谈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时,特里茜对卡妮表示一家人就应该多花些时间聚一聚,身体接触上也该更亲热一些,而卡妮则认为特里茜不必有那么强的“秩序癖”。每个人都学到了这条教训:不要太过远离密集型母职理想的甜区。
密集型母职带来的预期也富有悖论色彩,它认为女性天生就有带小孩的能力,但同时又得征求其他精于此道者的意见。这一张力在《超级保姆》里尤其显著,英国保姆乔·弗洛斯特(Jo Frost)教会了美国父母如何对付自家的顽皮小孩。从一开始,这档节目就把乔塑造成一个“拥有15年育儿经验”的专家。在向乔寻求专业建议的同时,节目上的女性还经常会为不知道该如何带好自己的孩子而表现出负罪感,俨然她们应该在基因层面就拥有相应的天赋。
但《超级保姆》所暴露的问题不只是个人在面对密集型母职之要求时的无能为力,它还揭示了这一模型缘何在社会层面也是难以实践的。2005年的某期节目追踪了一位“在家办公的母亲”,她成天都坐在电脑前办公,很难兼顾到4岁的双胞胎以及年长一些的哥哥(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此类场面想必要少见得多)。最终,乔的建议是她应该减少一些工作时间,将更多精力用于照看孩子。这个修正办法看似简单,但观众仍可能会怀疑它在经济上对这家人是否可行。更广泛地讲,他们可能会好奇那些没有能力提供密集型母职所要求的昂贵劳动的人将面临怎样的境况。
应当一直盯着自家小孩的观念具有阶级性,这部分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事实上,在一项分析了几十名背景各异的儿童的研究里,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发现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于让孩子参加成体系的课外活动,而工人阶级的父母则更可能“让孩子们自行探索业余活动”。相应地,密集型母职的框架会分别给这些策略打上“好”和“坏”的标签。看一看现实生活中因无力把孩子送到托管机构,工作一忙或者需要跑面试就没空照看孩子而被弄得十分窘迫的那些人即可。说到底,只有特权阶层才有搞密集化的余力。
当然,在真人秀节目以及其它一些地方,部分母亲并未遵守这一模型,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多少批评。在《斯努基与哇哇》里,两名参演过真人秀《泽西海滩》的演员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下诉说着自己为人父母的不足之处。但正如传媒学者拉克尔·盖茨(Racquel Gates)所指出的,一些观众之所以认同其叙事的吸引力,且能对她们的挫折一笑置之,原因无非是两名女性都是白人——或者说“以斯努基为例,她本身在种族上就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她们)的一些叛逆是可以被接受的,可以做得‘不好’而不承担任何后果,但黑人母亲若有相同的标志就会被指不称职。”盖茨写道。相对有特权的人不仅更有接近理想的能力,在她们偏离理想时,观众也表现得更为大度。
密集型母职的期望只适合特定的文化而不可能应用于每一个人,但许多支持者却视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哪位妈妈更符合要求?她们在家庭内部应扮演哪些“天然的”角色?真人秀节目凸显了这些期望之间的不连贯以及张力,同时也暴露出了节目的保守性是何等惊人。无论在设定上有多么新奇,人物又有多么滑稽,这些节目都依旧强化着某些根深蒂固的社会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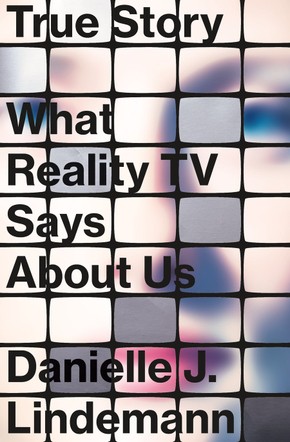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Danielle Lindemann即将推出的新书《真实的故事:真人秀节目告诉了我们什么》(True Story: What Reality TV Says About Us),有删减。Danielle Lindemann系理海大学社会学家,著有《霸权矩阵:地下城里的性别、色情与管制》《通勤夫妻:变化世界中的新式家庭》。
(翻译:林达)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