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寻找真我”是一个流行于当代畅销书与影视剧的语汇,又像歌曲里唱的“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少年》),想象真我的存在让人们倍感安慰,仿佛历经世事变迁,只要人们愿意就能寻回心中那个最初朴素的形象。然而,真我是什么?心中那个“少年”真的会在原地等待吗?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陈嘉映在新书《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一书中指出,认知自我是痛苦的,且也不存在一个现成的自我等待人们发掘。召回“从前的那个少年”的过程并不轻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已不易。

陈嘉映:认知自我需要穿过自欺与自我屏蔽
何为真正的自我?陈嘉映说,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自我,一个处于社会面具背后的真实自我;人在成为person的过程中经历了层层改造,自我总在形成当中,因此认知自我的过程并不是揭开屏障发现真我这么轻易。首先需要承认的是,认识自我需要穿过自欺与自我屏蔽——人们需要自欺,是因为自欺能够带来某一种好处,承认这点需要相当的勇气。
人们平常做事考虑的是怎样做成,而不问动机,似乎自我的动机是自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动机在行动的意义上是明确的,但上升为理知,中间却隔着一个自欺。比如说,人们做事往往认为自己拥有高尚的动机,也会认为自己因为爱或恨而行动,然而高尚的动机可能经不起推敲,爱与恨也经不得追问。陈嘉映举例道,“我以为自己爱国,跑到大街上砸日本车,我这么做,也许当真是认为大家都不开日本车,日本就会变成一个穷国,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富国,但我这么做也许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出于仇富心理,也许,我其实没啥动机,就是爱折腾、胡闹,发泄力比多。”他在书中写道,明白自己深层次的爱是困难的,而只有深层的爱会给人带来幸福。就像一个人以为自己爱大房子,可就怕挣到大房子之后才发现爱的不是大房子,这样的生活到头来也会非常郁闷。

因此,自我认知不像照镜子化妆那么轻松愉快,可能是撕心裂肺的、自我鞭挞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认识自我?因为人自我认知的动力来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依其本性求理解”,只有真实才能为理解提供保障,只有明白了真相才能叫活得明白,而当认识到自我的真相之后,将来可能以此为指导做得更好些,虽然更好也不意味着未来能够更轻松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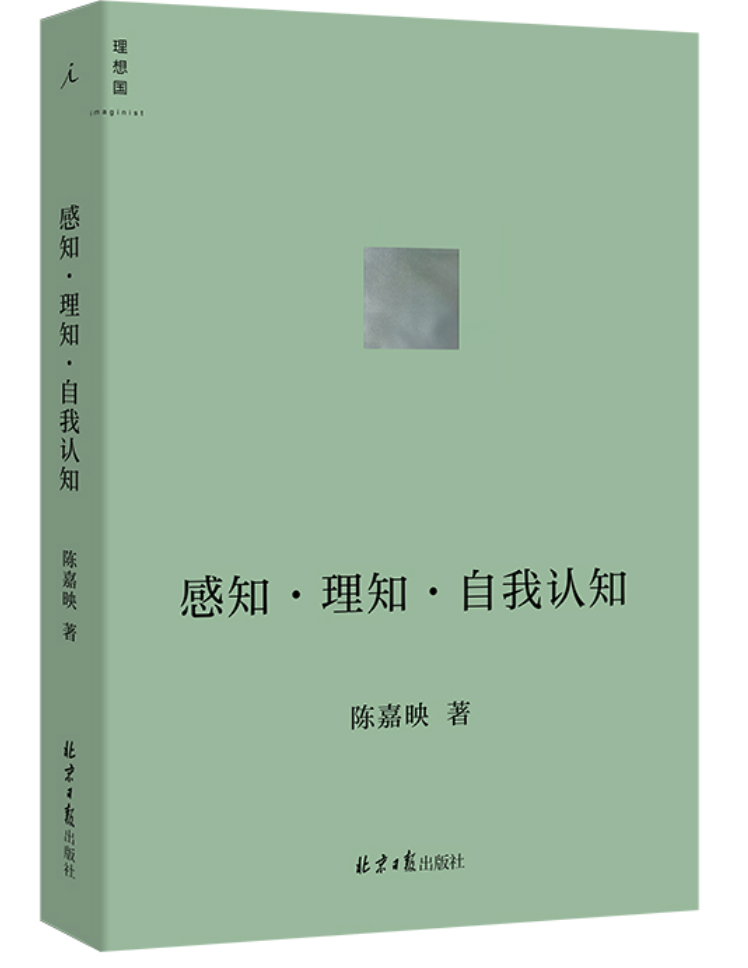
陈嘉映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年
陈嘉映提出的自我认知出现在许多层次上,从作为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者到自我理解,从“日用而不知到完整一贯的自我理解”,而这中间最重要的一层就是叙事。叙事能够帮助自我形成相对稳定的形象,比如对政治人物来说,完整一贯的形象就很重要——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是取信于人的重要方面,如果什么都做,就会被认为“机会主义者”,失去公众的信任。
既然认识自我是困难的,但又是足有裨益的,而自我又不是现成的、一成不变的,那么这样的自我就需要良好的建设。从承认自我需要形成连贯的叙事出发,陈嘉映接着提出,关注自我时重点应当不在于我们在组织自我的时候会删掉些什么、会改变些什么,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组织了一个健康的自我。他认同尼采的比喻,尼采将人的一生当成一件艺术品,它删掉丑陋的部分,呈现出整体的美;又认为人生与艺术品略有不同,艺术品有完成的一天,生活却没有完成的一日。因为人们面对的世界与生活在变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变化,因此需要不断重新的建设自我。
在当下,信息流通得过于快速也让自我建设变得困难,面对纷繁变化的外在世界,陈嘉映的建议是,每个人需要下点功夫,将自身的关切重新组织,要了解全世界的事情,但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能够感知和接触的世界,把遥远世界的信息放到适当的位置。
特里林:文化庸人是为了角色扮演否认自我的人
陈嘉映所分析的认知自我的困难,不禁让人想到20世纪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中用诸多经典举例证明的,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达到这种状态的。而其中有意思的一点即是分析卢梭对艺术取悦大众的担忧。卢梭的担忧在于,生活在大众环境中的个体容易不断受到他人心智活动的影响,这些活动影响、刺激与扩充着他的意识,个体最终发现,明白真正的自我、忠实于自我变得愈发困难。正因如此,卢梭认为现代社会在增加意见的同时,也控制了个体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戏剧、文学与艺术都是其中的重要意见力量。他认为,戏剧艺术会削弱自我的真实性与自主性:文学体现的是社会性的准则,按照这种准则,个人必须放弃自主自为以获得他人的宽容与尊敬,也就是说,观众也会传染上演员的疾病,由于扮演人物而削弱自身身份。(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对此,特里林解释道,当然可以批评卢梭所说的艺术的意义就是“取悦”,因为文学的功用恰恰在于撕破风雅的外衣而不是附庸风雅,但重点在于,卢梭关心的不是艺术上的美,而是实际的人的美,是在强制性的社会生活中能自主自为的人。他如此反对戏剧,就是因为认为戏剧用自我欺骗代替品性端正,“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欣赏精巧的故事情节,为虚构的悲剧而流泪,我们对他还能有什么要求呢?他难道对自己不满吗?他难道不会为自己美好的灵魂而欢呼吗?”——在这里,自欺又一次作为认知真我的敌人出现了。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著 刘佳林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
与卢梭提倡的自主自为的人相反的,就是所谓“随波逐流型”人格。这种人格的整个存在都是在捕捉社会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力量发出的信号,总在力求步调一致,以至于根本不是一个自我,而像一只学舌鹦鹉。特里林提示道,这类人如果能借由艺术领略文化的能量,发现并坚信个人的意义,却全然不是因为自主,而是因为来自他人的规则和意见。
这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体现为喜欢角色扮演的人物,像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亨利·克劳福德拥有惊人的戏剧才能,但这也成为了他的弱点,他将职业选择看作自我表现的机会,对于爱情也不是出于热情,而是情节需要的角色扮演。而在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中,特里林也由“随波逐流”进一步走向了“陈词滥调的地狱”,提示人们当代的每个人都可能如艾玛·包法利一般,试图逃出永镇那个陈词滥调的地狱,结果却走进了高级文化的陈词滥调的地狱。所谓的文化庸人,特里林写道,不再是指资产阶级对文化的抵制,而是指为了角色扮演而否定自我、参照优秀的文化事物形成自身经验的人。艺术即使不再取悦于人,也足够引诱人将自己的生存依附于他人的意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