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里战争无处不在,”越南裔美国作家王鸥行(Ocean Vuong)在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是一位母亲》(Time Is a Mother)里这样写道。“我讨厌这样说,但这的确是常态,”他在纽约对我(指本文作者Lisa Allardice)说道,我俩连线时正值俄乌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流离失所与穿越边境的难民,拖着孩子的母亲与父亲,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对我们这类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正如他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对自己的学生所说:“如果你想要研究文学,那就从研究战争开始——因为自从有了士兵,也就有了诗人。”
说王鸥行是从战争里走出来的诗人,绝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一名美国士兵强奸了一个越南农家女子,于是就有了我的母亲,然后就有了我,”他在其中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他在西贡郊外的一片稻田里出生,又在菲律宾的难民营里呆了一年有余,最后随母亲逃去了美国,当时他年仅两岁。他的小说《此生,你我皆短暂灿烂》(下文简称《此生》)从越南的稻田延伸到新英格兰的烟草种植园,从凝固汽油弹攻击写到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叙述了自己在9·11事件的余波中成长为“一个亚裔美国酷儿穷小孩”的历程。这本小说采用书信体,是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尽管她不识字。
王鸥行自己在11岁之前也没有阅读能力。但他的第一部诗集《带着出口伤的夜空》(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下文简称《出口伤》)却让他成为了新生代诗人里最为耀眼的明星,彼时他还不到30岁,评论家认为他可以与艾米莉·狄金森以及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比肩,而他也拿下了若干项文学大奖并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助金”。“你是如此地/幸运。你是同性恋并且你可以写一堆和战争有关的东西,”一名白人学生在他的创意写作课上曾有这样的抱怨,王鸥行在新诗里重述了这一插曲,“而我则一无所有。”
现年33岁的王鸥行“高5英尺4英寸(约1.62米),重112磅(约50.8千克)”,他在《此生》里写道。“我看起来很帅的角度只有三个,换了任何别的视角都会要命。” 凹陷的脸颊与棱角分明的面部线条,令他有了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气场(他不开车,也从来不用Uber,Instagram是他手机上唯一的软件)。他的声音就和他的诗《某一天我会爱上王鸥行》里的风铃一样温柔——听了他读这首诗,你也会对王鸥行有点心动。坦白讲,他的标题《此生,你我皆短暂灿烂》的确很吸引我,这部小说里有一种不多见的温柔与深情。他还是一名禅宗佛教徒。“和万事万物一样,”他说,“有时我很可怕,有时我又很好,但你总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

王鸥行 著 何颖怡 译
时报出版
他租住在纽约的一间空荡的、全白色的工作室里,西施犬豆腐——它和周围的环境一样白——正在他身后的沙发上卖力地“表演”,我们对谈时的严肃气氛也因之而稍有缓和。王鸥行说,它以前当过警犬,甚至于它身上也有暴力背景。与豆腐作伴的还有小狗罗茜,它是这个家里最年轻的成员,为王鸥行和伴侣彼得在封控期间收养所得。彼得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立陶宛裔波兰犹太人,新诗集中的散文诗《空无》(Nothing)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祖母距离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仅有一步之遥。他们都是创伤的后裔。
《时间是一位母亲》是王鸥行在母亲罗斯于2019年去世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她以51岁之龄去世,他坚信母亲的死因几乎肯定在于她多年在美甲店上班并因此而长期接触各种有毒的化学制剂。他的《一位前美甲店员工的亚马逊历史》(Amazon History of a Former Nail Salon Worker)这首诗罗列了包括止痛片、卫生棉、化疗用头巾以及最后的骨灰盒在内的一系列物件,记下了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惊人的节俭生活。“我10年前绝对没有能力那样做,”他说,“身为作家,你需要抱有极大的自信心,才有望做到让物件自己说话。”他自称工作效率极低——《出口伤》一书用了八年时间,《此生》则是五年。至于《时间是一位母亲》,他已经在母亲去世前写好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诗歌。但当他回望过往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失去(loss)的关注是何其多。“我的天啊,我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悼念了,”他说道,“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庭,都是集体性的悲悼。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方式在悼念一些东西,而诗歌可以提供一个让我们彼此在悲伤中相会的场所。”母亲是有能力分享王鸥行的部分成功的:虽然她读不懂诗里写了些什么,但她会来到他的读书会上,坐下来面对诸多观众,这样她就可以看见观众的反应。

诗集有两个极点,分别是失去和成瘾(addiction)。作为一个在工业衰落、一片萧条的康涅狄格州长大的青年,王鸥行目睹了许多友人的死亡——“地图上的小点一个个被抹去”——其祸首正是阿片类药物的大流行。“我们不会称它为大流行,”他在2000年代早期曾有此言,他的老师甚至也在那时死于吸毒,连葬礼都没有办。“这实在太耻辱了,”他如此形容当时的人的想法,“堂堂教师居然成了瘾君子?”肩负着家人的希望,王鸥行下了决心要避开类似的命运。“我拒绝去死,”他在《此生》里这样描绘年轻时的自己。如今他也承认,虽然自己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吸食海洛因,但的确也迷恋“一切你可以打碎成白色粉末然后洒在雪茄上的东西”。2012年,他在一家政府资助的诊所里呆了两个星期,新诗里也详细披露了这段经历:“在凌晨两点的窗户里瞥见麦当劳的拱门。”他想要“表达成瘾与康复的真实体验”。对他而言,“(成瘾)是人之常情。说明肉体与心灵正在谋求出路。我们有这种追求安宁以及更良好感觉的欲望,而这也强化了我们周围的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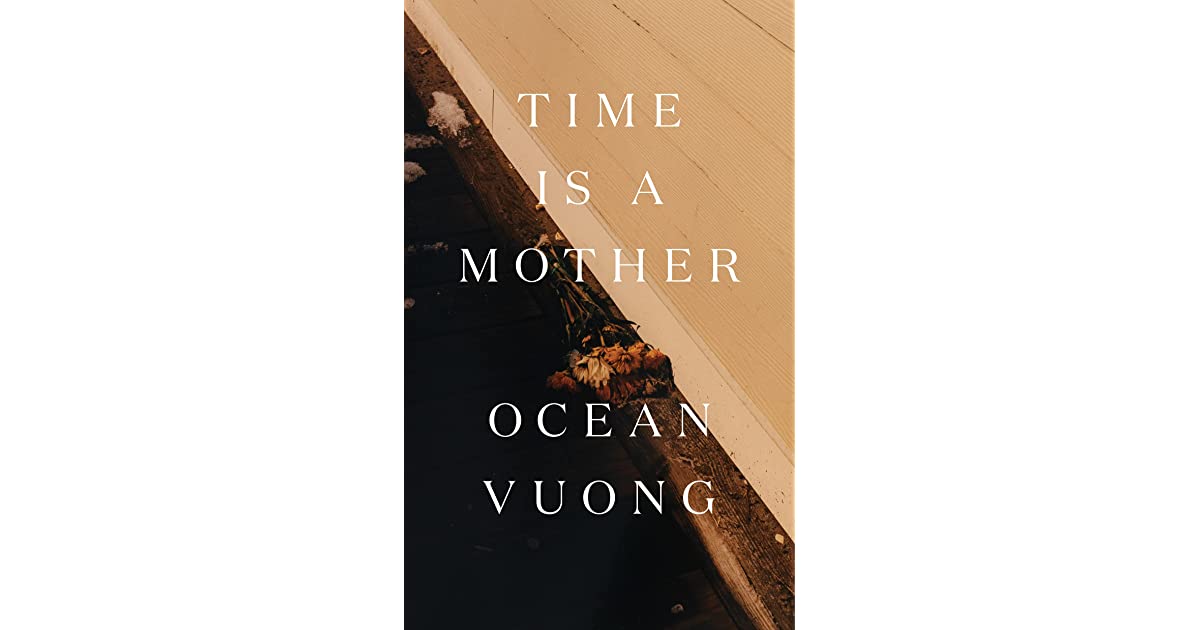
王鸥行在写诗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此生》兼有自传、书信以及散文诗的元素,是以同性恋难民身份来撰写美式成长故事的一次尝试。“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如何去推进这项追寻身份认同的谋划?”他问道。小说并没有走向一场自我提升与发现之旅,而是遵循东亚的“起承转合”( kishōtenketsu,日语写作“起承転結”——译注)叙事结构:没有戏剧性的高潮;没有受害者或反面主角;以及王鸥行十分看重的一点,没有逃往别处这一出路。“这些人都在自己原本所在的地方找到了欢乐。这对我而言珍贵非凡。”
小说糅合了两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母亲与儿子之间,我们只知道儿子叫小狗;第二个故事则发生在小狗和一个名叫特雷沃的白人少年之间。他曾想写一本有关“乡村酷儿性”的书,希望能借此表明“逃往大都市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对于大都市就是我们的唯一去处这一点,有不少猜忌和怀疑。一些人承担不起都市生活的开支,”他说,“我想让这两个男孩留在乡村空间里,使他们能维护彼此之间的那股小小火焰,而不必遵循什么模式。”
在这种亲切之外,王鸥行也很清楚,《此生》绝不是自传:他从一开始就有个比自己小10岁的弟弟,但如果把弟弟写进去就会对母子关系的强度构成干扰。他遵从艾米莉·狄金森的准则:“说出一切真理但不要太直白。”王鸥行不是小狗:“他比我要好得多。他的人生有十二份草稿。王某人只有一份,还没少碰壁。”但这就是他的世界:他搜寻着各类局外人和被抛弃者,例如特雷沃(他是王鸥行在成长过程中结识的诸多男孩们的“合体”),然后把这些人放到舞台中央,“因为这就是我之所是。我来自工人阶级。你极少能见到这些人的生活被放大并被赋予尊严。”
“被书本拯救”虽是套话,却正好符合王鸥行的情况。他回忆称,自己在15岁时的一个下午进了一间图书馆。“那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瞬间就有了一种越轨(trespassing)的感觉。”他开始从书架上抽出各种佛教书籍来看,“因为我需要药,”他说,“读那些书的感觉就好比是:‘痛苦欢迎你!’你已经身居其中了,这里有一些补救办法来找到出路。’”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而他也很快就开始转向读各种其它类型的书。“酷儿的想象力来自逃离的需要,也来自谋求安全的需要,”他说道。

如今,他仍然在经典的海洋里遨游,捡拾和挑选着任何便于他推陈出新的要素。“凭什么不能物尽其用呢?”他问道,“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以自由地回到垃圾场里并宣布:‘白人已经把这些工具用完,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我来说就也是垃圾,我要重新把它们利用起来。’”他对欧内斯特·海明威与雷蒙德·卡佛提出的极简主义、男性气概美学抱有怀疑,更偏爱浪漫主义者的宏大理念以及无拘无束的抒情。“对我来说,这就好比一场文学上的变装表演。我回到了19世纪,捡起从句,以认真而略显夸张的方式加以重复利用。读者可能想不到,《大白鲨》也是《此生》的参照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雄心及其对散文式迂回曲折的喜爱吸引了王鸥行。“我觉得这就很有酷儿的气质。没有什么主题是写不得的。”
与玛丽莲·罗宾逊相似,王鸥行并不忌惮道德严肃性(“认真”这个形容词在访谈里多次出现)。这种真诚也许是年轻受众青睐他的原因之一。“年轻人希望听直接的话。他们希望彼此能直截了当地交流,”他如此评论新近的诗歌复兴,“当我们集体陷入麻烦时,我们要的并不是背景和情节。最有意义的诗就是不加修饰的诗。它直达内心并触及到我们的共同感受。我觉得年轻人尤其讨厌背景和框架之类的东西。”
他没有时间来表现业已成为当代美国小说代名词的反讽或悲观主义。他也不和其他作家一起出去活动,因为这难免会导致流言蜚语“并让我的灵魂枯萎”。对他而言,这种“布鲁克林式的恐惧”是白人男子气概的一大局限。“在变得麻木不仁之前你只能一直重复‘这真是糟透了’这种话,”他说,“很多男人一直以来都在重复这些话。好吧,我们知道了。情况的确很糟糕。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身为作家的他也会反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在状态好的时候会想,“当世界把我打倒在地,也许在黑暗中啜泣一阵之后,我就会下定决心重新站起来并发问——现在要怎么办?”尽管在自己那份愤怒与悲伤之外还有更多东西可供利用,但他的创造力借这两样东西的余威才最有望得到发挥。“打个比方,在我离开地面之际——愤怒来来去去,悲伤也一样——我也会说:‘我该怎么对付它?’有时我们只需要离开一阵,去做个饭以及洗个碗就行,有时我们则会开始写作。”
写作对王鸥行来说仍像是在“偷窃时间”。他经常在夜里写东西,这个习惯是他读本科的时候在咖啡店打工期间养成的。《此生》有一部分——字面意义上讲——就是在厕所里写成的,那是当时他能找到的最安静的场所了。他的第一稿经常会用上速记法,因为要完整地写一个句子得多耗10至15秒。“如果你参照一本书的体量,把这个时间叠加起来,会发现你花在书上的时间比在电脑上写作的时间还要多出好几个小时,”他一面解释,一面拿起笔记本,里面满是干净利落的手写页。“句子写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已经能明白一些东西。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冥想过程。”长时间沉浸于他所称的“平行宇宙”之后,他也希望能“回到这个世界,看一看空气的样子”。他和彼得正计划收养孩子:“我的态度大概是,让我再写一本书先。”
他说,《时间是一位母亲》乃是他最“完整”的一本书,也是他在技艺方面最引以为傲的一本书。“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总是会有那么一丝羞耻感,而这一次就完全没有。”豆腐面朝大门蹲坐着,就像一团大棉球。“但即便人们喜爱你的书,即便你运气足够好,它在正式出版以后也至多只能接近你的预想而已。”王鸥行说。“我认为这是美事一桩。做一名作家也就意味着在失败之中穿行。”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