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孙歌为自己《竹内好的悖论》修订本所写序言。竹内好是新世纪前后中国思想界新的发现,其鲁迅研究等,对于中国学界启发很大,并且以此连接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的关系,可以说是继丸山真男后又一位重量级的思想者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二十年过去了,孙歌修订旧著之余,也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甚至继竹内好之后,又发现了鹤见俊辅,能以鹤见的思路补竹内好的某种“不足”。因此这篇序言,不只是修订的交待,而更像一篇孙歌本人的二十年思想历程,也有一定的学术史意涵。
《直视竹内好》
文 | 孙歌(《读书》2022年4期新刊)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开始动笔写作《竹内好的悖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不安分的文学研究者,从竹内好为我打开的这扇窗里探出头,尝试着眺望窗外陌生的风景:我看到的不仅是日本的一段历史,更是仅仅依靠文学研究的方式无法有效解释的人类精神世界。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经过社会科学的训练,要想进入这个陌生的世界,文学研究给我的感悟能力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
回想起来,促使我对竹内好产生共鸣的,并不是竹内好的著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到丸山真男关于“虚构”的讨论。当我写作了《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之后,竹内好的精神世界才向我敞开了大门。《竹内好的悖论》初版呈现了我这个时期思考的主要关注点,我当时将其表述为“文学的位置”。不言而喻,只有在大于文学的视野中,文学才谈得上找到“位置”。这个为文学定位的问题意识本身,让我一只脚跨出了文学研究领域。

其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与狭义上的文学研究渐行渐远,并且获得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一个接一个的研究课题,把我引向更为社会科学化的领域。但是,我其实并没有离开文学。只不过我没有再去讨论文学的定位问题,而是把文学领域给我的营养转变成为一种眼光,借以捕捉思想史研究中被理性过滤掉的那些纠缠不清的节点问题。说到底,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可以用逻辑解释,却无法仅仅依靠逻辑接近,更无法用逻辑解决。
让我了解这一点的是竹内好。他虽然被当代的学科习惯归类为中国文学评论家,但是他视野里的中国文学却不是狭义上的“文学创作”。竹内好的文学,相当于丸山真男的政治学。他处理的问题,与丸山真男以及同时代其他思想人物面对的问题形成了深层次的互补关系。
最初尝试勾勒竹内好的精神世界时,有两个离文学最远的问题超出了我的解释能力。一个是竹内好对于日本亚洲主义的整理与分析,涉及如何对待亚洲主义后来转变成为侵略意识形态等棘手的问题;另一个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涉及如何理解历史进程中中国革命特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牵涉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基本功,当时的我苦于分析工具的阙如,不敢贸然动笔。《竹内好的悖论》出版之后,我在研究其他课题的同时不断推进研究准备工作,先后在若干学术场合进行了相关讲座,在此基础上把这部分研究写成了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获得了研究这些问题的自信。当然,客观而论,除了需要自我训练之外,我也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使学界可以在不太突兀的情况下评价这部分研究。说到底,这本书初版面世的时候,中国学界还不太了解日本战后思想的脉络,竹内好这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即使不被扣上右翼的帽子,也很难逃脱被切割成“正确”与“错误”两大部分之后再进行“三七开”解释的命运。
在这二十多年里,历史在变,人也在变。我们的学术视野不仅更具包容性和理解力,而且开始拥有了关于日本的知识。中国的日本学家们勤勤恳恳的翻译工作,使得包括战后日本思想家著述在内的大量日文著作进入了中文世界,有心人可以从中得到必要的思考线索,很多伪问题也不再会形成干扰。或许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了解和研究竹内好了。

研究竹内好这个思想家,我的基本思路在于,跳出把人物的思想轨迹分期之后研究其“转变”的通行思维定式,从思想家一生各个阶段和各种经验中寻找其内在的根本问题。这一方法论最初也来自竹内好,用他自己的表述来说,就是不去追踪研究对象什么变了,而是探讨在变化的过程中没有变的是什么。可以说,我是把竹内好研究鲁迅的方法转用于研究他本人。就竹内好研究而言,这种认识论尤其重要,因为他不是一个在意政治正确姿态的人,因此他处理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用“进步/落后”“激进/保守”这类标签加以分类的。也许可以这样说:竹内好把那些最为激进的与最为保守乃至反动的历史事物同时纳入自己的思考范畴,而他在其中追寻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进入同时代史的过程中,形成日本社会健康的政治与文化主体性。晚年竹内好在《我的回想》中说: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关注鲁迅的,因为年轻时自己也喜新厌旧、追求时髦思想潮流,所以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最初创立时,竹内好关注的是与鲁迅对立的创造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有人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时代不断变化,曾经认为是新的东西,不断地变质。”结合竹内好《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中对于进步与反动的追问,我们可以理解,竹内好是在历史中探寻那些“不会变质”的思想,他最终找到鲁迅并且激活了一度被视为“过时”的鲁迅思想,正由于他并不遵从约定俗成的“进步与落后”的想象。
写作初版书稿时,我关注的问题是从文学如何开放自身开始的。初版在相对独立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使用“文学”这个概念,它在“思想”这一范畴中注入了不那么逻辑化的知性内容。竹内好的思想论述,虽然有着明确的理路,却往往在关键环节拒绝分析。或许也可以说,竹内好的思想带有“肉身”的特征。《鲁迅》有效地呈现了这种不能被概念所穷尽的思想形式,竹内好认为鲁迅最根本的特质是一位强韧的生活者,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第二义的。鲁迅至今仍然不朽,是因为他并没有活在观念里,鲁迅穿透了观念,抵达了人生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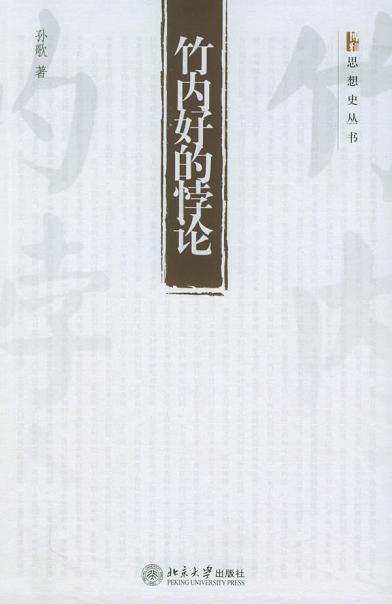
竹内好曾经慨叹过,日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没有找到共同语言,这影响了思想运动的涵盖面,削弱了思想立足于国民生活的可能性。他一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推进着这种促使社会科学与文学结合的“共同语言”的形成。竹内好的特别之处,只有走出社会科学与文学各自画地为牢的圈域才能体会,同时,这种特别之处提示了固守社会科学与文学、固守思想史学科内部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忽略的那些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含义,重新确定思想的功能。竹内好在今天仍然拥有足以复活的内在生命力,正是因为他立足于这个特别之处,他提出的“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
在重新阅读初版内容的时候,我对自己当年视野的狭窄和思想成熟度的不足感到惭愧。动手写作增订版,总觉得有很多需要改写之处,但是如果那样做,整体上就需要重新构思了。最终,在新增加了三章之外,我只把改写初版文本限制在最低限度,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章节,除了纠正若干处不准确的记述之外,只是增加了少量内容,并对部分原有文字的上下文位置进行了调整。但有一个重要的修改需要对读者交代,即我对鹤见俊辅的评价。

在初版中,我对鹤见的评价是不准确的。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难以定位。他与竹内好共同参与的讨论,他对竹内好的评价,都让我有一种隔雾看花之感。在初版中,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位执着于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为什么把“转向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课题,对我来说成为一个谜。直到近年,我的阅读逐渐深入到更多的战后思想脉络之后,才开始领悟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对于鹤见以自己的身心加以实践的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我缺少准确的把握,对于这位拒绝单纯的观念演绎却有着深厚理论背景的“身体力行的哲学家”,我缺少身体力行的理解方式。随着对鹤见阅读的深入,这位与竹内好相通却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在我心里逐渐鲜活起来,我开始意识到,他代表了与竹内好并不总是相交的另一种思考路径,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与竹内好产生了高度的共鸣。最大的共鸣,是他对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解释。
写作初版的时候,我仅仅参照了鹤见《竹内好》中关于这个《决意》的一章,就断定他对于竹内好的这个“错误”是以“转向”以及转向者战后的反省为基本视角进行判断的,这个解读简化了鹤见的想法。在《竹内好》中关于竹内好在上海凭吊鲁迅之墓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话:“祭扫鲁迅墓的竹内好,正是在前一年已经把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宣言发表在《中国文学》上的竹内好。这个人果断地选择了一条路。但是,他不是那种忘记当时由于决断而舍掉之物的人。他不是那种自己一旦抉择了并公开发表了这个抉择,其后就固执于一个不变的判断,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他并不假装自己的预言是没有错误的。这使他成为无可替代的思想家。”鹤见这里所说的“由于决断而舍掉之物”,显然是指竹内好宣言中放弃了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华战争的“道义的反省”。在发表这个宣言一个多月之后,竹内好在上海拜谒了鲁迅的陵墓,发现鲁迅墓碑上的塑像被严重毁坏,这个情景给他造成很大的刺激。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鲁迅即使死去也会遭受侮辱。竹内好无言地在鲁迅墓前低下头。鹤见言简意赅地说:“在日本占领之下墓碑被毁的鲁迅。墓碑的样子,在竹内出征前写下的他最初的著作《鲁迅》中投下了影子。”

当年,我并没有读出这段话里的微言大义。事实上,虽然鹤见认为竹内好发表这篇宣言确实是一个错误,但他并非是在指责竹内好犯了错误;相反,他看到了鲁迅墓前的竹内好拾起曾经因为决断而舍掉的“道义的反省”,因而强调竹内好并没有坚守和美化他犯的这个错误。鹤见并非是在通常的政治正确意义上对这个宣言进行裁断,他是在实用主义的“错误主义”意义上指出了这个错误的;鹤见本人一向主张,人需要通过“试错”才能把握现实,犯错误是人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这是他从早年在哈佛所受到的实用主义哲学训练中汲取的精神营养。而最集中地表达了他这个对待错误的特别方式的,是他写于一九五七年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
同时,鹤见强调发表了支持大东亚战争宣言的竹内好却拒绝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认为处在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竹内好,其立场是“很难自圆其说”的。这个分析,暗示了鹤见俊辅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逻辑实证主义要求在单纯的经验事实中求证,鹤见不可能无视竹内好的一系列实践性的事实而仅仅关注他的某一个主观言说。从尽可能客观地确认事实出发,鹤见必须找到足以解释竹内好各种看似矛盾的实践中潜藏的内在逻辑,这种努力最终引导他把发表支持日本国家的《宣言》、拒绝参加以日本国家之名举办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写作《鲁迅》等前后相继发生在两年内的事件,在语言符号的序列中重新加以审视,终于确认了竹内好前后一贯的思维逻辑,即作为国民参与到时局中去的意志;这个意志即使以“与日本国同体”表述,也不意味着在直观意义上认同日本政府。同样的意志,促使竹内好在战后写作了《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并引导国民文学论争,重新讨论“近代的超克”,推动反对安保的运动,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鹤见说:“在这些活动的深处,《宣言》一直鲜活地起着作用。”当然,《宣言》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个错误的意义却改变了。鹤见承认,终生不曾撤回自己这个《宣言》的竹内好,把它转变为战后从事思想建设的动能。

鹤见之所以称竹内好为“无可替代的思想家”,正是因为他从这样的哲学背景出发解释了竹内好的失误,并把竹内好对待自己失误的坦然态度而不是进行了多少正确的预测视为其作为思想家的标志。一九八三年,在写作竹内好的传记之前,鹤见发表《战争期间思想再考——以竹内好为线索》,集中讨论了如何从过失中学习的问题。鹤见尖锐地指出,那种在历史中寻找正确人物与正确思想的举动,只不过是大学或者传媒里训练优等生的“电脑规则”而已。输入电脑程序的正确与错误是确定不移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原则而已,它有意义有价值,却无助于分析复杂多变的现实。鹤见作为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尤其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哈佛大学经历了末期罗斯福新政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对竹内好无保留地支持太平洋战争的态度心存抵触,却仍然准确地分析了竹内好执笔的《宣言》究竟错在何处:他指出,竹内好在一九四一年底以政治浪漫主义的态度预测日本将通过太平洋战争彻底变革自身,从而承担起解放亚洲的重任。这个预测完全落空了,竹内好错了。按照电脑程序规则,错了的就是错了。但是,鹤见追问:错了的真的就只是错了吗?与此相对,太平洋战争时期鹤见用英语prognostic documents(预后[悲观],立此存照)隐晦地写下自己对这场战争的预测,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鹤见追问:正确的预测就是对的吗?在这样的追问中,鹤见确立了自己战后的思想课题。
当然,鹤见俊辅与竹内好在思想走向上仍然是不一致的。竹内好虽然坦承自己的一些时局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反思有多大意义,不曾把对于失误的反省作为自己的思想动力;鹤见俊辅则坚信对错误的反省才能激发更有活力的思想。年轻时受到的实用主义哲学训练,让鹤见把“犯错误”作为无法穷尽终极真理的人类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他把错误作为思想行为必然带来的伴生形式,并试图以试错的方式接近真理。竹内好的思想支点与鹤见并不相同,他们的一致性只在于拒绝固守自己的错误,同时也拒绝居高临下的政治正确姿态,但他们各自对于“错误”的内涵及其“思想功能”却想法不同。竹内好并没有把“犯错误”与“接近真理”结合起来作为必要的思想通路对待,因此他并不强调反省错误这一行为的思想含义。有趣的是,这种不一致并没有形成二人的思想分歧,他们成为日本战后思想史中的亲密伙伴。或许在安保运动高潮中辞职的竹内好获知鹤见俊辅也辞职的消息之后拍给后者的电报最能表述他们的关系:“走自己的路,携手共进,再分头前行。”
由于本书并非鹤见俊辅研究,这些改写都控制在最小限度。二〇一〇年岩波书店出版鹤见的《竹内好:一种方法的传记》时,我应邀为该书撰写“解说”,在解说中,我已经对自己在《竹内好的悖论》中过于肤浅地理解鹤见的“错误主义”进行了自省。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研读鹤见的实用主义哲学背景,所以没有把握住鹤见在思想错误问题上这种独特态度的真正支点。对鹤见的理解是慢慢进展的,至今我仍然还在这个艰苦的进展过程中。

不过,这个过程让我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通过对于鹤见的重新理解,我得以找到另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人物所谓“局限性”的维度。在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历史人物当时所做的抉择在事后被证明不正确时,善意的说法就是“历史局限性”;相比于居高临下的批判,“局限说”要温和得多。然而它却与粗暴的批判一样,几乎不具备有效的解释力。鹤见给出了另一个讨论历史人物过失的维度,这就是讨论者要把历史人物的过失视为自己也可能犯的错误。只有在这个维度上,讨论者才有可能深入地剖析对方过失的内在机制,也才能提供可供后人借鉴的教训。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如何才能不犯同样的错误”就不再是论述的目标,换言之,局限性与错误都不是论述的重点,重点是借助于前人的摸索与摇摆,深入历史过程最深处的腠理,谨慎地理解历史过程中无法用“电脑规则”裁断的要素。毕竟,理解历史是为了更有效地介入同时代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不把抽象的“正确原则”作为思考的前提,同时拒绝虚无和投机的诱惑,在流动的状况中以富于弹性的方式坚持原则——当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态度理解世界的时候,才可以说自己是成熟的。
回想起来,《竹内好的悖论》初版的序言写于二〇〇三年春天,是在北京抵抗“非典”的战役中完成的。那是一场仅仅持续了数月的有限区域的疫情,它让我意识到了在似是而非的状况中培养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增订版完成于新冠在全球大流行之际,人类至今还没有从这场大规模疫情中免疫。这场疫情提供了一个更加沉重的契机,促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认知历史的艰难。我们有什么样的明天,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和传承过去。直视竹内好,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思考未来,为了创造每时每刻都在成为“过去”的现在。
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读书》新刊 孙歌:直视竹内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