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林子人
我们的理性失落了吗?哲学家陈嘉映在新书《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人类理性的工具化发展招致了“理知时代的终结”。他写道:“理知走得越远,感知的切身性或丰富性就越稀薄,乃至最后完全失去感性内容,变成了纯粹理知、无感的理知。”陈嘉映对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抱以忧思,并提出当理知脱离了感知,当“智能”取代了“智人”,当“数理”取代了“道理”,当理性沦为了赤裸裸的工具理性时,理知时代便迎来了终结。

陈嘉映 著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1
与理知时代的落幕相伴而来的,是“智人”(或曰哲人)的落寞与当代“智识结构”的转变。2017年,在第二季的《十三邀》中,许知远与马东曾就“我们是否处于文化的粗鄙阶段”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探讨,引发公众关注与持续热议:当代的知识话语果真衰落了吗?以智识为核心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了吗?这些设问的背后是知识分子的“杞人忧天”与怀旧情绪,还是当前时代的真实处境?日前,在由“理想国”发起的以“文化-智识结构的当代转变”为主题的直播对谈中,陈嘉映与学者刘擎再度触及这些悬而未决的当代议题,并围绕“智识”于时代变革中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追问与探析。
文字时代:“智识人”与“文人共和国”
在谈论当代“智识结构”的转变之前,陈嘉映首先细化了他的论述对象,并提出了“智识人”这一概念,以强调它与传统“哲学家”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等意涵的区别。“智识人”是自中世纪以来,近代民族语言形成之后,随着文字阅读的普及而崛起的智者群体,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等追慕古典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法国启蒙时期以伏尔泰、卢梭等思想者为代表的哲人(philosophe),英国的休谟、德国的莱布尼茨等跨学科文人(man of letters),以及当代“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思考者与知识人(intellectuals)。“智识人”最本质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是“思想者”而非“行动者”,以“话语”(discourse)而非“行为”参与社会生产。
陈嘉映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前,绝大多数人都被排除在智识话语之外。文艺复兴之后,权贵阶层没落,近代民族语言进一步生成,拉丁文的垄断性地位被打破,能够阅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总体而言,文字阅读条件的改变促成了智识结构的转变与“智识人”的形成。


在识字率与文化普及率极高的19世纪,文字作品曾经是智性结构中最核心的形式,在人人都阅读报纸的纸媒时代,写作者曾经是智识结构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陈嘉映认为,“对智识人的追慕在19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顶峰”:在当时社会开辟出的崇尚智识的文化场域中,智识人与智识人之间可以忽略种族、国别、阶级、立场的差异,赤裸而真诚地交锋,进行系统的、理性的说理与探讨,形成蔚为壮观的“文人的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man of letters)。刘擎亦赞同类似“共和国”的提法,他补充认为,在曾经的欧洲知识分子共同体中,“道德与政治立场的不同并不构成对话与交流的障碍。”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亦对二战前的欧洲文化与文人的昔日荣光加以追思与缅怀,依照刘擎的说法,中国在80年代也曾赢来过与之类似的文人荣光和“文人共同体”。
图像时代:“数字”驱逐“智识”,“话语”沦为“表达”
陈嘉映认为,以线性逻辑、结构性思维为基础的“文字”,已不再是当代智识结构中最核心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图像”的泛滥。“在以前,图像是昂贵的,而如今,图像却是最最便宜的东西,比文字便宜很多。”陈嘉映提醒大众注意,在疫情的常态化过程中,数字对人的惊人的掌控力,以及俄乌战争中短视频作为重要媒介的历史性参与,这些现象皆为“数字时代”权力的新型表征。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智识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或者说图像时代、数字时代。”在陈嘉映看来,数字时代凭借“技术门槛”将人群割裂为了两个部分:其中一半是掌握数字技术的人,以硅谷、中关村的技术精英为代表。他们通过“数字”理解世界,于他们而言,世界不是感知的,而是数字的,因而是可复制、可衡量的。另一半的人则无法通过数字理解与掌控世界,而是通过接收“图像”理解世界,而图像恰恰是与数字距离最远的一种形式。于是,在当代,掌握数字的人炮制图像,不懂数字的人接收图像,形成无法互通的技术鸿沟,唯有“商业”能够将相互隔绝的两端联系到一起。在此种态势中,技术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对世界的诠释,进而将“智识话语”从社会结构中驱逐了出去。
然而,智识话语的衰落在当代究竟意味着什么?陈嘉映在界定“智识话语”(discourse)时,将其解释为一种“系统说理”,以此区别于智性含量更低的“自我表达”。“智识话语”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能够熏染、教化大众,容纳不同意见的文化场域和对话空间。然而,知识平民化之后,公众“表达”的愿望似乎远远超过了“获知”(being informed)的愿望:人人都想要表达,这种表达的需求在陈嘉映看来,并不尽然是从人的内在自行生发的,而是很大程度上被技术塑造与引导的。数字让图像变得“更便宜”,更廉价的表达成本催生了更丰沛的表达欲。我们因而进入了昆德拉所谓的,人人都是作者却没有听众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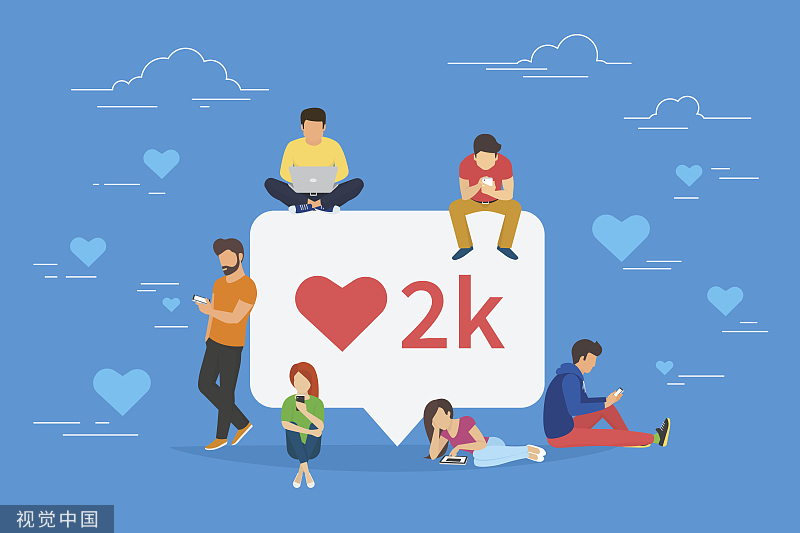
陈嘉映指出,理论上看,在智识话语的衰落之后,势必会有其他的智性力量涌入,以填充这一真空,但事实却是,智性含量更低的“表达”填充了“系统说理”的真空。陈嘉映进一步总结称,在图像时代与数字时代,“智识话语”沦为了“个人表达”:用以交换、修正、调和不同意见的“智识话语”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情绪化和政治化的“立场表达”。
“平民化”的悖谬与出路:让行动者与思想者各司其职
诚然,对知识的平民化、表达的民主化加以反思,并不是为了回归一个哲人理知专断的传统。“知识人有过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如武士、僧侣有过他们的时代,只不过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刘擎立足于不可抵挡的民主化趋势,进一步指出,“民主比明君更难”,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共生活,我们应当思索的是如何走向更好的民主,而非抱以知识分子对自身昔日荣光的怀恋与感伤。
刘擎进一步阐释了知识平民化的多面性:一方面,后中世纪“文人共和国”的兴起,与市场对大众的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大众音乐鉴赏力的提升是贝多芬备受推崇的时代基础;而另一方面,当代知识人声音渐趋微弱的态势,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民主自身演化过程中自然衰落的结果。在《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亦从大众传媒的角度阐释了知识平民化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正是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阅读文字,对文字的阅读竖立起了横亘在“成年”与“童年”之间的智识界限,导致了“深刻与浅薄”的文化分野;另一方面,电视市场的兴起又弥合了这种智识的界限,导致了成年世界的持续低龄化与浅薄化。基于这种由市场带来的知识平民化的悖谬性,刘擎诚挚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市场是好的、高雅的,什么样的需求是低级的、粗鄙的,今天的知识人还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吗?”

而在陈嘉映看来,文化平民化的两面性需要以更多维的智识结构去解决: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成为智识人,而是让“行动者”与“思想者”各司其职。依照陈嘉映对于“智识人”的定义,智识人是不参与社会物质生产的“思想者”,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行动”,且拥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浩瀚的信息系统。因而,“要求一个行动者,一个讨生活的人,在生活之余维持高强度的思考,在表达之余还得‘好好说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说理’并非他的本职工作”。相较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当代的智识人在数量与质量上也许都并未衰落,如刘擎所言,他们只是“比例被稀释”了、“声音被淹没”了。而陈嘉映似乎更为悲观,在他看来,“淹没”与“缺席”并无二致,“被淹没只不过是另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当前,让思想者与行动者能够各司其职的多维对话空间尚未被重建起来。
重建“知识话语”:放弃对“政治正确”的极端追求
在追溯当前大众与精英关系紧张化的原因时,刘擎声称“智识的边缘化一定程度上是知识人的‘内战’造成的”。他援引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后现代理论作为例证:在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中,德里达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极大程度上摧毁了语言的权威地位,并向大众阐明了语言说理系统自身的危险与欺骗性。而福柯对“知识话语”中所蕴含的权力结构的反思与披露,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于“话语”本身的不信任。在60、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论战中,同样有知识人站在了反精英的大众立场上,认为“贝多芬的音乐和街头巷尾的口哨并无区别”。刘擎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对知识共同体的破坏有时也是知识人自我招致的”。
然而,在福柯原语境的论述中,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实则要复杂得多,陈嘉映指出,“话语和权力的视角,虽然能帮助我们看到某种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话语就全然依靠权力,它所创造的就只有权力。”陈嘉映指出,这些武断的判断皆是政治立场的表达,而非政治立场的交流。
在美国当前的公共生活中,此类非此即彼的“立场表达”则更为普遍,“不管什么样的表达最后都会演变成‘yes or no’的立场站队。”卡尔·斯密特曾声称,“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我”,然而陈嘉映认为,“施密特的确是处理危机时刻的专家,但我们并不总是处于一个必须区分敌我的危机时刻。”陈嘉映坦言,自己对于当前舆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的“政治正确”倾向并不认同,亦对当前“表达”的高度政治化与高度紧张倍感忧虑:“彷佛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当下”,然而,“过度的政治化将使政治失去其原初的意义。”
在对谈的尾声,陈嘉映试图从古希腊先贤埃斯库罗斯的早期剧作中探寻出路,并提出,我们应当从雅典城邦的民主进程中汲取经验,尝试从一个追求“原始正义”的时代,进入“摆脱原始正义”的时期,从而成为一个“话语的城邦”。陈嘉映认为,在非此即彼的立场之外,还应当留有一些中立的空间,让智识的“话语”于松弛之中重新生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