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马克斯·佩雷尔曼的美国大学生在距离北京2400多公里的四川省旅行。在这个中国西南部省份的冬季,他遇到了一群前往西藏省会拉萨的藏族游客。他们拥抱了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分享他们背包里的食物,也许一起围坐在篝火边,或者是同住在一家青年旅社。这些藏族人从未远离过他们的村庄,也没有见过像佩雷尔曼的相机这样的新奇科技。然而,聊着聊着,一位藏族人问佩雷尔曼:迈克尔·乔丹怎么样了?
这些来自中国农村的藏族旅行者不仅了解美国体育联盟,而且还关注其中的一个明星和他的球队——“红牛队”,在亚洲被称为芝加哥公牛队,这揭示了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在关注美国。外国人像关注自己国家的新闻一样关注美国的新闻故事,听美国流行音乐,观看大量的美国电视和电影(2016年,仅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就占了全球票房的一半以上)。有时,对美国文化的关注是以牺牲外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为代价的。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加拿大人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往往多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美国人也只愿意关注自己的国家。例如,在美国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500部电影名单中,没有一部外国电影(《卧虎藏龙》排在第505位,略高于杰瑞·宋飞不太经典的《蜜蜂总动员》,但比《百货战警》低100位左右)。另一个衡量狭隘主义的指标是拥有护照的美国人的比例,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与66%的加拿大人和76%的英国人相比,只有大约40%的美国人有护照,因此可以出国旅行。
美国人的狭隘可能会变成美国人的无知。长期以来,这种状况让美国的地理老师感到沮丧,也让深夜脱口秀主持人感到高兴。在YouTube的大量视频片段中,比如吉米·坎摩尔的《你能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吗?》中,洛杉矶的几个路人在世界地图上连一个国家都认不出来。但这种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不熟悉,对美国和世界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做出了灾难性的假设——例如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混为一谈——然后发动了战争。
这是怎么发生的?20世纪的文化全球化是如何沿着这样一条单行道前进的?为什么美国——这个拥有700多个海外基地的全球巨头——会如此奇怪孤立?答案在山姆·莱博维奇的新书《正义的烟幕:战后美国和文化全球化的政治》(A Righteous Smokescreen: Postwar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中,他指出,这主要归因为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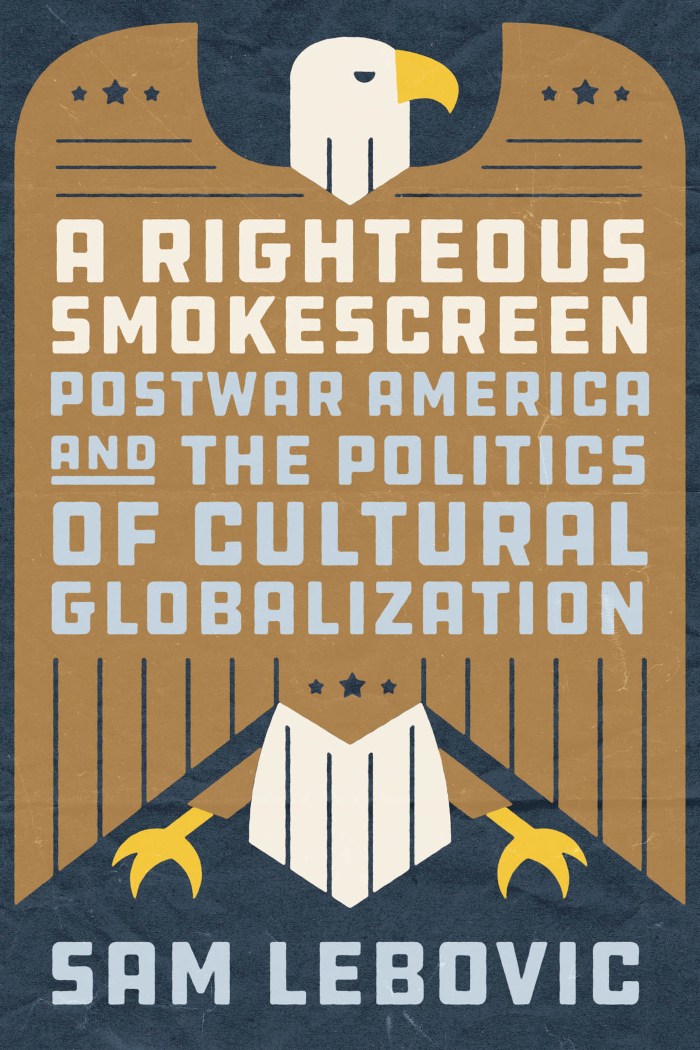
美国从其作为主要超级大国的新位置上俯瞰二战的地球残骸,承诺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相互依存、自由的国际秩序,一个自由的世界。为此,它将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和分支机构)拼凑成一个新颖的体系,将各国捆绑在一起,防止未来的冲突。世界将变成一个地球村。

信息和文化的自由流动是地球村的基本原则之一。人们想象,村民们将自由地旅行、贸易和相互交流,培养国际理解并建立互利的纽带。这个短语——通常被缩写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在20世纪40年代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报业巨头对此表示支持。国会通过了支持它的法律。外交官们也成了它的传教士。1946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必须齐心协力,打破世界各国之间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如果战后的美国政治中存在一种自由主义的共识,”莱博维奇平静地断言,“可能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
世界上很多人都同意——谁不是自由的拥趸呢?——至少原则上是这样。菲律宾传奇外交官兼记者卡洛斯·罗慕洛曾揭露日本在菲律宾的暴行,他甚至称信息自由是“联合国所信奉的所有自由的试金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规模和严重程度上都令人震惊,信息障碍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日本和德国寻求经济独立的努力,使本国公民与全球潮流绝缘,孕育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而且,从美国决策者的角度来看,把世界推入了战争。
但是,当约600名记者、媒体巨头和外交官于1948年抵达日内瓦,为《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起草新闻自由条款时,定义上的困难比比皆是。美国对“信息自由”的理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对美国代表来说,这个问题属于道德原则的更高层面。代表团希望将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概念扩展到国际领域,禁止政府审查新闻,并将记者获得消息的来源和跨国界传播新闻的权利置于神圣地位。但其他国家的代表则更关心现实问题。二战使地球上的通信基础设施向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消耗了世界新闻纸张供应量的63%。更确切地说,美国一天消耗的新闻纸张相当于印度一年的消耗量。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材料短缺会阻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报纸生产(尽管这确实提供了政治干预新闻界的附带好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8年大选前向意大利反共产主义报纸提供新闻纸张,而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削减了当地共产主义报纸的新闻纸张分配)。战争也摧毁了外国新闻机构——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和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已经彻底消失——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家国际新闻通讯社。与此同时,美国的美联社和国际联合通讯社都有全球扩张的计划,这使得《经济学人》讽刺地指出,美联社的执行董事“在发现他的自由理念与他的商业优势相吻合时,散发着一种奇怪的道德光芒”。
回到日内瓦,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指出了这些巨大的不平等现象。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巴雷维呼吁较富裕的国家公平分配“用于在所有国家之间传播信息的物质设施和技术设备的供应”。但美国代表否认全球不平等本身就是信息跨国界流动的障碍。此外,他们认为,再分配措施侵犯了新闻的神圣性。美国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强硬地提出其新闻自由的概念——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消费者跨国界接收信息的权利的结合,但联合国在定义和确保信息自由方面的努力却陷入了僵局。
资源重新分配的失败,在产生更均衡的国际信息流方面缺乏多边投资,以及战争结束时美国文化产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保证了信息和文化的全球传播中美国的权利。
美国新闻机构、好莱坞制片厂和摇滚乐在战后的扩张印证了这一点。例如,美联社出售新闻的国家数量从1944年的38个跃升到1952年的70个,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能从美国人的角度了解世界大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和电影业共同努力,取消了其他国家对外国电影的配额壁垒,此举巩固了好莱坞已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需求方面,外国人发现好莱坞的魅力和浮华很诱人,因为美国电影与战后重建的朴素、被炸毁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1949年,美国电影约占欧洲和亚洲市场的一半,非洲市场的62%,南美市场的64%,以及中美洲和太平洋市场75%。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迷恋美国文化。

关于美国如何主宰全球文化的故事——法国人称之为“可口可乐殖民”——以前就有人讲过。《正义的烟幕》的关注点更为广泛。这本书对全球化的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当美国以惊人的数量出口其文化时,它进口的文化却很少。换句话说,就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时候,它却出人意料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隔绝。一个地方性的帝国,但具有全球影响力。
莱博维奇通过关注他所谓的“世界秩序的静态化”,对“互惠”的崇高修辞——尤其是含糊不清的“信息的自由流动”——进行了批判。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签证管制、民用航空条约和教育交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奠定和限制信息和文化的跨国传播的过程。尽管莱博维奇声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是更多看似宏大的地缘政治问题,这有点夸张——想想丹尼尔·伊默瓦尔为螺纹标准的国际斗争作出的付出,或者阿里萨·吴关于冷战早期国际收养起源的研究。莱博维奇的方法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战后美国及其帮助构建的世界秩序的限制。他表明,遏制并不仅仅是一种旨在遏制苏联向欧洲和亚洲扩张的领土战略。相反,它始于美国边境,涉及对可能对美国现状不利的人员和思想流动进行监管(这种形式的遏制不仅包括前苏联的共产主义,还包括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用丘吉尔关于前苏联在东欧的政策的著名演讲来形容,美国周围已经出现了一道铁幕。
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阻止“宣传鼓动”的努力中,可以看到这种美国国内的冷战帷幕。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必须寻求政府批准才能从中国、朝鲜、柬埔寨、古巴和越南购买杂志、书籍甚至邮票。20世纪50年代,美国邮局和司法部的官员在邮件中搜寻是否有共产主义的宣传品。数不清的包裹从未到达美国的目的地——因为在该计划实施的数年中,政府不需要通知收件人,就可以销毁他们的邮件。但是,确定什么是宣传,什么不是宣传,是一种不太科学的程序,尤其是因为官员们并不总是精通外语(一名官员用一本俄英词典来判断邮件内容)。例如,一个研究生从来没有收到卡尔·马克思书信的德语版本,但一名英国国会议员撰写的一本关于1954年美国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的小册子,也没有通过边境。这种形式的审查制度将美国人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隔绝,甚至与本国的海外政策隔绝。
但即使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美国文化也有内化的倾向,大多数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莱博维奇写道,媒体生态系统尤其构成了一个“美国主义者回音室”。美国影院很少放映外国电影(这主要是由于电影业在1934年开始实施《电影制作法》,而且当局拘谨地反对欧洲电影中的性观念)。同时,很少有电视节目来自国外(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比例约为1%——相比之下,英国为12%,危地马拉为84%)。很少有报纸订阅外国通讯社的通讯社的内容,有外国记者的就更少了。此外,这些报纸中很少有专门报道外交事务的版面。这的确是个回音室。

由于旅行管制,与外国人的面对面接触也受到限制。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种族配额移民制度——尽管大量借鉴了早期将中国移民排除在外的立法——使得非洲人、亚洲人和许多欧洲人几乎不可能移民到美国,使此时的移民水平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从而切断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联系。1910年,近15%的美国人口在海外出生,但到196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5.4%。同样,在这个国家安全方兴未稳的国家里,官僚们阻止各种激进分子进出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从德国间谍、破坏分子到黑人国际主义者——发现通往美国的大门被锁上了。同样,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持有所谓“外来”信仰的美国人也被禁止离开。边境是一个双向的意识形态过滤工具。
冷战的开始加强了此类执法力度,两位艺术家试图通过边境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1957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巴勃罗·毕加索75岁生日举办了一场回顾展,而毕加索在50多岁时转向了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莫斯科举办了一场展览,纪念另一位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的75岁生日,这位美国画家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他的作品歌颂了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两个展览,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前苏联:但由于美国的边境政策,这两位艺术家都不能参加自己的展览。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就以意识形态为由拒绝向毕加索发放签证,并拒绝向肯特发放护照,理由是他据称同情共产主义。
知名度高的人物并不是唯一进出美国遇到困难的人(当然,确实有很多著名人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查理·卓别林、巴勃罗·聂鲁达、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莱纳斯·鲍林、保罗·罗伯逊、W.E.B·杜波伊斯,仅举几例)。所谓的“区域限制”禁止所有美国人前往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的更精确的数据是相当难以获取的——被拒绝签发护照,还有许多人由于担心背景调查会发现什么而从未想过要申请护照。另一方面,潜在的移民和游客被成群结队地拒之门外(在战后早期,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科学家中约有一半遇到了签证困难)。
美国国务院对边境的限制,加上美国媒体的地方主义和联邦政府消除外国宣传的努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减少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信息和文化的流动,当时威廉·沃西就已经机敏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打击“华盛顿的宣传工厂”,这位黑人记者在古巴和朝鲜——美国人被禁止访问这些国家——进行实地报道。作为回应,他的护照从1957年到1968年被吊销。菲尔·奥克斯的《威廉·沃西之歌》的歌词记录了这段经历:“不知为何,听到国务院说,‘你生活在自由世界,你必须留在自由世界,’这很奇怪。”沃西明白“旅行控制就是思想控制”。

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在怀念战后的那段时光。保守派叫嚣着要实现20世纪50年代的白板栅栏和草坪的郊区梦想——同质性、一致性,以及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宣扬的种族和社会等级。“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喊道。但自由派人士也渴望战后的美国,特别是它的外交关系。如今,自由国际秩序的捍卫者渴望回顾美国在结束战争和组织和平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他们列举美国走向全球治理的多边行动和横跨地球大部分地区的军事联盟——从北大西洋到东南亚——以及向朋友和前敌人延伸的经济生命线,帮助这个饱受战争困扰的世界恢复了元气。简单地说,正如路易斯·曼南德在他的新书《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的第一页指出的,那是一个“美国积极参与世界其他地区事务”的时代。
但美国到底有多“积极参与”呢?在曼南德对冷战早期文化的探索中,答案是非常积极。曼南德指出,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娱乐的贪婪消费,以及美国人如何“欢迎和适应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思想和娱乐”就是证据:杰克逊·波洛克把欧洲画家和墨西哥壁画家作为影响来源;新好莱坞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的风格;披头士乐队征服了美国。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外国文化都被控制了。
然而,在莱博维奇的叙述中,这条传播途径极为狭窄。许多外国引进的内容已经彻底美国化了。例如,披头士乐队就是在欧洲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的阴影下开始演奏美国摇滚乐的。虽然许多美国人试图体验外国文化,但没有其他美国人作为中介,他们很少能有这种体验。他们成群结队地去看以遥远的地方为背景、但由美国人创作和主演的音乐剧。他们还聚集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各地涌现的无数个提基酒吧里,享受着拙劣模仿的波利尼西亚美学(加勒比朗姆酒是鸡尾酒的主要原料,中餐是常见的菜品。“真正的波利尼西亚食物,”第一批提基酒吧的老板之一宣称,“是我吃过的最可怕的垃圾。”)
流入美国的外国文化和思想极为有限,于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成为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无论是黑豹组织在阿尔及尔建立外交使团,还是新左派活动家将《毛主席语录》放进口袋。甚至他们试图支持的人被异域化,也可以归功于难以从国外获得信息。莱博维奇写道,美国的左派也受到了“主要以输出美国文化为目的的国际交流体系”的限制。
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50年代了。民权运动的努力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消除了许多上世纪中叶阻碍外来文化流动的障碍。种族配额移民制度最终在1965年崩溃,美国边境向世界各地的外国公民开放,美国的人口结构得到了重组:2018年,美国有4400万移民。技术也起到了帮助作用。飞机旅行使出国变得更容易,而手机和互联网——用硅谷的陈词滥调来说——将世界带到美国人的指尖。
但这一转变并没有完全重新平衡文化和信息流动。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并继续以意识形态为由排斥外国人。美国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停止其重商主义的追求。而且,Web 2.0已经将世界上的许多在线活动集中到少数几家美国公司的平台上。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可能会消失,但我们依然不清楚美国人是否会作出改变。
(翻译:李思璟)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