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在达美航空1580航班自犹他州飞往俄勒冈州期间,迈克尔·德马尔(Michael Demarre)忽然向客机的紧急出口走去。一份联邦事件报告称,他取下了门上的塑料覆盖物,继而猛拉把手,几乎快要把舱门打开。附近的一名乘务员意识到了这一行为的性质并拦下了他。在余下的飞行时间里,其他乘客一直紧盯着他,唯恐他又离开座位。飞机落地后,调查人员问了他一个浅显直白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对一名特工表示事关新冠疫苗。德马尔称,他的目标是制造事端,促使人们把聚光灯移到他的身上。他希望借助他们的荧屏来把自己的感受公之于众。
“我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德马尔解释称,这是一个经典的美式桥段。德马尔冒险行为的阴暗讽刺之处——他的律师尚未就该事件发表评论——就在于他真的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关注度。我(指本文作者Megan Garber)明白,我现在的讨论相当于又给他带了一波流量。但我提及他的原因在于,他的吸睛之举构成了一项有用的推论。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微型文学体裁,此类作品认为,美国人当前面临的诸多紧急状况中也包括广泛的注意力危机。这些书的焦点和口吻各有不同,但其底层的论证套路在内核上都是一样的:作为民主的基本原子,注意力将左右我们的命运。
德马尔的出格行为对这些书的论证形成了支持,重点不一定在于该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威胁,而在于它冷酷地警告美国人,任何人在注意力战争中都可能沦为叛乱分子。美国人在谈论注意力时,倾向于诉诸控制的眼光——即认为它是某种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予或收回的东西。关注乃是我们最显见、最切身的“本钱”。但旧的语言难以刻画新的现实——注意力经济可能意味着在一处人头攒动的集市里做公平买卖,人们兼任生活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些书却认为,这种经济事实上让我们变得极为脆弱。我们的时间与关切本来都是我们自己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一天,一个男人登上了客机,且明显怀有劫持注意力的企图。同行的乘客以及其余的大众,都不得不陪着他把这局游戏玩到底。
在我撰写此文之际(3月初),得克萨斯州开始对选择相信孩子的父母进行犯罪调查(此处指今年2月得州州长下令调查所有允许孩童进行跨性别手术的家庭)。法庭宣布金·卡戴珊再次单身。佐伊·克拉维茨(Zoë Kravitz)身着猫女主题的服装参加了《新蝙蝠侠》的首映式。1月6日委员会将以潜在的犯罪对唐纳德·特朗普提起诉讼。科林·乔斯特(Colin Jost,约翰逊丈夫)协助斯嘉丽·约翰逊测试其新推出的护肤品系列。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在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召开前与参议员会晤。一项联合国报告警告称气候变迁的灾难正在迅速蔓延,若没有激进的干预措施,它们可能会令一切缓和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死于新冠者已达到5968096人。

“我的经验就是我同意予以关注的那些东西,”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世纪末曾有这样的论述。他对心灵的观察既细致又全面,也奠定了当今美国人谈论注意力的基本框架:注意力是兴趣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它受到选择的影响。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詹姆斯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当今的新闻有如漩涡,每时每刻都在旋转,带来的信息兼具琐碎性与历史性,轻佻与庄重同在,诱人、苛刻、有趣、可怕、令人振奋、尴尬、转瞬即逝、吵闹——不胜枚举,且尺度各异,要在这一切当中做出选择的想法多少是有些荒唐了。就此而言,詹姆斯的定义固然为真,但还不充分。有关注意力的诸多文献基于这个无限滚动时代(age of infinite scroll)的现状,对他的范式进行了修正。
在新书《被盗的焦点:为什么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如何重新展开深度思考》(Stolen Focus: Why You Can't Pay Attention—And How to Think Deeply Again)里,约翰·哈里(Johann Hari)访问了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这位碰巧同名的伦理学家,他目前在牛津互联网学会(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担任研究员。

威廉斯谈了他对注意力的三重界定:“聚光灯”(spotlight)是人们最熟悉的一种形式——它短暂、针对性强,是日常任务所需的那一型(例如考虑着装、看电视剧或是读新闻网站的文章);第二层是“星光”(starlight):它聚焦于长期的愿望与目标;第三层是“日光”(daylight),这一形式——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阳光让人们可以看清自己周遭的环境——聚焦于人自身,与正念有相似之处,即你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想要的方式。
这种层级化的框架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它令人回忆起弗洛伊德提出的三联式心灵结构,或瑜伽练习中的bahya drishti与antara dtishti之分,前者聚焦外部而后者将眼光转向内心。星光作为一件实用的东西,看起来可能有点像子弹日记(一种快速记录的方法)或者愿景板。但当未来的梦想被具体地理解为专注与分心时,它也就有了全新的清晰性。网络的诱惑也是如此。许多时候,我都发现自己会无意识地点击某个吸引眼球的标题,接着阅读里面的内容,继而后悔不已。我集中精神,我当即想要申请退款。星光也许能让我在浏览的时候更加有的放矢。我是否愿意匀出一部分随性而宝贵的生活来考虑糖果的包装选择?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至少我可以有意识地做出这个决定。威廉斯的框架强调了现在与稍后之间的深刻联系:短期的分心会造成长期性的影响。如果你始终找不到星光,那星光也就不能帮你定向。
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在2019年的《如何无所事事》里提出了类似的重新校准方向的主张。美国文化与詹姆斯式的注意力模型已拉开了相当远的距离——早已不再是独尊选择,以至于我们所用的词汇本身就可能有误导性。奥德尔提出,注意力已经与那些将业余爱好重塑为“生产性休闲活动”(productive leisure)的同一批机构绑在了一起,其重视私人时间的理由,不过是它到头来有经济上的价值。核心问题不仅在于互联网,相反,她故事里的罪恶源头“乃是商业性社交媒体的侵略性逻辑及其企图将我们困在一种有利可图的焦虑、妒忌与分心状态当中的财务动机”。

珍妮·奥德尔 著 洪世民 译
类似地,奥德尔并不反对一般而论的分心这一范畴。兼有艺术家与作家身份的她在新书中费了许多笔墨,对神游(wandering minds)的价值大加推崇。那说到底是创造力与好奇心之源。但允许自己有分心的可能与被迫分心也显然不是一回事。在奥德尔的分析中,无所事事并不意味着毫无行动,它是一种矫正的行动。它试图让原本自由的时间重获自由,难点在于如何用心地神游。
《如何无所事事》的论证呼应了网上的一些较新的提法:标题党(clickbait)、阴暗刷屏(doomscrolling,指将过多的屏幕时间用于吸收负面新闻的行为)及一些类似的术语,都承认注意力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如吴修铭(Tim Wu)在《注意力经济》当中所指出的,注意力确实是我们的,但也是他们的——是一种试图让我们的心灵物尽其用的大企业竞相争夺的商品。吴修铭的批判对象是Facebook、谷歌以及其它许多将人类化约为一群“眼球”并将心灵视为一种可开发资源的企业。他以反面乌托邦的口吻指出,数字领域的企业家们纷纷参与了他所称的“注意力收割”——攫取人们的时间与关切来谋取利润。
吴修铭推出《注意力经济》是在2016年(指英文原版)。与此同时,它也赢得了一本书所能期望的最佳奖赏:自那时以来,它变得更切中时弊了。和奥德尔一样,吴修铭的终极主题是抵抗。他提到,分心往往有利于增强企业家的力量并削弱所有其他人。如果人们不想看他们的脸色来生活,就此他写道,“我们就必须首先承认注意力的珍贵,不要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廉价地或不假思索地放弃它。其次,我们还必须采取个人或集体的行动,让我们的注意力再次成为我们自己的,从而重夺生活体验的所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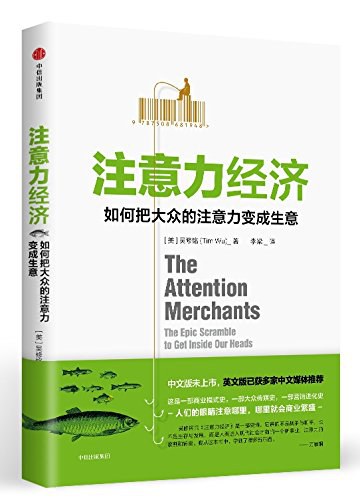
[美]吴修铭 著 李梁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4
有关注意力的讨论迟早会趋向于白热化:我们正以此种方式消磨时光,而我们本该以另一种方式来度过。这样做是轻浮的;那样做就充满了意义。不过,这些书里的有益元素之一,就是它们将最终的定义权还给了个人。虽然它们在表述上要复杂一些,但仍旧响应了詹姆斯的注意力理论。吴修铭的诉求是还一个人自己的时间以尊严;奥德尔则反复使用“人道的”(humane)这个词。你有你的星光,我也有我的。二者是不同的,二者也理应不同。
然而,在这些框架当中,注意力也有政治性。总的来看,注意力是一种集体性的善,分心的民主也就是危在旦夕的民主。前述的作者对集体之我们(the collective we)的运用,都遵循自由派路线,选择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粗暴地把共同性强加给一个业已碎片化的世界,而在于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在这个大家共享的政治体以及星球上,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星光尽管是个人化的,但也可以是社会的。从公共的角度考虑,一种共同命运感也许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些古往今来都不失其紧迫性的问题上:我们想生活在哪种国家?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里,拜登总统呼吁国会对那些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服役期间曾接触过有毒物质的军人伸出援手。拜登的儿子博就是一名老兵,2015年因癌症去世。当拜登谈及疾病将使士兵躺进“由国旗覆盖的棺材”,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伦·波伯特(Lauren Boebert)终于坐不住了。
“是你把他们送进去的。整整十三个人!”她怒吼道,这里似乎指的是去年在阿富汗死去的士兵。
那一晚拜登被打断了不止一次。波伯特与佐治亚州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总统演说期间多次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在幕僚团队进入会场时,两人有意背对他们,以展示波伯特披肩上的口号:“钻,宝贝,再钻一钻(Drill Baby Drill,2008年由共和党籍的马里兰州副州长迈克尔·斯蒂勒提出,主张以加强钻探来应对能源危机——译注)在拜登谈到移民时,她们又开始呛声:“建——墙(Build-the-wall)。”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两人在剩下的演说时间里不是报以嘲笑就是在推特上直播自己如何对他人发散恶意。“这里有另一种对抗通胀的办法,”波伯特一度发推称,“辞职。”

整件事有一种“套娃”的性质:立法者之所以能升到现在这个位置,部分就源于其公开制造事端的能力,而今这两人又故伎重演。此后的一系列动向同样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南希·佩洛西谴责了她们的行为(她们应该“闭嘴”,她说),接着人们又开始写一堆描述佩洛西如何提出谴责的文章,如此这般忙活一阵,到头来又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让劳伦·波伯特和马乔里·泰勒·格林捞到了政治利益。边缘化的观点以往尚且呆在它们应该呆的地方,即被边缘化,如今那些阴谋论支持者和狭隘偏执的人有了登台亮相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自然也得跟着赔进去——原因恰在于这些人的错误可以疯狂赚取点击率。
注意力的悖论是,在任何时候,关注都很可能变得不再值当。说到底,注意力太自我中心了(navel-gazy),总有许多其它的事情——更具体、更紧迫以及显然更有价值的事——要求人们的聚焦。不过,从来就没有思考注意力的恰当时机这回事,恰好表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思考它——就在当下,而且十万火急。气候变迁迫在眉睫,人民的权利正面临威胁,说谎者仍在妖言惑众,假消息加剧了混乱……这一切和所有分散的真相一道,激烈地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干扰的量级只会增加,就像波伯特和格林的哗众取宠一样,它们威胁要淹没一切其它事物。“民主党人无关紧要,”以制造各种噪音而闻名的史蒂夫·班农在2018年时曾有此语,“真正的对手是媒体。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狗屎淹没整个地区。”
这一策略奏效了。注意力具有零和性质,这让干扰成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注意力危机的时代同时也是“纸上恐怖主义”(paper terrorism)兴起的时代,它以官僚化的文牍主义来淹没人们的视野。在这个时代,最高法院对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施加有拘束力的判决的方式,不是走标准流程,也无关一切令人生厌的审查,而是通过所谓的影子诉讼(shadow docket)。一些活动家声称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笔一挥之间就取消人们来之不易的投票权,部分原因就在于许多本来会对倒退表示震惊的人根本察觉不到这一切的发生。“坦白讲,根本就没人关注过,”一名活动家说,“连我的团队都面面相觑,‘不会这么简单就办到了吧。’”
话虽如此,当人们不加关注,事情就的确会演变成这样。研究民主及其不满者的伟大学者汉娜·阿伦特观察到,宣传就好比一股永不散去的迷雾,它可以让人们变得倦怠和悲观,以至于从一开始就不想费力去区分事实与虚构: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真的。她的洞见包含着这样的推论:平淡无奇的旧消息同样会导致疲劳。为对抗这一倾向,一些书籍呼吁要重新聚焦注意力本身。它们推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正念——一种远离喧嚣的集体凝视,重新审视政治体,寻求洞见乃至于智慧。
我们面临的许多危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或者轻而易举地就被克服,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它们。但解决它们的第一步是承认其紧迫性。其次则是不受打扰地聚焦于它们,给予它们应有的关注。如果我们有心去寻找的话,星光就在那里。人会移动,但星座不会。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聚焦重要之事的办法,那我们也许就不必再这样向后代认错:我们并非有意要纵容这一切发生,但我们还是疏忽大意了。
(翻译:林达)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