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室内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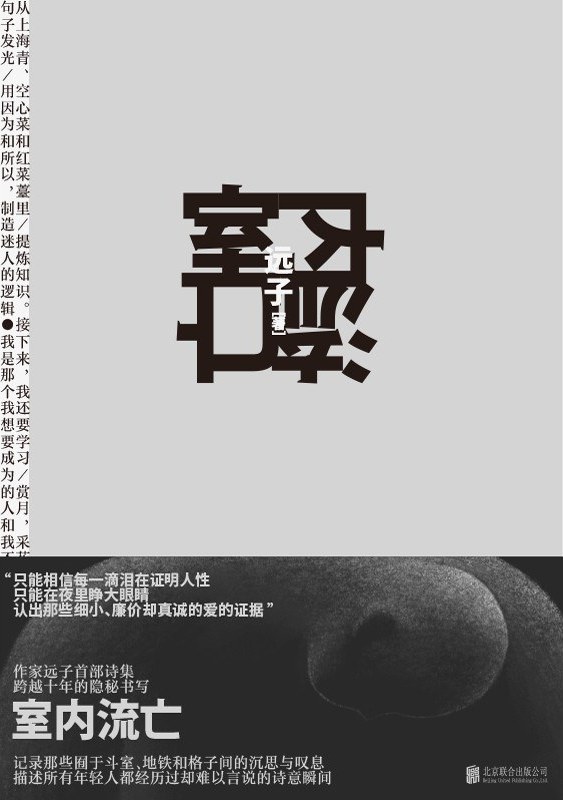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乐府文化 2022-4
本书是作家远子北漂十年以来发表的首部诗集。在北京的日子里,远子发过传单、做过书店店员、在豆瓣阅读做过六年编辑,短篇小说集《白日漫游》曾入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现在的远子已经离开了北京,他在某次采访中提到,“自己已经认定要过一种从世俗标准来讲是失败者的生活。”
或许正是这种“失败”,让他得以从底层视角出发,在诗中写出中国年轻人都曾有过的沉重感受——那些对自我的怀疑,和以一己之力面对时代洪流的无奈。诗中有着日常之处的静默抵抗,比如“每次去倒垃圾总像是在报复整个世界”,也有静默的愉快,比如“跟在一对恋人身后走了很久,努力从他们身上窃取一点快乐”。远子发现,诗歌除了反刍式的抒情,也可以用来介入现实、击打和讽刺身外的世界,而这本诗集就是击打后留下的深深印痕。
《偶然的创造》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 2022-4
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费兰特应《卫报》编辑的邀请,每周按照一个指定主题撰写专栏,最终集结成书。正如书名《偶然的创造》所暗示的那样,相比起费兰特情节跌宕的过往作品,本书所收录的短文更像是偶然的即兴乐曲。这大概也满足了读者们的隐秘愿望:从作家本人那里,获知她对于某些议题最直接的看法。
费兰特在书中坦言,这种全新的写法颇为挑战,自己习惯于细心地寻找故事、人物、逻辑,专栏则充满了紧迫感,需要遵循一种“突然而来的直觉”。在书写这些碎片时,她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锐利的女性触觉和直率干脆的态度,描写自己充满焦虑和喜悦的怀孕经历,费兰特呼吁女性不要把子宫和孩子交给任何人,因为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创造;谈起友谊,她诙谐地说“女性朋友就像真爱一样稀少”。本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阔,从初恋、烟瘾和失眠的经历、母女关系到气候变化,似乎没有什么是费兰特不愿意写的,比起写新东西,她对平凡的主题更感兴趣,并认为“通过挖掘平凡并造成混乱,便可以超越表象”,而我们应该继续写出不合时宜的语句,去揭示出隐藏其中的超凡之处。
《三叶虫与其他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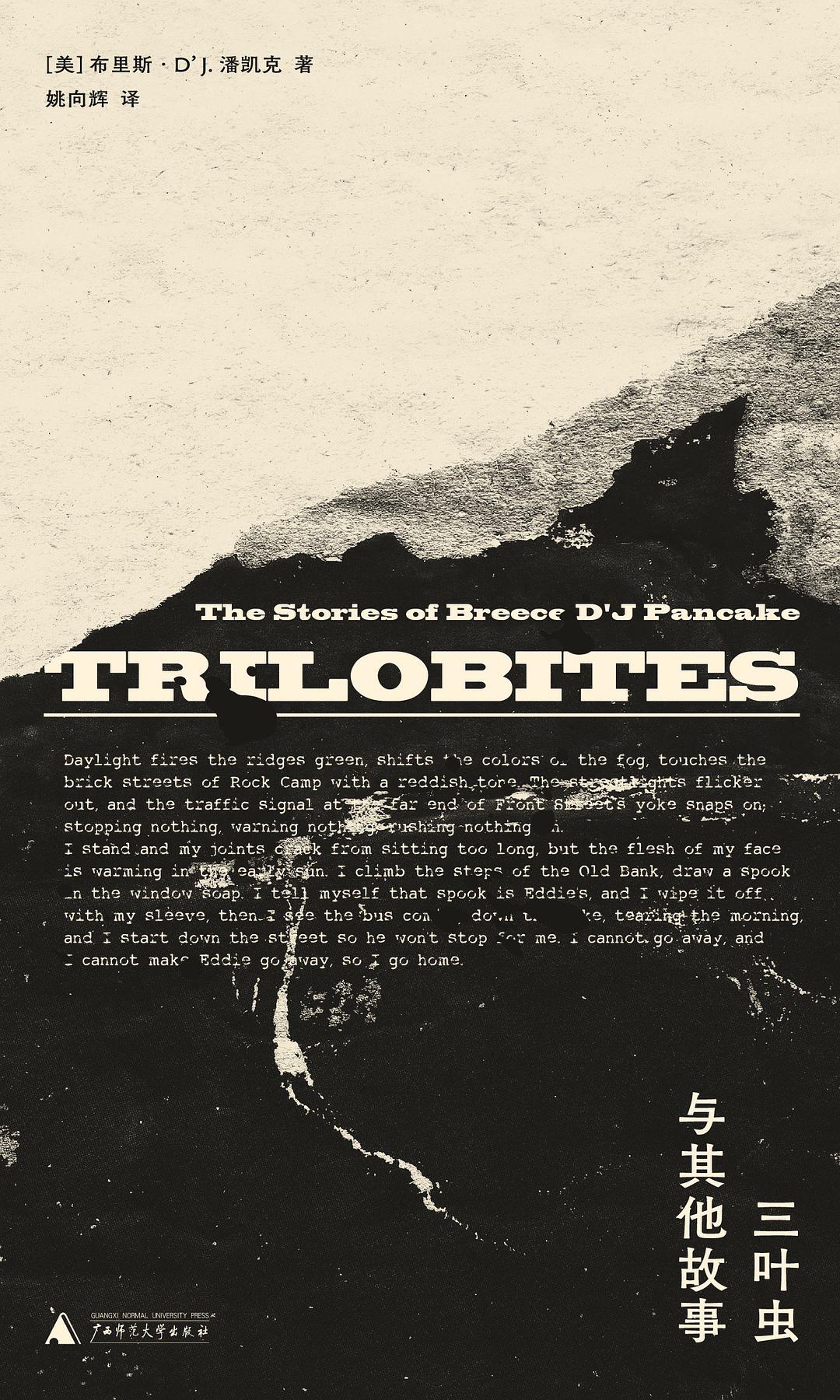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 2022-4
天才陨落的故事总是令人伤心,美国作家布里斯·D’J. 潘凯克也是其中一员。1979年,他在家乡弗吉尼亚枪杀了自己,年仅26岁,甚至比那些“27俱乐部”的摇滚乐手还要短命。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潘凯克仅发表了六篇短篇小说,这本小说集是他在死后唯一出版的书。
潘凯克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山谷,他的故事也来自于此地,这里残存着大规模工业化的痕迹,以及随处可见的死亡与衰败:金属碎片卡在脑中致死的人、肺部因煤尘而出血的人、被剥夺了农场和财产的人,以及一名悲惨的矿工,他的女友即将与别人私奔,而他只得无能为力地扛着枪独自走上山顶……潘凯克书写的是一个遥远山谷中破灭后的美国梦,而这些被损毁、挫伤的小人物的命运看上去又如此熟悉。他们拥有不幸的命运,也拥有爱与被爱的渴望,在充满暴力的冷峻情节之下,潜藏的是一个个想要变得温柔的人。
《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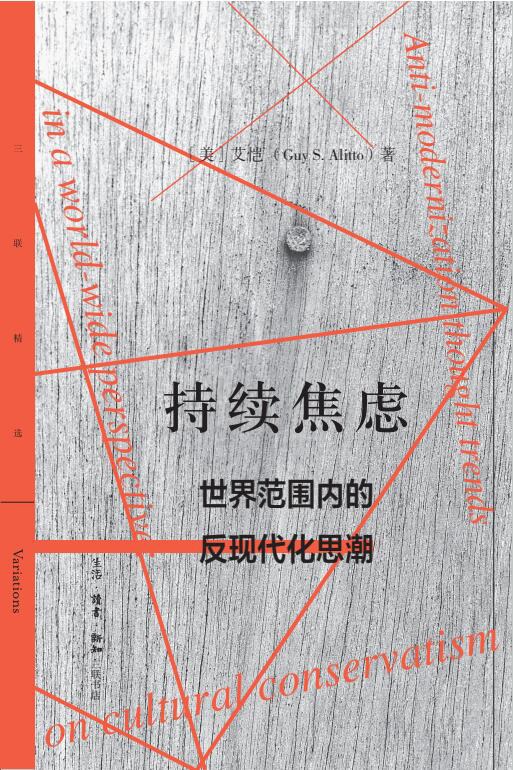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4
二十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学者卡伦·霍尼曾经指出,现代人的内心时刻处于矛盾与焦虑之中,这被她称为“我们时代的神经性人格”——想要亲近他人,同时又想对抗或逃避他人。
将视野从心理分析放到历史语境中,这种内心冲突来源于现代化过程引起的割裂,一方面是对科学与现代工业的赞扬,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生活与自然的怀恋。在《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艾恺认为,关于现代化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人们忽略了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思想隐患,这一隐患的表象便是世界范围内迸发的反现代化思潮,如德国浪漫思想、斯拉夫主义,以及中国面对西方力量时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等。通过对反现代化论者的思想做出全面梳理,本书意图去了解这一思潮的历史蕴含,从而辨明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真正性质。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2022-4
刘瑜于近两年推出了音频课程《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本书由课程讲稿整理而成。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来自于俾斯麦在1867年的一次谈话,表达出了政治的灵活性,但是刘瑜也提到,政治是艺术而不是魔术,它有着社会结构、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边界,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有边界的可能性呢?她认为,我们应该适时地从“此时此地”的政治事件中抽离,深入宏观的多样性,才不会掉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在书中,她将不同体制与经济水平的国家纳入视野,以民主制度为横轴,国家能力为纵轴,分析了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并为读者建立起比较政治学的综合视野。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2022-4
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应该如何应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发现,美国的汉学研究总会表现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么突出西方的优越性而将中国置于“他者”的位置,要么过分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优越性,这两者都无视了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的本土现实是多样且杂糅的。譬如,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和乡村糊口经济的并存、西方律法与人情社会的并存,或者道德化的儒家体系与理性化的法家体系的并存——也正是在各方力量的冲突与调和中,才形成了复杂的中国经验。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黄宗智以社会经济史为脉络,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机制,突出了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主义运作的二合一治理理念。他相信,只有破除对中国研究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式二元框架,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
《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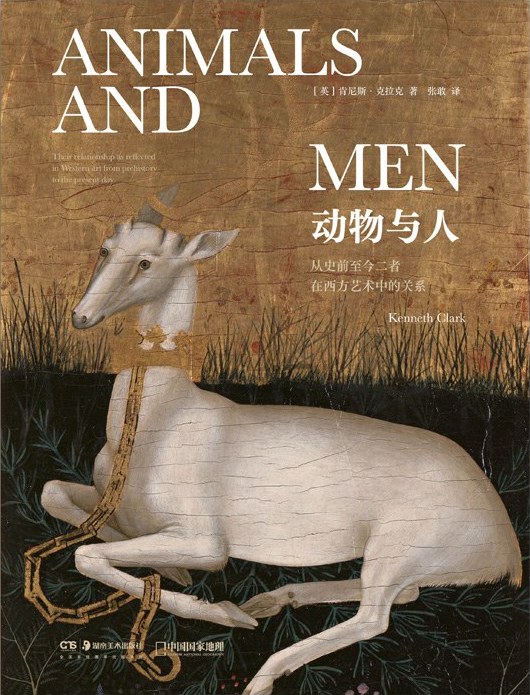
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地理 2022-4
在艺术史上,动物往往是容易受到忽略的存在之一,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通过梳理20世纪前的动物画作,展现出了西方艺术作品中动物与人的关系之变迁。
按照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在《动物与人二讲》中的看法,动物与人的关系存在着一道意味深长的分水岭,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人与动物的灵魂被设想为同一性质,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仅仅源于身体功能的差异;随着苏格拉底哲学的出现,人与自然界被彻底分开,人因为独特的智慧能力而区别于“受本能约束的动物”,从而拥有了优越的地位。这种历史断裂也可以从《动物与人》收录的作品中看出,拉斯科的早期壁画表达着人面对动物力量的谦卑,古希腊的灵缇犬雕像也蕴含着对完美的动物姿态的崇敬,然而这种感情逐渐被人类的征服欲所取代,捕杀毁灭动物的残忍场景屡见不鲜,这些冲突也一并收录在书中。说到底,对于动物神圣、可爱与可怜的看法,都是人类的自我投影,如何重塑万物统一、相互友爱的未来,才是我们在掩卷之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非常植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2022-4
热带雨林往往会让人觉得危险而神秘,然而,84岁的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一生与树为伴,是热带雨林坚定的捍卫者,他认为,人们对森林的恐惧只是因为不了解,当树木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时,森林是最宁静的避风港。
这一观点与弗朗西斯的儿时经历有关。为了躲避战乱,他和全家人曾来到距离巴黎40英里的森林居住,森林给予了家人果腹的食物与乱世中的片刻庇护,也成为了他一生着迷的事物。弗朗西斯从小就喜欢拿着纸笔在大树上写生,他认为,当植物学家面对植物,解剖或拍照的记录方式都不够好,由于树木是结构复杂的庞然大物,唯有细腻的笔触才能捕捉到这些独特的生命形式。在这本书中,弗朗西斯与自由插画师卡琳·朵琳-弗罗热合作,画出了世界各地奇妙的植物,这些画作质朴动人,充盈着对植物们的爱意,也以毫不说教的方式传递着温和的环保信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