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期主持人|徐鲁青
近日,杭州的柳树上了新闻。西湖断桥边的7棵柳树被移走换成月季花,景点“柳浪闻莺”新栽的柳树尺寸远小于原树,大量杭州市民对此提出批评,“没有杨柳的西湖缺少灵魂”、“破坏了文化”……压力之下,杭州政府向市民道歉,并重新补栽了柳树。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关心城市里的树。2021年,广州市政府在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提升”等工程中,砍伐了三千多棵榕树,市民发起了“榕树保卫战”。2020年,成都桂花巷的20棵大桂花树被砍,市民表示不满。2011年,南京为建造地铁,计划移除2000棵法国梧桐,也激起了许多人的反对。植物承载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在上海与南京生活过的人不会忘记,走过植满梧桐的街道时叶隙漏出满地明灭光影;重庆最常见的黄葛树能深深扎根陡峭坡道,春夏之交,金黄的树叶洒落一地;每年春天的北京,满城飘荡的杨柳絮在让不少人过敏的同时,也颇引离人怀念。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肖毅强认为,植物和古建筑一样,也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他认可广州人对榕树的保护,“五十年代,因为修路、埋市政管道,北京拆了不少老城墙;八十年代,因为道路拓宽,广州也在拆老骑楼。如今我们对城墙和骑楼是历史风貌的载体、应该呵护它们的存在有了共识,但却对珠江两边的榕树漠然,其实是历史性认知错误的重演。”然而,在许多城市规划中,树木只被当作提高城市绿化率的工具、打造网红景观的零件、基建设施建设的阻碍,这不仅忽视了树木的文化与历史意涵,也掩盖了它们承载的情感与记忆。

在路旁、身边与心头:扎根在我们城市记忆里的植物
姜妍:北京其实很多植物都让我印象深刻,童年时窗外是一排杨树,日日盯着这排杨树发呆和胡思乱想,当然是很难抹去的记忆。北方干燥,秋冬树叶落下,我很喜欢枯叶踩在脚下的那种感受,但唯有银杏叶因为水分含量大,无论如何不会变得彻底干燥,也会让我多一分注意。有一年去台北,天心老师讲起自己第一次去日本,坐在列车上看到银杏树的时候很惊叹,刚好是银杏树金黄的季节,她就问身旁的老师那是什么树。老师偏偏绍兴口音很重,回答了两遍天心老师都没听清,又不好意思再追问,只好循着发音给友人写信道,“我在这边看到一种好漂亮的树,叫——银行树。”天坛北天门至祈年殿的路上也植着两排银杏树,每年秋季很多人从地上捡白果吃,去年却几乎无人问津。想来是因为去年气温骤降,大风一夜间把银杏叶都吹掉,而白果也还没真正成熟的缘故。银杏叶虽然好看,但落地上的白果却并不易清理,气味也很感人。

林子人:杭州的市树是香樟,但市民最有感情的应该是市花桂花,几乎每个街道都种了桂树,从8月下旬开始,杭州人就开始期待桂花盛开,满城桂香的时节,杭州人会去“满陇桂雨”游玩,找一家农家乐,和三两好友坐在桂花树下喝龙井,消磨时光。你们能想象杭州有些幸运的小学生的课外活动是“打桂花”么?宋乐天在《无尽绿》里记录了她在2014年9月底随一群小学生“打桂花”的经历。满觉陇的村民有感于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文《桂花雨》中的配图谬误(图中母女二人通过摇动树干来收集桂花,但与事实不符),邀请了杭州的“小伢儿”(杭州话里的“孩子”)来亲自体验“打桂花”:三人结成一队,二人手持纱帐站在树下,一人用竹竿轻敲枝干,金黄色的花雨就簌簌而下,落在纱帐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羡慕这些孩子,这样的童年记忆应该是杭州独一份的吧。打下来的桂花会被加工成桂花糖或桂花干,我当年出国留学特地带了一罐桂花干,在泡龙井的时候加一点桂花干进去,添上一缕幽香,聊以慰藉思乡之情。就像宋乐天所说,桂香最是抚慰人心,“这时我忘记我是一只骆驼,我身上负有人生的重担。”

潘文捷:香橼是我老家的市树。这是一种本地树种,结出的果实颜色形状有点像柚子,可以散发柑橘的清香,并能存放很久,据说也可以做中药材,但是不能直接吃。一般家庭就把果实放在家里做装饰,还能清新空气。
香橼树在老家随处可见,也有儿童艺术团、本地企业起名为“香橼”的。我们和邻居家的中间地带就种了一棵。生活中为了土地吵架的例子很多,据说这棵树苗是对方的,土是我家的,结出来的果实两家分享,有以示友好的意思。虽然不清楚当年的具体情况,但我想他们选择香橼而不是其他树种或许有一定的寓意。对我来说,这种植物已经算是一种情感的维系。
叶青:成都简称“蓉”,是因为市花是芙蓉花。据成都博物馆的介绍,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遍种芙蓉,以此花承载他的政治理想,愿国家如芙蓉盛开般昌盛。但民间流传的说法称芙蓉是为了他心爱之人花蕊夫人所种,因此芙蓉花还象征着爱情。根据成都市林业园的统计,成都在2017年就已经种了14万余株芙蓉,但我平时走在街上并不常看到(很有可能是我没认出来),个人觉得成都最多也最好看的还是银杏,春夏还不明显,深秋时节街上金灿灿的一大片,好看极了。

网红景观、忽略当地生活与植物年限:城市绿化有哪些问题?
徐鲁青:很多时候,城市绿化太注重追求景观造型,忽略了植物与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学学者杨永川提过一个例子,上海在2000年初准备世博会的时候提出要把全世界同纬度的树种都移来栽种,但同纬度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于是上海移了很多棕榈树,后来发现这些树冬天都快冻死了,只能给他们“穿衣戴帽”。后来虽然上海停止了这类移栽,但其他小城市的绿化都朝大城市靠拢,也开始种棕榈树。
尹清露:虽然济南被称为“泉城”,也常被评价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但就植被覆盖率和树种多样性来说,肯定没法和南方城市相比,到了冬天,城市也会变得灰扑扑,街上往往就只有稀疏的行道树(即使最近两年经过规划已经好一些了)。最近属于济南的植物高光时刻应该是泉城广场的大片郁金香,四月正好是花期,好些朋友都去打卡拍照来着,近看是很好看,但是密集的花海在混凝土城市背景里还是很突兀,如此一来,花变成了人们瞻仰的景观,反而说明了城市里植物的贫乏。
这些问题和地形地势不佳、北方城市气候肯定有很大关系,但是“先天条件”的缺乏是不是也会导致居民对植物的重视不足,从而影响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比如我就从小和植物的关系比较远,体会不到植物的美,去过植被丰茂的地方之后才发现它们的重要性。

徐鲁青:“花海”之类的网红景观好像在中国城市中经常用来吸引游客,我印象里有县城会打造“薰衣草花海”或“玫瑰花海”,称自己是“小普罗旺斯”之类。也有一些城市为了旅游业或者“花园城市”的名号喜欢追求植物奇观化,比如广州砍掉榕树的一个理由是要打造“花城”形象,让榕树为开花树木让道,但这不一定适合当地人的生活。实际上,很多广州市民都喜欢在榕树下乘凉,榕树如果砍光,广州夏天的街道会非常热。这里也涉及到城市到底为什么而建的问题,无论是“花城”也好,还是不允许人亲近的大块绿地也好,都像是为观光、为展示而建,但如果真的从当地生活出发,只能看不能躺的大绿地并没什么意义。
姜妍:不太了解这次杭州柳树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由于不同的植物确实有不同的寿命年限,所以在做城市景观决策的时候需要纳入这一考量因素。比如日本的樱花树其实也是在替换的,而且不会说等到植物年限快到的时候再进行操作,这个替换可能对偶尔到访的游客来说感知不明显,但是在地居民肯定能捕捉到。
徐鲁青:植物年限确实是城市规划需要考虑的一点,学者杨永川也提到,现在的城市绿化相比于培养小树,更喜欢大树移栽,但很多树现在放在路上可能大小合适,等五年十年后,作为行道树就太大了,会阻挡行人通行,而且移栽也会破坏大树本来有的生态系统。大多数城市管理者可能就只在一个地方待几年,小树并不能马上见到绿化成果,于是倾向直接用大树,而不是等待一个生态系统慢慢建立起来。
除了“被驯服的自然”,也要有肆意生长的自然
尹清露:深圳的城市和植物的关系很近,坐在出租车里都觉得心情愉悦,因为窗外都是果树、椰子树。去年住在南山区,每次出门都会路过沿着海岸线而建的深圳湾公园,感觉如同度假,还因为家门口的桂花太好闻,特地买了桂花味的香薰蜡烛摆在家里,不过也就能还原30%真实的花香。
林子人:和许多其他城市相比,杭州的幸运在于自然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2000年以后,杭州施行了环西湖景点免费的政策,进一步将西湖整合进城市景观之中,姑且不提此举对提振杭州旅游业产生了多少积极的效应,对于杭州市民来说,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亲近自然本就不应该有经济门槛。
搬到上海,我一开始的确有些不习惯,觉得这座城市绿色好少,但慢慢地我发现上海的自然是靠各种城市公园堆砌起来的,甚至在街角都能划出一片小小的空地做成一个花园,还挺可爱的。
这两天社交网络上流传环贸iapm的阶梯上杂草丛生的照片,有人感叹,当城市无人时,自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占领空地,也有人指出这本就是iapm的园艺设计。我是觉得它提醒我们注意,城市中的绿意或多或少都是“被驯服的自然”,需要人类不断地去修剪和维护,即使是西湖也是如此,因此它是“世界文化遗产”而非“世界自然遗产”。但我们需要承认,植物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和建筑一样能让城市居民产生深刻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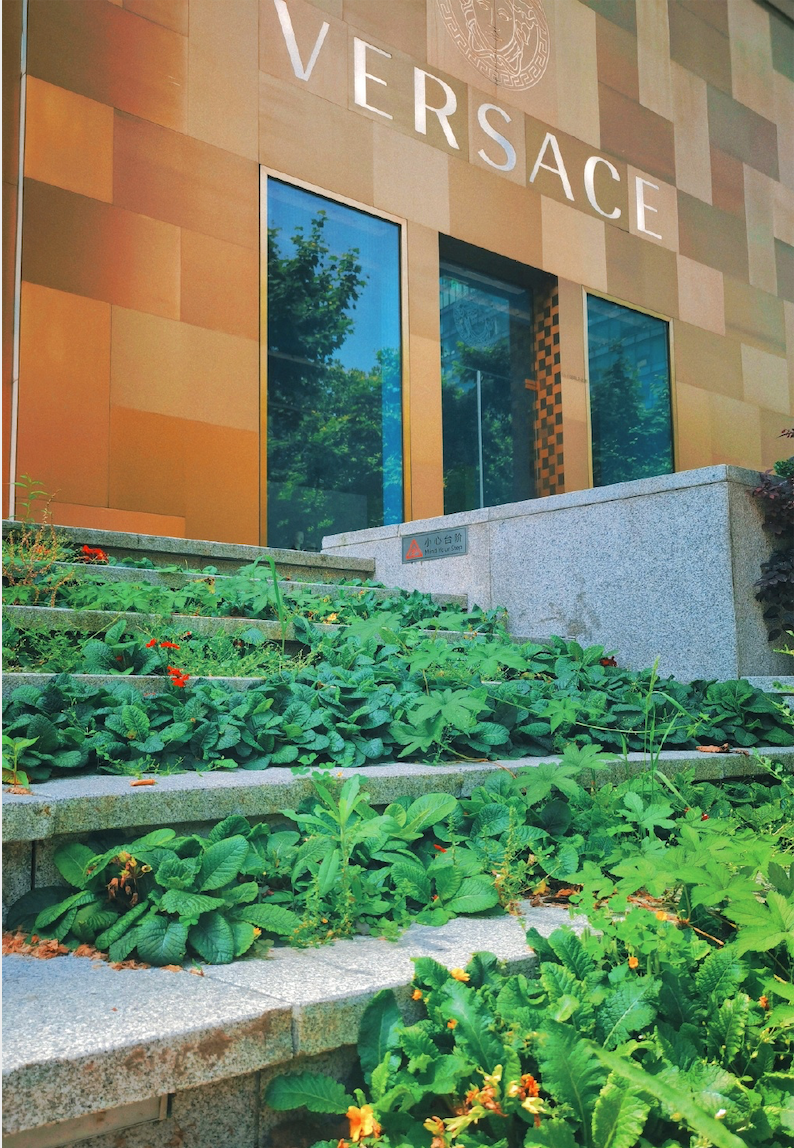
徐鲁青:很同意亲近自然不应该有经济门槛。这让我想到北欧一些国家的“自由漫步权”,也叫“自然享受权”。北欧大多数原野和森林都是私有的,但是法律规定人们有权利进入私人的林地,采摘野果、蘑菇、野花,或者搭帐篷露营等非破坏性活动,这保证了人人都能享受美丽的自然。
一直羡慕一些西南城市,喀斯特地貌让市民在城中心走几步路就能够到山野与林地。上海确实有很多可爱的小公园,但在我看来它们太过修整,光有“被驯服的自然”是不够的。一些城市规划学者也开始批判传统“绿化”概念缺乏对人类中心的反思,提倡城市绿化不应只是整整齐齐的人工景观,而是再现田野和森林的真正生态系统——让人行道旁长出灌木与野草,让公园里的野花肆意生长。植物也不能只被视为服务人类的工具,它们同样是城市的居民,同样应该有空间自由生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