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6
刘以鬯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香港作家,他写作的《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影响了一代香港文艺创作者,导演王家卫就受到了《对倒》《酒徒》的启发——《2046》的经典台词“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便是出自《酒徒》;在《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也是以早年的刘以鬯为原型塑造的,一位南下小说家,靠给报社写黄色小说谋生。
在香港的标签之外,少有人知的是刘以鬯曾作客南洋5年,先后于新加坡、吉隆坡担任报刊编辑。南洋生活是刘以鬯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在报馆的工作坎坷不顺,长期缠绵病塌,最后在异乡邂逅妻子。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不少都刊登在《南洋商报》上,据蔡澜回忆,同在南洋长大的他,小时候就是刘以鬯的书迷,会逐篇从《南阳商报》剪下文章收藏。《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收录了刘以鬯在南洋时期的创作,这些作品曾散落于不同港版图书之中,这本故事集是它们的首度集结汇编。
《契诃夫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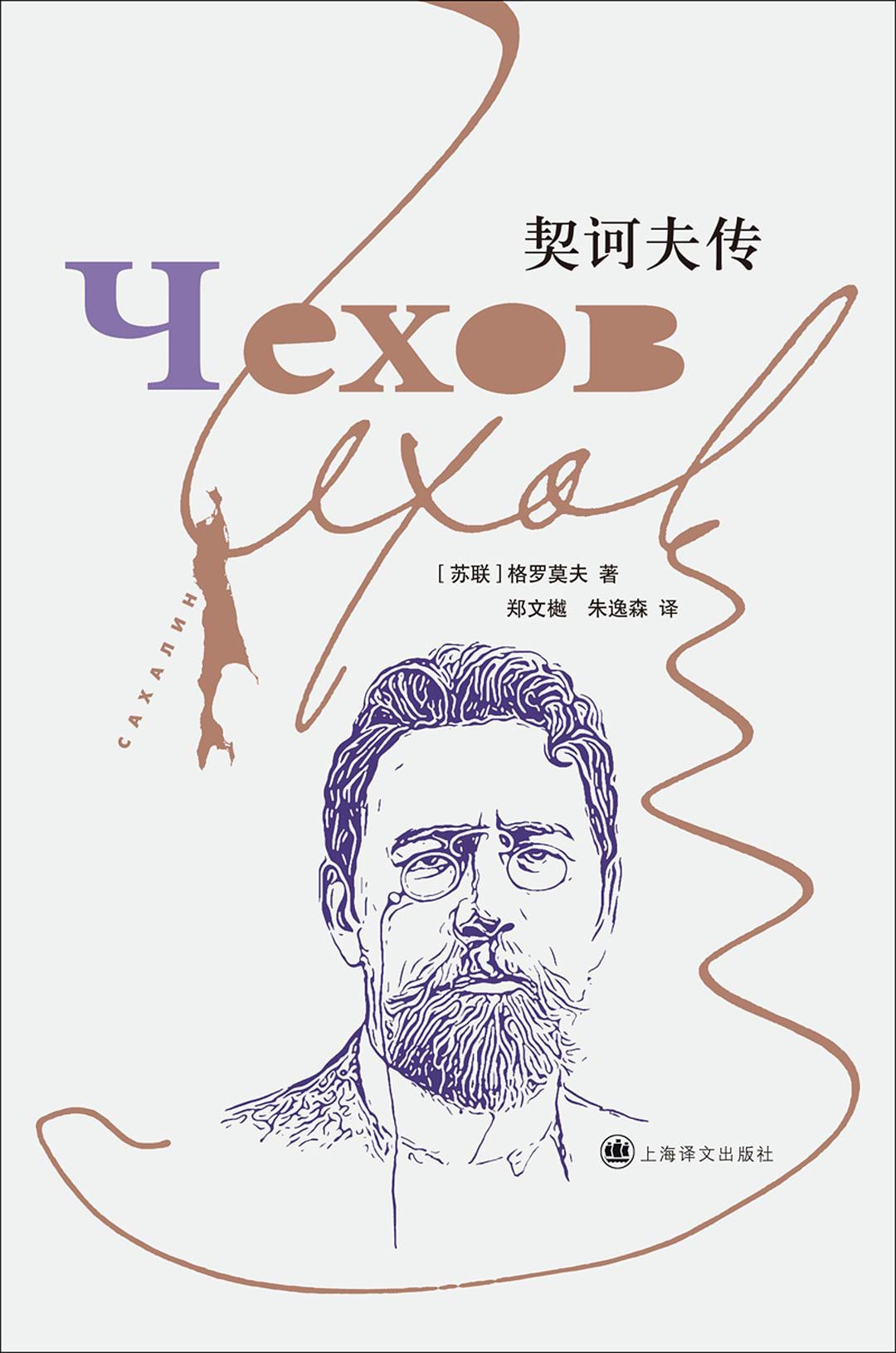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4
契诃夫似乎与大多数俄国作家都不一样,他没有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集中于短篇与戏剧,他也很少处理俄罗斯文学常涉及的生命意义等主题,大部分笔墨都在书写小人物的生活百态,比如《小公务员之死》里因为打喷嚏溅到领导、最后沮丧自杀的小官员;《醋栗》里实现地主梦后却陷入空虚的尼古拉;《套中人》中信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的别里科夫。纳博科夫曾评价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这本《契诃夫传》的作者是前苏联重要的契诃夫研究者格罗莫夫,他打破了苏联评论界将契诃夫作品认定为仅仅是“幽默”小说的评价,重新阐释了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契诃夫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的俄罗斯文学血脉。在这本传记中,他也梳理了契诃夫的创作生涯,并认为其小说与戏剧、书信、日记中存在着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世界观。
《土里不土气:知识农夫的里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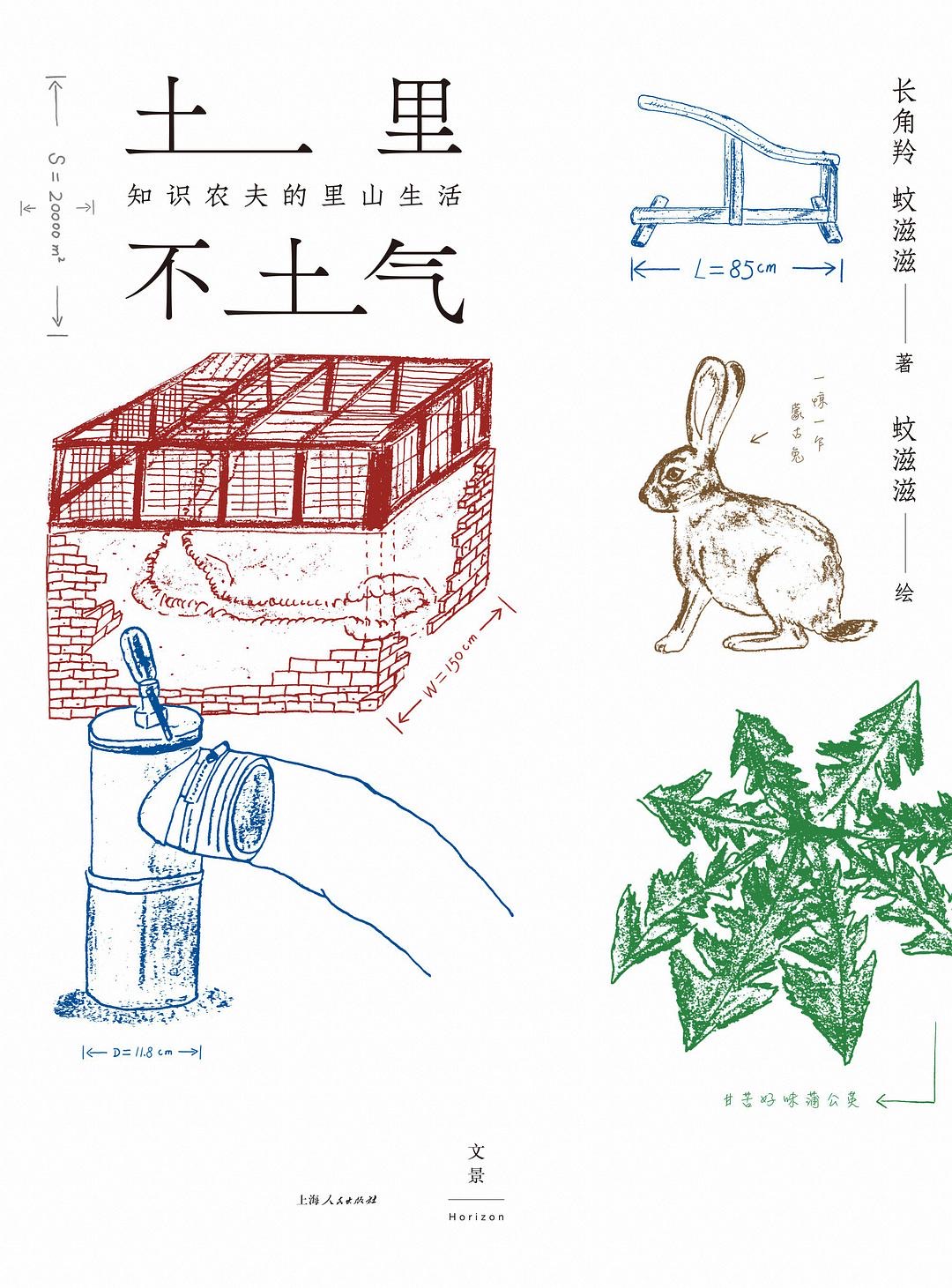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4
长角羚和蚊滋滋这对恋人拍档在多年心恋山野后,决定把自己的家也搬上山,过上环保的“里山”生活。“里山”一词来自日语,指有人居住的山区,它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人们在山间开垦种地,并保留周围的山林,低度利用山林资源,实现生态永续。近几年,里山生活方式开始流行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人群体中。
《土里不土气》是长角羚和蚊滋滋在北京东北浅山地带的7年生活记录,这是一块离城70公里、占地面积30亩的土地,他们在此自耕自食,养鸡养羊,垃圾分类,把废旧轮胎变种植床,将生活废水引入沉降池过滤,将粪便回收为果蔬肥料,在劳作生息里思考人与自然的平衡。他们也认为,自然并非只有在山林里才找得到,“生活在城市不意味着就与土地失联。把购物车越填越满还不如自己试着把问题清空。”
《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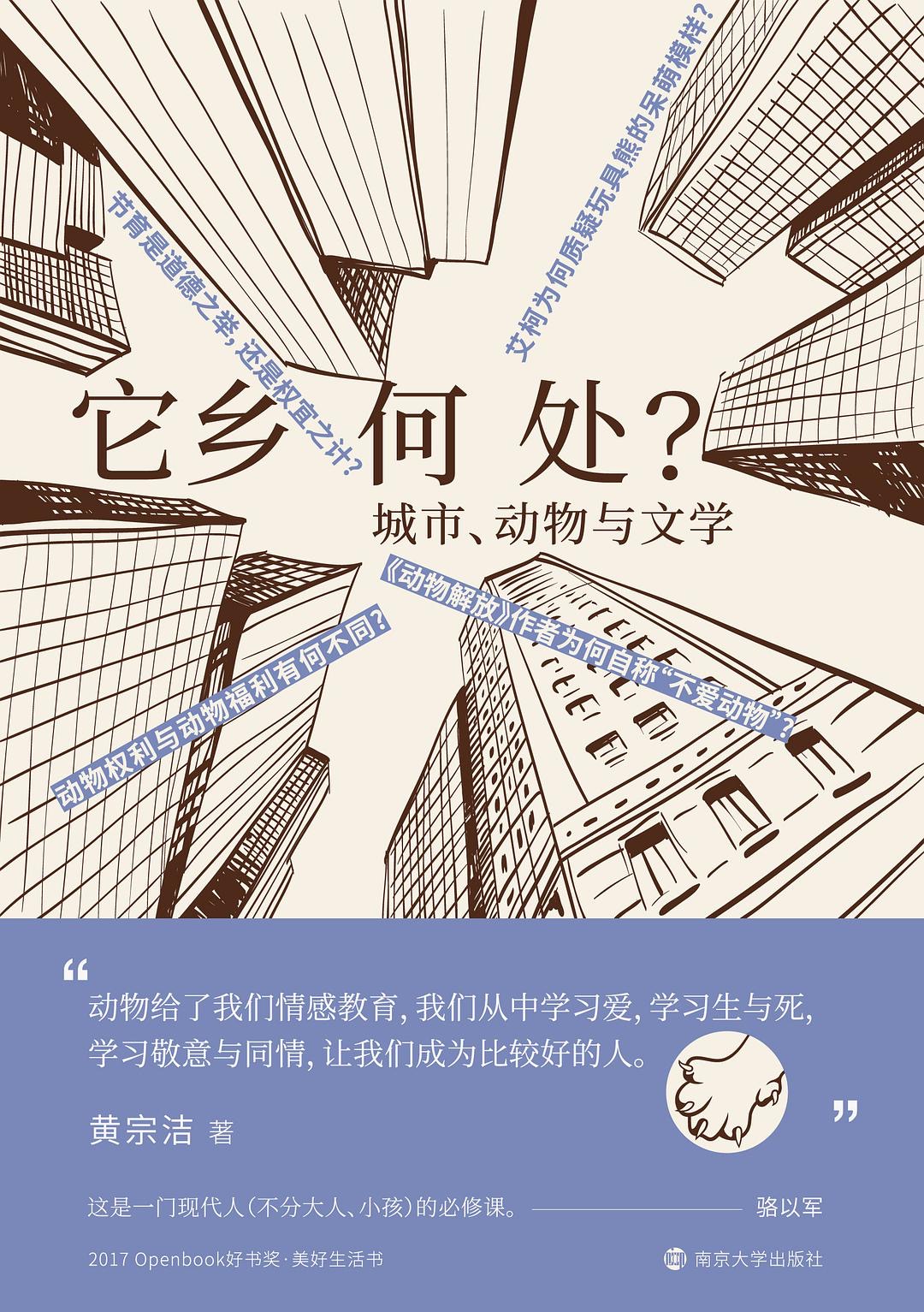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4
2014年8月,一只无意闯入的小狗让港铁轨道列车暂停,在几分钟的驱赶无果后,列车被指令继续行进,最后小狗被列车撞死。这一事件激起社会巨大批评之声,香港作家韩丽珠在当时撰文:“只有在职责和‘正常运作’大于一切的情况下,而群体又把责任摊分,活生生的性命才会成为‘异物’,必须把它从路轨上铲除……清晨的鸟鸣、山上的猴子、流浪猫狗、蚊子、树、草、露宿者、低下阶层、吵闹的孩子、反叛的年轻人、示威者、双失青年、不够漂亮的女人、性小众、意见不同的人……才会逐一成为‘异物’,给逐离和排挤。”
在我们进步的文明里,动物要么是卫生与秩序的威胁与“异物”,要么被物化成商品,禁锢在惹人怜爱的形象里。在妖魔化与物化之外,真实的动物于何处容身?人类应该同动物建立怎样的关系?《它乡何处》探讨了一系列“动物书写”作品,作者黄宗洁是中国台湾地区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她认为,所谓动物书写并非只是将动物拟人化,实际上,许多这类作品呈现的动物形象与它们本身的特质并无密切关系,她所认同的动物书写是以动物为主体进行的相关思考与写作。从《哈利波特》到海明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写作,借由文本分析,黄宗洁重新审视动物园、实验室、艺术馆、街头和超市等不同城市空间中,我们与不同类型的动物的真实遭遇,以及其中关涉的伦理议题。
《重返昨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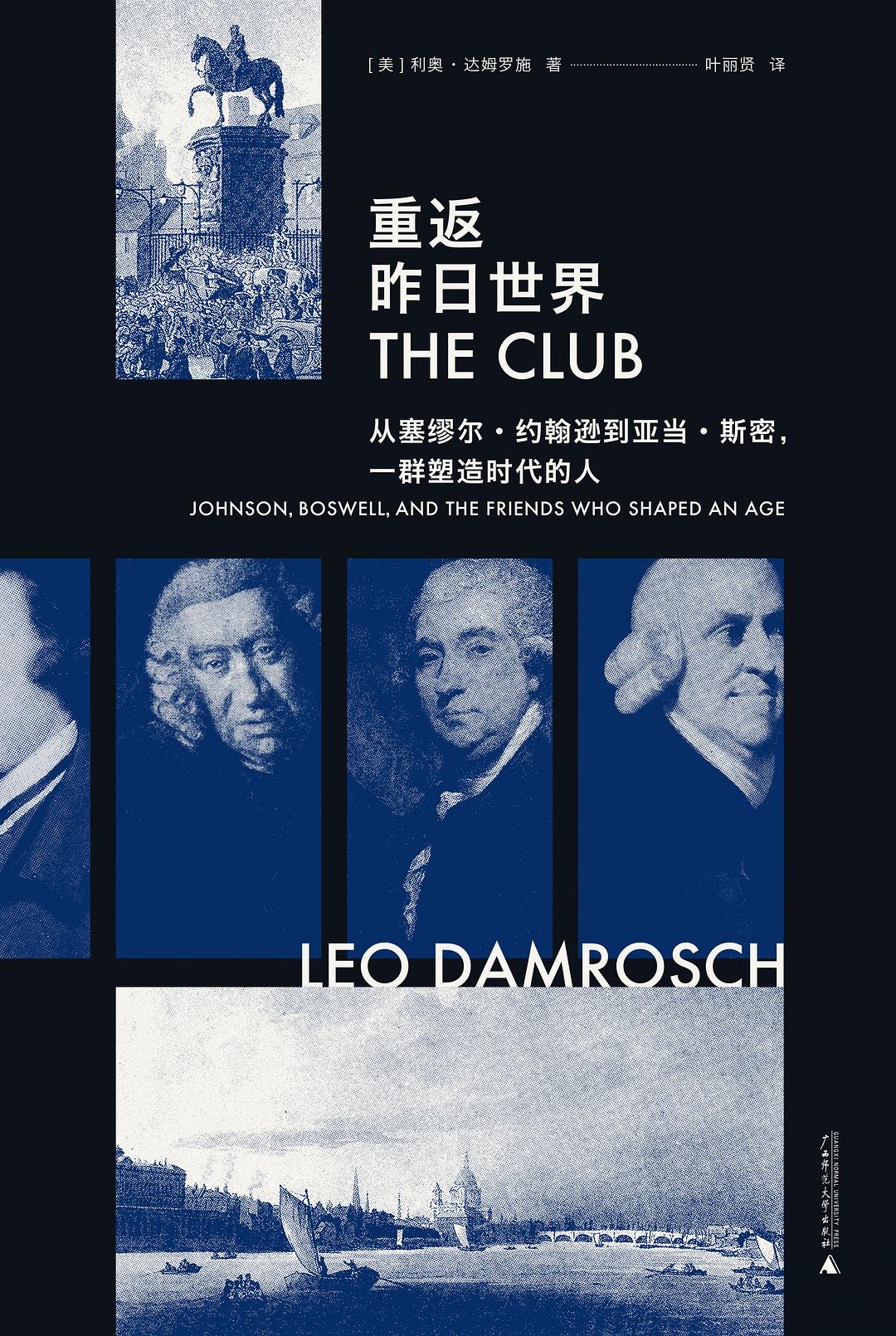
一頁folio|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6
如果说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书写的是欧洲黄金年代的消逝,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达姆罗施的《重返昨日世界》,则勾勒了18世纪的生机勃勃的伦敦图景——按达姆罗施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喧嚣热闹,矛盾横生,不乏粗暴的世界”。在这一时期,成群而来的天才包括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以及传记作家鲍斯威尔等人,他们活跃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和政坛,不仅影响着英国,也塑造了现代世界。
这本集体传记涵盖了天才们的成就与功绩,也描绘了他们有趣的特点。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一生都在严厉责备自己“怠惰”,他应对焦虑的方法是不去想它们。“反思自己的焦虑,”他对《约翰生传》的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说,“会让人疯癫。”鲍斯威尔则觉得人生在世是为了寻欢作乐,他在年轻时写道,“我有一个吓人的毛病,就是为了逗人发笑,几乎什么都可以牺牲,连我自己也不例外。”《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不认同伏尔泰的历史写作,他曾讽刺道:“会对材料加以汇编,用自己的奇妙风格润色它,就这样写出了极其有趣、极为肤浅、极不准确的著作。”除了人物细节,《重返昨日世界》也着眼广阔的社会图景,比如英国政坛的斗争、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女性的生存困境及文艺创作等。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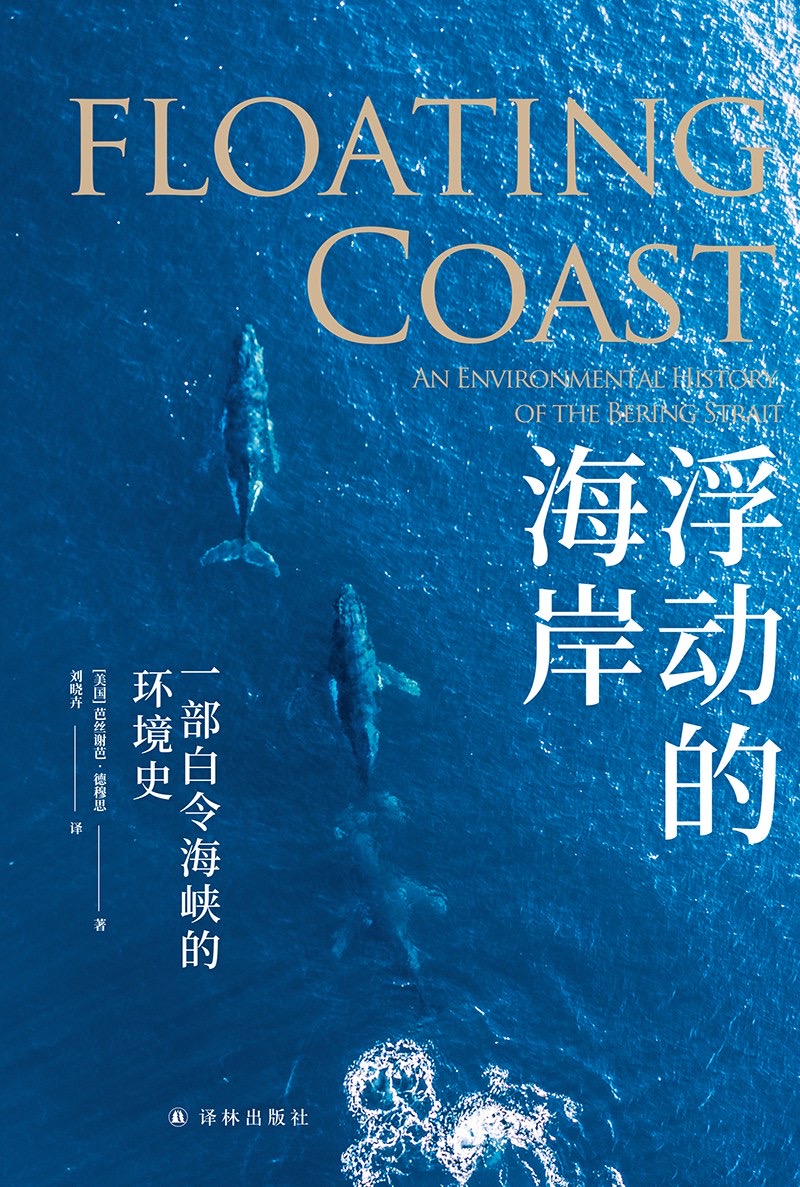
天际线|译林出版社 2022-5
白令地区,是阿拉斯加大部分地区和楚科塔北极的土地和海洋,那里生活着尤皮克、楚科奇和因纽皮亚特等土著民族,鲸鱼、狐狸、海象等动物代代在此生息繁衍。自19世纪以来,人类致力于将这一地区的动物和矿产资源转化为经济财富与国家力量,无论是19世纪的商业捕鲸业、狐狸与海象的捕猎,还是20世纪时的金矿开采项目。土著人的生活逐渐崩坏,当地资源遭到破坏。
《浮动的海岸》一书是首部关于白令海峡的历史研究。此书作者、布朗大学历史系的芭丝谢芭·德穆思从小在白令海峡长大,她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与迁徙的动物比邻而居。在书中,德穆思将她对土地的情感融入历史书写中,一词一句都透出脉脉温情,她如此描述一只18世纪末出生的鲸鱼:“在没有夜晚的漫长慵懒的日子里,鲸鱼妈妈给宝宝喂食,宝宝嬉戏玩耍,有时短暂地游散开去,然后成环形向前游。夏日过去,进入了九十月份,鲸鱼又一次向西游入楚科奇海,鲸鱼宝宝游动时抓紧妈妈的鱼鳍。”她这样书写驯鹿:“它们喜欢柔软的地衣,喜欢缓慢流淌的河流,喜欢微风拂面、罕见熊出没的地方。”在她的笔端,白令海峡的一切都不只是被描述的“物”,而是充满丰富感受的生命主体。
《自说自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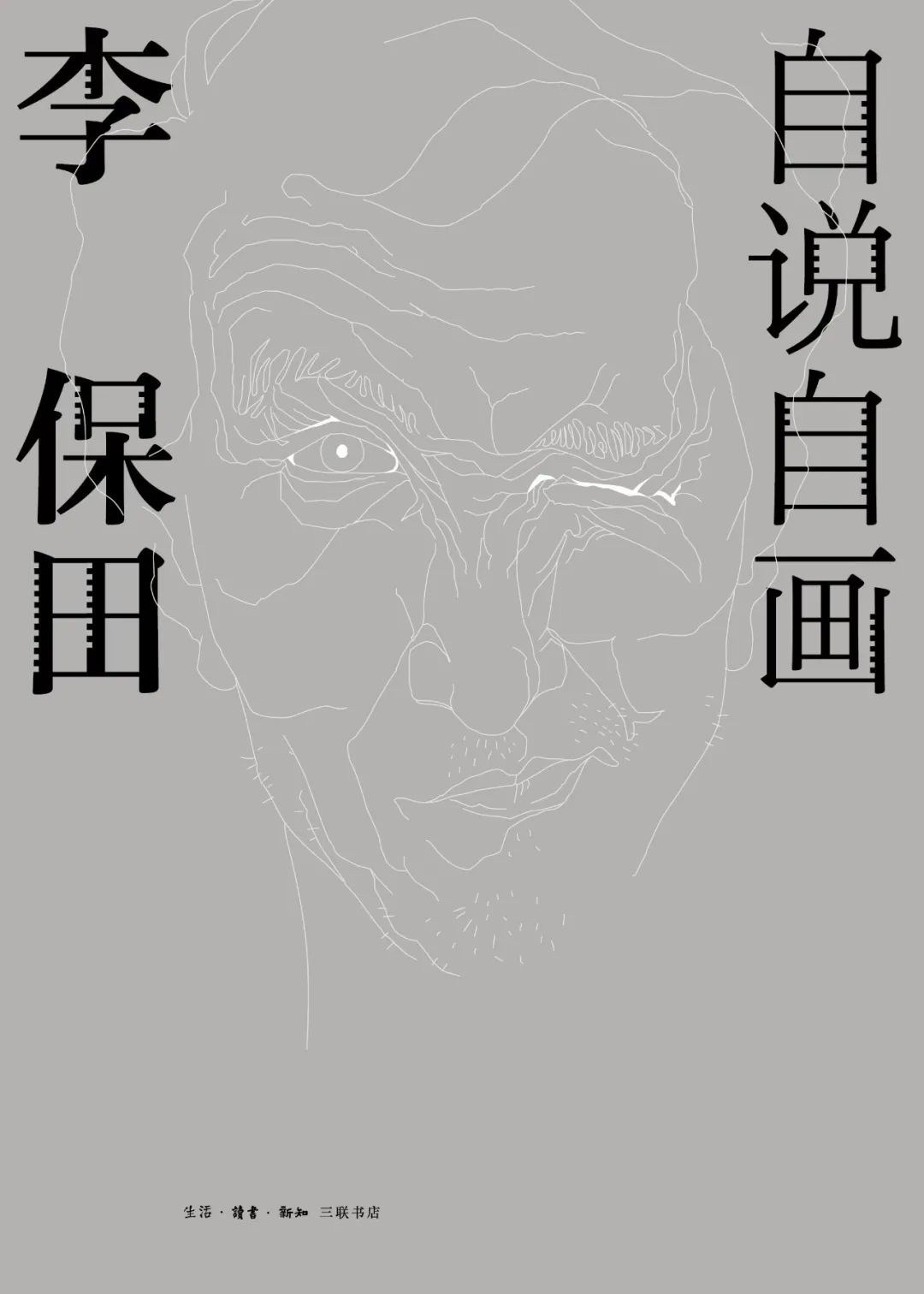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3
李保田演过很多戏。在张艺谋的《菊豆》里,他是饱受压抑的男人杨天青;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他饰演三十年代上海滩黑社会唐老大。他最为人所知的角色之一,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宰相刘墉。90年代,几乎人人都会哼唱这部剧的主题歌:“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作为演员,李保田从未接过任何广告,也不出席任何活动与综艺,2005年,他将自己电视剧《钦差大臣》的投资方告上法庭,控告他们偷偷给剧集注水。官司打完后,他被多家制作公司联合“声讨”,李保田从此沉寂许久,在家写字画画。
这本《自说自画》是李保田的绘画创作与随笔集。在闲暇时间,他绘油画,做剪纸,研究木雕。他的画里有许多“苦楚、彷徨、自哀、孤独和死亡”,他认为这是自己生命底色的重要部分,在采访中李保田曾说:“一个人经历过长年饥饿,经历过因贫困而濒临死亡,自然会形成这类心理这类情绪,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反应在绘画作品中。”
《蛇、日出与莎士比亚:演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爱与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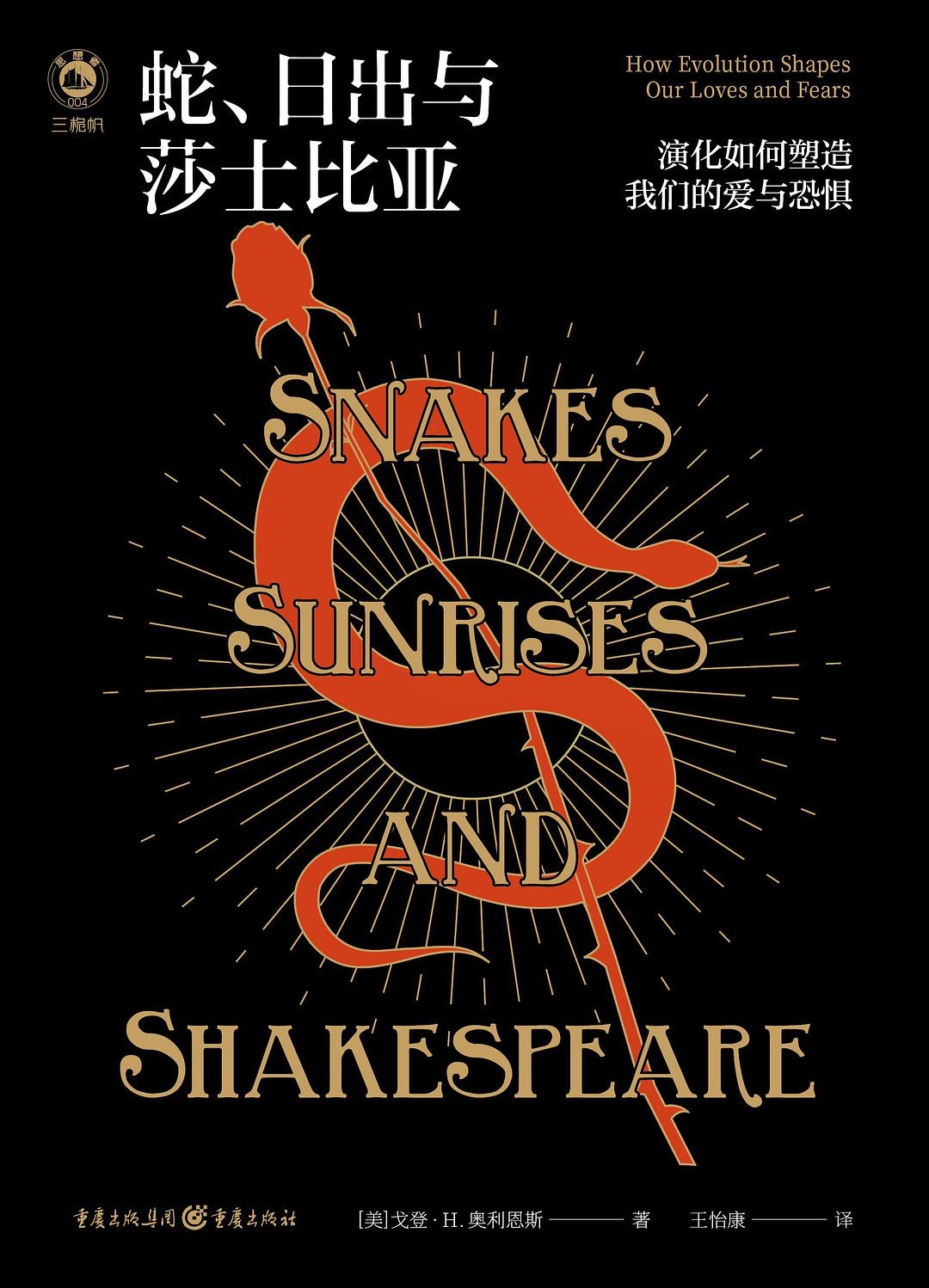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2022-4
我们为何一看见蛇就毛骨悚然,面对日出总能感受到崇高之美?实际上,这些情感反应并非偶然,它们都深刻在人类进化历史中—— 蛇的毒液对我们有致命作用,纵使城市化与医学发展大大降低了它们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日出的到来意味着危险的黑夜消失,即便现代社会里黑夜对人类早已不是高风险时段。
进化生物学家戈登·H.奥利恩斯的《蛇、日出与莎士比亚》一书,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情感偏好是如何被先祖的生活经验所塑造的影响的。在原始狩猎时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当反应决定着生死存亡,好恶因此在大脑中形成了稳定连接。奥利恩斯指出,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审美倾向,都是埋藏在人类演化历史中的深层记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