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你好天府 三井
8月的一个夜晚,近百名年轻人带着飞盘,占领了成都一处综合运动基地的足球场,彼时的成都依旧高温不灭,即使在晚上也未有明显降低,但4片场地依旧满员,有自己组队训练的,也有报班参课的。以我当晚参加的成都飞盘大队俱乐部的F1课程为例,40个班额配置,两个小时的课时,即使在工作日,也有约30人参加。
这是疫情后的第三年,飞盘带着自身的低运动门槛和强社交属性,迅速风靡全国。根据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中国参与飞盘运动的玩家大约有50万人。进入2022年,飞盘近乎强势地在各个社交平台继续获得暴增流量,据统计,今年清明假期,飞盘相关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4倍,五一假期飞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约40倍。
在高人气之外,飞盘离产业化也越来越近。新思界发布的《2022-2026年飞盘行业深度市场调研及投资策略建议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飞盘产业市场规模超过8500万。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指导的首届中国飞盘联赛首站比赛已在西安落幕。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飞盘正走向正规和主流。
阶段的飞盘 正在浮出水面
飞盘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的铁饼比赛。但它真正成为一项竞技运动,是在20世纪中期。1968年,美国新泽西州的哥伦比亚高中制定了极限飞盘比赛规则,并在70年代逐渐完善。
2001年,世运会将极限飞盘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事实上,由于上海外国人群体的引领,飞盘赛事早在2000年便在中国出现,但直到2008年,飞盘俱乐部也只极少数地存在于北上广深几个城市,一年只有不到10个俱乐部参加飞盘比赛,甚至飞盘也需要海淘,一个在100块人民币左右。

“飞盘大队算是成都最早的飞盘俱乐部,2010年左右就成立了,不过那时候经常参加的成员也不会超过 30 个,每次活动能够凑够两队人打比赛就很不错了。”郭铮铮将自己定位为这个俱乐部的骨灰级玩家,已经十年盘龄的他也确实能撑起这个称呼。但郭铮铮最初接触飞盘的契机,是因为他试图找到一个更适合中学生的体育项目。
除了在飞盘大队担任教学顾问,郭铮铮还是成都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最开始玩飞盘是为了教育,这话可能说得有点大,但确实是这样的。”郭铮铮那时打比赛时受了伤,手术后柱着拐站在操场上,突然发现校园里柱拐的学生还不少,“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是因为那个春季有体育联赛,高对抗性的项目和少年心性的碰撞,受伤的学生就多了。”
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体育项目,能够好玩、上手快、性别对立较少、具有一定团队性和教育意义,“因为是学校教育,选择项目不能只关注体育本身,还要顾及教育性。所以我希望这个运动能够有很好的体育道德规范,并且最好是团队运动,能够满足孩子们社交需求的释放。”为了囊括这几个元素,郭铮铮几乎查阅了国内外存在的一切运动形式,“最后我找到飞盘,它几乎完全符合我想要达到的运动目标。”

郭铮铮觉得飞盘还是一个很浪漫的运动,“从运动本身来说,能够飞行的东西永远都是人类的梦想,翼装飞行、滑翔······飞行对人类来说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无法抗拒。”
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不仅对于学生,对老师来说也是如此。在正式教学之前,郭铮铮已经深深”入坑“飞盘。“即使最基础的扔盘动作,扔出去扔回来,都会给玩家快感,立竿见影。加上飞盘独特的社交属性,我自己的社交圈子都扩大很多。”世界飞盘联合会将极限飞盘精神浓缩为“SOTG”图标,即熟知规则、避免身体接触、公平竞争、享受比赛、真诚沟通。独特的精神内核似乎自这项运动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蕴含其中。
为了积累经验,郭铮铮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在那个年代,国内一丝一毫有关飞盘教学的参考资料都找不到,没有课程、没有教材,连一个教练都找不到。我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一个飞盘运动员,到处去打比赛,跟着成都队一起训练。”
在此基础上,郭铮铮任教的中学自2012年开设飞盘选修课, 2014年实施模块教学后,飞盘也被纳入常规体育课的一个模块。“每学期我们那个校区就有上百名学生来选修这门课。也就是高中三个年级会有 300 人长期参加飞盘课程,这也是我们学校女生参与度最高的体育项目。”
关于飞盘进入学校课堂,有一个更加积极的信号。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极限飞盘作为新兴体育项目被正式列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这意味着这项新兴且曾经小众的运动,正在转变为官方认可的教育资源。“可以预见的是, 9 月份会有很多中小学开设飞盘课程,我们最近也在开设教练培训班。”郭铮铮说道。
除此之外,官方层面的飞盘教练培训也已经开始。今年6月,四川省第一期飞盘运动初级教练员实践培训班在成都举办,课程连续两天,省内40余所高校的飞盘运动推广教师参加了培训。据了解,中国的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正在牵头,已经制定了《全国飞盘运动教练员管理办法》,今后,无论在校园中教授飞盘的体育老师还是商业俱乐部中的教练,都将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及培训规范,并且按等级进行考核。该委员会副秘书长薛志行表示,委员会正在寻找机会,将全国主要俱乐部的主理人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讨行业的规范以及共识,建立行业联盟。

对于行业规范的建立,郭铮铮所在的俱乐部也十分重视。“以前成都基本就只有飞盘大队一个俱乐部,现在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在增加新的俱乐部和社群,这当然是很好的信号,说明大家都在关注飞盘。但有经验、有资质的教练员实在太少了。”郭铮铮给了一个自己的估算,在成都,拥有1年以上飞盘教学经验的教练不会超过10个,而培养一名成熟的飞盘教练,至少需要1年时间。这与成都数万名飞盘玩家对比而言,显得杯水车薪。
飞盘大队现在拥有约20名教练,根据教学水平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和实习教练。“我们专业性更强一些,但我们也鼓励玩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创建自己的社群,这样更利于培养成熟的竞技队伍。”在郭铮铮看来,飞盘这个市场是不会由一家俱乐部独大的,但作为成都最资深的俱乐部,他们希望成为这个行业的标杆。“飞盘突然爆火,这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俱乐部教学不严谨、仅仅把飞盘当做社交工具,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即使作为一门生意,我们也想要展现给大家它最好的一面。”
目前,飞盘大队的重心在社群培训和青少年培训。在社群培训方面,飞盘大队开设了面向零基础玩家的F0课程和入门玩家的F1课程,主要教授基本的技术和规则。“后期这类型课程会减少,会增加面向进阶玩家的F2课程,去培养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俱乐部或小分队,让一个区域的玩家能够建立固定的圈子。如果成都有更多俱乐部,这个运动被推广得会更好一些。再进一步,就可以组织城市小型联赛,通过赛事带动运动本身发展是永恒的逻辑基础。”郭铮铮说。而在青训方面,飞盘大队的青训体系分为U19、U17和U15,“有成熟的培养体系,一来可以成为成都青少年培训的标杆,另外也是为未来的成年队储存新鲜血液。”
朝着产业化极速前进的飞盘
中国的体育产业在经历了近三年的疫情肆虐后,正处于迫切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阶段。即使有未来五年五万亿的产业规模作为“终极希望”,也无法在当下给所有“局内人”灌注信心,此时的体育圈,任何可能涉及到体育产业的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
在线上观赛无法满足运动的深度需求的情况下,飞盘这种入门级、社交性强的运动爆火,无疑是传统体育运动方式的进化。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之前,全国的飞盘俱乐部不超50个,而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有高校飞盘队157支,飞盘俱乐部、社群206个,竞技队伍112支。
赛事的安排也越来越快。实际上,自2018年开始,飞盘就在逐步迈向系统和正规。2018年,第一支飞盘国家队成立;2019年,中国体育总局将飞盘纳入管理,同年,亚洲大洋洲飞盘锦标赛在上海举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的最高级别飞盘赛事,也是中国国家飞盘队第一次组队参加的国际A类飞盘比赛。自此,飞盘锦标赛被国家体育总局纳入年度外事计划和国际A类赛事。
如果联系上述中国飞盘联赛的落地速度,或许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7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发布通知,拟于8月开始举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7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印发通知,公布了中国飞盘联赛陕西·西安站竞赛规程;8月6日,中国飞盘联赛首站陕西·西安站正式打响。前后不到一个月,这是以往国家级联赛筹办难以想象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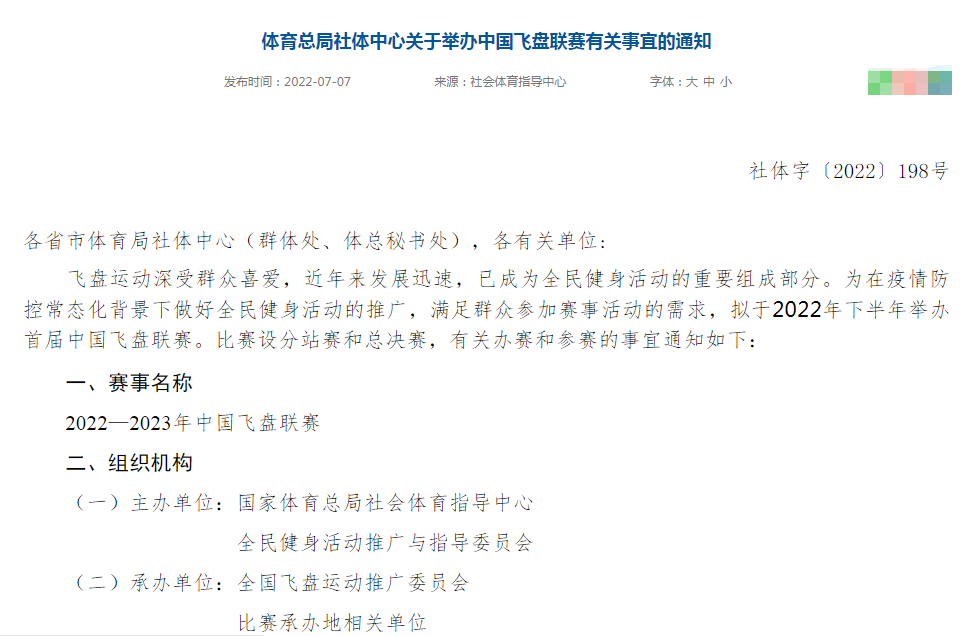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无法和规模性的联赛分割开来,而地方性的协会组织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聚焦飞盘,目前国内仅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特大城市拥有区域飞盘协会,但飞盘协会对于各省、市申请联赛、统筹资源却是必不可少。一位接近四川省体育局的人士透露,目前四川省飞盘协会正在筹备当中。
“飞盘在成都是挺火的,但是在其他市州,还存在局限性。第一是场地问题,现在大部分还是租用足球场,而足球场本身就不多。第二是产业化运作,可能二三线城市没有那么多人有成熟的商业思维,又同时有资源来组建当地的俱乐部或飞盘协会。所以我们组建省级飞盘协会的出发点就是要搭建平台,能够为四川省二十一个市州的飞盘发展做好基础。”四川体育产业集团运营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兼四川体产赛事管理公司总经理吴明宇说道。据了解,四川体育产业集团是筹建四川省飞盘协会的发起单位。
在吴明宇看来,若省飞盘协会成功落地,组织赛事将作为重中之重。“除了积极申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四川站,还要组织省级比赛,但最重要的是举办市级赛事。这样能够在每个市州搭建起飞盘运动生态,实现赛事常态化。”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体育协会与体育行政部门脱钩。而在更早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就已经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包含了88家项目或行业体育协会。
“市场化体育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吴明宇表示,低门槛、强社交、性别友好的飞盘无疑是市场化属性非常强的运动项目,且属于持续上升态势。郭铮铮的直接感受是,社群繁衍得很快。“最近的频率是每周新增一个微信群,500个人加满,这周建的12群,上周建的11群,而在一年前我们只有两个群。”郭铮铮说道。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目前组织飞盘赛事、俱乐部等服务项目的盈利能力并不突出。以成都为例,租一片五人场在 400 元钱左右,一片八人场在800-900元,学员报名费在40-60元之间,一场比赛配备一位主教练、一位副教练,兼职教练课时费约为300元,跟拍摄影师一场约200元。以40名班额,60元报名费为例,即使满额也只能收入2400元,除掉上述费用与基本成本外,一场飞盘活动的净利润仅在1000元左右。
飞盘大队的兼职教练“周黑鸭”是成都大学的研一学生,他每周有3-4节课程,一个月收入大概在3000块左右,“现在俱乐部的教练基本都是兼职,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恰当的方式,不需要承担太多成本。而且俱乐部的教练可以互相流通,也比较灵活。”

吴明宇认为省级协会或许能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发展是提前迈入市场化的核心,而不是像之前等着财政扶持。协会需要组建一个成熟团队,招商、竞赛、裁判培训、场地运营和设计等各方面都要有专门的人去负责。”
相比较马拉松等大型赛事的超高成本,小规模的飞盘赛事正在吸引着一众品牌与企业的关注。“飞盘是不涉及对外的,它是一个场地封闭性的比赛,不需要像马拉松一样去封路,不需要做赛道上连续的救援站和补给站,包括直播也只需要几个固定机位。”吴明宇说道。以常规计算,筹办一场马拉松赛事需要花费百万上下,而举办一场基础的飞盘赛则只需要几千块。“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大家都希望能够以赛养赛,而不是像之前全靠政府出钱。”
产业化运作很重要的一点则是通过整合平台把品牌资源嫁接到地方,“比如品牌赞助、冠名赛事,可以自然地延展到市州。”吴明宇表示,飞盘的运动属性很适合主打时尚和年轻的品牌调性,“年轻化的场景是很适合品牌导入,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品牌想要发布新品,举办IP赛事,其实是很好进行嫁接的。如果能够搭建一个良好的生态,是完全可以惠及所有俱乐部的。”
随着官方站台、主流媒体入场,品牌的青睐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在吴明宇看来,中国的体育产业正处于关键阶段,疫情后全民运动需求极速增加,体育消费意愿上升,而这些,都是适合发展飞盘的土壤。“飞盘运动起码还要花两年才能走入正轨,而要完全实现市场化、产业化,至少也需要三到五年,很多配套产业是需要去培养的,这是需要周期的。目前最缺的,是专业场地和专业教练。”
2025年成都将举办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成都也将成为近年来继上海后中国内地第二个举办大型国际飞盘赛事的城市。可以预见的是,在赛事聚光灯效应下,飞盘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飞盘在之前算是潜泳,浪头才刚刚冒出来,远远没有达到最高点。”郭铮铮告诉我,他现在收集了很多在不同高校的学生寄来的飞盘,“有清华大学的、同济大学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些东西会成为我非常美好的回忆。有可能当我的教学生涯、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我会开一个飞盘博物馆,用飞盘来讲述我的故事。因为对我来说,飞盘甚至是一种生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