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诺·迪亚斯,有人说他是美国当代的天才作家。作为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他身上另一个显著的标签是移民作家的身份。
出生于1968年的迪亚斯,在多米尼亚成长到6岁,随后移民到了美国,“父母总是告诫我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这个父母眼中“危险的世界”里,迪亚斯开始了他的写作。在新泽西读大学时,他每天晚上埋头写作,只是从未发表。写的都是“抢银行的暴徒”,用他的话说,“那些都是垃圾,像糟糕的香港动作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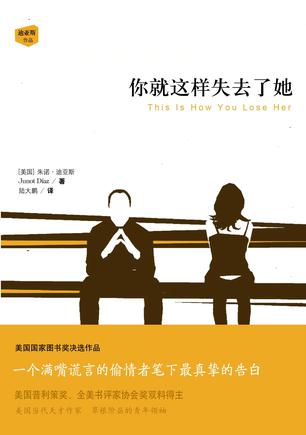
如今,已经48岁的迪亚斯,至今却只出版了三部作品。他说写作是件困难的事,而自己又有拖延症。拖延更多来自于“纯粹的懒惰”而不是批评界认为的“身份焦虑”。1996年发表处女作《沉溺》之后,他的第二本书《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花了11年,第三本书《你就这样失去了她》花了14年。
人们喜欢盯住他“移民作家”的身份,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自己却消解了这样的身份,他并不会觉得移民作家就理应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但是他却喜欢在书写中以性别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加以区分。或许,他对性别的关注超过了移民身份。这一次,借着来参加上海书展的机会,界面文化对他进行了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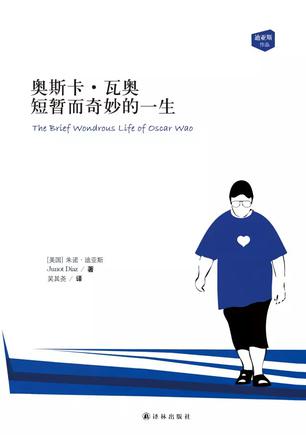
界面:在《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充斥着各种流行文化元素,你认为流行文化对于你的写作有很大影响吗?
迪亚斯:因为我们这代人,无论贫富,生长环境的语言库就是流行文化,我们不在抒情诗和《圣经》的语言环境下长大,人们不再经常引用荷马史诗、维多利亚典故,而会引用《x战警》或者《兔八哥》。用流行文化来组织小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方法,并且也是描绘人物的好方法,对于流行文化的密度描写符合奥斯卡的人物逻辑。并且,书写流行文化也不是我独有的,三十年前,就有《美国精神病人》,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
界面:奥斯卡这个人物如此热爱科幻,你是不是对于科幻也很有兴趣?
迪亚斯:除了科幻小说,我也读很多其他作品,人类学、社会学、维罗利亚研究,我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在塑造奥斯卡时把一部分书架给了他,不是全部;对奥斯卡来说,热爱科幻是一件自足的事情,因为他喜欢的都是科幻的经典之作,他喜欢弗兰克·赫伯特(美国科幻小说家,代表作《沙丘》),但我其实并不喜欢那么经典的,我喜欢很多恶俗的,比如皮尔斯·安东尼(美国科幻小说家,以“赞思小说”著称)。他写得真的很糟,如果我现在把你扔到楼下去,你应该也会比他写得好。
界面:书写家庭是一种你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吗?我们经常在移民文学中看到大量家庭的描写。
迪亚斯:写家庭对我来说更像一个书写策略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剥开《权力的游戏》那些喷火龙、神奇魔法的面目,还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我们来说它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家庭,所以明白其中的政治。我写家庭对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捷径,即使你不了解多米尼加,你总知道家庭故事里,妈妈想要孩子结婚,孩子很敏感这样之类的情节。
至于移民文学是不是喜欢写家庭——外面的人永远想看到一种模式,但是移民也是一个个个体,可能永远不会相见,而不是一团面目模糊、有同一模式的群体。如果《权力的游戏》是一个移民写的,人家就会说,这因为是移民所以才关于家庭,那《超人》也是讲家庭的呢。移民文学只是让家庭问题更加明显了,当你变成一个移民,要更多依靠家庭,所以有家庭对话。
界面:就算不移民,现在也可以旅行到其他国家,感受“局外人”的生活是如何的?
迪亚斯:是的,问题是很多人不旅行,也会有“局外人”的感觉。我只知道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当我们年轻时,总觉得自己是外来者,不知道是因为外国人呢,还是因为青少年的缘故。我土生土长的美国朋友也觉得家庭、朋友、学校都不好,总想改变,去别的地方。我与他们相同的一点是,都在向往一个真正的家,向往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从没见过年轻的还开心的人。小说里的奥斯卡不是移民,但他跟他妈妈一样疯狂。到底是因为是移民还是青少年、才觉得与社会格格不入?有什么分辨的方法吗?你得有两次生命才知道。
界面:那么“局外人的感受”并不是移民文学的特点了?
迪亚斯:人们永远不懂大道理,而明白具体特殊的经验。移民也是经验的特殊性一种,这能产生共识。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到学校,第一天去工作吗?你一定觉得非常尴尬……三年以后,你就懂得了一切。现在我们还在读二三百年的书,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些书讲述了可以引发共识的特殊经验。我最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是《白鲸》,这本书是讲捕鲸的,我们现在没有人捕鲸了,但是那种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精神,会让人产生共识。爱是难的,人人都懂得,但是如果我给你一张男女朋友分离的图,人们就懂得爱有多难这个道理。所有的文学都基于这一点。
界面:你似乎并不同意移民文学的特殊性。
迪亚斯: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普通化”了。
界面:你的书中有很多性和爱的因素,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迪亚斯:我觉得,女性的每本书,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是关于爱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找到爱,找到另一半;男人的主题则是毁坏爱,毁坏亲密感,写爱会强迫他们面对与爱情的真正关系。数一数男性在社会中毁坏了多少爱情吧,在美国和多米尼加社会里,男人毁坏爱情的数量都是远超女人的,中国估计也差不多。
男人对于女人没有“共同”感,男人总觉得女人是对手,是要角逐的另一半,她们是不是工作不开心,是不是没有安全感不重要。我笔下的人物尤尼奥(《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人物),虽然是个“感情混蛋”,但和女人有“共同”感,部分原因是他承受过性虐待,因此对女人被强暴、被虐待的经验很敏感。
界面:一直在说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你是不是特别关注性别问题?
迪亚斯:男女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窃听男人的电话,会发现他们很少用细节描述自己的感受,通常都是,“啊,我干了她,啊。”特别无聊。而女人,天哪,我从小在我两个姐姐中间长大,她们每天说的话,真是太多了。女作家通常也比男作家狂野多了,就像我看到的中国作家盛可以,《北妹》开篇描述就是一个人物的胸部太大了。女人不是在假装“狂野”,我知道你们女人只会在公共场合假装“正常”。
如果把我的书上作者名字擦掉,很多人会觉得这本书很像女人写的,不是因为我笔调柔软,一点也不柔软,而是我写身体的方式,女人写身体,男人则不。还有感情,如果不对感情感兴趣就不会写感情,我写这些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世界的规则。光让我看两个人约会,我就可以了解地区、权力还有亲密关系。我很好奇人们在不平等的世界里如何生活,因为我从小就被各种不平等、不公正包围。如果女人有足够的权力,这个社会就不是这样的,约会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种状况下女人仍然争取到了可以争取的空间,可以生活,可以浪漫,可以做梦。
界面:有什么跟男女关系相关、揭示着不平等的例子吗?
迪亚斯:举个例子来说,我的翻译就要结婚了,他未婚妻说,下个月不要晒太阳,这真的很怪异!因为晒得黑会显得阶层低吗?在这样一个女人们到处举着雨伞、带着手套的社会里,肤色的禁忌究竟是什么?这让我突然想到,如果一个男人从外面回来了,晒得特别黑,他的妻子还有周围的人会不会很生气?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开头呀!




评论